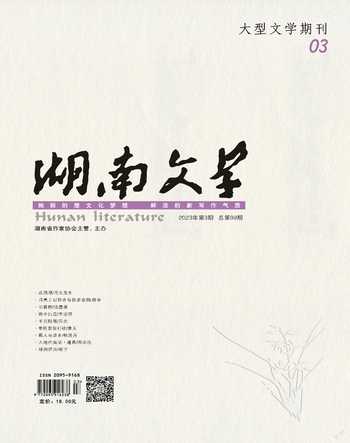濂溪记(外一篇)
张雄文
心头恒久淌着一条小溪。
溪流水色沧浪,并不浩瀚,甚或有些寒瘦与幽寂,颇宜李煜笔下的渔父孑孓而行,闲云野鹤般吟唱“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自然也宜先秦清寒雅士行吟侧畔,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与《沧浪歌》之水不同的是,心间哗哗作响的小溪或其近岸池塘,莲叶田田,茎干亭亭,苍碧无边漫涌。水边时常踟蹰一位男子,面容清癯,峨冠青衫,目光灼灼,向着莲叶茕然而立,沉吟不语。或许,随一阵清风徐徐拂过,莲叶微微而漾,男子吟啸之声也陡然而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小溪名濂溪,男子则被世人尊称为濂溪先生。心头长久存储他们,如夏夜一天星河飞泻而入,润泽肺腑,涤荡灵魂,是因学生时代的课文《爱莲说》。
上课老师出身寒微,个头不高,黑瘦精干,眼睛深凹下去,却颇有神,往台下一扫,教室某处细碎如蝇鸣的声音便戛然而止,像凉水泼于暗弱火烛,而课桌抽屉边偷看的某本诸如《瓦岗寨》一类连环画,也会倏然被塞入深处,身子笔挺起来。听屋场讲古的父辈们说,他毕业于北京某名校,原在城里教书,磊落不羁,常与管事者意见不合。譬如学校教学楼栏杆,先一年为水泥,次年翻修为不锈钢,再一年,又换回水泥,他愤懑难耐,挺身直言其中猫腻。不久,他便被交流到乡间,成了我的语文老师。
那天,上到《爱莲说》,他讲解作者、字词与文意外,还一个人前后诵读了三遍全文。每到“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一句,他神情照例端肃,声音格外沉郁悲怆,最后一次,眼里还分明闪着泪花。屋内鸦雀无闻,所有人都沉浸在震荡四壁的抑扬顿挫里。我头一回领略到文字与吟诵的魅力,也勒刻下流光深处早已背影模糊的作者周敦颐,亦即濂溪先生,还有他家乡那条濂溪。少年心事并不多,却对数百里外的濂溪充溢神往,只是暗自固执以为溪名应为“廉溪”。
终于抵近濂溪,是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暑月。那天午后,一场阵雨骤然而来,天空收敛了一路追随不止的酷热,与濂溪一道散逸浩漫的清凉。雨后的湘南道县楼田村,也便像掺有芝麻、莲子与红糖的一碗本地凉粉,格外清爽宜人,将我坠入“天凉好个秋”的意境。溪水叮叮淙淙,似有若无,横亘周敦颐故居门前的旷野,湮没于岸侧池塘莲叶的无穷碧意间,向远处的潇水、湘水悄然延展。我欣慰的是,溪流与多年来心头所淌似乎并无二致,仅少了一个茕然独啸的身影,多了些人迹与喧腾。
清凉而外,四野还漫溢廉的气息,无声无形,却浓郁逼人,似溪边香远益清的荷香。濂溪先生已弃千余年的故舍主体为青砖黑瓦,低矮灰暗,临水背山。门框为厚重青石所砌,可容三四个人并立。除门匾为当代书家欧阳中石所题,其余并不打眼,属典型湘南古民居。门内天井、房舍、门窗、梁柱与陈设,虽有后人修缮或重造痕迹,依旧素朴简约,内敛自抑,无官宦人家惯常的幽深宏阔,与曾国藩的乡间侯府富厚堂不可同日而语。富厚堂建于曾氏老家湘中双峰县山峦间,有门楼、八本堂主楼、求阙斋等三座藏书楼,还有后山鸟鹤楼、棋亭、存朴亭与思云馆等,亭台楼榭、假山池沼一应俱全,蔚成大观,占地广袤,极尽奢华。
濂溪先生生活于北宋,生前官衔不显,最高仅至江南东道南康军刑狱,却也被南宋理宗赵昀追封为汝南伯,居“公、侯、伯、子、男”五爵之第三等,仅次于曾国藩所封的勇毅侯,与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诚意伯相类。先生之父周辅成进士出身,一子周焘官至宝文阁待制,正三品,可谓名门世家。故舍之所以清寒,主要还是缘于先生之廉。
犹如虔诚朝圣的信徒,我久久徘徊于故舍的厅堂、台阶与天井,偶尔轻扣刻满沧桑印记的门窗、木柱,似乎希冀与濂溪先生猝然相逢,而后执同乡晚辈礼请教。我想,先生必定慈蔼谦恭,令我如沐春风,像待当年登门的再传弟子侯师圣一样,“留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
濂溪先生在道县家乡生活了十五年,日夜与潺潺濂溪相伴,勤苦攻读。饱读诗书,晓畅作文外,他似乎更得濂溪之灵气,感悟莲叶之净植,将廉洁二字刻入了骨髓。辞别家乡,远赴外地入仕后,他清廉高洁,淡然名利,与宋代官场盛行的歌舞喜乐之风格格不入。同僚们嬉笑宴乐、推杯换盏时,他与家人就着昏暗灯烛,吃几碗淡饭,喝一盅粗茶,说:“芋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
每到一地,公务之暇,濂溪先生总要寻空地,凿一眼池塘,种上满池莲花。我想,无论案牍多么劳形费神,仕途如何苦涩多艰,见到滴翠的莲叶,他眼前必定会浮现家乡清澈照影的濂溪,也必然心身俱宁,怡然自得。就任桂阳县令时,他照例种了莲花,还积多年来的情愫,饱蘸笔墨,写下了《爱莲说》,以莲自况,借以明志。这便是后来收入课本,令老师和我都感佩的那篇杰作。《爱莲说》仅一百一十九字,却字字珠玑,像一泓清泉,洗涤每个读者的灵魂,也确立了先生古中国廉洁文化奠基人的地位。
高洁如莲,濂溪先生的日子便颇清苦,“举箸常餐淡菜盘”。其至友潘兴嗣后来回忆先生在南昌为官时的住所:“视其室,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因家境清寒,营养不足,先生还曾“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苏”,也就是到阎王殿打了个转。他外出仕宦多年,家乡人常引以为傲,希图沾光进入仕途者自然也有。担任永州通判时,侄子仲章登门,捧着茶杯嗫嚅一会,说想求个官职。先生笑脸瞬间收敛,肃然拒绝。侄子临走时,他取过笔,写了首诗相送,解释说:“官清赢得梦魂安。”
流連濂溪先生故舍,门外濂溪细碎的奔淌声里,我一遍遍摩挲暗色板壁,似乎那些写入《宋史》的往昔,也刻入了斑驳纹理间……
濂溪先生少年时聪慧卓异,将濂溪边上五个土墩依金木水火土五星次序,命名为五星堆。后又在七公里外的都庞岭东麓月岩筑室读书,参悟“无极而太极”之道。成年后,他精于《易》学,喜谈名理,清廉从政之余,勤于灯下著书。他撰写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正式提出了宇宙构成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这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起源,像天际星辰,照亮了当时混沌的知识界。先生也以微官之身,跃升为宋明理学与湖湘学派的开山始祖,还被后世朝廷下诏从祀孔庙,迈入屈指可数的万世师表行列。
诏令像一只报春的雀鸟,跨山过水而来,栖止在濂溪之岸。或许,安谧流淌千万年的溪水,此时也会因其中“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的至高褒奖,而跃然欢腾吧!
濂溪先生的学说,经南宋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等人弘扬,明末清初王船山承继,清季邓显鹤、魏源与曾国藩等人再度中兴,前后接力上千年,形成了声名远播的湖湘文化:尊奉理学、重经世务实、包容众家之长……谭嗣同、黄兴、杨昌济、毛泽东等湖湘后来者,无不受其影响,最终各有所成,也让“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更如雷震重霄,响彻天下。饮水思源,濂溪先生创始之力,功莫大焉。
坐落岳麓山的湖湘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悬有近代名士王闿运一副霸气的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称道的正是濂溪先生的开创之功。我想,门外濂溪跌跌宕宕,入潇水,奔湘江,盘桓岳麓山脚下,感受名联蓬勃四溢的气息时,一定分外亲切吧。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的濂溪先生,濂溪也成为无数人向往之地。明代踏遍万水千山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便不辞劳苦,追慕而来。崇祯十年三月,他一路辗转跋涉,终于进入道县,来不及喘口气,又急急奔赴楼田村。徘徊濂溪岸边,拜谒濂溪祠,夜宿月岩,他心潮起伏不已。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其前扩然,可容万马,乃元公所生之地……”元公,即濂溪先生。
濂溪先生十五岁离家后,再也不曾回过濂溪岸边。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先生却不屑于此。熙宁五年(1072年),时年五十六岁的他决定辞官归隐。踌躇一阵,最终卜居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先生对桑梓并未忘怀,将门前小溪命名为“濂溪”,溪边建了濂溪书堂,又开始登坛讲学。风晨雨夕,漫步新的濂溪之畔,他澎湃于胸的故园之思,或许稍稍得到缓解了吧?
我兀自遐想着,出了故舍大门,向后山走去。后山名道山,东南脚下翠竹掩覆的石隙间,汩汩淌出一眼清泉,岩壁镂刻“寻源”“圣脉”数字。泉水大旱不凅,积雨不溢,出道山后,淌入濂溪,成为濂水之源,自然也是濂溪先生常来之地。壁上还题有古诗:“山根活水静成渊,不作人间第二泉。一自派分伊洛去,千秋遗泽任流连。”不经意间,我抵近了理学与湖湘文化的最初圣脉,也寻到了廉洁文化的最早源流,于是欣然蹲身,掬一捧入口。水尤清洌,甜美异常。如甘露洒心,我尽日奔走的疲惫瞬间消隐。
登上道山极顶,放眼四望,雨后的天空纯净如洗,龙山、豸岭、都庞岭等峰峦四面环列,凝碧攒簇,似乎正赶来参拜道山。濂溪如镶上绿边的白练,恬然躺卧湿漉漉的原野,依旧是先生当年依偎时的风姿。我迎风感慨着:此溪不老,斯人亦不老……
清韵满勾蓝
勾蓝是一首唐人笔下的山水诗。
流水声细细碎碎,像琴弦滑落的音符,和着一缕缕午后的阳光,将我引入群峦深处的寨门,唐诗的意境便陡然漫漶开来:
四围山峦苍翠而别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算险峻也难称壮硕,各呈独立的圆锥形,却在山腰处情人般握手相牵,恍若耸立的驼峰。不同的是,骆驼仅驮两座肉峰,而眼前山峦却耸峙如林,贴着纯净的蓝天绵延开去,缓缓消失在天尽头。一湾早已激越入耳的清流,像躺卧葱碧间的透明飘带,在我的惊喜里横在屋舍与林木间,也将环列的“驼峰”连同蓝天、屋舍、亭台、人影慨然装入怀中。小溪两旁远远近近的屋舍或齐整或错落,红砖黛瓦,翘角飞檐;檐下檐端勾着白线或白点,漫溢遥远岁月的气息,像排蹲或围坐着一群衣冠古朴的老者。屋舍前后直达四周山脚的原野,铺陈古树、果林、稻田、池塘與菜园,浓翠满目,果蔬飘香,荷叶田田,玉米蓊郁。我伫立溪边一座木质黑瓦的凉亭下,一时恍惚起来,不知置身天上还是人间……
这是地道的“永州之野”,江永县隐伏深山与凝固了时光的勾蓝瑶寨。
隋朝末年,勾蓝瑶先祖便因避乱而卜居于此,寨中古碑刻有“盘王出世,秦王(李世民)开基”,无声叙说瑶寨的起源。先祖环顾四野,见“山勾联透,溪水伏流,色蓝如锭”,“故名勾蓝”,欣然“不复出焉”。然而,饶是深山更深处,也有烽火与刀剑跟踪寻觅而来。子孙们只得高筑寨墙,连片屋舍也砌成可守的堡垒,且耕且战,顽强生息繁衍。大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一纸诏令飞入重山,勾蓝瑶被恩准招安入籍,摆脱了“蛮”族的称号。或许,勾蓝人此后才有了较安生的日子,且耕且战也渐渐更换为且耕且读。因房屋只建不拆,开枝散叶多年后,便有了眼前古色古香、烟火气依旧弥漫的民居,多达三百余栋。这还不算散落寨中,供节日里祭祀、祷告的盘王庙、相公庙、水龙祠、关公庙和社坛土地,或平素娱乐休闲的舞榭歌台、歇息行走的凉亭桥梁。
我很快领略了保寨中老少平安的寨墙雄姿。溪边草地躺着一条青石板古道,侧身穿过一座碑刻乾隆某年修建的戏台与一株四百六十年高龄的重阳木树荫,向不远处的山头延展而去。小心踏上青石板,阒寂无声,却有一股清凉似乎透过鞋底奔爬而上,直冲头顶。惬意间,我似乎听见了千百年前那些往来的足音,铿锵而又缥缈。
古道在寨中的尽头,是名为井头坳山头的寨墙与古寨门。山头古木参天,叶叶相交通,遮蔽了七月毒辣的阳光。寨门早已豁开,行人可自如出入,但硕大青石筑就的门框依旧苍古遒劲,斑驳苔藓间,似乎还残存着箭镞与刀斧的痕迹。门框两侧是向深山延伸而去的寨墙,照例是大青石所垒,披覆古藤与茅草,时隐时现,最终消隐在幽暗的丛林深处。有如此坚固的寨墙与寨门,只需三两个壮汉扼守,便可万夫莫开,寨子也便稳若金汤。摩挲墙根一块黧黑而古拙的巨石,我久久慨叹勾蓝先人筑城的智慧与勇力。
古道穿过寨门,并未止步,而是枕着形状不一的青石板,继续向深山幽壑绵延。山的那一边,是鸡鸣入耳的广西富川。两地或者更远的地方,从来以古道互通有无,青石板上便常年商旅熙熙,挑在肩上的茶叶、粮食、柑橘、盐巴与各种日用品往来不绝,勾蓝人的日子也便丰润起来。然而,世事沧桑,因后来凿山而入的现代公路,古道渐渐人影罕至,只能在苔藓与杂草间默默反刍往昔的喧腾,唯有鸟影不时掠过。青石板则沉淀幽古的光芒,以时光深处的辙痕守护瑶寨返璞的安谧。
勾蓝淌着诗意,清韵最绵长的还是水。无数道山间清泉与寨中散布的水井,汇聚成大小溪流,几乎挨家挨户盘桓后才穿村而过,甚或从一户人家地板下淌泄而出。出村乃至出山后,它们奔入湘水还是潇水,我一时无从得知,只是无端想起宋人秦观“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句子。寨子深处的门槛边、窗户下,都奏着和弦的水声。水面或窄或宽,宽者显然为寨民依需而拓。垂柳、古樟与老槐的树干爬满藤蔓,随处傍水而立,倒影婆娑可亲。三两只鹅鸭偶尔戏逐水面,一种山外难得的闲雅便悄然弥散开来。我疑心误入江南平原水乡同里,但瞬间又醒悟:同里虽也是上佳之地,却无此处古雅的屋舍与抬眼可见的“驼峰”。
水边书香漫溢。沿一道叮咚作响的陌生水流,我与欧阳门楼猝然而遇。欧阳是瑶寨十三姓之一,门楼建于明时,典雅端庄,古意弥漫,呈八字形敞开。两根木柱像寨中所有屋舍大门一样,贴有遒劲隽永的对联。瑶寨刀枪入库后,推崇耕读传家,文气昌盛,先后考取过八名进士,勾蓝也随之名闻天下。进士们以儒家为法,进则外出做官,兼济天下,退则回寨子任瑶王,反哺桑梓。欧阳家也不例外,设有私塾,聘请名师,勉励子弟灯下苦读,门楼隔壁便出过一任江永县长。私塾至今风物依旧,后人别出巧思,建起了书院主题餐厅,主打书香文化。时近黄昏,炊烟袅袅,菜香喷薄而出,我却隐隐闻到了淳古的书香。
小憩横跨水面的风雨廊桥,我披裹落霞,品一碗寨中手搓凉粉。清凉入心也入骨时,十几米外的屋舍门忽然打开,一个男孩端了盛满碗筷的木盆,下到溪边清洗。我见其虎头虎脑,神情专注,动作熟稔,便隔溪询问年龄。他抬头笑答,今年十岁,读小学三年级。说着,又埋头忙活了。不卑不亢,应对大方,透着诗书之家早慧的儒雅与勤勉,全无山外独生子女的骄娇之气。我倚着廊桥木质靠背,默叹良久。
寨中人也乐于戏水。蒲鲤井是勾蓝溪流主要源头之一,深不可测,水面宏阔,刚出地表便奔涌如溪涧。寨中人于水面以一步距离为点,横铺石礅,虚实相连,方便两岸往来。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洗泥节,这里便是最欢快的场所。瑶寨被咫尺间的山峦所围,田地有限,需到遥远的寨外地界开辟新土,耕种劳作。一日之内难以往返,寨民索性在耕作处建了简易“牛庄屋”,吃住都在那里。春耕完毕,离家多时的寨民裹一身黄泥,牵了牛,扛了犁耙回来,先到蒲鲤井掬一捧甜水仰脖而尽,再洗却满身泥巴。这一天,也成为勾蓝人的节日,家家酿苦瓜,冲油茶,打糍粑,杀猪宰鱼,闹热远胜过大年。外出的子女无论多远,都会日夜兼程赶回家中,陪父母过节。
摸鱼是洗泥节最盛大的节目。一声口令,瑶家壮汉们纷纷扑入蒲鲤井前的溪面,成为“浪里白条”,或露或潜,或俯或仰,围追堵截。水花四溅而起,鱼则跳跃不止。谁摸的鱼越多,寄寓收成越好。疲累而发蒙的鱼儿一条条被摸上来,岸上老少人头攒动,拍掌声、欢笑声一片。惜乎我来时,洗泥节已过,只能对着空荡荡的水面,怅然想象那些生动的场景。犹如唐人元稹笔下那位白头宫女,独坐“宫花寂寞红”的行宫,想象开元年间的繁华。我比宫女幸运的是,开元逝去,永不可再,而洗泥节我可明年从容相约,终有一逢。
夜幕缓缓降临,勾出四下黑黝黝的山影,水声却更清亮了。这时,寨子中心处的相公庙里,篝火熊熊燃烧起来。劳作一天的瑶家汉子与阿妹,就着溪流洗去汗渍,围了火堆,载歌载舞。篝火照亮静默的山峦,也映红了一张张素朴的笑脸。廊檐下的长桌宴也早一字摆開,凉菜、糍粑、土鸡、烧鸭、肥鱼、蜂蛹、茶香饭、勾蓝芋和南瓜等一一陈列,一壶壶寨民自酿的甜糯米酒也端了上来。勾蓝人好客,又承继千百年来的敦厚古风,似乎在倾其所有,招待山外来者。我也顾不得斯文,随众人急急伸缩竹筷。推杯换盏间,火边的歌舞一直未曾停歇,像门外溪水一般洗涤我白日转悠的倦乏。
篝火越烧越旺,歌舞也进入高潮,正演绎勾蓝之名的另一种由来:瑶寨昔年盛行招郎习俗,“好女不出石墙门”,若哪家女子看中某位汉子,会大了胆,拿着鸡蛋上门提亲,外人称为“勾郎”。日子一久,瑶寨便被称“勾郎瑶”,又讹传为“勾蓝瑶”了。勾蓝女子的热情奔放,令我蓦地有了“我有所思在远道”之念。须臾间,思绪随糯米酒催生的醉意绵绵而涌。
篝火已尽,夜已深,勾蓝的清韵依旧在四野流淌。我借宿一家民宅,枕着汩汩流水,咀嚼勾蓝无边的清韵,渐渐入梦……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