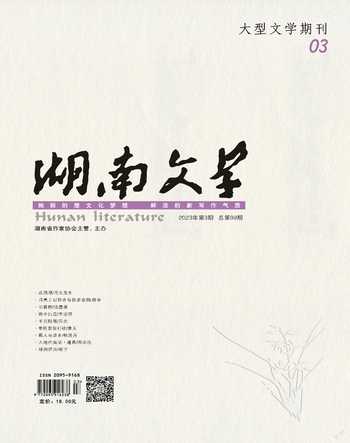在审美干预下的艺术创造
卢辉
让地域的“史迹”与“现状”,通过审美干预在一个瞬间呈现艺术再造的能力与特征,这的确需要有一颗强劲有力的智性的脑袋。胡丘陵作为对地域诗有着独具创生力的诗人,将自己对地域的审美干预与艺术创造,融入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中,并在《长沙三帖》的内部构造上,实现了自己孤悬而又坚定的美学抱负。
一、地域:审美干预下的极致化表达
说真的,地域诗要写好很不容易。因为,单靠几次游历很难“积淀”成有内涵的地域诗。特别是地域诗一旦局限于应景的视觉快感,就可能导致它只有在“像”或“不像”之间游离。而胡丘陵的地域诗,根本不在“像”或“不像”之间纠缠,而是将长沙这个特定地域的自然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历史属性、时代属性糅合在一起,让长沙不仅仅作为游历的视觉意象,而且把它作为一个“历史异象”与“现实具象”互为交错的地方视域。即,不是地域的图景式重现,而是地域的瞬间历史异化与现实表达:“长沙,一个天天被媒体刷屏炒卖的城市/我用诗歌,慢慢赎回,用微信原图发给你/那些直播的网红,只关注颜值/免得她们,忽略毛润之/问苍茫大地的风范,谭嗣同在菜市口的脾气”。可以说,长沙,既是一个政治符号,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隐喻,胡丘陵敏锐地抓住这两条线进行不断地打磨。他一方面不为既定的伦理、政治的定性所左右,另一方面致力于个人化的经验表达与审美创造。很显然,胡丘陵《长沙三帖》一开笔就已经让细心的读者感觉到:这不是应景的地域诗,更与所谓的主题诗没有任何的关联。在胡丘陵看来,他所认定的地域诗从来不是地域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个体生命的一部分——最好的、最可珍惜的、像捍卫自由那样的那一部分。同时,他坚持认为,与地域匹配的历史与现实,意味着自由的,同时又在无情消逝的那部分,而只有这一部分,才能被诗人“倾听”到:“湘水匆匆,不知是去赶路,还是去赶时髦/河水,同古城墙经历的事物一样/常常犯白沙的井水”。的确,在人们眼里,湘江本来就不需要设问。因为,它已经是一个足够耀眼的政治符号。那么,在政治的、时代的伦理主导下,是死守既定的伦理与政治的定性?还是努力激活更为繁复的情感伦理与政治诉求?胡丘陵仿佛在进行一场干预与创造的审美历险。也就是说,他更加明确地将地域写作置于某种“无穷”,置于个人与群体、与社会、与历史、与政治、与时代的交错中。这里的“交错”,如此孤悬又如此明亮,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词语调到最适合内心的温度与湿度、宽度与高度。
说到胡丘陵内心的温度与湿度、宽度与高度,不得不说到他的审美干预与艺术创造。从《长沙三帖》上看,长沙既有“被固定”的历史宿命,也有“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的现实自洽。读胡丘陵的诗,之所以微妙到每读一次都会使人有新的感受,那是因为在他的审美干预下,他的诗歌常常有极致化的表达,尤其是他并不急于去表现一切新的可能的情节,而是能把幻念中不可思议的、相悖的东西,同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应该说,凡是具有审美干预与艺术创造的诗人,他的语言一旦置于地方视域、时代场景、心理景深,他总能迅即将其抽离为一个个关键语词,通过语义的重新编码,使之在悖反、归谬、反讽、智取的逻辑演绎中,呈现出古今交错、似是而非、光怪陆离的历史幻影与现实群象:“一个叫作太平老街的小巷,超过神童的记忆力/白天,我用臭豆腐的偏爱/对岳麓书院,顶礼膜拜/晚上,我以咀嚼槟榔的方式/与岳麓书院,争论不休”。在这里,诗人将白天与晚上错落交叠在一起,像一场捕捉、组织或拆解各种踪迹的审美历险,并把这场审美历险介于历史与现实、雄辩与察识之间。在这个过程中,胡丘陵对長沙这个特定的视域空间所表现出的审美干预,足以让读者在主流话语之外,倾听一个类似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白”。这样的独白,在《长沙三帖》里已经形成一个系列,读者已经明显感觉到胡丘陵很想从地方视域,寻找到政治的、情感的新伦理:“对于长沙的工程机械,任何竣工的高楼/都是奠基的一块石头/永不酸痛的手臂,挖掘到东方十八层地狱的根部/也将泥土,举到西方上帝的高度”。的确,当胡丘陵恍然领悟到地域诗再不是一股浅表式的情绪释放时,随着他自己身份的转换,价值的转换,伦理的转换,情感的转换,他没有在审美干预中停下来,而是将《长沙三帖》从个人化转向历史化、现实化与公共化,尤其是他富有穿越感的审美干预,让读者找到了地域的归宿感,且多了一层政治的、伦理的、现实的、生命的诉求,而这一切都源于胡丘陵苦苦追寻的内心秩序:“岳麓山的枫叶,是拾荒老大爷的手掌/为有一个干净,而不饥饿的冬天/在秋风中忙碌地抖动//我也曾经想过,住在清水塘附近/只是,翻遍长沙所有的衣袋,没找到一片钥匙”。是呀,碌碌尘世里,过眼烟云的往事并不鲜见,所匮乏的应是一种情感储存、情感冲动、情感释放的驿站。凭借这个驿站,胡丘陵把他自己在地方视域里的所见、所为、所思、所想,以不动声色的“神秘感”,延拓了人间情怀的“宽度”和“景深”。而寻找这一把钥匙,正是他极力对理想世界的召唤。
二、诗人是地域最有灵性的命名者
地域诗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对地域重新定义、重新命名的过程,所以说,诗人又是地域最有灵性的命名者。从地域的史迹、地域的时运、地域的命理出发,最终指向历史与现实的生命体征与社会属性。胡丘陵的地域写作,采用的是“有根”写作:历史、现实、时代、家乡留给诗人的,都是有血脉的根,有人文的根,有代代相传的灵魂与信仰,并深深地烙刻在自己的骨髓里。在胡丘陵看来,一个地域要变成一首诗,一次审美干预要变成诗意指向,一次审美创造要变成诗歌情节,这就要看作者如何来分配历史的章节、现实的驻点和情感的节点。当然,在地域诗中,要维持好个人化的审美干预与审美创造并不是容易的事。就《长沙三帖》而言,地域诗必然要钟情于心与物产生奇异关联与连锁反应,钟情于幽微而深远的语境,形成自己心理意义上的一道若即若离的“距离”风景,让地域诗不至于陷入“应景”的窠臼。《长沙三帖》最大的妙处:无论是它可见的空间,可听的时间,还是它可触的生命,可感的经验,都能把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生命的“影调”作为文字编码与灵魂密码“嵌入”诗篇中,使地域诗总有一种如影随形的神秘感、时空感、时代感和历史感,呈现出情感的波段与理性的密度,构成了诗歌“别样”的世界。同时,胡丘陵对地域的审美创造,不是简单的语言再生,而是形成有一定干预性的个性经验,能把“干预”与“创造”双双置入母语,照亮那些美好而又令人纠结的记忆:“几支画笔,将繁华装进美术馆,躲过了冬天”全国的电视机,结满芒果/桥上的石头,都可以创意成猴子/长沙的灯光,总是帮助白昼,欺负夜晚”。可以说,地域诗里历史与现实的间离性,总会产生某种陌异的效果。在很多人看来,地域,只是一个被书写的对象,只是一种象征的符号;但在胡丘陵看来,地域却是一个“自洽者”,它能够左右事态,这也便是“长沙的灯光,总是帮助白昼,欺负夜晚”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胡丘陵不屑于写那些应景式的“华灯”“璀璨”等光鲜的词语,而是将这些看似光鲜的词语“收编”过来,用审美干预去弱化那种主题吟诵的惯性思维,这是艺术观念上的一场变革与拯救。
其实,别小看这种变革,在胡丘陵凌厉而又自然的笔调里,一种细小的尖利,和不经意间的放大,以及漫溢的多义性,无不透露出他审美干预的深度。而这个深度表现在《长沙三帖》善于把地域应景的那部分“打入”异质的环境中,启开另一个隐秘世界,避开地域诗的伪抒情。同时,将自己的一次次精神探险嵌入其中,并与当下进行合理的互换、摩擦、融通、渗透,由此产生精神历练和精神探险之后的“主观景致”与“精神空间”。与此同时,由于《长沙三帖》采用“异质”的切入,没有停留在观照描摹事物本身,而是以“心灵总态度”的内视点介入外部与内部世界,成功地将其幻化成了溢满内在精神的历史符号、文化符号与时代符号,使得《长沙三帖》阔大繁复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取向得以实施:“曾经我与橘子洲的沙粒,比谁/更能擦洗,湘水的波澜/现在,我与沙粒,势不两立”。由此可见,思维的“可逆性”,决定了诗歌写作的“能动性”,更决定了一首诗展开的思想层次、情绪密度与多维审美。《长沙三帖》以“我”的情感、伦理、观念、价值为圆点,并围绕“我”这个圆点画出千姿百态的“长沙群像”,这是胡丘陵特想勾画的长沙秩序图像。可以说,“长沙群像”既是他个体诗学的核心谱系,也是他把握生命存在与语言临界点的方式。正是因为胡丘陵凭借长沙这个特定的地方视域,能够深切体验并透彻反思这个地域在历史与现实交错中的反制与反哺的双重特性,所以,他的《长沙三帖》总能迸射出急迫的能量,且音质丰富:
从河东到河西,快如中车高铁的
第1节车厢到第8节车厢
而我,从此岸到彼岸
世界上最快的天河计算机,也算不出
哪一年抵达
从此岸到彼岸,从审美干预到审美创造,从穿越时空到激情现实,《长沙三帖》释放的能量,有时像风驰电掣的高铁,有时像浩瀚的云端数据。一方面,它带给我们以想象、激越和焦渴;另一方面,它带给我们以反思、察识和放旷。它不仅给人带来强烈的反差效应,而且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震撼。胡丘陵就像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话语场,对知晓的、未知晓的事物重新进行位置上、时间上、意义上的确定,以确保地域诗歌的内在含量。更重要的是《长沙三帖》里的那些鲜活、灵动、异样的文字仿佛是要冲出词语的排列组合,给人一种直观的视觉与感觉上的冲击力。尤其是他以少有的虚拟手法,把历史的截面与现实的片段缝合起来,并把历史的既定场景与现实的偶然变数汇于一体,表现出一位成熟诗人的风格与底气。应该说,《长沙三帖》这首诗,从审美创造、语言密度、语言质量、写作姿态、意境进入等方面对瞬间创造,对微小意境进行循环反复式的无限扩大,创造和拓展了艺术的新境界。
三、让地域成为一种艺术再造的神奇存在
纵观《长沙三帖》,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诗人就是想通过审美干预下的艺术创造,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一种反思,一种拷问。在胡丘陵身上所洋溢出的一直是那种竭力想在现实与历史中拷问人性、赎回人的本身。或许,胡丘陵已经认识到,当下,我们生活的范围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自动化程序的强迫形式之中,人的精神客观化了,人已越来越认识不到自己,认识不到自己的精神本身了。为此,一向有着质疑精神的胡丘陵,一直在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可以高扬精神的场域。在胡丘陵看来,长沙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时代的一部分,更是人间的一部分,只有人才能倾听到长沙的历史之声。换一句话说,只有每一个人了解了长沙,才能认识到自己。是的,作为诗人,胡丘陵既有放旷的激情、燃烧的创作和反讽者的姿态,又有经验的顶托、执念的渗透和知性的气质。但这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结果。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就必须在更沉、更高、更远的穿越中,创造出审美创造的新境界。可以设想,当《长沙三帖》更趋向于一种“普世价值”的存在方式时,它把人的灵性、激情、想象、回忆、反思统一调动起来,成为无限的极致表达,成为一种再造现实的神奇力量。不管是探究长沙史迹的元象,还是挽留长沙现实的激越,胡丘陵都在技艺追求的过程中力图保证艺术创造的高度完整,并对写作的题旨、构架和速度进行有效控制,从而避免了由于文本实验而导致的文本虚化。
可以说,以大气度、大景别、大视野见长的胡丘陵,并没有被“大词”所吞噬。恰恰相反,他更倾向于自我情感律动的内省,哪怕是“自我”的精神隐私也毫不去遮蔽。可以说,因为社会的回暖,正好是万千气象的交接点,胡丘陵凭借时事突转、新旧错落,采用局部隐喻、时空穿越等方式,从历史与现实交错“投影”中提取出艺术再生的审美特质。特别是他的一次次审美干预,挑动了我们的筋肉组织,刺激了我们的语言本能,引示我们察识一种无处不在的现实秩序。特别是《长江三帖》的历史隐喻、现实隐喻与仪式隐喻,必然牵涉到一个更广大的范围,这就是想象性文学的整体功能的问题。为此,在这首诗中,我们还获得少有的扩张意象与强合意象:“在这个现代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在阳极,被詩歌电解/到了阴极,成了含人量99.99%的人”。可以说,这种扩张意象与强合意象,对胡丘陵来说,也许还比较生涩,因为这种表达还只是停留在技术性的层面。但是,这并不影响整首诗的艺术追求与艺术表达。对胡丘陵而言,用惯“坚实的现实感”来进行诗歌写作,一旦改用“宏阔的虚拟性”来进行诗歌创作,难免会留下某种“强合”的生涩痕迹。好在胡丘陵对历史,对现实,对现场,对虚拟的介入,总是保持高度的激情,保持高度的平衡力:一步步的情感节奏,一程程的理性速度,既有历史风物的鲜活与灵动,又有生命的大度与豁达,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侠客”在穿越中所拥有的从容与醒悟,形成了一种高远而辽阔的精神境界。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