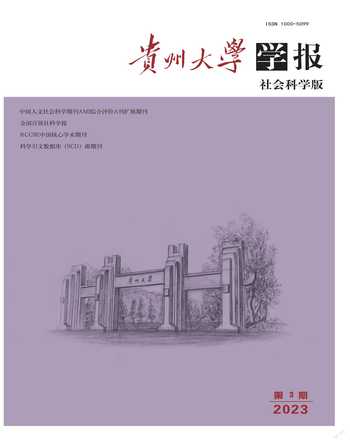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方向与路径
作者简介:李勇,男,安徽霍邱人,博士,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东南大学反腐法治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方向与路径
摘要:企业合规的本质是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的自我变革,属于企业自治、协商治理,应当是“软法”治理范畴。合规入法不是“条件-行为-后果”反向制裁的“硬法”立法模式,而是“合规-从宽”正向激励法律化的模式。“软法”意义上的法律化,既包括刑事法、行政法、公司法等正向激励的“软法”条款,又涉及官方指引、行业规范、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二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这是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基本方向。在法律化路径上,刑事法应立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和完善刑事激励措施;公司法设立法定代表人前科登记豁免等合规从宽的行政激励措施,建立“检察罚”制度,完善刑事激励与行政激励衔接与配合的机制。然而,合规有效性标准以及监管、评估机制属于“最佳实践”,不宜通过正式立法的方式建立,应通过官方指引、行业规范、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来解决。
关键词:企业合规;合规计划;法律化;软法
中图分类号:DF6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3-0060-12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合规是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企业合规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时期(2017-2018年)。我国最先引入企业合规的是金融领域,早在2017年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出台了《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2018年的“中兴事件”进一步激发了业界对企业合规的关注,这一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合规元年”。同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出台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国际标准ISO19600-2014《合规管理体系指南》的基础上制定发布了GB/T 35770-2017《合规管理体系指南》。该阶段企业合规主要停留在行业倡导层面。第二阶段是制度试验期(2020年)。2020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六个地方开展第一批试点。检察机关的介入,企业合规从行业倡导转入制度引进,面貌为之一新。检察机关的行动表明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措施呼之欲出。第三阶段是企业合规法律化的曙光期(2021年至今)。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0个省级检察院61个市级检察院381個基层检察院,开展更大规模的第二批试点;同年5月13日,国资委高调宣布中央企业已全部成立合规委员会;同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国家八部委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2021年,还发生了一系列合规事件,如阿里巴巴被罚事件、滴滴公司被罚事件、美团公司被罚事件。2022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检察长(扩大)会议上提出,3月份第二批试点结束后将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试点,为推动立法打好基础[1]。2022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试点企业合规改革全面铺开,由此表明企业合规的法律化已经进入快车道。
企业合规(又称合规计划或合规)本质上是企业自治、协商治理的模式,在法律上属于“软法”范畴。企业合规入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硬法”的立法化,而是“软法”的法律化。一般而言,立法是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法律的活动,立法过程是国家意志确认的过程,其条文的基本结构“条件-行为-后果”,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法律后果实施。但是,这样的“硬法”立法模式并不适用于合规。合规本质上是一种公司自治和协商治理模式,体现的是国家化到私人化的发展趋势[2],是合规计划与私人规范融入法律制度[3]。合规融入法律的过程并不是以“条件-行为-后果”反向制裁的立法模式出现的,而是“合规-从宽”的正向激励的法律化模式。一般的立法化,是在法律中规定实施某种行为或不实施某种行为,将会引发何种法律制裁后果。但是,合规入法是企业建立和实施有效合规计划将会获得怎样的激励,并非是企业不建立合规将会引发怎样的处罚后果。换言之,合规入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立法化,并非将合规设定为企业的法定义务,也不是制定专门的“企业合规法”。合规入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行法律中设定正向激励的“软法”条款,这不仅仅涉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更为重要的是涉及行政法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二是制定出台配套的官方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标准、行业规范、协会标准化文件等“软法”,这些文件虽然不是正式立法的结果,但它们属于广义上的法律。当今的法律体系包括“硬法”和“软法”。它们不是以立法机关的意志为基础,也不是国家权力的命令或者来自上层权威的强加,这是因为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时,它的存在取决于公民与立法、执法官员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规入法是合规的法律化,而非立法化。当前,学界讨论企业合规立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合规作为“软法”治理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片面聚焦于刑事法的修改,而忽视行政法规、公司法等经济法的修改,企业合规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刑热行冷”的现象。企业合规的法律化是一项体系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更不是通过修改刑事法就毕其功于一役的。
二、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方向
当前,实践中存在将企业合规肤浅化和庸俗化的现象,有的把合规理解为遵纪守法,有的把合规理解为“合乎法律规定”。企业合规从20世纪90年代诞生至今,被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纳吸收,经历了从预防犯罪内部机制到企业治理结构变革、从注重管控到注重企业文化的发展历史。当下,企业合规本质内涵在于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的自我变革,这决定了合规入法的方向是引导型、激励型的“软法”模式,而不是强制型、制裁型的“硬法”模式,这也是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基本方向。
1.以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自我变革为目标
首先,企业合规的核心在于塑造合规的企业文化[5]。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合规是为预防、发现犯罪行为而由企业实施的内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措施、机制(组织体系)[6]。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内涵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企业合规在美国诞生之初的界定,可谓合规的“古典定義”。这种“古典定义”来源于美国《组织量刑指南》(1991年),该指南将企业合规界定为旨在预防、发现和举报组织犯罪的内在机制,如果组织能够证明曾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适当的合规计划来阻止不当行为发生的话,为被判有罪的公司减轻刑罚处罚。《组织量刑指南》确立了有效合规计划的七项基本要求,包括采用政策和程序来预防犯罪行为、高层人员对合规计划的适当监督、将合规的要求传达给所有员工,并根据需要进行监控并持续更新合规计划等。这种古典意义上的企业合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为预防、发现犯罪行为避免被制裁、处罚而建立完善的内部机制。二是建立了合规计划的企业,国家给予鼓励回应,作为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依据。这样,企业建立合规计划类似于“种植胡萝卜”[7]。
这种“古典定义”的合规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发展。2004年美国量刑委员会对《组织量刑指南》进行了修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引入组织文化,特别使用了“合规和道德计划”(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的表述,强调组织文化对合规的重要性,要求企业不仅要促进“守法”,还要促进“道德行为”。这将组织文化正式作为组织量刑指南的一部分,将有效合规计划描述为旨在“预防和发现犯罪行为”以及改善组织文化的内控机制,这种组织文化是“鼓励符合道德的行为和承诺遵守法律”的文化[8]691-692。2010年以后,组织文化作为企业合规的内涵进一步强化。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于2010年再次修订了《组织量刑指南》,提高了设立首席道德与合规官(CECO)(或类似角色)的重要性[9]。从合规计划到合规道德计划,从首席合规官(CCO)到首席道德与合规官(CECO),体现企业文化(组织文化)在企业合规内涵中的地位变化。到20世纪末,组织文化在合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0]942。201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19600)的推荐标准,后于2018年11月启动修订,形成了2021年《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37301)的认证标准,其最大的特点是融入企业文化,在引言第一句就指出“为获得长期成功的组织需要,基于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建立和维护合规文化。”
从企业合规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经历了从强调管控(control)到重视企业文化(culture)的历史。早期的合规计划主要侧重于通过从宽处罚来激励企业建立管控合规风险的制度,后期以诚信为基础的合规计划则侧重于建构组织文化。据此,现代意义企业合规的基本内涵应当为:旨在预防和发现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改善企业文化(即“鼓励合道德的行为和承诺遵守法律”的企业文化)的企业内控体系[8]689-692。如今,以诚信为基础的合规计划占主导地位,合规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合规的核心所在。合规的“规”不限于刑事法,其预防的也不仅仅是犯罪,还包括违法甚至不当(不合道德)的行为。《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ISO37301)指出,“一个有效的、组织范围内的合规管理系统使组织能够证明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行业规范和组织标准,以及良好治理标准、普遍接受的最佳实践、道德和社区期望的承诺”。美国《联邦商业组织起诉原则》(2019年修订版)对合规计划的界定是“由公司管理层制定,以防止和发现不当行为,并确保公司活动按照适用的刑事和民事法律、法规和规则进行。”[11]
从上述两个代表性的文件可以看出,合规的“规”具有开放性,涵盖了刑事、民事法律、法规,以及“软法”意义上的规则。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合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预防、发现不当违法犯罪行为的内控体系;二是塑造合规的企业文化。企业建立事前合规,就是要塑造合规的企业文化;涉案企业重建合规计划(事后合规),就是要重塑合规的企业文化。企业合规之所以重视文化建设,原因在于企业文化决定员工的行为选择。一个行贿成风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内部形成以行贿获得销售业绩为荣的氛围,其员工开展销售业务时必然倾向于选择行贿。反之,一个廉洁的企业文化氛围,会向每一位员工传达廉洁行事的信号。建立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应当以世界的眼光,与最新的国际标准接轨,以塑造合规的企业文化为目标。
其次,企业合规的关键在于改善治理结构。人们习惯于望文生义地将企业合规理解为合法经营、遵纪守法。其实,这样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甚至会产生重大误导。人类社会自从有法律以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法律。作为一个企业,合法经营、遵守法律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也不是一个新想法。当今的企业合规,是崭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其特别之处在于在公司内部设定一个独立的部门或者专门人员来检测和阻止违反法律和政策的行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将合规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改变其原有的领导层权力架构和管理模式。传统公司治理结构主要体现为业务管理(首席执行官CEO)和财务管理(首席财务官CFO),现在增加了一个首席合规官或者首席道德与合规官(CCO或者是CECO),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从原来的主要是“两驾马车”变革为“三驾马车”。在这种权力框架下,通过系统的制度体系将合规融入企业管理全过程。合规是一种崭新的公司治理模式,颠覆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12]。企业内部权力架构、运行模式至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不触及企业治理结构的合规不是真正的合规,不能改善企业治理模式的合规不是有效的合规。改善了治理结构的合规能够阻止和预防企业违法犯罪行为,节约了国家治理企业犯罪的成本,因此,国家鼓励企业建立合规计划。这样,国家其实是通过减免处罚的方式将预防企业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转移给企业自身,这是一种企业自我管理、协商治理模式。
总之,企业合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本质目标是塑造合规的企业文化,法律的任务是给予这样的企业以激励措施。
2.以正向激励“软法”模式为基本方向
如前所述,企业合规是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合规文化是其本质目标。文化需要一种合作、柔性的力量,靠强制压力可能会适得其反。“政府关于合规文化的政策可以通过充足的‘阳光和关怀在公司内部培养亲社会、守法的力量。”[10]976因此,“软法”是合规法律化的基本方向。
一般认为,“软法”是不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并不一定都是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软法”以协商一致为法律通过的要件,而不是采取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在制定程序上,从严格的法定程序、立法程序到简易的磋商、谈判、协调等多元化方式。与“软法”相对应的是传统的“硬法”,“硬法”来源于国家意志的確认,来源于议会的代表,来源于议会议事的多数票决规则,来源于严格的立法程序等[13]。“硬法”的立法模式是“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而“软法”没有明确的行为模式,一般不规定法律后果,即使规定了法律后果,也是正向激励的积极法律后果。“软法”是提倡性法律规范,是激励和引导人们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行为人遵守这种规范能获得相应的激励,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照顾等;行为人即使违反这种倡导性的法律规范,也并不会导致承担法律责任。“软法”具有自律性或引导性、建议性、激励性、协商性等特点。“硬法”强调他律,“软法”侧重自律。“软法”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正式立法中的“软条款”;二是政治组织形成的规则和社会共同体形成的规则[14]。前者如《公司法》第5条第1款“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后者系指未经正规程序成立之法规范,比如政治组织的章程和规范性文件、行业协会对本行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章程[15]。上述两种渊源的“软法”均属于广义的法律范畴。
合规和“软法”一直是法律学者和社会学家热议的话题[16]。如今,商业、金融和其他国际商业交易越来越多地在“软法”规则下进行。我们正在见证传统监管的衰落,监管体系逐渐被一套无定形且不断演变的非正式“软法”治理机制所取代[17]。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软法”和合规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落后。近两年,随着企业合规理论的热议,有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话题,针对《公司法》第5条第1款指出,“公司软法重心在于激活公司自我规制和守法效应”,在公司内部建立一种长效的监督性守法约束机制,据此建议公司法通过提倡性条款,鼓励公司通过章程规定建立科学的自我管理机制,积极培育合规守法文化[18]。此前,公司法学界主要从“软法”角度研究该条款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问题,尚未触及企业合规理论,认为该条款是倡导性规定,并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或后果,以鼓励或一般性义务的形式向企业提出要求,但法律并不能直接强制企业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可称之为狭义的软法责任[19]400。
合规作为一种企业自治,是企业的自我选择,法律的任务不是将合规规定为企业的法定义务,而是通过法律设定激励措施来鼓励和引导企业建立合规计划。对于事前合规而言,企业建立并有效实施合规计划,将来涉案时可以成为切割企业与个人责任以及获得从宽处罚的事由;对于事后合规而言,企业可以自愿重建合规,经评估有效后,执法、司法机关将给予从宽处罚。美国《组织量刑指南》确立的合规计划正是这个思路。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大量的“软法”来鼓励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美国学者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几乎完全是由稳健的民间社会组织和企业本身来完成的,往往是为了响应来自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市场压力而增加非政府组织的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开发了各种合作执法工具来促进企业自愿遵守监管规定,其典型例子包括20世纪90年代“重塑环境法规”倡议下推出的40多个合规项目,以及与职业健康和安全相关的类似联邦和州的合规计划项目[19]389。意大利作为较早从美国移植企业合规的大陆法系国家,于2001年6月8日通过首部企业合规法令《关于法人、公司、协会及非法人组织行政责任的法令》(简称第231号法令)。根据该法令,如果企业在犯罪后的悔改表现较好,检察官可以建议对企业适用一系列激励措施,例如,减少经济处罚的数额,或者不再对有悔改表现的企业适用褫夺资格处罚等。如果企业在犯罪之前已经通过并有效地实施了适合于预防此类犯罪的组织、管理和控制模式(即合规计划),则可以排除企业不履行监督或者管理义务的责任[20]。
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基本方向,应当坚持“软法”治理理念。合规是企业治理理论,本质在于改善治理结构和塑造“良好企业公民”的文化,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企业社会责任讲究自愿履行,政府采取“软性”管制,政府应当作为参与者、组织者、促进者和引导者,采取积极的激励措施而不是惩罚措施。一方面,合规是企业的自我选择,不应将建立和实施合规计划作为企业的法律义务[21],通过法律上从宽处罚的制度设计来激励企业自主合规。这里的法律不限于刑事法,也包括行政法、公司法等。另一方面,合规也包括制定配套的官方指引、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标准、规范、协会标准化文件等“软法”。事实上,在我国企业合规早期兴起的金融领域,已经存在大量的合规“软法”,例如,《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等。这些“软法”规范的最大问题在于大多停留于口号式宣传,缺乏实质有效的激励措施,往往流于形式。
三、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路径
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路径,在刑事法领域应当立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刑事激励措施,在经济法领域建立合规从宽的行政激励措施,这属于在正式立法中设定“软法”条款;同时,通过制定官方指引、行业规则、协会标准等“软法”规范建立合规有效性标准、监管及评估等机制,两方面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1.建立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基础的刑事激励机制
2018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给予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从宽处罚的激励,但不会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认罪认罚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选择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是一种典型的激励性“软法”条款,也是中国特色企业合规在刑事法领域法律化的基本路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试点文件也明确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企业合规试点改革的基本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求开展企业合规试点改革要与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起来。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4条规定,涉案企业开展合规的首要条件就是“涉案企业、个人认罪认罚”。笔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在未来立法上引入企业合规的立足点仍然应当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基点。
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适用对象原本就包含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理当具有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余地。
其次,自然人的认罪认罚态度通过其言行征表。作为“没有灵魂和肉体”的企业,其认罪认罚体现在合规计划上。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具有“企业公民”的地位,企业文化影响和塑造员工的行为,“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员工”。企业作为一个组织体,企业文化类似于自然人的灵魂。一个合规的企业文化,再犯可能性降低,预防必要性降低,进而导致量刑中的预防刑降低。“如果个人刑法要求个人只在他或她的行为应受谴责的情况下才受到惩罚,那么公司刑法也应该对公司提出同样的要求”[22]。企业因有效的合规计划,预防犯罪的必要性随之降低,预防刑减少,进而获得从宽处罚。这与自然人认罪认罚导致预防刑降低而获得从宽处罚的机理是一样的。
最后,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均属于合作型司法的范畴。企业合规是一种企业违法犯罪控制和治理的合作模式,国家将治理企业违法犯罪的职责转移给企业自身,实现企业违法犯罪治理由“对抗模式”走向“合作模式”。在美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协议本来就是和解和辩诉交易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可见,企业合规从宽与认罪认罚从宽均属于合作型司法的范畴。
近年来,关于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关系问题在理论界出现了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合规不能单纯作为量刑从宽的因素,而应当作为出罪因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效率为导向,强调节省资源、降低成本、快速处理案件,通过给予认罪认罚的嫌疑人、被告人较为宽大的处理,形成一种激励效应,使得更多的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程序,实现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相比之下,合规考察制度则强调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要求设置足够长的合规考察期,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司法资源[2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首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企业合规在本质上都是“协商治理”模式。“协商治理”是这两项制度的最根本特征,也是二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次,效率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追求之一,而非全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程序从简的效率目标只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特征之一,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实体从宽,通过实体从宽实现犯罪治理模式从“国家-被告人”二元对立向合作型司法转变。再次,认罪认罚从宽中的从宽既包括量刑上的从轻,也包括不起诉。事实上,不起訴本身就是一种程序出罪。从合规的实践试点情况看,大部分案件都作了相对不起诉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程序上的出罪。最后,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一样,都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产物,二者在追求诉讼效率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趣旨。由于企业内部结构具有高度复杂性,侦查和调查成本极其高昂,指控难度极大。企业合规通过控辩协商实现节约侦查、调查成本,降低指控难度,进而实现诉讼经济和效率的目标。企业合规在美国诞生的重要契机之一恰恰是公司犯罪、白领犯罪,其侦查和指控成本高昂。例如,著名的西门子案件,案件事实涉及向65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14亿美元。西门子进行内部调查就花了5亿美元的费用[24]。暂缓起诉协议(DPA)通过让涉案企业承认犯罪事实,从而节省调查成本。至于说企业建立合规计划之后的考察周期长、成本高,其实已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诉讼效率问题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本身就是一个诉讼程序的终结,案件侦查、审查以及罪名适用等实质性的实体和程序事项均已经办结,合规计划的考察评估主要是检察机关依托第三方的社会资源进行,一旦有效性评估考察通过,只是程序性地作出最终不起诉决定;评估考察不通过,则提起公诉,也无需再次审查证据。因此,与其说合规不起诉的评估考察是诉讼程序事项,毋宁说是在诉讼程序“延长线”的一个社会治理事项。
总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企业合规进入刑事法律之中的路径依然是“不二选择”,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基础,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起不捕、不诉、量刑从宽三位一体的激励机制。对于企业犯罪来说,现有的相对不起诉面临诸多瓶颈,对涉罪企业相对不起诉之后,缺乏监管措施进行后续监督。无论是相对不起诉之前还是之后,检察机关都无法触及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无助于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久而久之,会导致对企业犯罪“网开一面”甚至“变相放纵”。只有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合规计划的建立和实施作为不起诉的附加条件,并设置足够长的考验期,给予涉罪企业以“考验不合格随时被起诉”压力,才能真正激励和倒逼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美国的DPA(暂缓起诉协议)一样,附条件不起诉是企业合规的“标配”,需要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的条款。笔者曾建议采取修正案模式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第182条之一和第182条之二,分别规定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范围、考验期等[25]。这是企业合规在刑事法领域法律化亟待解决的事项。
企业合规除了不起诉之外,还有量刑从宽。当前试点有一个误区,将企业合规的“火力”集中在不起诉方面,无论是发布案例还是改革政策宣传,都集中在不起诉。有些地方甚至提出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也可以不起诉。其实,合规从宽既包括不起诉,也包括量刑从轻、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企业可以减少罚金的90%[26]。将量刑从宽作为企业合规刑事激励措施的意义在于:一是解决企业合规适用对象的问题。如果说合规不起诉一般适用于轻罪案件,那么合规量刑从宽则适用于所有案件和罪名。这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案件和罪名是一样的。二是防止以合规之名违反罪刑法定。如果将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措施仅瞄准不起诉,那么对于一些重罪案件,动辄以合规为由进行不起诉,那么就可能存在违反罪刑法定的风险。从法律化的角度来说,合规量刑从宽并不需要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规定,完全可以作为合规从宽量刑的依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刑法是否需要同步修改呢?笔者认为刑法无需修改。在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有人提出刑法应当同步修改,但并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甚至有人认为,仅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给予从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片面割裂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违反刑事一体化的基本法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企业合规制度是典型的实体与程序交叉的领域,是在程序法中规定还是实体法中规定,只是一个立法技术选择的问题,不能因为是实体与程序交叉的问题,就要求实体法和程序法必须重复规定。例如,追诉时效也是典型的实体与程序交叉的问题,有的国家把追诉时效问题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日本的追诉时效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250条。我国的追诉时效是规定在《刑法》第88条之中的,从立法表述上看,“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里的立案侦查、逃避侦查或审判、被害人、控告、立案都是程序性术语,但却规定在实体法之中。不能因为追诉时效规定在实体法之中,就否认追诉时效是一个程序问题;不能因为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对此进行规定,就认为执行刑法的规定是违反程序法的。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来说,对于实体与程序交叉的问题,立法上没有必要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进行重复规定。从节约立法资源的角度来说,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上已经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因此,企业合规的内容在刑事訴讼法中进行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更加科学合理。
2.建立合规从宽的行政激励措施
对于企业来说,因违法面临行政处罚的风险比较多见,因犯罪面临刑事处罚的风险并不多见,且企业犯罪以行政犯为主,而行政犯具有行政从属性,以违反前置的行政法规为前提,因此,企业合规的法律化,如果只考虑在刑事激励措施而忽视行政激励措施,不可能实现企业合规的治理目标,更何况企业合规的“规”原本就具有开放性。我国关于企业违法的行政处罚措施主要分布在公司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税法等经济法领域《行政处罚法》与经济法中的行政处罚条款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分散在经济法中的行政处罚条款属于广义上的行政处罚。同样,“行刑衔接”不仅仅是指《行政处罚法》与刑事法的衔接,还包括经济法领域的行政处罚条款与刑事法的衔接。。合规计划的建立和实施,是一项高成本的事业,如果没有充分完备的激励措施,对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相关经济法中增设合规从宽激励的“软法”条款,是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的基础性工程。
首先,增设行政处罚从宽的“软法”条款。企业合规在经济法领域的法律化,并不是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之中强制企业必须建立合规计划,也不是规定不建立合规计划给予相应处罚的“硬法”条款;而是在这些法律中设置“软法”条款,规定事先已经建立了合规计划的企业,在违反行政处罚条款时可以获得从宽处罚;事先没有建立合规计划,在违法行为发生后自愿建立和有效实施合规计划的可以获得从宽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与涉案企业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并要求企业建立合规计划,经考察有效的合规计划,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隐含了企业合规的行政激励措施,其中第25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法定情形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反倾销法》第31条、《<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保护条例>的实施办法》第27条、《证券法》第171条均规定了行政和解,遗憾的是没有明确使用“合规”的表述。但是行政执法实践已经走在了前面,引入了合规的因素。例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公司作出罚款3442亿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同时,向美团公司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美团公司全面整改并连续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合规报告[27]。
现行法律在已有的行政和解基础上,进一步增设合规激励的“软法”条款,明确将企业合规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建立企业合规的附条件行政处罚制度,这是我国企业合规在经济法领域法律化的重要路径。如前所述,我国《公司法》第5条第1款的“社会责任”条款,属于典型的“软法”条款,只规定了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公司法领域的学者认为,这个条款用意不在于确定具体的义务责任,只是指出一种价值方向,没有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违反义务的后果[28]。有学者批判认为,该条款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后盾,从规范意义上讲是不完整的,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行为后果的内容,难以起到规范主体行为的作用[29]。其实,这是对“软法”的误解,“软法”的特征就是正向激励,没有规定违反该条款的后果并非该条款的缺陷,真正的缺陷在于没有规定履行了该条款的责任将会获得相应奖励。只有配套规定激励措施,才符合合规“软法”治理以正向激励为基本模式的要求,而不同于传统“硬法”负向制裁模式。遗憾的是,《公司法》当时修改并无合规理论支撑,没有规定相应的激励措施,导致该法第35条第1款成为“沉睡条款”。在庞杂的经济法、行政法之中增设合规“软法”条款,是一项系统工程,虽然任务艰巨,但却不得不努力推进。
其次,建立合规行刑激励的衔接机制。行政激励措施、刑事激励措施的相互衔接和配合是企业合规得以良好运行的基本条件。刑法是其他法的保障法,行政犯的典型特征是以违反前置的行政法规为前提,而企业犯罪的常见类型都是行政犯。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说,在到达刑事违法之前,通过行政处罚予以截堵无疑是最理想的。当前,亟待解决的两大行刑衔接问题:一是“检察罚”制度。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检察机关对企业犯罪做出不起诉决定后,并无罚款权。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发现企业涉嫌犯罪时移交给公安、司法机关,检察机关针对企业合规做出不起诉决定后,会给行政机关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行政机关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大大影响了合规不起诉在替代刑事处罚方面的功能发挥。实践中,还存在检察机关颇费周折地让企业建立并实施合规计划,进而作出不起诉处理,努力救活企业,但行政机关没有将合规作为行政处罚从宽的因素考虑,甚至把企业“罚死”了。为扭转这种现象,对于那些由行政执法案件转化过来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时,可以直接科处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在立法上建立类似于“检察罚”的制度[30],这是我国企业合规法律化值得考虑的选项。二是改革企业法人前科职业禁止制度,建立企业合规法人前科登记豁免制度。2021年4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2条延续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不得担任企业法人。涉案企业单位犯罪中的责任人如果是法定代表人,通过合规考察,被判处缓刑,按照《条例》规定,这个企业必须变更法定代表人,但是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银行贷款授信、客户合作都是基于对法定代表人的信任,一旦变更法定代表人就意味着企业倒闭。这样,检察机关通过企业合规试图实现“放过企业”的目标就落空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倒闭了企业”。这是迄今为止企业合规研究领域尚未关注的。从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角度来说,应当对这样的企业法人前科职业禁止制度进行改革,在《条例》中设立企业合规法人前科登记豁免制度。
3.建立合规有效性标准及监管、评估的“软法”规范
企业合规始终面临的灵魂拷问是合规计划能够有效地阻止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吗?美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合规计划经过努力可以是有效的,有效的合规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如何监管和评估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有效性的标准如何确定问题远未达成共识[31]。合规计划有效性的监管、评估问题在其发源地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如影随形,原因在于合规计划的体系很容易被模仿,通过模仿而搭建合规计划体系,并没有真正降低不当行为的发生率,司法机关和监管机构也很难确定其有效性[32]。合规有效性标准、监管、评估配套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是这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合规有效性标准、监管、评估是典型的“最佳实践”,属于非正式政府行动的产物,但是其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比正式的立法更大[10]964,合规有效性标准、监管、评估等机制难以在国家正式立法中进行规范,但是专业标准领域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软法”更有灵活性,效果更明显。
首先,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标准和办法。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主体多元化,其中小微企业数量庞大。截至2021年10月,我国小微企业主的数量已达到了8 000多万,它们占据了中国90%的市场主体,贡献了80%的就业,60%以上的GDP。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平均每户小型企业带动8人就业[33]。小微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市场经济主体中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但是我国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家族式管理、合伙人式管理,经营管理方式粗放,人治色彩浓厚,企业与企业家合二为一、家企一体。公司战略定位、生产、营销及售后缺乏专业流程管控,缺乏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同时,还面临经营成本压力大、市场竞争激烈、融资困难等难题。一般而言,企业合规作为高成本的事项,适用于中大型企业。对于小微企业来说,不仅成本高昂是不可承受之重,更为重要的是其规模和结构决定了不可能建立完备的合规计划。这种现状决定了中国的企业合规制度,不能忽略小微企业这样如此庞大的市场主体。小微企业涉案时,同样不能“一诉了之”,应当给予其重建合规计划的机会和关怀,在对其合规计划实施的监管、评估标准和方法上应当不同于大中型企业。《合规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ISO37301)对合规计划列举了组织环境、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行、绩效评价、改进7项要素26个子要素,并规定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不论其类型、规模和性质。但是,对于一些小微企业来说,整齐划一地全部满足26个要素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譬如,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企业,成立合规委员会就不现实,至多设立合规专员,要做到“一案一企”“一企一策”。什么样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合规计划,不同规模企业的合规计划是不同的,关键是符合“四性”“三C”。“四性”即适应性、针对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适应性要求合规计划要符合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针对性要求合规计划应当针对识别的风险而不能漫无边际,具体性要求合规计划的制度设计要融入业务流程且具体可见,可操作性要求相应的措施、政策易于实施操作。“三C”即清晰(clear)、简洁(concise)、完整(complete)。清晰,即政策必须易于理解;简洁,即说你需要的和需要你说的(Say what you need,and need what you say);完整,即策略和计划全面覆盖业务流程[34]。
其次,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通过行政诉讼监督、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机关具有监督职能。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問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在政策上支持了检察机关监督违法行政行为,这种特殊的监督构造,有利于检察机关统合行政机关的力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协同监管模式。企业合规是社会系统工程,检察机关应协同地方行政机关与之形成合力。检察机关可以牵头工商、市场、税务、审计、建设、司法、环保等行政机关联合成立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委员会,组建企业合规监管专业人员名单库,选派第三方监督评估小组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实施监管。在行政违法案件中,以行政机关为主导,委托第三方监管组织,对涉及行政违法的企业合规计划实施监管。在刑事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作为涉案企业合规的办案机关,委托第三方监管组织监管。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八部委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确定的原则是“检察主导、各方参与,客观中立、强化监督”,可以说这是一种协同监管模式。协同监管模式被认为是这一种合规监管的成功模式,原因在于它创造了由资源共享、合作、信任而产生的共赢局面。
上述有效性标准以及监管、评估机制均属于操作层面的制度建设,无需在立法层面规定,不是立法化的问题,而是作为“软法”的法律化问题,可以通过官方规范性文件、行业规则、协会标准等“软法”予以规范。对于事后合规,可以借鉴美国的《组织量刑指南》《企业合规计划评估》(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的做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对于事前合规,可以由行业协会等制定相关推荐标准。例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于2022年5月23日发布了《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团体标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12日发布了GB/T 35770-2022/ISO 37301:2021《合规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这些都属于“软法”的范畴。
四、余论
当前,企业合规试点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刑事司法领域,截至2023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企业合规案件5 150件,已有1 498家企业整改合格[35]。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了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在行政执法领域,国家工商总局针对阿里巴巴、滴滴、美团等大型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指导、督促其合规整改、提交合规报告,但是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合规行动乏善可陈。从试点的情况来看,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也暴露诸多问题。例如,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差异问题、放过企业还是放过责任人问题、合规计划流于纸面问题、行刑衔接问题、监管评估标准不明确不规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中,既有企业合规领域的共性问题,也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单纯的移植国外制度、直接套用国际标准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针对中国国情,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合规制度,必须全面系统建立“软法”体系,绝非仅仅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
参考文献:
[1]孟亚旭.最高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将在全国推开[EB/OL].(2022-07-12)[2023-03-05].https://t.ynet.cn/baijia/33051271.html.
[2]托马斯·罗什.合规与刑法:问题、内涵与展望——对所谓的“刑事合规”理论的介绍[J].李本灿,译.刑法论丛,2016(4):357.
[3]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换[M].周遵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71.
[4]J.ELLIES.The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A Reply to Matthias Goldman[J].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2(2):370-371.
[5]李勇.涉罪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研究——以A公司串通投标案为例[J].政法论坛,2021(1):137.
[6]M.GOLDSMITH,C.W.KING.Policing Corporate Crime:The Dilemma of Internal Compliance Programs[J].Vanderbilt Law Review,1997(1):9.
[7]Growing the Carrot:Encouraging Effective Corporate Compliance[J].Harvard Law Review,1996(7):1794.
[8]C.FORD,D.HESS.Can Corporate Monitor-ships Improve Corporate Compliance?[J].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09(3).
[9]D.HESS.Ethical Infrastructure and Evidence-Based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s: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Empirical Evidence[J].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Business,2016(2):340.
[10]D.C.LANGEVOORT.Cultures of Compliance[J].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2017(4).
[11]The Department of Justic of the United Stated[EB/OL].(2023-03-01)[2023-03-05]https://www.justice.gov/jm/jm-9-28000-principles-federal-prosecution-business-organizations#9-28.010.
[12]S.J.GRIFFITH.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Compliance[J].William & Mary Law Review,2016(6):2 077.
[13]羅豪才,周强.软法研究的多维思考[J].中国法学,2013(5):104.
[14]罗豪才.公共治理的崛起呼唤软法之治[J].行政法论丛,2008(11):5.
[15]刘宗德.台湾证交法强制公开收购制度之合宪性及改革论议[J].月旦法学杂志,2015(10):86.
[16]D.E.Ho.Compliance and International Soft Law:Why Do Countries Implement the Basle Accor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02(3):647.
[17]S.L.SCHWARCZ.Soft Law as Governing Law[J].Minnesota Law Review,2020(5):2 471-2 472.
[18]王兰.公司软法定位及其与公司法的衔接[J].中国法学,2021(5):274-275+281.
[19]V.H.HO.Beyond Regulation:A Comparative Look at State-Centr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w in China[J].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2013(2).
[20]刘霜.意大利企业合规制度的全面解读及其启示[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1):59-73.
[21]孙国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与刑法修正[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3):55.
[22]C.G.DíEZ.Corporate Culpability as a Limit to the Over criminaliza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Regulation,Corporate Compliance,and Corporate Citizenship[J].New Criminal Law Review,2011(1):95-96.
[23]陈瑞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八大争议问题[J].中国法律评论,2020(4):5.
[24]B.L.GARRET.Globalized Corporate Prosecutions[J].Virginia Law Review,2011(8):1 575.
[25]李勇.企业附条件不起诉的立法建议[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2):143.
[26]J.W.NUNES.Organizational Sentencing Guidelines:The Conundrum of Compliance Programs and Self-Reporting[J].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1995(3):1046.
[27]孫志成.因“二选一”垄断被罚34.42亿元,美团回应:诚恳接受,坚决落实[EB/OL].(2021-10-8)[2023-03-05]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1-10-08/1937822.html.
[28]蒋建湘.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J].中国法学,2010(5):129-130.
[29]周友苏,张虹.反思与超越:公司社会责任诠释[J].政法论坛,2009(1):58.
[30]袁雪石.整体主义、放管结合、高效便民:《行政处罚法》修改的“新原则”[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4):21-24.
[31]M.E.STUCKE .In Search of Effective Ethics & Compliance Programs[J].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2014(4):775.
[32]K.D.KRAEED.Cosmetic Compliance and the Failure of Negotiated Governance[J].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2003(2):492.
[33]看看新闻.中国小微企业主的数量已达到了八千多万[EB/OL].(2021-09-15)[2023-04-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929689677065167&wfr=spider&for=pc.
[34]K.L.SHAPIC.10 STEPS TO A BETTER DAY:The key components of compliance[J].Business Law Today,2003(1):40.
[35]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2年3月7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3-3-18(4).
(责任编辑:蒲应秋)杨洋杨波,张娅,王勤美,蒲应秋
Abstract:The essence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s the self-chan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culture, which belongs to corporate autonomy and negotiated governance and should be the category of "soft law" governance. Compliance into the law is not a "hard law" legislative model with reverse sanction of "condition - behavior - consequence", but a positive incentive legalization model of "compliance - leniency". The legalization in the sense of "soft law" includes both "soft law" provisions of criminal law, administrative law, corporate law and other positive incentives, and "soft law" norms such as official guidelines, industry norms and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the two par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i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legaliz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n China. In the legalization path,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recognizing punishment,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riminal incentives; the company law should establish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s for compliance leniency such as the exemption of legal representatives from registration of previous convictions, establish the "prosecution penalty" system,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riminal incentives and administrative incentives. However, the compliance effectiveness standards,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re "best practices" and should not be established through formal legislation, but through official guidelines, industry norms, association standards and other "soft law" norms.
Key words:corporate compliance; compliance program; legalization; soft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