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驴、坎土曼与“西气东输”之间
——论刘亮程小说《凿空》的乡土书写
□ 唐艳丽

刘亮程乡土小说《凿空》封面
作家刘亮程被誉为“20 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他的小说《凿空》传承和发展了乡土文学传统,小说通过张金的回忆叙事,讲述南疆地区阿不旦村庄的驴、坎土曼等为表征的传统乡村文化与国家“西气东输”现代性工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以挽歌式的情韵笔调进行“反现代性”的乡土书写,饱含着深刻的社会之思,彰显了作者对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共处的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刘亮程曾说,小说《凿空》是他一个人的新疆,也是他第一次面对新疆现实生活写的一部书,这部小说也被学者认为是“边地现实的另一种思索”[1]。小说中,张金这个被炮震聋了耳朵的失聪者,将阿不旦村庄,“一个被大工业开发包围的寂静村庄的声音世界”“说”了出来。张金听从医生的建议,即通过“那些过去的声音唤醒听觉”,而那些“过去的声音”,以驴、坎土曼、“西气东输”工程等“记忆之物”为主要依托,他也由此把阿不旦村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往事”和盘托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一种对消逝的忧虑”。在作者刘亮程看来,这正是作家意义的体现,即“必须给出一个生命终将消逝的死亡一个赋有道德审美的回答”[2],在这种“回答”中,能让读者看到,“消亡的过去在我们身心中有一种未来,即生机勃勃的形象的未来,向任何重新找到的形象展开的梦想的未来”[3]。因为“赋予文学以意义的一切其他要素——对语言和形式的精通,作者的人格,道德的权威,创新的程度,读者的反应——都比不上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重要。文学,尤其是小说,毫无疑问是关于我们在文学之外的生活的,关于我们的社会活动,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以及具体的时空感”[4]。作家永远是现实主义者,作家用文学书写的形式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探讨与呈现,并通过读者阅读再次抵达“现实世界”,实现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并返回生活现实的双向循环。同时,文学是一种在传承中发展的语言艺术,小说《凿空》在传承厚重“文学传统”的同时,把“具体的时空感”圆融自洽地内嵌在文本叙述当中,显现出作家对当下“凿空”的乡土中国“现实世界”的积极关注与关怀。它是一曲悲怆挽歌,也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之音,它充盈着浓郁的回忆往事的格调,饱含着深刻的社会之思,又洋溢着对美好和谐的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与执着追求,这是一部诗与思相融合的精品佳作。

南疆乡村生活
一、村庄的声音世界
小说《凿空》是一部关于声音的小说,“声音”自始至终贯穿了整部小说,小说中张旺才、玉素甫挖洞的土声,铁匠铺的打铁“叮叮”声,石油卡车、拖拉机、挖掘机的轰鸣声,毛驴的叫声、早晨的枪声、市场的喧闹声、张旺才在地洞喊张金的声音等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声音构成了故事的主体。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小说以失聪者张金作为叙事者,由他“把那个世界的声音都说出来了”[5],这样特殊的叙事视角使小说更具叙事张力。作者巧妙地通过“回忆”的方式,使“聋子的声音世界”成为可能,并使张金的“声音世界”更具有内倾性,或许正是源于叙事者张金现在的失聪,他能够更好地抵御现实中各种“杂音”的叨扰,直抵阿不旦村往昔的“真实世界”。在小说中“那个世界的声音”最具代表性就是阿不旦村驴叫的声音,它们总是不平则鸣,乃至于发出了万驴齐鸣的浩瀚无垠的“有形”之音;还有坎土曼,这个不会直接发出声音的维吾尔族古老农具,却以无可辩驳的“无形”寂静之声,使人于无声处听到社会历史变迁之惊雷。小说《凿空》主要选取驴及坎土曼作为阿不旦村传统农耕文明的表征,在“有形”声音与“无形”声音的双重演绎中,合奏出作者对于现代性振聋发聩的反思之声。
(一)驴——心不平而万驴齐鸣
在《凿空》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叙事者张金的回忆,一方面以驴作为阿不旦村传统文化的表征,并显现出对这种文化的特点:“驴是阿不旦声音世界里的王”“驴是一种倔强的牲口,它顺从人的同时又保留自己的骨气。人得给驴把这点骨气留着,让驴在驴群里过日子”“最早拖拉机来的时候,驴就用鸣叫抵抗”,作者认为“阿不旦的声音世界还在驴嘴里掌握着,只要驴一叫,其他声音都被它压住,包括拖拉机的声音”。这是一种“隐喻的直白”,驴的倔强和反抗,表现的是阿不旦村民在坚守传统乡村文明的过程中,对现代性既期待又本能抗拒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作者也借着阿赫姆,这个养驴“土”专家之口,说出那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驴被拖拉机和三轮摩托车替代是迟早的事”。所以,当“更多的东西在驴叫声里来到村子,驴知道不管自己叫不叫,世界都在变成另外的样子。”如此看来,最后“万头毛驴的鸣叫直冲天空。驴鸣的蘑菇云在天空爆炸,整个老城被驴鸣覆盖”“从老城巴扎,到阿不旦村,到塔里木河边的草湖乡,到盛产小白杏的色满乡,全龟兹的驴在同一个时辰大叫,驴叫覆盖天空,驴蹄震动大地”。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驴叫”不过是对工业化声音的抗拒,驴以真正的倔驴式的鸣叫步步反抗,乃至于绝望地万驴齐鸣,使得“驴叫覆盖天空,驴蹄震动大地”,在增添某种悲壮之外,似乎一切都是于事无补。龟兹县用了十年的时间,“让毛驴和驴车从老城和所有村庄消失”。作者强调动物消失之后,人的生存方式及精神世界的转变。每失去一种动物,人的内心就会被掏空一次,其包含孤独感在内的现代情绪就会增加一分。驴这种决绝的反抗姿态如此让人动容,同时也让人心生惭愧,因为“人的脾气被谁驯服了,驴不知道,但驴知道人得有脾气,驴替人也替所有动物保留着倔强脾气”,小说通过驴完成对人的自我审视。
(二)坎土曼——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小说的一开头,就写镐头凿进硬土,发出“腾”的声音;写张旺才拿着铁锨往地洞深处走,扭头时听到自己转脖子的声音;写张旺才在地洞中听到离他不远的土里,有好多把坎土曼在挖洞的声音。事实上,坎土曼是维吾尔族的主要农具,挖土、锄地、修渠、浇水等农活都是靠坎土曼来完成。“不仅仅是阿不旦村,整个龟兹县的农民,都在使用这种叫坎土曼的古老农具……”;甚至“阿不旦的每一寸土都被坎土曼挖过,每一粒土里都有坎土曼的声音”,坎土曼就是一个无声的历史见证者。坎土曼研究专家王加和他所创立的学问“坎土曼学”,“通过龟兹各个时期坎土曼的形状以及磨损速度,勾画出两千多年来龟兹人的世相和心态,也就是坎土曼和它面对的世界”。并认为“坎土曼就是坎土曼。它不会变,变不了。如果它变了,那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变了”[6]。也就是说,坎土曼除了作为劳动工具外,它的形状变化也与时代有着密切联系,坎土曼的历史就是一部新疆的文明史,虽然它“不言不语”,但我们还是听到诸多历史深处的“声音”:1958 到1960 年间,“坎土曼”的大小是与人们高昂激情的涨落紧密相关的;20 世纪80 年代初到20 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坎土曼回到平常模样——大而厚实,这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有了生产的动力;二十世纪末的坎土曼,坚韧锋利,头稍长些,这源于人们的浮躁情绪;“西气东输”工程准备动工时,坎土曼明显变大,寄托着人们的“大希望”等等。

驴的“不平则鸣”

坎土曼的“沉默与诉说”
小说《凿空》中的驴及坎土曼等,“‘物’的存在与发声不仅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关键,而且成为人物主体的精神表喻,成为主体之间的情感维系和伦理中介,其本身的形态、属性、本质兀自得以凸显,同时也蓄积着精神与文化的价值”[7]。小说通过这些“物”及其所发出的“声音”,在呈现阿不旦村往昔“现实世界”的同时,也呈现了一种现代性发展困境,即以驴叫、农具坎土曼等一切传统村庄文化都消失了,地面和地下都被凿空,与“村庄的灵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逐渐空虚了,人们在精神世界中流离失所,“凿空”一词似乎成了乡村世界最贴切和精准的概括。作者在反思现代性时,也在强烈呼唤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全方位全区域的持续推进,希望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和谐美好的现代生活。
二、“凿空”的乡村世界
小说《凿空》是一个现实寓言,它通过阿不旦村庄坎土曼、驴等事物的命运变迁,以及整个阿不旦村在以“西气东输”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书写,在传承乡土书写的文学传统中,进一步凸显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物质与精神等之间的矛盾冲突,彰显出对以阿不旦村为代表的被“凿空”生存状态的反思。小说中的“凿空”,有学者指出:“首先指涉的,当然是小说中诸如张旺才、玉素甫他们的挖洞故事,是石油人为了攫取油气所采取的挖掘行为,也包括由王加引出的遥远历史中挖掘龟兹佛窟的行为。然而,从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说,作家所欲思考表达的,大约就是一种现实与历史乃至于人生的空洞虚无化问题”[8]。小说《凿空》,从表面上看,以玉素甫等为代表的阿不旦村民,或是因为“睡眠被凿空”而试图寻找一份宁静安稳,选择了挖掘通向麻扎的行动;或像张旺才那般,因为“他在地上太孤独了”,不得不向地下挖掘,寻找一份依靠;或仅仅是出于自然的挖掘天性等等,使他们不断地向地下挖洞,从而导致了整个村庄“物理性”被凿空了。从更深层次看,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被凿空了的,他们似乎成了一个“空心人”,在精神、信仰的世界中,他们无所依靠,流离失所。所以这些挖洞行为,是一种积极寻找精神寄托的体现,或是在不断的体力劳动之中,寻找着一份安宁,又或者说,这本身也是一种反抗的行为。他们“用凿洞的方式将自己退回到动物的生存状态,用地下的空洞来抵挡地上的空洞,以动物性的行为来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的焦虑感,将肉身深埋于地下,将灵魂与信仰归置原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9]。在现代社会中,像玉素甫、张旺才等精神世界出现被“凿空”现象的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存在,作者以寓言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人类普遍面临的一种精神信仰的困境。

西气东输工程
刘亮程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村庄”其实有一种人类共同家园的含义在里面。小说《凿空》中张金的个人回忆,是村庄的往昔,但也正如梁鸿所书写的“中国在梁庄”,一个村庄也许就是整个中国的缩影,阿不旦村的“过去”也就是整个中国,起码是西部地区的“过去’,阿不旦村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就是一个地域时代性的问题与困惑。在他看来“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的村庄国家,所以我们建立的哲学、道德观念、文化习俗,从根子上讲都是农业文明这个大环境里面造就出来的”[10]。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中,深居内陆的地区,它们承受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小说中提到国家的“西气东输”工程,按照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是要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它的起点就在阿不旦村,最初,这样的消息给阿不旦村带来期待,村民们认为他们手中的坎土曼,必将在这“西气东输”工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他们的收入也将有大大的改观。为此,阿不旦村的村民们摩拳擦掌,每家每户至少准备好了两把坎土曼,试图以一种迎合的姿势服务于“西气东输”工程。但是,阿不旦村的村民们苦苦等了半年,发现轰轰烈烈持续推进的“西气东输”工程,无论是勘探测绘、打井出油、铺平道路、挖填管沟等,这些就发生在村民们眼前的大事却与他们没有关系。作为阿不旦村的村主任,亚生试图从中为村民谋得一份挣钱的机会,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处跑,跑县里,跑石油工地,但最终都是徒劳。阿不旦村的村民们最后以失望与愤懑收场,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坎土曼根本不在工程的考虑范围。在这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落后的农具是无法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机械相较量的,后者以整齐划一、能量巨大的挖土机为代表,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处于前现代的乡村文明,乡村只能步步后退,以至于无路可退。而坎土曼“让路”,并遭遗弃的现实际遇,真正体现了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悲哀境地,这也成为西部许多地区生存状况的缩影。也就是说,“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11]。作者在高唱挽歌之中,也深刻意识到,现代化进程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在小说中,也借助于驴师傅阿赫姆之口说出,“驴被拖拉机和三轮摩托车替代是迟早的事”的必然性“预判”。作者通过坎土曼、驴等即将要消逝的物象,他们或者不断进行“自我改造”,或者坚持反抗到底,在万驴齐鸣的绝望反抗中发出不屈之声。其实坎土曼的改造也好,驴的绝望反抗也罢,都是弱者(阿不旦村的村民们)的武器,当然,它们也都是“武器的弱者”。阿不旦村的村民们成了村庄的“他者”。“村子下面挖出石油,人们以为村庄得救了,穷日子到头了。然而,这些石油真的和村里人没有关系。他们不光没免费用上半斤石油,没干上一坎土曼石油工程的活,连立在村边的石油井架,都没福气上去一下”。这种巨大的现实落差,以及感情上极力彰显即将消逝的“美好”,这种挽歌情绪越是浓烈,在不可阻挡的现代性进程的映衬下,所构成的艺术张力越是强烈。正如吴晓东所说“挽歌的美必然与一种对现代性的焦虑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双重的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叠合铸就了审美倾向的复杂性。沉迷在‘过往的东西’中的小说家们一方面获得的是易逝以及丧失的深刻体验,这种挽歌般的惆怅体验中有一种天然的感伤性和抒情性……同样,对现代的渴望也伴随着对现代的警惕和疑虑,现代性固有的内在紧张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小说家们的文化和审美的感知领域,从而带给他们文化和审美的两难困境。而正是这种两难境地,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的一大幸事”[12]。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两难困境”,正是文学创作绝佳的艺术源泉。

行走在南疆小巷里的毛驴车
文学有“根”,这个“根”既源于现实生活,也存在于无数的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文学传统”。“与传统的乡土文学创作一样,刘亮程在他的乡土世界构筑了一种独异的生命世界,既关乎传统、家园,更关乎他认知生命的独特方式。刘亮程的乡土世界跨越了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某些既成创作苑囿,呈现出属于自己的创作景观”[13]。他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自然而然地传承了“文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创新,使小说《凿空》既有文学传统的厚重,又饱含现实的深刻反思。如小说中的玉素甫,自己的睡眠被“凿空”后,陷入困惑之中,到后来的豁然开朗:“这一年来我也在这个地下转晕了,不知道洞要挖到哪里。我只知道要不停地挖,挖。可是,就在今天,我突然脑子一亮,知道往哪儿挖了。我们把洞挖到村外麻扎去。”这与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是如此的相像。他们都是停不下来的,或者是不停地挖、或者是不停地往前走,而终点都是一样的,走向坟(麻扎)的地方。如果说鲁迅笔下的“过客”是我们人类命运的抽象式的寓言象征,那么刘亮程笔下的玉素甫、张旺才等则是以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负载、表达着人类命运的深刻主题。对此,刘亮程也曾借着小说《虚土》说道:“这种对人生的追问和疑惑,才是我想表达的。”另外,小说《凿空》延续和深化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土文学中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关系的主题书写,通过展现坎土曼、驴等“物”与“西气东输”工程之间的复杂关系,艺术地表征了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凿空》所描绘的是南疆地区阿不旦村的乡土生活,也被认为“开拓出边疆乡土叙事的新领域”[14]。如小说《凿空》中提到的“西气东输”工程的实施,对于阿不旦村,犹如铁凝小说《哦,香雪》中那辆呼啸而过的火车,让处于边缘、前现代文明的村民,除了激动不已和主动迎合,再次确认自己的落后之外,似乎获益不多。而对阿不旦村人原生态的生活状况的描写,让人仿佛看到了萧红笔下那个“让人忙着生、忙着死”的凝固式日常乡村景象,“驴叫让阿不旦村很快回到以往的日子,这个冬天就在驴叫声中过去了。虽然村里发生了那件大事,艾布和黑汉死了,玉素甫老板跑了,但春天照旧来了,毛驴照旧在叫,忙起来的春耕春播,让人觉得,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作者进行挽歌式的文学书写,从而使小说明显带有“反现代性”意味,这也是作者一贯“不慌不忙地叙述着一种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15]状态的延续,也由此彰显着自然万物一同诗意生存与栖息的理想色彩,这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现代性生活状态。我们可以说《凿空》是一部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彰显追求理想的现代性生活的乡土文学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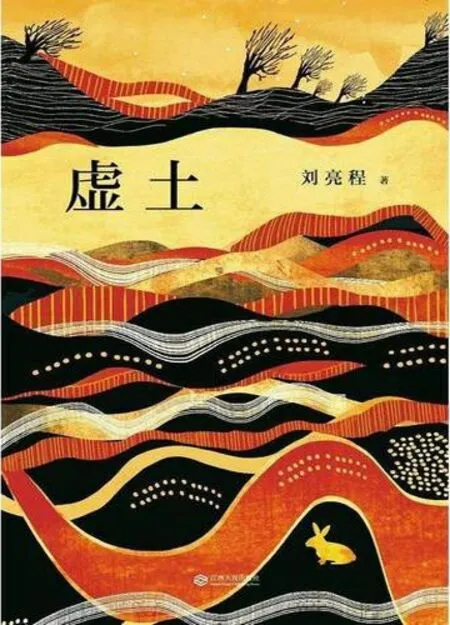
刘亮程作品《虚土》
三、结语
回忆与文学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它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有学者指出:“文艺作品正是作为一种记忆和痕迹的承载者,作为发自过去的语言信息的承载者,跨越时间地从充满死人声音的过去、从属于那个过去的传统向观众诉说”[16]。所谓的文学,就是讲述人类的往事,读者通过故事进入的是过往时间。小说《凿空》中,叙事者是失聪的张金,不过作为回忆的主体,它的“地点”是阿不旦村,这个村庄上不管是驴,还是坎土曼,都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们作为阿不旦村庄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是民族的象征符号的承载之物,也是社会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在当下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加速、社会日益碎片化的时期,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正该起到终极价值关怀、维系族群心理认同、保持共同记忆等重要作用”[17]。作者以一种文学民族志的写作模式,通过“隐喻”方式,追忆和呈现了以驴、坎土曼等传统乡村文明在以“西气东输”工程为表征的轰轰烈烈的现代性进程中进退无路,村庄人们身心被“凿空”的困境。小说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位“乡村哲学家”最深刻的现代性焦虑和反思,也看到了他对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能够和谐共生共处的现代性生活状态的向往与执着追求,这或许也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