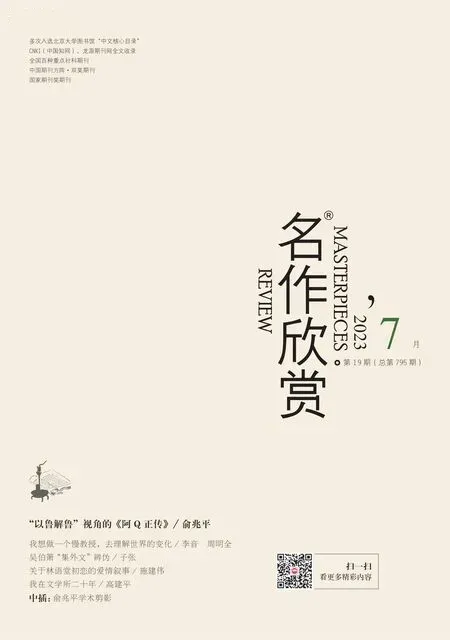关于林语堂初恋的爱情叙事
——追忆和林语堂女儿林太乙的台北相遇
上海 施建伟
自从“幽默大师”林语堂成为我的学术选题之后,我就不断“巧遇”许多很幽默或者不幽默的事情,这些经历几乎都尘封在我那庞杂的记忆库里,按照出库问世的可能性的顺序排队。天有不测风云,不料这两三年来视力骤降,所有的文字工作被迫刹车,暂停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天,一条微信,唤醒了休眠中的我。
那是2022 年10 月13 日,北京的陈漱渝学友在私聊中谈及当年陈涌前辈甄选林语堂传撰稿人的往事。刚好,陈涌前辈也和我讨论过同一件事。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幽默”,所以,随手就把相关的几份原件拍照后传给了他。漱渝立即回复了几个字:“珍贵手迹!”这条微信提醒了我,也鞭策了我,于是我又重新进入了角色……
日前,华文出版社明华编辑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为支持她的工作,我挑出相关资料优先入场:一厚叠精美的相册里珍藏着数以千计的有关林语堂的图像资料,老照片里的那些事真精彩!这简直是个聚宝盆。
其中,摄于1994 年10 月台北之行的那部分,最具资料价值。1994 年10 月8 日—10 日,“纪念林语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中国在台湾省台北市召开。作为大陆以林语堂研究学者身份受邀与会的唯一代表,我与中国台湾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教授、专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虽然偶尔也遇到过意外,但总的来说,收获的成果超出了我的预期,特别是与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等社会名流的交流互动,使我受益匪浅。

1994年10月8 日—10日纪念林语堂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施建伟(左一)宣读论文。侧坐者为余光中
20 世纪90 年代初,两岸学术层面的交流访问方兴未艾。这次在台北的纯学术交流大概可以算是林语堂研究领域的破冰之旅。在两岸林氏宗亲会的林姓乡亲们的积极参与配合下,这次学术交流基本顺利,还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图像资料,首功则是台湾林氏宗亲会的林添福先生。默默做实事的林先生,受大陆方面福建林氏宗亲会之托,在我访谈期间全程陪同,兼任摄影师、导游、司机三重身份,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志愿者。我离台前,他把所有影像照片整理成册……林先生,你功不可没啊!林先生以精湛的专业技术,抢拍了那些稍纵即逝的珍贵瞬间,这些老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和林太乙促膝谈心的画面,一张颇有深意的工作照。
记得当年回上海后,文友们曾相争在相册里寻宝。其中那张我和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的合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照片里的林太乙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赏阅一堆山水风景照,而我则神态自如、脸带笑容地在一旁插话。文友们不约而同地发问:“你们在讨论什么,这样投入?”我笑而不答,这就更激起了他们的好奇:“有什么不能说,还保密?”

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赶紧搭腔:“是学术问题,还是留一点悬念的好。”
光阴似箭,将近30 年过去了,现在该为那张老照片揭秘了,这张工作照摄于1994 年10 月10 日,地点是台北市建国南路二段125 号。我和林太乙促膝交流的议题:关于林语堂的那些事,从故乡大自然的魅力到家庭生活,最后的重点则聚焦于“初恋情人”的话题。
起先,林太乙的夫婿、三妹林相如、林语堂在台湾的秘书黄肇衍、马骥伸等名流也参与了寒暄与合影,当进入交流的正题后,小会议室里就只留下了我和林太乙两人。
我们先从林语堂的小说《赖柏英》的自然背景——坂仔,美丽的山水切入,我开门见山地说:无限深情地怀念家乡的山水,就是林语堂的创作源泉,也是他久盛不衰的创作题材。家乡山水的力量,是林语堂艺术生命和思想信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入”了他“浑身的血液”之中①。我又强调了林语堂把对故乡山水的爱“拟人化的艺术嫁接”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
我边说边拿出一大叠林语堂家乡景色的风景照来,这是我走访平和县坂仔村时自己拍摄的资料,我和林太乙一边欣赏大自然的原生态面貌,一边交流……我情不自禁地把拙著中的一段话几乎是背诵出来了:“林语堂痴恋坂仔山水的奥秘是:他以乡情、乡思、乡恋为载体,寄托了铭心刻骨的初恋之情;把爱情寄托于乡情,爱情和乡情互为表里;通过对家乡山水的痴恋折射了对恋人的思念,于是自然美和爱情美融合为一。”②
我还说:林语堂借男主人公“新洛”之口对女主人公的那段表白是破译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文化密码,“真正的点睛之笔”。“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③
倾听我侃侃而谈的林太乙,起初一直很安详地思考着什么事,趁我停下来喘口气的瞬间,马上针对我在叙述时常插入一些客套谦辞,说:“请以后不要客气,不要用请教、求教这样的字眼,不然的话,我会显得很拘束。其实,我久闻你的大名,我在港台是有很多朋友的,他们提起过你,香港三联书店的潘耀明,你熟吧?台湾的张世珍,你熟吧?”我答:“潘先生,我曾请他去华侨大学访问过;张世珍女士是昨天她送资料时才第一次见面。”林太乙说:“我在拜会你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拜读你提交给大会的那两本新著④,也知道你发表过很多论文。”接着,林太乙从文件袋里找出一本浅蓝色封面的书,对我说:“这是台北的张世珍女士赐赠的《论语时期的林语堂研究》。”我答:“我也刚收到了她的新著,但还没来得及拜读。”
林太乙说:“我倒是昨晚把她的大作和你的那两本大作、大会的论文提要都翻了翻。”她掀开《论语时期的林语堂研究》的封面,指着第一章“绪论”说:“张女士在绪论里高度评价了你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你的论文和专著。”林太乙停下来半开玩笑地说:“她对你很崇拜啊。”接着,林太乙指着张著中的一段话说:“你看,她是这样评价你的:‘至于研究方面,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施建伟教授曾在一九九〇年发表《林语堂研究综述》,全面而详尽地引介两岸对林语堂研究的成果……一九九一年八月,施建伟发表《林语堂在大陆》专书,可以说是有关林语堂在民国二十五年以前的一切研究的总结,他广泛搜集原始史料及第一手资料,以传记的笔法刻画林语堂的前半生,力图还林语堂以真实的本来面目……综观大陆的林语堂研究……以作者个人研究的质量及影响而言,施建伟教授独占鳌头……施建伟则新近出版《林语堂在海外》,他广泛地搜集资料,详实地记下林语堂的后半生。书中许多资料是首次在大陆披露,应该可以为将来的研究,铺下康庄大道。”
林太乙笑着说:“不瞒你讲,我昨晚拜读了《幽默大师林语堂》……”我连忙回应:“请多指教,在你面前,这些都是班门弄斧而已。”她接嘴道:“共同切磋吧。你猜猜我最欣赏的是哪一段?”我猜了三次她都摇头,说:“还是我来说吧,我最欣赏的是你在后记中的那些话。”她翻开随身带的这本书,指着第321 页上的后记说:“林语堂和他的一团矛盾对我来说是一个谜。这些年来,为了解开这个谜,我阅读了林语堂的全部论著,查阅了数以万计的各种资料,走访了林疑今、周劭、章克标、徐铸成、施蛰存等耄耋老翁,发掘和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又到林语堂生活过的平和县坂仔村、厦门鼓浪屿、厦门大学、上海、北京等地作了实地调查。我特别要感谢我在中国台湾的亲戚王应铮叔、美国的亲戚温明战和北京的学友陈漱渝先生,在美国的文友非马先生,在中国香港的文友卢玮銮女士、潘耀明先生,在新加坡的文友槐华先生等人,他们热心地为之穿针引线,搜集并寄赠了林语堂在海外和中国台湾、香港生活时期的各种资料。中国台湾的严鼎忠先生不仅为我寄来了馆藏的有关林语堂著述的资料目录,而且把目录中的研究资料全部复印寄赠给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上述师友们的鼎力相助,就不可能有拙著。”
她说:“原先在香港我读到您的《林语堂出国以后》⑤还真想问问您我们全家离开上海后的那些事,您是怎么打听到的。看了这篇《后记》全明白了……您在《后记》中的自述证明您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我和我的妹妹要对您说一声‘谢谢’!”
我立即回答:“这是集体的成果。”我随手指着《后记》中的另一段话:“拙著实际上是海峡三岸和海外文友们共同创作的成果。在拙著撰写的过程中,我运用了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林语堂本人的作品、自传、林太乙的《林语堂传》以及许多有关回忆纪念文章中的原始资料,特此说明,并致以谢意!”
林太乙又说:“从我懂事开始,我就记得在学校里、在一些公共场合中,常有人会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道:‘这是林语堂的女儿。’虽然我为父亲的声誉自豪,但父亲的声誉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压力。所以我从小就希望别人把我当成普通人家的一个普通的孩子来对待。刚才我赞赏你的成果,绝不是庸俗的恭维,而是希望你不要觉得是在和林语堂的女儿交谈,此时此刻,你我之间就是两个普通的传记作家之间的交流。虽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现在都是在以作家的责任来写好林语堂的传记。正是这个共同目标,使我们今天能在这里推心置腹,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彼此做点什么……”
这个气场太难得了。我终于决定端出那个憋在心里很久很久的困惑。因为唯有真正的知情者才能为我解这个惑,千载难逢。对于林语堂,难道还有比亲生女儿更合适的知情者吗?
然而,即使在脱口而出前的最后一秒钟,我也深陷于林语堂式的“一团矛盾“之中。因为,“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毕竟也是人之常情!提出的问题会不会破坏两位传记作家之间刚刚才建立起来的学术互信?回顾几分钟前林太乙的表态: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传记作家……
林太乙作为传记作家的敬业态度,使我鼓起了勇气,终于在林语堂所倡导的“冬夜炉边”式的谈话氛围中,说出了我的困惑,我指着拙著的那段话向林太乙请教:“既然在现实生活中的这段恋情,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越轨行为,而在自传式小说里,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林语堂竟虚构了‘赖柏英‘和’‘新洛,做爱并怀孕的情节?”⑥
“没有这回事!”林太乙的回答很干脆:“全是虚构的,没有什么初恋情人赖柏英这个人!”
林太乙的回答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在和林太乙交流前同样也做足了功课,拜读过她不久前出版的《林语堂传》⑦。
我是这样解读林太乙上述回答中的两个“没有”。第一个“没有”是指没有“未婚先孕”这回事,第二个“没有”是指林语堂没有“赖柏英”这个初恋情人。
值得注意的是,林太乙并没有否认林语堂有过初恋。她在《林语堂传》中也承认:父亲在年轻时爱上在坂仔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的名字叫“橄榄”⑧。
接下来的讨论围绕着林太乙在《林语堂传》第28 页里关于自传小说里赖柏英的那段话:父亲在集中作品中,提过他年轻时爱上在坂仔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姑娘。在《赖柏英》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述写他爱赖柏英的故事。这部小说全属虚构,但赖柏英倒真像他小时喜欢过的一个名叫橄榄的女孩。乡下人为女儿取名,往往是取农作物的名称,如韭菜、红柑、甘蔗、橄榄等。橄榄和和乐非常要好,一起在小溪中捉鱼捕虾。他记得有几次,她蹲在溪子里,等一只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地站起来,不把蝴蝶惊走。橄榄伺候双眼失明的祖父,后来嫁给了坂仔的一个商人。

施建伟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右二)、三女儿林相如(左一)、秘书黄肇衍(右一)合影
女儿和父亲的观点看似对立,其实并不对立,只是父女俩在艺术视觉和艺术支撑点上的差异,或者说是他们对自传体小说的文体属性在认知层面的落差。因为“自传小说是传记体小说的一种,是从主人公的自述生平经历和视觉角度写成的一种传记体小说。这种小说是在作者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经过虚构、想象、加工而成”⑨。换句话说,传记的史料性和小说的艺术形象性这两个主要元素构成了自传体小说的文体特征。我耐心地讲解道:“你认同林语堂先生对‘赖柏英’的文体定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吗?”林太乙回答她认同。我接着就点题了:“既然你们父女两人再加上我,我们三人都认同林语堂先生对《赖柏英》的文体定位是自传体小说,那么按照自传体小说的文体特征和创作规律来撰写《赖柏英》时,就允许作者(林语堂)在自己‘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虚构想象’。而《赖柏英》之所以能成为林语堂小说创作系列中的传世佳作,就是因为他忠实地遵循了自传体小说独特的艺术创作规律。”
“根据《赖柏英》的艺术特点”,我又强调说,“与其说是自传体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因为自传体小说是一种传记,主要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一般用第一人称,也有例外的;而半自传体小说,则可以并不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经历。虚构的成分占比更多,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上,运用了虚构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
我对林太乙说:“你在《林语堂传》中也提到父亲年轻时爱上‘在坂仔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名叫橄榄的女孩’,这就是在你父亲亲身经历的这个叫‘橄榄’的女孩的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经过虚构想象、加工,而创作了那个名为‘赖柏英’的女主人公。这是符合文体学的艺术创作规律的。现在文体的症结在于小说女主人公的姓名被林语堂命名为‘赖柏英’,而在坂仔又有一个叫‘赖柏英’的人,但这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赖柏英’,无论是年龄还是生活经历都与林语堂没有交集,但她有个二妹叫赖桂英,小名也叫‘橄榄’,这个‘橄榄’倒和小说女主人公的生活轨迹有相似之处,现实中赖柏英的‘二妹’极可能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⑩。
这段绕口令似的“讲解”真把我自己逗笑了:“不要嫌我啰嗦,其实全部内容一句话就能概括: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半自传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艺术形象,这个艺术形象源于生活,又大于生活。”林太乙也笑了:“这堂关于半自传体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的科普课,教授讲得很到位。”我和林太乙相视而笑。女承父业,想不到我被幽默大师的女儿“幽了一默”。
接着我们又提到在林语堂的家乡,有许多热心的“林迷”,一直在调研赖家的家谱,和赖柏英、赖桂英等赖家兄弟姐妹的真人真事。关于林语堂“初恋情人”的议题不断发酵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着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研究的全面深化。
也有人认为,因为林语堂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所以把“赖柏英”和“赖桂英”的名字张冠李戴了。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因为林语堂在最后的十年里老当益壮,完成了即使年富力强的学者也难以胜任的工作,主编和出版了《英汉大字典》,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系列的杰出贡献。
我认为生活原型和艺术形象不同姓同名,这是艺术创作中常见的现象,考证清楚就行了。不必把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名(地名)百分之百对号入座。
我一直以为林语堂为追求《赖柏英》的艺术效果,故意在姓名设置上,把读者引入一座迷宫。小说中的姓名原本不过是一种艺术符号罢了,而林语堂故意把一个简单的符号命名,张冠李戴成一团乱麻,以期达到激发读者好奇心的艺术效应。综观这个话题在林语堂家乡持续发酵的状况,我不仅赞赏:只有“一团矛盾”的林语堂、只有“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只有提倡“中西文化融合”的林语堂才会有这样的“幽默”大手笔,故意把读者引入“一团矛盾”中,这很符合林语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逻辑。
最后我和林太乙已接近一个共识:初恋女孩“橄榄”的那些真人真事,经过作者林语堂依据半自传体小说的艺术创作规律的艺术加工,一场来自现实生活的浪漫初恋升华为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中跌宕起伏的“爱情叙事”。《赖柏英》这部小说问世至今几十年来,一直是“林迷”和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充分展现了林语堂的艺术功力。林太乙女士不断点头的表情,暗示了她对我许多分析的认同。
在告别时,大家都有一种只恨相见迟的遗憾。林太乙坦率地告诉我,由于各种原因,她很少接触大陆的学者,“像今天这样的交流是第一次”。⑪走出小会议室之前,她停下脚步,不好意思地试探:“你拍摄的照片太迷人了,能不能借我一天?我想和妹妹他们分享家乡山水的美景……”
她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明白她想带回去翻拍,这不正证实了祖国美丽山河对游子的向心力吗!我立即爽快地说:“不要借了,全部赠送给你和你全家。因为林语堂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公约数。”她喜出望外,一叠声地道谢:“谢谢您的厚礼!”
次日,林太乙送来一份回礼:台湾省邮局为纪念这次活动而印发的林语堂邮票和首日封。邮票和首日封上都印着笑容可掬的林语堂的头像。首日封的正面是林太乙的签名,背面则是林语堂三女儿林相如和黄肇衍、马骥伸等名流的亲笔签名,这份礼物见证了两位林语堂传记作者在纪念林语堂诞生一百周年活动期间的那次学术交流,对林语堂研究而言则是两岸学者的“破冰之旅”。

在为这本小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正像过去一样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不是了结了一件事后的轻松,我被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所折磨。似乎觉得应该说的话还没有启口。也许是因为徐訏所言:‘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给了我无形的压力,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位博学型的文化名人之间,有着一条历史的沟。要越过这条沟,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和汗水。”
因为至今,林语堂和他的“一团矛盾”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从他留下的那些爱情叙事中,我仍不住感叹:只有“一团矛盾”的林语堂才能写出如此“一团矛盾”的爱情叙事。林语堂一生都在追求真爱,以他自己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价值取向为导向,融合了多元文化中的各种女性观中他所认为的“优质”内容,他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理想女性的系列,他把自己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的真爱,移植到虚幻的文学世界里“过了一把瘾”!从爱情的浪漫到生活的幽默,这也是“一团矛盾”的幽默大师对他自己所倡导的文化理想,在情爱世界和家庭世界中的一种实践。
①②③⑥《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第4 页,第53 页,第53 页,第53 页。
④我提交给大会的两本新著是《幽默大师林语堂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 年5 月版)和《走向世界的幽默大师》(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9 月版)。
⑤《林语堂出国以后》,《文汇月刊》1989 年8 月号。
⑦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2 月修订版。
⑧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2 月修订版,第28 页。
⑨参见“搜狗百科”条目。
⑩ 我1991 年3 月赴泉州华侨大学,受命于陈觉万校长,创建“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所”,将林语堂研究列为该所的重要课题,形成了一个学术团队。林语堂家乡平和坂仔和漳州的林氏乡亲们,闻讯后多次来访。在交流中得知他们在整理和发掘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几年后,我因工作调动离开华大,林语堂家乡的研究者和乡亲们继续不辞劳苦,深入调研。有关林语堂初恋情人的命题,也是这个群体长期关注的选题,他们的付出取得了傲人的成果,形成了初步共识。
⑪《故乡不能再回去》,《林家次女》,西苑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8 页。
- 名作欣赏的其它文章
- 书海钩沉,边缘识小
——浅评《梅川千字文》 - 本期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