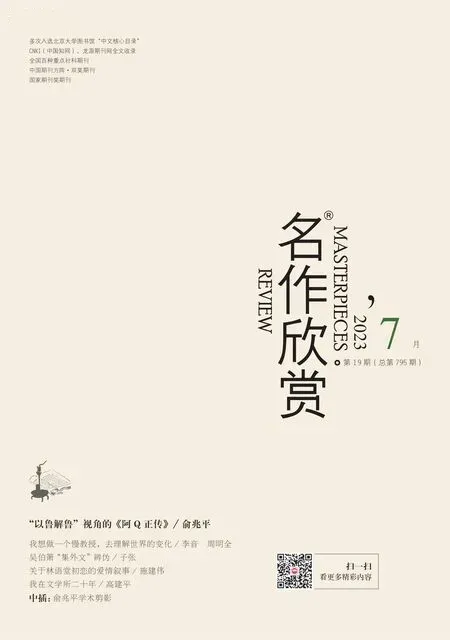书海钩沉,边缘识小
——浅评《梅川千字文》
山东 王贵豪

《梅川千字文》
陈子善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出版
手头这本小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3 月初版首印,32 开精装,简体横排,正文352 页,护封和封面均有同一造型的猫猫,优雅、沉静、慵懒,只不过前者涂绘,后者是镂刻。装帧很简雅,淡米白和橙黄色的暖系搭配令人心怡。
《梅川千字文》是陈子善继《不日记》和《识小录》之后第三种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札记集。陈子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史料研究领域深耕四十余年,善于也乐于从“边缘”看“中心”,以“小”见“大”。辑佚、考辨和编著的过程中积累下许多有趣、有意义的材料①,他一一写来,“以极经济的篇幅,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某个鲜为人知或尚未弄清或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②,刊于《文汇报·笔会》,集结为《不日记》系列;刊于《明报·世纪》,结集为《识小录》和当下这本《梅川千字文》。
“梅川”者,书屋也;“千字文”者,谓专栏之短也。千把字的篇幅,“有的只能略评一本书,有的只能释读一封信,有的只能发掘一桩文坛故实,更多的只能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③,但文章所载史料及作者细致的钩沉与生动的讨论,实在可以引起读者对现代文学诸多侧面的兴趣,为学界提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勘正文学史的某些舛误,甚至具备重写或部分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潜质。④
陈子善在《边缘识小》“楔子”中夫子自道:
“边缘”者,相对于“中心”而言;“小”者,则相对于“大”而言也。我所讨论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并非当下学界关注的具有理论深度的中心论题,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只是我个人感兴趣的自以为有点意思甚至比较好玩的人、书、事。⑤
中肯的自我评述,也是《梅川千字文》很好的注脚。这段话有三个(组)关键词,一是“边缘/中心”,一是“小/大”,一是“好玩”。
近年,从“边缘”重构“中心”的意义已为学界公认,文学“主流”独霸的价值为文学“非主流”所共享,过去的文学“边缘”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无论是向来受冷落的作家、作品获得更多关注与讨论,还是关于非中心地域、非核心作家的文献史料的考掘、钩沉与阐释开始大量出现,都证明着文学史书写理念和权力关系的变迁。
放在这一视域中考察,我们惊奇地发现,陈子善的学术路径一开始就暗合了文学史的未来主潮。《梅川千字文》介绍了大量历来受忽视的作家和作品,譬如曾虚白和他的小说集《德妹》、黄肃秋及其新诗集《寻梦者》以及李金发译著《托尔斯太夫人日记》等,这些作家和作品都是“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参与者、建构者。官方序列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固然重要,重写文学史中的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和张恨水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意识到,现代文学史绝非只有寥寥几位大作家星光熠熠,也绝非只有《呐喊》《边城》《雷雨》《骆驼祥子》《传奇》《围城》等几部“大”作品值得聚焦。一部活的文学史是无数鲜活的声音和面容汇聚的结果,不应由抽绎出的几条本质化描述和总结取代——毋庸置疑,大叙事(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对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的细致讨论等)是文学史书写的题中之义,但同时需要为历史深处微弱的声音和晦暗的表情留有空间,让过去隐而不彰的作家与作品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边缘”向“中心”突围,不断丰富、补充和校正历史的诸种叙述,形成完整而立体的文学历史场域。
如果说从“中心”到“边缘”更侧重思想观念的革新和考察视域的转移,那么从“大”到“小”似乎更在于具体范式的转换和切入角度的变化。《梅川千字文》为我们推开八道湾周家大院的一扇窗,基于作家日记,钩沉周氏兄弟与郁达夫在1923 年大年初二的交往、鲁迅的最后一个春节和周作人1955年的书单等;从胡适和郁达夫的两张合影出发,引出1925 年达夫先生在北京、武汉的两段文坛交游故实;谈林语堂和老舍的声音,听其音笑,遥想其人,多享受亦多怅惘。从这些饶有趣味、别出心裁的角度切入,缠绕着大作家的未可亲近之感得以祓除,它们提供了接近、进入作家日常生态及其心态的有效路径。
虽然《梅川千字文》总在历史无声处的尘埃里行走,书中八十二篇札记所指向的文学史问题,却并未止步于“边缘”和“小”。作者无意于构建大而新的文学史框架,但这些存在于“边缘”的“小”自会生成某种力量,对原文学史的“中心”和“大”形成对照、补充或消解,照亮被遮蔽的,回召被放逐的,安置曾经离散失落的。同时,占有和处理的史料可以具体、微小,从事史料工作的人却必须拥有开阔的整体文学史视野。
《梅川千字文》中的钩沉、考证与诠释就反映出作者卓然不凡的文学史眼光。书中对在张恨水进入“海派”序列过程中严独鹤的重要性的分析⑥,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据说1929 年严独鹤约稿张恨水时特别提出三个要求——言情、武侠和噱头,我们今天看到《啼笑因缘》里的一男三女模式、精通武艺的关秀姑和相貌一模一样的两个女性(卖唱少女凤喜和富家千金何丽娜)⑦,一定程度上是严独鹤准确把握上海市民读者心理的产物,张恨水本人并无充分的上海生活经验,仅凭自己恐难做到精准预估当地读者的阅读期待。《啼笑因缘》为张恨水打开了上海读者市场。倘不是严独鹤膺任《快活林》主编,不是1929 年他初识张恨水并向其约稿,《啼笑因缘》会不会创作出来,是未知数;倘不是谙熟上海读者群心理期待的严独鹤去约稿并“约法三章”,《啼笑因缘》的写法是否会如此契合上海市民的白日梦,同样是未知数;倘不是以《啼笑因缘》这样一部作品敲开上海文坛大门,张恨水能否顺理成章进入“海派”作家序列,或许也是未知数——其中任何一个假设成为现实,海派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将被改写。作者对严独鹤的高度评价,确乎体现出史家之卓见。
与其把《梅川千字文》的题材摭拾和写作风格视作学术的自觉追求,不如视为陈子善有趣灵魂的自然流露。札记体裁,自古便有。⑧这种文体没有明确要求和严格限定,很能反映文人情趣。我虽无缘与作者接触,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陈子善之好玩、爱玩,一望即知。华东师大朱国华教授说:“如果我说陈子善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如沐春风的人,一个对别人平等和尊重的人,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子善首先是一个好玩的人,一个未必摆脱低级趣味,但肯定拥有高级趣味的人;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一个充满好奇心和玩赏心情的人;一个永不言败但是不会显示悲壮姿态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性情中人的一个侧影。”众所周知,陈子善是书痴兼猫奴。“毛边党”、签名本的收藏嗜好体现的是古拙的审美趣味;甘为猫奴的生活姿态则显示出好玩、自由和裕如的生活趣味——这种生活状态不像一般学者,更似纯然一文人。
《梅川千字文》中,那些明媚的情趣俯拾即是。作为执教华东师大四十余年的资深学者,陈子善并不把文章打扮得玄之又玄,反任其简朴随和,不摆架子,不掉脸子,有时带点儿上海人的冷幽默,目之所及,是大学者的严谨、谦逊与亲和,而丝毫不染“学术规范”的呆俗气。书中有一处对叶灵凤日记用词的“纠正”:“严格讲,‘翻脸’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因为鲁迅与叶灵凤从未交好过,正如叶灵凤自己接下来所说的‘从未通过信。也从未交谈过’,那又何来‘翻脸’?不像鲁迅与胡适、与林语堂,原先是朋友,甚至是好朋友,见过面,通过信,吃过饭,写文章也曾互为奥援,后来才真的‘翻脸’了。”⑨文字一本正经又处处透着幽默,我看了几乎笑出声来。抚读此书,可以想见作者摩挲珍藏爱书时的灼灼目光,可以想见其漫步在充栋的旧书刊中,和过从甚密的文坛故人一一打招呼的样子,穿过几十年的历史积尘,坚定、优雅、面带微笑,俨如护封上那只猫。
四川大学李怡曾批评过某些庸俗的史料研究,“怀着窥视作家生活隐秘的心思,将一切可靠与不可靠的所谓‘史料’都视作珍宝,那边可能将文学研究本身引入歧途,而这些所谓的史料其实也不过是历史的唾沫和垃圾”,他唇焦舌敝,指出:“对作家的研究,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对作品的研究……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最终还是体现在它与作品认知、作品解读的关系中。”⑩毋庸赘言,陈子善的史料考掘与文学史微观察,始终以文学为导向,略无猎奇、花边与刻意逆反“主流”之意,实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史料研究领域“最美的收获”之一。⑪
本书也难免白璧微瑕之憾。近来重温《不日记三集》,发现正文之前附有23 张精美的彩色照片,正是书中所涉部分手稿、书籍和杂志的小影——有这些照片,读者阅读时便有实在的参照。《梅川千字文》却少此一附加,诸如胡适和郁达夫的两张合影、《知堂回忆录》里周作人致曹聚仁信的手迹⑫、《飞影阁画报》“时妆士女”专栏之第二十六号图等,依我之见,确也该附上照片以资对照。本书如再版,不知能否实现这一祈愿,以飨读者。
前段时间看到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对陈子善的采访(其实是一年前的采访了),里面有段旁白很触动我:
然而不同于一般学者陪伴寒窗冷板凳的苦苦考察,陈子善是快乐的、随和的、好玩的学者。读书、编书、写书、藏书,半个世纪的坚持,时光流逝,很多人被弄得灰头土脸一身世故,陈子善却越活越年轻,岁月不老童心灿烂,是真正的心无挂碍,真正的纯粹。
这不是溢美之词。
的确是值得钦慕的人生境界。我对“献身学术”的说法会偶发调侃之语:“献身”一词太惨烈,太峻切,太惊悚,如果“学术”自己知道那么多人为之前仆后继地“献身”,不知该感激还是恐惧。所有人都认可最大的幸福是爱好和工作合二为一,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真少之又少。
陈子善先生即这样幸福的一例,《梅川千字文》亦即一部幸福之人写出的幸福之书。
①自不待言,陈子善分量最重的学术贡献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史料保障体系的构建,他“力求作品搜集、研究资料整理和回忆录汇编三项工作并重”,整理、出版了大量作家文集和研究资料集。只要看看郁达夫、周作人、张爱玲、梁实秋、叶灵凤等作家书上的“陈子善编”,这一点便很清楚了。
②陈子善:《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 页。
③陈子善:《不日记三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2 页。
④20 世纪80 年代曾掀起“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意在反拨“前三十年”社会政治革命史对文学史书写的干扰,在重新树立文学史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同时,似乎不免于落入二元对立和一元主导的窠臼,实践过程中亦有“以论代史”之流弊,仍然指向着某种意识形态偏好。“绝对脱离当下心灵的‘纯粹’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是不存在的,进入人们阐释视野的文献史料不可能是一堆与主观思想理论无关的干枯的材料”(李怡语),但从具体史料起步的考掘、钩沉和阐释工作至少因更具备“历史”与“思想”之间的张力而获得某种克制,这种基于丰富、真实史料的“重写”可能是更佳的文学史路径。
⑤陈子善:《边缘识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1 页。
⑥1929 年严独鹤随上海报界观光团赴京津等地考察交流,此行中结识张恨水并向其约稿,催生了张恨水脍炙人口的《啼笑因缘》,并撰写《关于〈啼笑因缘〉的报告》和《〈啼笑因缘〉序》二文向上海读者力荐,自此张恨水正式登上沪上文坛,进入“海派文学”序列。(《严独鹤主编〈快活林〉》)
⑦“1929 年5 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到北京向张恨水约稿。‘言情’当然是必须的,还附带一个要求——上海市民要看武侠,要看噱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具体的文化产品订货单。于是,小说里后来就有了一男三女模式。其中有个女的,关秀姑,就会武功。噱头是另外两个女的,卖唱少女凤喜,和都市富家女何丽娜,相貌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就引出了男主人公跟读者的不少困惑和白日梦。”(许子东:《重读20 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191—192 页)
⑧“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矣。”(章太炎:《国故论衡》,岳麓书社2013 年版,第86 页)
⑨陈子善:《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9 页。
⑩ 李怡:《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花城出版社2019 年版,第243 页。
⑪ 李怡在《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一书中特别指出“陈子善先生及其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特别值得一提。陈子善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尤其对张爱玲佚文的搜集研究贡献良多”,殊可记也。
⑫1970 年5 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初版《知堂回忆录》发行,插图中有周作人1958 年5 月20 日和1965 年10 月13 日致曹聚仁两封信的手迹照片,前者有批评上海鲁迅墓前塑像“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和抱怨许广平“对我似有偏见”等句,受到压力,曹聚仁不得不抽出两封信的手迹照片,重以“听涛出版社”名义发行。(《〈叶灵凤日记〉中的周作人(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