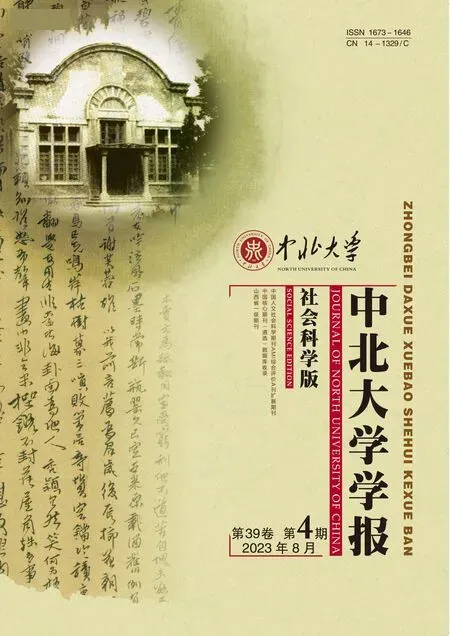传统女性成长叙事比较研究
——以《母亲》和《汉家女儿》为例
李秀梅, 彭丽颖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0)
美国传教士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在其长篇小说《母亲》(TheMother)中讲述了“母亲”饱经挫折但不畏艰难的一生。 诺贝尔授奖词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这个母亲是赛珍珠对中国女人形象描写最成功的一个,而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1]120无独有偶, 美国传教士女作家、 社会活动家——浦爱德(Ida Pruitt)在其长篇小说《汉家女儿——一个中国女工的自传》(ADaughterofHan:TheAutobiographyofaChineseWorkingWoman)中也讲述了一位名叫“宁老太太”的主人公长达70年的人生浮沉。 1967年, 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并连续成为该出版社最畅销的图书之一。[2]116两本小说均以20世纪20、 30年代的中国女性为创作主体, 书写了她们的成长故事。 目前, 国内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两部小说展开研究, 其中, 对《母亲》的研究相对较多, 如从女性主义、 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框架切入并展开研究; 而《汉家女儿》的研究则略显冷清, 只有学者朱春发在其《民族志自传与庶民言说: 〈汉家女儿〉的中国书写》中对该书的内容形式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民族志自传这类体裁所共有的特征及意义。[3]迄今为止, 对两部小说同时展开考察的尝试尚无人进行。
在19世纪, 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女性往往是悲惨、 苦难的受害者形象。 她们依附于丈夫, 没有独立人格, 遭受苦难却又默默忍受、 不愿反抗。 这种刻板印象深入西方读者的内心, 成为西方有关中国女性形象的主导面。 然而, 赛珍珠和浦爱德却敢于打破这种西方凝视, 她们塑造的中国女性体现出成长的光辉。 林中明指出, 赛珍珠在书中“细腻诚实地描写了‘母亲’的身心情感成长, 以及情欲收敛、 压抑、 迸放、 悔伤的过程”[4], 言明了母亲的成长性特征。 而《汉家女儿》作为人物传记的同时, 同样也是一本成长小说。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指出, 成长小说能够“表现一个生命过程中的普遍人性”, 即从个体观察和审视整个人类的存在意义。[5]324《汉家女儿》便是透过宁老太太的生平经历来阐释她所属的族群与社会, 并且宁老太太的性格品质处于动态变化中, 符合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特质。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尝试将两位主人公放在成长小说的框架下进行考察, 从成长主人公、 成长主题以及叙事视角3方面对女性形象进行比较, 以探究赛珍珠与浦爱德各自的困境言说与身份建构, 从而对女传教士群体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1 女性成长的差异
巴赫金(M. M. Bakhtin)在《小说理论》一书中指出:“成长小说中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不是简单的静态统一体, 而是动态的统一体。”[6]230也就是说, 成长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出动态性变化。 因此, 要考察这两位女性的形象, 需要将她们各自的成长过程纳入考察范围之中。
1.1 成长主人公: 妥协VS救赎
作为小说样式之一的成长小说, 塑造典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无疑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7]23而内部与外部成长环境的差异使得成长主人公的形象千姿百态, 母亲和宁老太太就分别属于不同类型的成长主人公。
赛珍珠在《母亲》一书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位“妥协式成长”的母亲。 孙胜忠指出, 经典成长小说的主题是妥协, 是回归家庭和社会, 这标志着分裂主题的结束, 从虚幻的理想中解放出来。[8]14母亲私下打胎的行为其实就是对封建枷锁的妥协, 腹中的孩子是母亲偷情的证明, 为了免受众人非议, 母亲只能选择偷偷打胎回归家庭, 放弃幻想, 转而向现实妥协。 除此之外, 母亲的妥协还体现为一开始对丈夫无休止的原谅以及话语权的丢失。 每一次母亲与丈夫的抗争都是以母亲的让步妥协而结束, 比如, 母亲让男人买眼药水医治女儿红肿的眼睛, 男人带着气地拒绝了, 母亲没有进一步劝说男人, “她虽然生气, 但是过了一会, 又把这事儿给忙忘了”[9]14。 当男人买金戒指时, 母亲虽然也生气, 但不过一会儿“她急着想回去替她男人做菜, 表示她已经原谅他, 不再埋怨他了”[9]29。 这其实都体现出母亲对父权制的妥协, 即使敢于同男性抗争, 最终也无法摆脱这层枷锁。
妥协的同时母亲也表现出成长的倾向性。 丈夫的离家出走使得母亲的情感无处释放, 而收租人作为“负面引路人”的出现恰恰弥补了母亲情感上的缺口。 在成长小说中, 不只有正面人物会对成长主人公产生影响, 负面引路人“为主人公的成长提供了反面参照, 在与‘坏’的比较中, ‘好’获得了清晰的界定”[10]135。 管事的无情抛弃让母亲看清了依附他人的不现实, 她不再对管事抱有任何期望, 而是悄悄地打了胎, 重新做回了自己, 并且卖掉管事送的首饰来医治女儿的眼睛, 这一行为代表母亲的顿悟, 选择与过去天真的自己决裂。
“救赎式成长”则与“妥协式成长”不同, 即使有着艰苦的成长环境以及各种磨砺挫折, 成长主人公依然能向阳而生, 一步一步走出困境, 完成自我的人生救赎。 宁老太太的成长之路十分坎坷, 她年轻时嫁给了一个吸食鸦片的渔夫, 男人为了鸦片不仅变卖家产而且试图卖掉女儿。 正是男人偷卖女儿的行为, 让老太太实现了成长之路的顿悟。 顿悟是一种突发的精神现象, 通过顿悟, 主人公对自己或者对某种事物的本质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知。[10]143失去女儿的悲痛促使老太太下定决心离开丈夫, “现在我不能待在家里, 必须‘出来’, 即使我家里的女人以前从没有出走过”[11]73。 出走也是成长路上重要的一环, 不仅是成长者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移, 更包括个体在精神上对原有文化的反思和逃离以及对自我的追寻和重新建构。
虽然老太太有着艰难的成长历程, 但是她的人格却在逐渐完善。 她不会因为雇主与自己的身份有所差别而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也不会为了安逸而草草把自己交付于一个男人。 当有人给老太太介绍对象时, 虽然与那个男人结婚意味自己悲惨生活的结束, 但老太太决心不再依附于男性, “我有足够做的事来养活我自己, 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人呢”[11]197。 老太太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带大一双儿女, 等他们都成了家, 自己才开始享受晚年生活。 尽管老太太成长路上遭遇了各自挫折磨难, 但是, 她却在混乱的世界里实现了自我救赎。
1.2 成长主题: 小我VS大我
母亲的成长主要体现为情爱之中的成长, 是个人小我的成长。 首先, 母亲大胆与丈夫争夺话语权为母亲后续的成长埋下伏笔。 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 话语是“一种社会工具, 是权力施展与再现的一种形式, 也是社会文化构架中的必要因素之一”[12]。 在传统社会中, 话语权通常由男性操纵, 女性只能选择缄默。 然而, 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却敢于同丈夫理论争辩, 她不仅会用白眼阻止丈夫赌钱, 也会在男人偷钱买长衫时同男人扭打在一起。 虽然这些行为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但却挑战了男性的权威, 按照福柯所言, “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抗争过程实际上是自我建立的过程”[12]。
其次, 丈夫的出走为母亲的成长提供了契机。 丈夫本是一家之主, 但他却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把一家老小扔给了母亲。 丈夫离家后, 母亲独自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不仅要在田间劳作, 还得操持家务、 侍奉婆母、 抚养孩子。 她还敢于打破封建枷锁对女性的束缚, 勇敢追寻自己的情感。
最后, 收租人的无情抛弃让母亲幡然醒悟。 母亲遵循自己内心的欲望与收租人苟合后又惨遭抛弃, 这之后, 母亲认清了私情的不切实际, 从个人情爱转而回到家庭之中, 母亲再次将爱放在老人和孩子身上, 她为老人置办丧事, 为眼瞎的女儿求医问药。 虽然母亲在两性关系中多次遭受男性的抛弃, 但是母亲没有因此逃避, 母亲责任感的回归代表着母亲由天真走向经验和成熟。
如果说母亲的成长是个人小我的成长, 那宁老太太的成长则是大我的成长, 她的成长与民族紧密相连。 巴赫金提出了“人与世界一起成长”的主要命题, 认为人与世界一起成长, 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6]232浦爱德所写的《汉家女儿》呈现了宁老太太近乎完整的一生, 她本出生于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嫁给了一个吸食鸦片的渔夫, 丈夫为了购买鸦片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物品甚至自己的女儿, 宁老太太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出走, 寻求生存。 她先是靠街头乞讨为生, 而后在大户人家或者传教士家里做女工, 凭着双手养活了一双儿女。 老太太虽然处于底层, 生平也毫无轰轰烈烈的事迹可言, 但是她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特有的精神特质: 勤劳、 乐观、 坚韧。 不管是怎样的逆境都无法将他们打败, 对苦难有着极强的忍耐力, 正如李维斯(Hodous Lewis)在书评中所言:“虽然此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妇女, 但是她的生平触伸到了其他的中国人民。”[13]
除了将个人精神特质与民族性格特征相联系外, 她的命运起伏在一定层面上也体现着整个民族的遭遇。[3]宁老太太的成长历程中不断穿插着日本侵华的历史, 她的一生也被这种外来势力所影响。 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依据《天津条约》, 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 这也造成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传教的局面。 宁老太太所在的山东也同样如此, 老太太出走后一直在传教士家庭里做工, 她的儿子和孙女后来也进入教会学校读书。 此外, 鸦片也给老太太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她的丈夫因为吸食鸦片导致家徒四壁、 妻离子散; 她的女婿也是一个鸦片鬼, 为满足烟瘾竟想把老婆卖掉。 作为时代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在一定意义上, 宁老太太因鸦片所遭受的个人痛苦经历也正是此阶段中国因鸦片而带来的民族受害史。[3]
1.3 成长叙述视角: 第一人称自述VS第三人称他述
成长小说描述的是成长主人公的成长历程, 这种叙事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个由“谁”站在什么“位置”来叙述的问题, 也就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问题, 这就是叙述视角问题。 而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由叙述人称决定的, 叙述人称一般来说包括第一、 第二和第三人称。[14]18采用不同的叙述人称会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不同的效果。
赛珍珠的《母亲》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他述”视角, 即叙述者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叙述母亲的遭遇, 母亲则是一个被观察、 被讲述的对象。 由于“他述的视角”是从外部对母亲进行观察, 因而, 母亲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被有意淡化掉了。 母亲的内心独白几乎被隐藏起来, 并没有太多情感的外露, 读者似乎并没有进入母亲内心的情感世界。
“大多数成长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叙述, 让人物自己塑造自己的身份, 锤炼自己的声音, 突出自己的个性特征。”[10]162浦爱德所写的《汉家女儿》采用的即为第一人称自述视角, 全书都是从老太太的视角讲述她的所见、 所闻和所感, 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我”的成长经历。 首先, 这种叙述者自己讲述自己感悟的方式能够更容易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作者从叙述者的视角来袒露她的内心所感, 可以使读者跟踪叙述者的思想矛盾、 迷惘困惑和性格发展的心路历程, 读者可以看到叙述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局限, 对他的真情袒露产生同情和理解。[10]174
其次, 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往往包含“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 前者为叙述者 “我” 追忆往事的眼光 , 后者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15]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叙述的过程中, “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不断交叉, 叙述者可以有选择地回避自己的某些经历, 在叙述过程中也附带了自己长大后的反省与感悟, 可以全方位、 多层次地刻画人物形象, 使其更加饱满与成熟。 比如, 文中宁老太太发现丈夫卖孩子而质疑丈夫时, 丈夫笑着回应她只是开玩笑, 而老太太竟然选择相信了他, 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单纯, 只有二十二岁”[11]66。 这句话中, “那时候我还年轻单纯”其实是“叙述自我”, 即老太太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以往的自己, 从而发出感慨, 觉得自己当时年轻单纯, 过于好骗。 这种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交叉使用使得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 主人公的形象也更加饱满成熟。
2 成长差异的原因与作家的自我言说
虽然“母亲”与 “宁老太太”的精神品质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 但就形象的塑造来看, 两者存在着诸多差异。 因此, 有必要对这一文学现象差异背后的深层动因做进一步分析。 总体而言, 作家创作受到多重外在因素的影响, 即与当时的创作心境、 创作意图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 作家呈现异国形象时并不以真实性为诉求, 而是以表述自我为中心, 借助他者完成自我的建构。
2.1 身份困境与消极发声
赛珍珠身上一直带着“神秘、 矛盾、 复杂”的色彩, 正如姚君伟先生表示“称她为‘一团矛盾’也许并不过分”[16]。而这种身份的矛盾与复杂性也体现在赛珍珠“母亲”形象的塑造上。 首先, 赛珍珠从小就在一个中国人世界里长大, 她不仅与王妈朝夕相处, 而且经常跟随王妈一起走街串巷。 她先是在王妈那里学会了中国话, 又在说书人的道场中听到了不少民间的传奇故事。 此外, 她还拜孔先生为师, 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 因此, 赛珍珠认同中国文化并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处世准则。 儒家思想讲究“仁爱”, 而“仁爱”就包含孝悌之爱。 《母亲》中的“母亲”总是顺从地应和着婆婆的唠叨, 尽心照料婆婆。 即使是被丈夫抛弃, 她也一如既往地承担孝敬老人的责任, 甚至在婆婆病重时花大价钱为其买寿衣并独自操办葬礼。 同时, “母亲”也遵循着儒家“夫为妻纲”的原则, 虽然敢于同男人争夺话语权, 但每次的抗争都是以自己的妥协而结束。 “母亲”的形象是一位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贤妻良母。
其次, 赛珍珠还在父母所在的长老会世界中成长, 赛珍珠的母亲经常给她讲述华盛顿、 杰弗逊、 麦迪逊等政治家的故事, 将这份文化遗产塞进了赛珍珠幼小的心灵之中。 除此之外, 还在家为其讲授英语文学。 赛珍珠长大后到美国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教育, 对西方的自由、 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中西方两种文化在赛珍珠的脑海中碰撞, 正如她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父母的小而干净的长老会式的美国世界和不那么整洁却充满欢爱的中国大世界”[17]27。 这种文化冲突被赛珍珠不自觉地带入到创作中, 其塑造出的人物往往具有矛盾性。 如“母亲”的形象既折射出传统的儒家道德观, 又包含了西方文化所崇尚的性自由观念。 赛珍珠在书中毫不避讳地描写了“母亲”旺盛的性欲与生殖欲, 在情欲的推动下, “母亲”打破了当时封建礼制对女性的束缚, 大胆遵循自己内心的渴望与收租人苟合。 “母亲”这种与传统妇女既相似又背离的形象特点恰恰反映了赛珍珠矛盾的文化身份。
“母亲”的形象塑造不但折射出赛珍珠的文化纠结, 还映照了她的性别困境, 这主要表现在其在婚姻生活中的失语地位。 明明是作为荣誉生从伦道夫梅肯学院毕业, 但是她并没有选择去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 而是选择在幕后辅佐丈夫的工作, 照料女儿, 将自己拘囿于家庭空间里, 在婚姻关系中自愿充当着附属品。 没有性激情的婚姻生活以及女儿的残疾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她只能将所有的感情与心理都融进她的创作, 试图通过写作来治疗她的心理创伤。 后现代思潮下诞生的叙事心理学认为, 故事本身反映了个体心理发展与变化的过程, 强调生活故事叙述与自我构建之间的联系[18], 因此, 《母亲》里处处充斥着赛珍珠的影子。 虽然赛珍珠尝试通过写作为自己发声, 但却不敢也不愿轻易吐露自己的心声, 是一种消极的发声。 “这以后, 她仍然苦于没有安全感, 她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感情, 不再轻易亲近别人, 透露心迹, 让外人看透自己, 对朋友也不例外。”[17]113所以, 她曾想将《母亲》的手稿全扔进废纸篓, 宣称是自己觉得作品的质量低劣。 不过, 说得更确切一点, 她想放弃这本书是因为它有内心独白的危险倾向, 一不小心就会让人看穿她心底的秘密, 即性爱和女儿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 赛珍珠后来在传记中指出, 主人公的原型是在南京期间服侍过他们家多年的李嫂, 实际上主人公的另一个原型就是作者本人, 这一点她不愿公之于众。[17]187由此可见, 赛珍珠是不愿向读者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的, 也不愿承认“母亲”的原型就是自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会采用“第三人称他述”的视角来讲述“母亲”的一生。 这种叙述视角会弱化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 从而不容易暴露“母亲”的内心情感世界。
2.2 他者认同与自我救赎
宁老太太自我救赎式的成长以及将个人成长与民族紧密联系的成长主题饱含着作者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首先, 浦爱德对中国民族的认同影响着她对中国女性成长的书写。 她童年在中国的经历为她以后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埋下了种子。 她称中国是她的“母国”, 美国是她的“父国”。 这种民族认同感也使得她的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后殖民色彩。 书中塑造的宁老太太坚强不屈, 不管任何磨难都无法将她打倒, 是一种自赎式的成长, 而不是以往传教士笔下软弱卑微的女性受迫害者形象, 这种自我救赎式的成长也使得成长主人公的个人意志得到有效突显。 另外, 个人成长与民族紧密结合的主题也让西方读者不仅看到老太太个人的精神品质, 同时。 还关注到了老太太所代表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意志。
浦爱德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这本书的叙事视角上得到佐证。 以往有关中国书写的文本都是从西方视角出发审视中国人, 而该书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视角, 让老太太自己言说自己的成长历程。 在这种叙述中, 自我和他者的位置被置换, 本来是中心的西方成了文化他者, 成为被描述的对象, 西方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已习以为常的“中心”世界。[3]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也是浦爱德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她的字典中, 中国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的传记作者金敏女士认为她始终“全心全意与中国普通民众站在一起”[2]pxv是有道理的。 当西方传教士指责中国女性缠脚的恶俗时, 浦爱德敢于站出来为中国人辩护; 当中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时, 美国政府坚持走孤立主义路线, 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姑息的态度, 浦爱德却积极参加中国国际工业合作社运动, 为抗日战争募集了不少物资与资金, 帮助邓颖超、 宋庆龄等地下工作者开展工作, 她因此被称赞为“与中国大地和人民血肉相连有对中国历史有所贡献的优秀美国女性”[19]176。
读者“对人物的同情……是由在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20]22。 首先, 浦爱德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的自述视角来操控读者的同情心, 即通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及与人物距离的远近来实现。[21]书中有关宁老太太众多的心理描写其实给了读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机会。 这些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发能让读者与老太太感同身受。 随着读者对老太太内心世界和情感了解的越多, 读者便会对老太太的认知越深刻全面, 与老太太的距离也会越亲近, 从而对这一人物产生同理心与认同感。 浦爱德也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西方读者对中国女性产生认同, 拉近西方读者与中国女性的距离, 而不是带着刻板印象审视中国女性。 其次, 浦爱德着重突出宁老太太顽强不屈的精神, 也是出于自我救赎的考量。 20世纪20年代末, 正是浦爱德采访宁老太太期间, 浦爱德经历了自己人生中一个难熬的阶段。 爱情方面, 她与杰克的恋爱关系出现了危机, 并最终分道扬镳; 事业方面, 为了给地下工合组织筹措资金, 她需要在各种势力间进行斡旋。 但是, 老太太的不屈不饶的精神给予浦爱德极大的鼓舞。 她像宁老太太一样在面临压力和内心苦闷时, 努力维护自主权, 将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 浦爱德也是借助老太太的顽强精神来完成自我救赎, 在挽救宁老太太生命的同时也挽救了自己。[2]110
3 结 语
尽管《母亲》和《汉家女儿》在成长主人公、 成长主题以及成长叙述视角上存在着明显差异, 但是, 两部小说都描写了女主人公们在成长中的挫折与磨难, 以及由迷失走向顿悟、 由天真走向成熟的过程。 赛珍珠和浦爱德不约而同地关注了中国农村妇女的苦难境遇, 在呈现她们的形象时, 她们将上述境遇与传教士个体的身份困境相勾连。 赛珍珠和浦爱德倾向于呈现中国女性的成长而非重复西方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化印象, 这一做法既是出于她们对中国民族的认同, 也源于她们表达自我的需要。 她们尝试以中国女性为载体, 阐发她们各自的身份困境与救赎路径。
成长小说的主角基本上以男性居多, 女性相对较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 赛珍珠与浦爱德对中国女性的书写就显得难能可贵。 更可贵的是, 她们选择的并不是备受各方关注的新女性, 而是那些在19世纪传教士眼中身份卑微的传统女性, 她们对中国传统女性的别样关注, 丰富了女性成长小说的内容,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 女性成长小说通常以讲述女性主体的生存困境和艰苦奋斗的成长历程为模式, 她们独特的体验能够警醒同时代及其后世的女性, 促使其反思如何让生存更具意义, 具有鲜明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