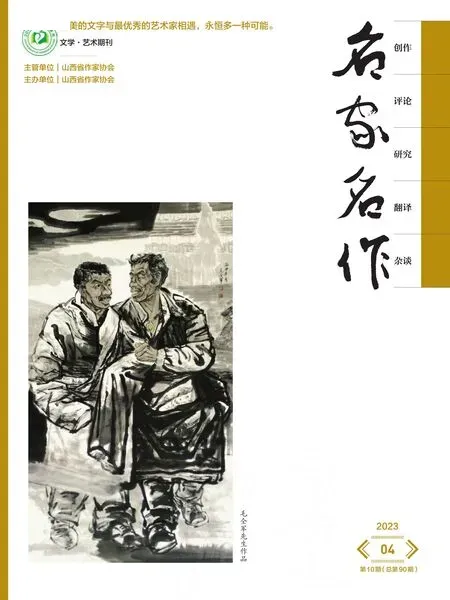浅析哈蒂嘉·玛斯杜尔文学创作中的女性形象
——以小说《庭院》为例
杨柳青
巴基斯坦卡拉奇艺术委员会于2005年9月2日举行“传统背景下的乌尔都语小说研讨会”,对哈蒂嘉·玛斯杜尔(Khadija Mastoor,1927—1982)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评价。诗人和评论家萨希尔·安萨里(Saher Ansari)在致辞中指出:“哈蒂嘉的创作既不是虚无缥缈的意象,也不是朴实无华的叙事,而是两者的完美交融。她的小说分布广泛,基于社会价值观,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她的创作前无古人。她凝望四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从未定型,这就是其创作多样化之所在。”
小说家菲尔多斯·海德尔(Firdous Haider)高度评价了哈蒂嘉的长篇小说《庭院》(Aangan)和短篇小说集《甜而凉的水》(Thanda Meetha Pani):“她以自身生活为范例……其现实主义得到了进步文学运动的支持。”
与会者以平实的语言对哈蒂嘉·玛斯杜尔的小说内容、创作风格及其为进步文学运动所做贡献做出中肯翔实的评价,话语间流露出对哈蒂嘉的尊重和敬佩。学界对进步文学运动已有充实介绍,但对哈蒂嘉·玛斯杜尔的评介尚不充分。本文试分析哈蒂嘉·玛斯杜尔文学创作中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为评介研究哈蒂嘉·玛斯杜尔的文学作品贡献绵薄之力。
一、生平简述
哈蒂嘉·玛斯杜尔是巴基斯坦著名的乌尔都语作家,于1927年12月11日诞生在北方邦勒克瑙的一个家庭。其父德哈乌尔·阿赫默德·汗(Tahawwur Ahmad Khan)从事医学行业,同时也是一名政府雇员,哈蒂嘉幼时不断随父调岗奔波,洞察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近景。其母是一名知识分子,常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良好的家庭氛围是哈蒂嘉从事文学创作的诱因,因此,自幼时起哈蒂嘉的文章就常刊载于儿童杂志上。长大后她的作品也常刊登于《文学世界》(Adabi Duniya)等巴基斯坦的文学杂志上,受到编辑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1937年,父亲骤然离世,年仅10岁的哈蒂嘉只得客居异处,俯仰由人。这段艰难的岁月在她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其笔下的人物塑造上也可窥得一二。《庭院》一书中的阿利娅就如同作者哈蒂嘉的化身,二者有极其相似的经历。1947年,哈蒂嘉移居巴基斯坦拉合尔。当时的她居无定所、无依无靠,受到了巴基斯坦文学大家艾哈迈德·纳迪姆·卡思米(Ahmad Nadim Qasmi)的帮助。1950年,她与卡思米的侄子扎希尔·巴巴尔·阿万(Zaheer Babar Awan)成婚,同年当选为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拉合尔分会书记。1982年7月26日,哈蒂嘉因心脏病发作于伦敦去世,死后葬于拉合尔。
二、创作概览
哈蒂嘉·玛斯杜尔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后来以写长篇小说见长。1962年发表的著名长篇小说《庭院》奠定了其在乌尔都语文学界的地位。《庭院》一书将历史与虚构故事巧妙结合,聚焦少女阿利娅一家的内宅生活,以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变迁映射出印巴分治时期社会的巨大变革。通过不同人物的生活碎片反映出分治时期被迫卷入国家政治旋涡中的印度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小说创作围绕女性生活聚集之地——内宅展开,塑造了许多在封建宗教压迫下求生的典型女性形象,其中饱含对主人公阿利娅等敢于追求自主平等的新时代女性的歌颂与赞美,也不乏对谢米玛等旧社会压迫下的传统女性的同情和怜悯,为印巴分治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范例。
此外,哈蒂嘉·玛斯杜尔还有5部短篇小说问世,分别是《游戏》(Khel)(1944年)、《降雨》(Bauchhar)(1946年)、《再过几天》(Chand Roz Aur)(1951年)、《筋疲力尽》(Thake Haare)(1962年)和《甜而凉的水》(1981年)。
三、女性形象简析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提出了“民族寓言”的概念,指出“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为分治时期的女性文学提出了一种恰如其分的见解。哈蒂嘉亲历分治时期家国分裂的历史悲剧,着眼于妇女的“苦难”,以沉重与激愤为笔,为研究英属印度逐步向独立的巴基斯坦转化的这一时期内,社会大众尤其是女性群体经历的集体创伤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
身为现当代女性作家中不可忽视的一员,哈蒂嘉·玛斯杜尔始终从女性视角出发,以锐利的笔锋刻画女性在社会、阶级、种姓、文化等方面受到的种种压迫,以通俗细腻的笔触描摹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真实境况。她笔下的女性角色逐渐摆脱以往印巴文学作品中被动受害的负面形象,展露出积极主动的一面,获得多元化发展(见表1)。

表1 《庭院》女性形象特征不完全统计
(一)新时代女性的抗争与追求
西方文明的输入将自由民主的种子播撒于人们心间,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人民内心对包办婚姻的抵触与批判。在新旧社会交替的节点,哈蒂嘉在《庭院》中塑造了大量以姐姐达米娜、寡妇卡丝姆和主人公阿利娅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们向往爱情、追求真爱,接受教育、收获自我,她们不断寻求自我解放的途径以及自我意识的完善,以期获得真正的自主和平等。
1.向往自由恋爱的新时代女性
在哈蒂嘉的女性书写中,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达米娜与瑟福达的爱情由于阶级差距遭受世俗反对,瑟福达送给她的书籍进一步充盈了她的思想,“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游客”,激起了她对自由恋爱和自主权利的向往,“你哪里知道,我活了这么大,是像只乌龟一样,一点点爬过来的啊!”却也催发了她的悲剧,“这花也真怪,它既散发着吉祥的芳香,又让人感觉到爱情的冷酷。同时,它那鲜红的颜色又意味着希望是要有血的代价的”。她在封建压迫下宁愿为爱放弃一切,包括生命,也决不放弃守护自己的爱情。
月下弹琴一段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情人啊,如果预料到你会离去,我就把面纱烧成灰烬”。寥寥数言,卡丝姆思念爱人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纵使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成见让卡丝姆备受歧视,“当别人知道我已是个寡妇,就都像躲避瘟神一样不理我”,纵使无可避免被爱人抛弃的结局,她也如同飞蛾扑火般勇敢追爱。
新时代进步的思潮催生出女性内心的女权意识,促使她们向往美好爱情,追寻平等自主,寻求自我解放的途径。纵使这种进步的思想在宗教压迫的巨大洪流中显得无比渺小,但她们捍卫爱情的决绝是对巴基斯坦传统观念的有力反击。
2.追求独立自我的新时代女性
新时代的女性意识觉醒,催生出一大批渴望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理想的独立女性。幼时不和谐的家庭因素让阿利娅本能地排斥婚姻,目睹两位姐姐为爱而死的惨剧,她对爱情丧失信心,“我根本不相信男人会有真正的爱情”。她回绝了捷米尔的爱情,拒绝了医生的财富,对瑟福达的庸俗感到失望,她渴望有理想抱负的人,有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追求,不为世俗观念所桎梏。阿利娅是《庭院》一书中知识女性的代表,她渴求知识,获取了乌尔都语文学硕士学位,并且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阿利娅心中对知识的渴望,是新时代女性渴求发展进步的缩影,也是个人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开始。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无畏坎坷,决不向妈妈代表的传统势力妥协,充分彰显了自我人格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如果一个女人企图摆脱作为男人附庸的命运,显然可以把她的这种努力理解为防御性的倔强吧。”以阿利娅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的生活空间由狭小的庭院生活逐步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拓展,吹响了新时代女性独立的号角。
(二)旧社会女性的妥协与奉献
《庭院》聚焦妇女狭小的生活环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妇女们平淡真切的日常生活,传达出作者对传统妇女所处社会地位的思考。传统妇女在情感和观念上被禁锢于家庭当中,因此无法像年轻女性一样接受新思潮,打破家庭的桎梏与壁垒。对此,作者予以深切的同情和谅解,歌颂她们为家庭做出的妥协与奉献。
伯母是传统女性的代表,她在丈夫的满腔政治热血中默默奉献自己,操持全家人的生活,“我跟他爸爸一起生活,整个青春就这样消磨掉了”,只能寄希望于儿子日后成才。先后经历丈夫入狱、儿子从军的巨大打击后,伯母仍未一蹶不振,“在阿利娅看来,伯母在家里好像是一具可怕的尸体。她的眼睛里凝聚着几个世纪的痛苦。她却又是支撑着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也正是因为伯母等传统女性为家庭做出的无私奉献,才为阿利娅这样的新时代女性提供了成长的沃土。作者笔下的传统女性是时代变革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她们以“蜡炬”精神为时代进步提供养分,值得人们唏嘘怜悯。
谢米玛从小寄居在伯父家中,不顾自身拮据,用生活费帮助捷米尔完成学业。“三年里我没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你都看见了。我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她渴望同阿利娅一样获得知识,并通过为努奇玛姑姑劳动获取学习英文的机会,但经济窘困的客观现实阻碍了她向上的步伐,也造成了她与阿利娅的迥异命运。她为爱情牺牲一切,也最终赢得和心爱之人相伴终身的机会。谢米玛的命运展露出作者对传统女性以自我牺牲方式体现自身价值的无限同情。
四、结语
哈蒂嘉·玛斯杜尔基于分治时期的社会环境及生活背景,聚焦描绘中、下层阶级女性的生活碎片,以充实的写作展露出对印度妇女社会地位的深切思考,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大量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对广大旧社会传统妇女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对立足解放的新时代进步女性予以歌颂。她着眼于各阶层、各年龄段不同女性的内心实感,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展露了分治时期女性心中真实的迷茫困苦与渴望追求,为分治时期的进步文学点亮女性创作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