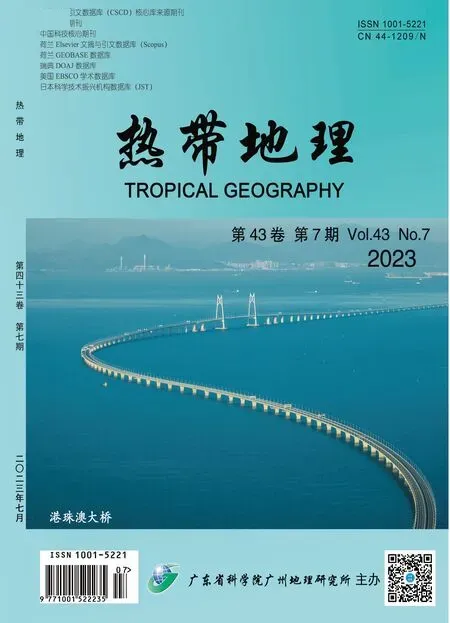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
柯钦华,周俏薇,孙传谆,2,李景刚,李 灿,朱庆莹
(1.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642;2.自然资源部华南热带亚热带自然资源监测重点实验室,广州510700)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土地利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土地利用结构失衡凸显,各类用地矛盾日趋激烈,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冲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邹利林 等,2020)。土地利用冲突是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对土地利用方式、数量等方面的不一致、不和谐,以及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与环境方面的矛盾状态(于伯华 等,2006)。土地利用冲突研究能为稳定土地利用结构,缓解土地利用冲突,优化国土空间资源配置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邱国强 等,2022)。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土地利用冲突内涵及其原因作进一步的阐释。一些学者从人与人之间价值冲突视角阐述土地利用冲突,如王越等(2021)认为土地利用类型竞争是土地利用冲突的表象,其深层原因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阮松涛等(2014)认为土地利用方式所引发的土地冲突本质上是土地价值的客观博弈和社会对土地价值取舍的主观误判。一些学者从空间视角阐述土地冲突概念,如赵旭等(2019)认为,由于一定空间内土地资源的数量有限性及功能的多宜性,土地利用冲突内涵可以纳入空间因素,延伸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即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土地利用方式、效果等方面在空间表征上的不和谐,以及空间资源利用的负面生态环境效应。从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效应看,人们改变土地利用类型会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竞争或者损害多种服务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引起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不利的权衡关系,降低生态系统服务总供给(傅伯杰 等,2014)。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指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人类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取舍进行权衡的行为(彭建 等,2017)。如人类将林地转变为耕地,虽然能提高食物供给服务,但会降低木材供给服务和森林的气候调节服务(Schneibel et al., 2016);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能增强水土保持和碳固定服务,但在一些地区会削弱产水量服务(Feng et al., 2020)。因此,可以理解土地利用冲突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由于偏好某种生态系统服务而选择特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问题。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是一定空间范围内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重要结果,能更进一步有效表征土地利用空间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的内在原因(吴蒙 等,2021)。
当前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方法主要有参与式调查法、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法、景观指数法等。其中,参与式调查法(甄霖 等,2007;Hjalager, 2020)从微观尺度界定具体的土地利用冲突类型及其根源,但难以判断土地利用冲突强度;PSR 模型(杨永芳 等,2012)可以诊断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但缺点是难以准确定位冲突空间范围;景观指数法(蒙吉军 等,2020;Jiang et al., 2021)可以识别冲突的具体空间位置,但对社会经济因素考虑不足(李晨欣 等,2022)。更多学者基于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评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潜在空间冲突(田若颖 等,2020;Dong et al., 2021)。但目前为止,该类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冲突识别指标体系框架与标准,指标构建主观性较强(罗莎莎 等,2022),且其对于土地利用的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尤其是生态环境负面效应的表征不足。如部分研究仅从植被覆盖度、生态用地比例等指标表征土地利用冲突的生态环境负面效应(肖练练 等,2020;Dong et al., 2021;王检萍等,2021),缺乏对生态环境效果的进一步刻画。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概念由于可以表征土地利用引起的生态系统整体的过程特征,在表达土地利用冲突负面效应及其冲突内在原因上具有重要优势。鉴于此,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分析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在不同类型空间上的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和空间分布特征。以期一方面为土地利用空间冲突研究提供新的冲突识别方案,另一方面为高人口密度和经济发达区域缓解土地利用冲突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中国华南沿海(21°25'—24°30' N,111°12'—115°35' E),由香港、澳门2 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城市组成,总面积5.6万km2(图1)。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年均温为22.5℃,年均降水量为1 500~2 500 mm,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超6 800万人,GDP生产总值达16 418亿美元,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刘汉仪 等,2021)。2020 年,大湾区耕地和林地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29.09%和38.77%,耕地主要沿城镇用地外延分布,林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北部、东北部地区;城镇用地的面积占比为13.60%,主要沿珠江口岸分布,整体呈现“马蹄”状。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区位Fig.1 Land use types and loc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1.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基础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高程数据、土壤数据、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净第一性生产力数据、气象数据、流域数据以及粮食产量数据(表1)。
1.3 研究方法
1.3.1 冲突区域划分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取决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强度空间分布特征(彭建 等,2017;Wei et al., 2022),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域具有不同的冲突特征。因此,划分不同冲突区域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识别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冲突大小及其内部空间差异,可科学地表征土地利用冲突。刘晓娜等(2020)研究发现,大多生态系统服务随植被覆盖度和土地开发程度呈现明显的梯度效应,即存在植被覆盖度和土地开发程度变化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突变点。梯度效应直接影响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
本研究突变点寻找方法为:将研究区划分为1 km×1 km 的网格单元,获取每一网格的植被覆盖度、土地开发程度和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值。为避免空间自相关性,随机选取网格总数的10%作为样本,分析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分别随植被覆盖度、土地开发程度变化的梯度效应,寻找突变点。利用R 语言的The Change Point Model(CPM)包识别突变点,该方法可识别1组连续变量中突变点的位置(Ross, 2015),并采用R 语言的trend包进行趋势性检验。其中,植被覆盖度取2010—2020年的归一化植被指数平均值,取值范围为0~1;土地开发程度为耕地和建设用地面积之和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取值范围为0~100%;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图层为对本文的5种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进行极差标准化后叠加的结果,计算公式(Jiang et al.,2021)为:
式中:Supplyj是像元j上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Si,j是像元j上第i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Si,min为第i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小供给量;Si,max为第i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大供给量;n是生态系统服务数量,本研究n=5。
1.3.2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选择5项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评估对象,包括2项供给服务(食物供给、产水量),2项调节服务(碳固定、土壤保持)和1项支持服务(生境质量)。这5项生态系统服务受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较大且容易显现。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过程中,土地利用是这5项服务的最主要变量之一。评估方法主要运用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radeoffs)模型,该模型由斯坦福大学等机构联合开发,主要采用土地利用等数据评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获取其空间分布特征(Natural Capital Project, 2022)。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评估方法和计算过程如表2所示。

表2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Table 2 Methods for evaluating ecosystem servic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1.3.3 土地利用冲突测度与空间表征
1)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土地利用冲突概念模型 基于以下思路构建土地利用冲突概念模型:①土地利用通过影响生态系统过程而改变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权衡特征;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表征土地利用冲突。模型基本原理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供给与无形的服务提供2方面。土地利用变化通过对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的影响,改变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能力,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关系也随之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果,反映土地利用冲突的重要原因。基于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土地利用冲突概念模型(图2),利用相关性系数和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分别测度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及其空间分布,以此表征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和空间格局。

图2 土地利用空间冲突模型Fig.2 Land use conflicts model
2)区域土地利用冲突指数构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构建区域土地利用冲突指数。具体方法为:以1 km 网格统计2010—2020 年的各生态系统服务变化量的平均值,并利用SPSS软件,获取各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变化关系的相关性系数。正相关表明生态系统服务间为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即不存在土地利用冲突。负相关则表明生态系统服务间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即存在土地利用冲突。用负相关系数大小表示土地利用冲突大小。土地利用冲突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LUCI 为土地利用冲突指数,指数越大,土地利用冲突越强;i为显著负相关的关系类型;n为显著负相关的关系类型总数;|Pi|是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
3)土地利用冲突空间表征 以空间网格为基本单元,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两两高低聚集特征表征土地利用冲突空间范围,采用两两高低聚集的个数显示空间冲突强度。首先,冲突空间范围表征的具体方法为:利用1 km 网格统计2010—2020 年的各生态系统服务变化量的平均值,然后利用GeoDA 软件的双变量局部莫兰指数(Bivariate Local Moran'sI)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Liu et al., 2021)。空间上如果呈高高集聚及低低集聚均表示协同关系,呈现高低集聚及低高集聚均表示权衡关系(钱彩云 等,2018),Moran'sI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Zi=xi-xˉ,xi和yj分别为网格i和j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值,xˉ和yˉ分别为所有网格i和j的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均值;n为网格数目;wij为每个网格i和j之间的空间相邻权矩阵。Moran'sI>0 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Mo‐ran'sI=0表示空间呈随机性。
冲突强度的表征方法为:以上述网格为基本单元,土地利用冲突单元的冲突强度以单元中生态系统服务两两高低聚集的个数,即权衡类型个数表示。权衡类型个数越多,冲突强度越大,冲突强度范围为0~8。将土地利用冲突强度按等间距法划分土地利用冲突等级,分为无冲突、弱冲突、中等冲突、强冲突、极强冲突5个等级。
2 结果分析
2.1 冲突区域划分结果
生态系统服务梯度效应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随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呈显著上升(P<0.05),随土地开发程度的增加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这2 种趋势均存在显著的突变点,突变点分别是植被覆盖度为0.45、土地开发程度为28.27%时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供给(图3)。因此,以0.45 的植被覆盖度和28.27%的土地开发程度为划分依据,将粤港澳大湾区划为4个土地利用冲突分区(表3、图4)。其中,I区的土地利用现状以林地为主,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外围;II区以水体为主,主要分布在珠江入海口;III区以耕地为主,主要分布在城市区域外围;IV区以城镇用地为主,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心。

表3 土地利用冲突分区及特征描述Table 3 Land use conflicts zo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图3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随植被覆盖度(a)和土地开发程度(b)梯度效应Fig.3 The gradient effect of ecosystem services with the vegetation coverage(a) and l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b)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图4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分区Fig.4 Land use conflicts zoning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2.2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较为剧烈。其中耕地面积减少了1 440.90 km2(减幅为8.20%),其主要转变为城镇用地(表4、图5)。林地面积增加了485.48 km2,大部分由耕地、农田与自然植被混合用地转变而来。草地减少幅度较大,为44.03%,其主要转为城镇用地。从空间分布看,耕地转为城镇用地的区域集中分布在III、IV区;耕地、农田与自然植被混合用地转为林地的区域主要分布在I 区;草地转为城镇用地的区域集中分布在IV区。可以看出,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镇化快速扩张,在III、IV区,大量耕地和草地转换为城镇用地,而在I 区,耕地和农田与自然植被混合用地转变为林地的比例较大。

图5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空间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in land-use types convers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0
2.3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特征
总体上,2010—2020 年碳固定、土壤保持、产水量3 项生态系统服务均呈上升趋势,而生境质量和食物供给服务则呈下降趋势(表5)。其中,碳固定、土壤保持、产水量的平均变化量在不同分区的差异性较大。碳固定和土壤保持在I 区有较大的增幅,而产水量在I 区下降较多。另外,研究期间耕地面积减少量与食物供给服务减损量具有空间一致性。在IV区,有大量耕地转为城镇用地,该区的食物供给服务下降的最多,平均变化量为-1.58 t/hm2。生境质量的平均变化量在不同分区的差异性较小。

表5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平均变化量全域及分区统计Table 5 Average change in ecosystem services for the whole region and sub-reg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0
从空间分布(图6)看,碳固定、食物供给、产水量、土壤保持服务的减损区域和增益区域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粮食供给的减损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与耕地转为城镇用地区域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粮食供给和碳固定的高增益区均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产水量的高增益区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土壤保持的高增益区与林地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产水量与土壤保持的高减损区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

图6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Fig.6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0
2.4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特征
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为1.05,土地利用冲突较强。主要原因为研究区权衡服务类型较多,且权衡关系较强(表6),共有5对生态系统服务属于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包括土壤保持与食物供给、碳固定的权衡关系以及产水量与食物供给、生境质量、碳固定的权衡关系。其中,产水量与生境质量的权衡关系最强,相关性系数为-0.43。

表6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分区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系数Tabl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n ecosystem services for the whole region and sub-reg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0
从分区看,各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I 区(1.10)>III 区(0.97)>IV 区(0.77)>II 区(0.45)。I区与整个研究区的情况基本一致,也存在多种权衡服务类型,且权衡关系较强。该区土地利用冲突较强的主要原因是权衡关系数量较多,即食物供给和碳固定均与土壤保持、产水量保持较强的权衡关系。III 区和IV 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相近,且这2 个区的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原因均为产水量与食物供给、生境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II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最弱,而且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关系数较小。
综上可知,I 区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区域,而产水量与食物供给、生境质量、碳固定的权衡关系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主导因素。
2.5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特征
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以弱冲突和中等冲突为主,二者的面积之和占研究区面积的66.43%。强冲突和极强冲突的面积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5.43%和0.08%(表7)。

表7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分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面积及比例Table 7 Area and proportion of land use conflict levels for the whole region and sub-region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2020
从空间分布看,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从外围到中部整体呈中等—弱—中等的结构,局部地区土地利用冲突强烈的空间分布特征(图7)。即弱冲突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两侧,中等冲突区域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和四周,而强冲突和极强冲突区域集中分布在研究区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其直接原因是研究区中部及其四周存在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而中部两侧较少(图8)。其中,共有3种权衡类型,即产水量分别与食物供给、碳固定、生境质量的权衡关系所表征的土地利用冲突区域集中连片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致使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冲突等级以中等冲突为主。共有6种权衡类型,即产水量分别与食物供给、碳固定、生境质量的权衡关系以及土壤保持分别与食物供给、碳固定的权衡关系所表征的土地利用冲突区域集中分布在研究区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局部地区,是强冲突区域主要分布在该区域的原因。

图7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等级空间分布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conflict level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2010 to 2020

图8 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表征土地利用冲突区域空间分布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conflicts characterized by ecosystem services trade-offs from 2010 to 2020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从分区看,4 个分区的土地利用冲突等级均是以弱冲突和中等冲突为主。强冲突和极强冲突区域均主要分布在I 区。根据各分区的冲突差异及其内部冲突特征,不同区域冲突缓解策略可以分为:1)I 区有较多的耕地和农田与自然植被混合用地转为林地,其产水量和食物供给有所下降,同时出现多种权衡服务类型,导致该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最强。因此需在考虑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评估该区域的土壤流失和水资源状况,因地制宜地实施退耕还林。2)II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较小,其面积仅占研究区面积的2.53%,而且土地利用类型以水体为主,因此要在现状的基础上集约高效利用水资源。3)III区和IV区土地利用冲突较强的原因是二者的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大量耕地转变为城镇用地。因此该区域在未来的发展建设中,要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度。严格控制城镇发展边界,避免城市建设侵占III区和IV区的耕地。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2010 年—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剧烈。主要变化为大量的耕地和草地转为城镇用地,以及大量的耕地和农田与自然植被混合用地转为林地。与此同时,研究期间区域碳固定、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服务均呈上升趋势,而生境质量和食物供给服务则呈下降趋势。其中,粮食供给和碳固定的高增益区以及产水量与土壤保持的高减损区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
2)从土地利用冲突指数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土地利用冲突较强。主要原因是研究区权衡服务类型较多,且权衡关系较强。其中,产水量与食物供给、生境质量、碳固定的权衡关系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主导因素。从分区看,各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I区(自然或半自然区域)>III区(半自然-半人工区域)>IV区(人工区域)>II区(半自然区域)。其中,I区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区域,主要原因是该区存在较多的权衡服务类型,且权衡关系较强。
3)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范围以弱冲突和中等冲突区域为主,局部区域土地利用冲突较为剧烈。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冲突等级从研究区外围到中部整体呈中等—弱—中等的空间分布结构。强冲突和极强冲突区域均集中分布在I区。
3.2 讨论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分析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在不同类型空间上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和空间分布特征,较好地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揭示了研究区因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而产生的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和空间分布特征,为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提供依据。本文的土地利用冲突结果反映的趋势与其他研究存在差异。如于伯华等(2006)指出城乡过渡带是土地利用冲突的热点地区之一。而本文得出自然或半自然区域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区域,也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最高的区域。主要原因是,本研究的冲突结果侧重反映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潜在冲突,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维度的冲突表征,而自然或半自然区域的对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的敏感度较高,因此潜在冲突会更强。现有相关研究则更重视区域土地利用的冲突现状识别,对城乡过渡带的冲突现状表征更为明显。也有相关学者将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纳入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的研究中。如吴蒙等(2021)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冲突风险这个维度的表征指标,分析空间冲突的形成机理,对未来研究国土空间生态适宜性评价具有借鉴意义。但该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以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基础,未能反映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或协同关系。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将借鉴该文的多维度研究思路,并同时纳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概念。
本文在选择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时,偏重选择与土地利用关系较为直接的服务类型,但对于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的都市区而言,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层次应该更高,如其对休闲游憩等文化服务的需求较高(徐迪航 等,2021)。未来应把休闲游憩等文化服务纳入评估范围,使得土地利用冲突的识别方案更为客观。
本文以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的个数表征土地利用冲突强度,暂未考虑每个评价单元每类权衡关系的相对大小,未来可以进一步构建权衡个数与相对大小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指数,更客观地反映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