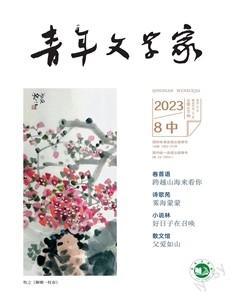论王维山水诗对《楚辞》的继承与新变
刘浪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两千年来,《楚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陈贻焮认为:“《欹湖》《椒园》《送别》‘山中诸作,境界精美,且一往情深,所受《楚辞》(尤其是《九歌》)的影响,也莫不隐约可辨。”(《论王维的诗》)王志清认为:“王维追步楚骚,在形式迹象上一目了然。”(《王维追步楚骚文化的文学背景和美学意义》)
从历来相关研究可看出,盛唐著名诗人王维的诗歌创作也受到了《楚辞》的极大影响。当今学术界多从其九首骚体诗的词语、句式、体制等方面分析其诗作对《楚辞》的借鉴之处,大致未能出古人所论之畛域,而关于其山水诗创作对《楚辞》的继承之探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山水意象、山水观念、审美意识三个方面具体分析王维山水诗对《楚辞》的传承与创新。
一、山水意象书写
《楚辞》中的山水意象书写,不是单纯表达山水之美的感触,而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媒介。其一,《楚辞》的山水景物大多被赋予了人的思想特征,多是拟人化、人格化的山水。最早对山水进行大量描写的是《九歌》,其中楚人祭祀的河伯、山鬼、湘君、湘夫人等神灵,是将黄河、湘水、山岳等自然景观的拟人化。《楚辞》之所以将自然山水人格化,赋予它们各种情感,这其实与楚地先民筚路蓝缕的艰辛和楚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关。其二,楚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孕育了诗人们丰富的浪漫主义思想,诗人在跋山涉水中,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自然山水,并加以内心的想象与创造,虚拟出各种奇思异想之境。诗人们在虚幻的自然山水中,感受文学艺术赋予自然山水的魅力。比如,《離骚》中写道:“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其中所提到的“咸池”“白水”“阆风”都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山和河流,是诗人所想象的山水景物,这些虚幻的山水充满了浪漫色彩,笼罩上一层“虚无之境”的缥缈氛围。《楚辞》中出现的山水意象,虽然有部分是诗人亲身经历的美景,但因诗人创作时所蕴含的情感颇为丰富,他们无法忘怀日月倏忽而逝,楚王和自己就要步入衰残的暮年,而自己无法为国效力的事实,这种悲哀之情难免投射到所见的山水景物之中,这就使他们笔下的山水不再是纯粹的书山写水,而是寄予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之物。
王维的山水诗借用了《楚辞》中的比、兴传统,但又淡化了自己的主观意识,他将山水作为真正的描写对象。《楚辞》中对山水描写的目的不是为了审美,山水意象仅处于陪衬地位。王维更注重对山水的直观描写,将山水有意识地引入创作,由此派生出万物生生不息的世界。
王维赋予了山水意象丰富的文学意蕴,多是对其进行体验式的意境书写,如《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意在说明,在万事万物都不断生长的春天,只要用心去体会,一切都是美好的。正如诗中所写,桂花落下,只有静心去感受,才能够感知到桂花的飘落,只有心静,世界才能变得清静。在夜深人静的夜晚,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山的空旷、山的寂寥。王维通过对山中景色的描写,丰富了山的内涵,细心品悟,的确独具一格,别有一番风味。
王维对夏天的山的描写又是另一种形象,如《送梓州李使君》:“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诗人描写了雨后泉水流淌在山涧之中,从远处眺望,如同树上下雨一般,构思清奇,写法巧妙,这是王维诗中的夏天的山。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是王维对秋天的山的描写。诗人将“空山”“新雨”进行意象组合,使其形成了一种幽清明净的意境。
“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赠从弟司库员外絿》)是王维对冬天的山的描写。在清冷的冬季,向远看去,远山深处覆盖了层层积雪,但仍然有松柏苍翠。在这压抑、沉重的灰暗氛围之下,闪烁其间的苍翠绿林,又透出勃勃的生机和清新的气息,让人的心和眼都为之一亮。
王维描写了不同季节的山景,丰富了山的内涵。
王维对水的刻画也是极其丰富的,常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展现水的灵动美,如《汉江临眺》:“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其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两句,诗人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以山光水色作为远景,重重青山在水的映照下若隐若现,时有时无;以层峦叠嶂的山峰布景烘托出江势的浩瀚广阔,营造出绝美的山水之境。
二、山水观念表达
《楚辞》中关于山水的描写不在少数,自然山水在诗人眼中,最终大多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成为表达自我情感的工具。《涉江》云:“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其中,涉及的山水描写有溆浦、山高、阴雨。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也,徘徊江河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诗人的高洁行为不被世人所理解,欲涉江而去;诗人登山临水,目之所及,情之所触,激发了自己满腔的郁情。但在南夷之地,无人知晓诗人的存在,于是诗人又离开长江,到达湘江。接着,诗人转换地点从鄂渚出发,面对着山水景色,触景生情,诗人感慨自己的遭际,发出无尽的哀伤。当到达溆浦时,眼前所见幽林深谷、山高蔽日、多雨霰雪,诗人想到自己得不到君王的重用,只能独处幽山。诗人借山水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使自然山水不觉染上了感情的色彩。这便是王国维说的“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离骚》中写道:“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其中的“阆风”,是神话中的地名,传说在昆仑山上。屈原想象自己能周游求索,以冀担当重任,实践己志,这一切在空间上是以山水为中心的,渡水登山,访求高丘山上的神女,是有深刻意义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写道:“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虽去,意不能已,犹复顾念楚国无有贤臣,以为之悲而流涕也。”这表明,屈原其实是为了求贤,这里的山水被幻化成了诗人的想象,追求志向的自由之境。
由此看出,《楚辞》中的山水观念弥漫着浓厚的忠君报国之情。诗人虽有奔向山水以求自我解脱的观念,但被济世救民的忠君思想牢牢牵绊,所以便不觉山水之秀美,只感浊世之悲。这与王维享受山水,寄心于自然,以观赏山水的美感为主题的山水诗的创作观念截然不同。
受佛禅思想的影响,大唐时代积极进取、豪迈自信的时代精神及王维本人独有的气质,将他的宗教信仰转化成超脱功利的审美追求。布洛的“心理距离说”认为:“审美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的‘距离产生美,要摆脱功利的、实用的考虑,用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来观照对象,才能产生美感,距离过远或过近都无法引起美感。”由此可以看出,在诗人的创作活动中,诗人主体与景物客体之间实际是存在着一种非实用性、非功利性的关系。创作主体必须具备一种超功利性的自由的创作观念,才能真正与客体相辅相成。只有在这种心态的感召下,当诗人与笔下描写之景物处于“零”接触的状态时,此时,诗人才能对它作出心灵上的体验,达到物我交融的状态,获得一种心灵净化,得到真正的审美愉悦,如王维的《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这里,“我”融于自然的山水现象中,主客不分,物我相忘,在对生命的敏锐感悟中,万物自然地呈现本来面目,显得自由清新,而诗人也那样无我齐物,融入自然。人与山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人对山水的自然美的发觉,还是上升为对整体生命意识的思考,这就是回到与山水同一、不分你我的和谐状态。诗人将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山水,以物观物,得到了真实的诗意之美、自由之美。
三、山水审美意识承变
从《楚辞》中的“山水有灵”审美意识到王维山水诗中的“天人合一”,不难看出,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与《楚辞》的山水摹写在情感上是有共鸣之处的。
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例》中认为:“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莞,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这种“光怪”之气其实就是指的“灵动浪漫”的楚地山水。屈原《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描写了楚国境内河流湘江水神的祭祀歌曲。关于湘君和湘夫人究竟为何人,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认为:“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屈原将上古神话中的他们刻画成一对热恋的男女,他们在相爱的过程中遇到阻碍,两人表现出的那种欲见不成、内心充满失望的感情便具有了真实的人情味。这让本来就充满温柔、灵动的湘水,又蒙上了一层浪漫、多情、神秘的意蕴。另外,祭祀山鬼的祭歌《山鬼》叙述了一位“多情”的山鬼在山中与心上人幽会的场景。山鬼再次等待心上人来,但心上人始终未来。全诗把山鬼起伏不定的感情变化、千回百折的内心世界,刻画得非常细致。巫觋在扮神的过程中,试图将山川的力量通过神秘的方式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获得在普通民众中的权威,这也是潜意识里认为人与“山川”可以沟通、转化和相合。诗中的神灵降临在巫觋身上,变成了“神化”的人,而山水之神也有人的情感,与人相恋,又成了“人化”的神。这种民神杂糅的原始的自然意识,反映在《楚辞》的山水文学中,就是崇尚灵动、虚无的审美意识的彰显。
王维在山水诗中也注重人与自然的交融,但他对山水景物常采取静观的审美观照方式,营造出的是一种“无我之态”,即一种对山水“自性美”的尊重。王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更深刻的思考,他笔下的山水景物都保持着本初的无人干扰的状态,自荣自衰,如《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時分明,夕岚无处所。”诗人通过对光的捕捉,展现了一幅瞬息万变又寂静的秋山夕景图。夕照中的鸟追逐着遁入山林,与末句“夕岚无所处”相照应,让人感觉山气缥缈,捉摸不定。王维诗里的万物都是自性发展的,无人干预,显示出一种“无我之态”。诗中虽然有人的视角,但只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人不是自然世界的中心,山水风物本身才是主角,这是一种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思想,是一种以宇宙为中心的生态审美意识。王维在对自然山水进行审美观照时的心态,是一种摆脱“案牍劳形”后的超然,是寻求心灵自由的悠然的心境。诗人作为审美主体遇到山水外物时,闲适的审美心态的介入为审美对象“披”上了闲意。万物皆有“闲情”,诗人观照的山水常被自己闲适的心灵之光所烛照,事物因此皆着“闲”色,皆作“闲”态,皆具“闲”情,表现出“闲”之享受。此时,诗人的情感与山水世界融为一体。
鲁枢元先生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在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在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王维的山水诗中也蕴含了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审美理想和人在自然本真状态下呈现的真实而纯粹的自我。他在处理诗歌中人与山水之关系时,遵循还原了山水本真的状态,在尊重山水的“自性美”的基础上,真正地将“心与物会,融入自然”的审美意识贯穿在山水诗创作过程中。
从《楚辞》中对山水的摹写到王维山水诗的大成,《楚辞》中描写山水所用的象征、拟人的比兴手法影响了王维对自然山水的观照方式,同时他又融情入景,极大地拓展了山水意象书写的意境。
《楚辞》中的“以我观物”的山水观念注重对个人情感的抒发。至王维山水诗的“以物观物”的超功利观,他更侧重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演进同步,从《楚辞》中“崇尚灵动、虚无”的审美意识延展到用“复归万物之本性”的审美意识对人与山水关系再次重构。相比《楚辞》,在王维山水诗创作中,他对自然山水的敬重及对宇宙人生的哲思有了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