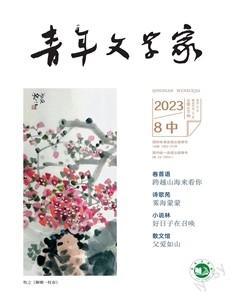《北上》中兄弟的隐喻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杨雅雯
家族小说在我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占了很大的比重,如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这些小说往往通过家族的兴衰来表现相关年代的历史社会变迁。家族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产生和存在都与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集团为了巩固皇权对同姓贵族和异姓贵族进行统治,就对贵族阶层进行了分封,分封意味着封土建国(给贵族土地),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邦国。封土建国的行为使贵族接受新的统治者的统治,缴纳赋税,这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统治制度封建制的来源。在这个制度当中,封土建国最低等级的分封贵族是卿大夫,卿大夫的封邑被称为“家”,这里的“家”意味着由相同姓氏与血缘关系而聚合起来的集团,也是“家族”与“家庭”这些词的语义来源。
家族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是无法分割的。想要表现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这一背景下的人物故事,势必要对其所在的家族构成、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进行描写,也势必会以家族为单位来描写家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家族间关系的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中国小说史上最为著名的表现家族故事的应当是小说《红楼梦》,表现封建家族在国家政权建立方面的小说是《三国演义》,表现对封建制度的反抗,进而描述个人在这一制度中的对抗性成长,最终形成与政权抗衡的类似家族或帮派组织体的是《水浒传》。
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中,家族是这一制度当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在这个背景下,个人所受到的教育(以儒家教育为例),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在家族(人群)当中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个人内在品德的要求,还是外在与他人相处之道的要求,都在教导个人如何收敛个人意志,如时常考察自己的行为品德是否与传统道德相违背(“吾日三省吾身”),如何在与他人交往当中与他人和谐相处(“仁者爱人”),将遵从父权君权意志的《孝经》列为想要实现功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目。个人意志被融入家族意志当中,个人的发展势必与家族的整体利益相一致。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制度的变更,贵族特权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已经消亡。家族这一组织体也不复存在,随之分散成诸多小的家庭,这些小的家庭或许能实现几代同堂的人数盛况,但已没有了家族原本的实质。
一、消解了的家族与仓促登场的兄弟
曾经以血亲和地域来确定的家族关系将由什么来取代?家族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家庭伦理的消解,家族的人口缩减,使得家族由原本众多族人的局面逐渐缩减为家庭。仍保有一定经济实力背景的家族原型转变成了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经济实力不复当初的家族则随历史与时间的变迁,成为常住人口只有三人或四人的普通家庭。以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为背景所进行的文艺创作,仍然将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置于其中,作品中矛盾的展现也常常表现个人与家族之间的矛盾,宗族、伦理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矛盾。
在进行普通家庭的故事描述中,兄弟这一社会角色仓促登场,取代了家族的其他成员,成了家庭伦理的主要表达方式。为什么当代作家选择兄弟来代表亲情、代表家庭伦理,而不是通过父子或母女的关系来代表家庭伦理?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最让人诟病的并非以亲情维系的家庭伦理,而是以父系家长制为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家族宗法制,家族的意志、父系家长的意志的建立削弱了个人意志的表达,在文学表现的角度,个人意志的表达和个人精神的建立无疑意味着自由思想的实现,与封建社会下大一统的父系家长宗族制度是相背离的。在此时,兄弟情谊的描写开始取代父系家长制在个人发展中的角色。兄弟的表达意味着双方地位的平等,这种平等打破了宗族家长制的专断与权威,也意味着在这种平等地位当中,兄弟双方具有平等的人格和地位,没有了专断和权威的表达,使个人精神和意志可以最大程度的表现。
徐则臣的小说《北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家族小说,讲述了几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实质上讲述的是两个時代的故事,为了消解家族中长辈对晚辈的思想约束,也为了更好地反抗家族的宗法制度。徐则臣在描述清末时期的故事情节时,将所有可能产生家族意志的场景都分解成了家族退场、个人登场的表达方式:谢平遥过家门不入,于是他的想法后人无法得知,同样他的意志后人无法继承,文中也没有出现任何他需要服从与继承的意志。孙过程的父母在水泊梁山这一代表个人意志与自由的地方因与同村村民发生冲突被杀,孙过程的意志也成了独立与自由的个人意志的表达。邵常来则是背井离乡作为挑夫的身份出现,即使有家族也无法实现意志的传达。这些人中,除了谢平遥可以称得上是小知识分子,其他人的阶层与地位都是家族没落与消解后的贫民与农民,文中所有人都没有家族作为依托。
徐则臣仿佛为了避免家族意志的产生,他刻意孤立了前代人与后代人的意志,使他们的意志不相通达,不能互相理解,两个时代的人,仿佛只是遥遥相望的陌生人。对前辈意志的理解,要通过后辈用历史遗迹的碎片进行拼凑,才能逐渐得出故事的轮廓。这种互相不理解的状态,反而间接表明了家族的影响力。对于父权的影响力,已经被小说作者用情节的展示进行了消解,将权力的能力展现压制到了最低。
二、以兄弟来指代的亲情伦理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兄弟之情有较多的描述。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写:“使布立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兄弟是亲情的一部分,也是伦理实践的一部分。
当代小说中,兄弟之间的关系并非总以正面积极的形象出现,如余华笔下的两对兄弟—山峰、山岗及宋刚、李光头。兄弟之间的亲情伦理因为某些突然萌生的念头或某种隐秘的自我癖好而被尽皆抛弃,进而描述兄弟之间在没有道德感束缚下利己自私的人性。这些描写既可以理解为时代变化导致的传统文化式微,也可以理解为自古以来对亲情的重视在这一阶段被个体以名义上的自由与虚无的追求所替代,亲情伦理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阶段被归入家族宗法制度的残余当中,成了腐朽与腐败之物。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伦理与家族宗法制度并无必然的联系。当家族宗法制度失去了原本的存在根基时,必然会消亡;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维系方式,情感所能够产生的牵绊却无法随之消亡。在徐则臣笔下,主人公在面对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的时候,亲情伦理已经不再是需要断绝之物。这里亲人之间情感的表达不再是宗法家族中的强权式命令和被动式服从,也并非地位不平等的父子之间那种父权的引导和规劝,而是兄弟之间平等的协商,是带着对亲人的遗憾和情谊来完成的个人自我成长和实践家族及父权的概念,而这些在徐则臣笔下被消解掉了。无论是《耶路撒冷》中为了给儿子初平阳攒钱凑留学费用而卖房子的父亲初医生,还是《北上》中纵然万般不愿意脱离船民生活但为了儿子邵星池的前途和幸福,或是毅然决然脱离水上生活的父亲邵秉义,老年父亲对成年儿子所作出的人生选择本着尊重的态度,并尽一切力量支持其选择,在不平等的父子身份背后,是平等的尊重。
父子之间情谊的表达是父亲权威逐渐收敛的过程,也是儿子作为个体逐渐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在邵星池儿时,父亲的权威能够通过行使暴力来实现,但当邵星池逐渐成长,父亲承认其“长大了”,与此同时象征父系权力和暴力压迫等一系列否定父子平等地位的实施手段反而被父亲收拢,暴力压制的方式被否决掉,父亲邵秉义开始认可儿子的独立性和自我主张。儿子选择卖掉家里的船,父亲虽然心里不赞同,但也尊重儿子的选择。邵秉义没有阻止儿子的行为,因为他回忆起了当时的自己。成年后,为了成家与父亲分家时,父亲对自己作出的选择并不赞成,但当时的父亲也选择了尊重理解的场景。双方处于情感平等状态下的亲情表达,正是作者所想要建构的亲情体系。在这种亲情体系之下,家庭不再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洪水猛兽,个人的自由建立在个人的自我实现之上,家庭成了养分,滋养着家人自我实现的根茎。家庭成员实现了事实地位上的平等后,家庭成员就成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和基本行动原因。
三、亲情产生的内驱力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北上》描写了两对兄弟。意大利人费德尔为了实现理想而远赴中国,他的理想是像偶像马可·波罗一样游历中国的大运河。他的哥哥小波罗并没有什么自己的理想,小波罗来中国的目的是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弟弟,在寻找的过程中,小波罗踏上了游历中国大运河的船,感受着弟弟所想要感受的运河风光,追寻着弟弟想要实现的游历大运河的梦想。他没有找到他的弟弟,却发现了大运河的美好,最终小波罗死在了大运河上,而弟弟在中国隐姓埋名,与一个中国姑娘在中国定居生活。
孙过程的人生之路似乎也在遵从哥哥孙过路的意愿,哥哥因为父母遭到洋人的杀害而立下誓言杀死洋人,于是孙过程一心阻碍小波罗的北上行程,并将小波罗绑架,但他的哥哥孙过路认出恩人谢平遥之后就改变杀小波罗的意愿,并放他们离去,甘愿自己赴死。孙过程遵从了哥哥的意愿,护送小波罗等人一路北上。最终,他没能阻止那些想要为哥哥报仇的人,使小波罗被刺伤,并间接导致了小波罗的死亡,一段故事戛然而止。
这不是徐则臣第一次用“兄弟”之情来推动故事发展,回顾其小说《耶路撒冷》,故事中的“弟弟”天赐死了,曾经出现在他自杀期间却未能够阻止其死亡的小伙伴们,似乎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谁也不曾主动参与天赐的死亡,但也都没有阻止天赐的死亡。于是,心中的愧疚成为他们之后人生的遗憾,也成为他们必然要回乡弥补愧疚的理由,也成了驱动小说发展的核心。
众人面对“弟弟”自杀时选择的逃避行为,在逃避行为产生的那一刻,他们逃避了亲情的束缚,获得了所谓自由的实现,所付出的代价是之后若干年心灵上的桎梏。他们无法释怀自己曾经的逃避与怯懦,在自由过后却不得不接受新的枷锁。这种逃避与余华笔下的兄弟之间既刻意又明确地舍弃亲情伦理,并肆意展示自我与自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亲情伦理在某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实现自我及获取自由的负累,或者可以理解为亲情伦理所代表的某种意志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负累。
在《北上》中,兄弟间的亲情已经不再是一种负累,小波罗和孙过程都选择了带着亲人的意愿上路。在路上,小波罗并没有找到弟弟费德尔,孙过程也没能如约保护好小波罗,但是不再背弃亲情,心灵也就不再会被愧疚的情绪所牵制。在寻找弟弟费德尔的过程当中,小波罗和孙过程看到了运河两岸的生活,参与这种生活,使得他们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意大利人小波罗没有什么自己的理想,中国人孙过程也是做好眼前事情的人,他们都属于没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普通人。普通人的人生历程大多是在带着亲人的殷切期待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逐渐有了自己的人生计划和想法。可以说他们就是在寻找和观看的路上开始创造自己的价值,也可以说是亲情的指引使他们获取了自身的目标和价值。小波罗的死对于孙过程而言,是另一个“兄弟”的肉身消逝的过程。小波罗对运河的情感,对运河的痴迷也影响了孙过程及孙过程的后代,他给孙过程留下了照相机,留下了在运河两边安家立业的念想。小波罗想要实现在照片中描绘照片背后故事的想法,随着小波罗的死亡似乎已经无从实现,而他留下的相机在无形当中影响了孙过程的后人们:孙宴临在大学里开设的课程就有与小波罗相似的观念。小波罗想要沿着运河每天上下来回讨生活的念头,被小波罗情同手足的邵常来和他的后代们实现了,邵常来开始买船,成了船民,最终他的后人成了船老大,过上了在运河上下来回跑,来讨生活的日子。
生活在現代的人们终于不用再背负沉重的家族使命缓缓上路了。父权和宗族是历史的产物,终将被消融在历史的进程中。与此同时,亲情伦理在现代生活当中仍然是值得人们期待和重视的情感,以兄弟为指代的亲情伦理不应是阻碍个人自我实现的枷锁,而应将其当作为实现自我价值而提供的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