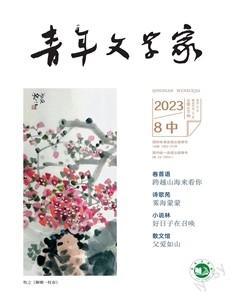对不能谈论之物开口
李黎
《墙上的斑点》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早期作品,被人们认为是她的实验之作,也被认为是她的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甚至是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实验小说为何会有如此地位?本文从意识流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文体角度出发,结合伍尔夫自己的小说理论,论述《墙上的斑点》。虽然在技巧上它并非意识流小说的巅峰,但它已是一种在文体上成熟的意识流小说,是对伍尔夫小说理论的成功实践。
英国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名作《逻辑哲学论》开篇即言此书可以概括为“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这也是他早期哲学思想的总结,他认为语言的边界就是人类认识的边界,语言之外存在着一个神秘而庞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人类仅能说清已知的世界,而面对更广阔的未知只能保持沉默。这并不表明维特根斯坦保守或者是一个怀疑论者,相反,在一个人类自信心空前膨胀的时代,提醒人们承认自己的无知、保持自己的谦卑是一个需要勇气、智慧并且有必要的行为。
在各种全球性问题频发的当下,回首再看维特根斯坦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高瞻远瞩。但20世纪前期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时代,一个大胆的时代,人们对新事物的开掘始终要高于对旧事物的缅怀。伍尔夫就是一个在文学领域开疆拓土,试图在文学语言上对不能谈论之物开口的文学探险家,她的意识流小说理论就是对维特根斯坦那句名言在文学上的一种背离。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针对的是普通语言,而伍尔夫强调的是文学语言的无限可能性。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可能受到了语言规则的约束,从而无法到达未知的世界,但文学语言给了我们朝向未知、对不能谈论之物开口的机会。伍尔夫没有止步于理论探讨,她用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墙上的斑点》就是她表达自己小说理论的成熟之作。
一、作为文体的意识流发展
“意识流”一词最早不是文学术语,它来源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领域的创造。在《心理学原理》中,他否定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把人的内心意识看作是一幅幅随时间不断出现的片段式图像的观点,颇具文学性地把人的心理比作是一条不断延续的意识流。行为主义心理学受“刺激-反应理论”的影响,认为人类心理是受到外界的刺激而出现的,并不是连续的,没有刺激人类就不会有内心活动。但是,詹姆斯认为,无论受不受刺激,人的内心始终在活动,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受到刺激时这条河流可能会更加汹涌,但不受刺激时这条河流依然在涓涓流淌。可以这样说,行为主义心理学只看到了人类显性的、表层的心理,忽视了在两个明显的内心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着心理暗流,也就是说只注意到了“可以说的东西”,而忽视了“不能谈论的东西”,这与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是相通的。詹姆斯试图探究那些在人类知识版图之外的人类心理,把人类意识之核全部纳入心理学研究范畴。在文学领域,伍尔夫做着类似的工作。
意识流被用于文学领域,并没有取得在心理学中那样的统一用法。梅尔文·弗里德曼在《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中提到了文学批评家们在使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这两个词语时的混乱现象。他认为“当批评家把这两个名词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们正好是把‘文体-意识流和‘技巧-内心独白混淆起来了”。当批评家们在使用意识流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意识流是一种小说文体,而一种文体显然不只是文学技巧的堆叠。尽管意识流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内心独白这一手法,但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因此,“意识流小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主要挖掘广泛的意识领域,一般是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的小说。‘意识流是小说的一种形式,正如‘颂歌或‘十四行诗是指诗的某种形式”(梅尔文·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意识流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文体,把意识流当作一种文学技巧是错误而又狭隘的。意识流作为一种文体,有着大量使用内心独白、内心分析、感官印象等手法的特点,但这些技巧并不是意识流小说特有的,在伍尔夫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表现。伍尔夫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对这些技巧的纯熟使用,而在于她是这种小说形式的开创者之一,她在理论上阐明了这一文体并进行了成功的创作。
二、伍尔夫的小说理论
伍尔夫的文论作品众多,本文选取她的三篇代表作分析其意识流小说理论。这三篇文章体现了她想要开拓小说语言、扩大小说表现内容、改革旧式以模仿论为尊的小说体制的观点。
伍爾夫认为,小说应该更加注意开掘人类的心灵世界。在《论现代小说》中,她称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为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令我们失望,因为他们关心的是躯体而不是心灵”。她把他们称为物质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把他们的故事编写得扎实紧凑,过于重视结构、情节、环境等,却忽视了人物的内心。伍尔夫不无可惜地写道:“他们写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浪费了无比的技巧和无穷的精力,去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也就是说,她觉得过于精细的外部描写反而让写作失去了对生活本质的把握,这导致小说呈现出来的仅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一个更为广阔、幽微的世界却无法得到表达。《墙上的斑点》就舍弃了物质主义式的老旧描写,通篇呈现的都是主人公涌动的心灵世界。这并不意味着意识流小说与外部世界无关,只是说明小说更看重的并不是外部世界到底如何,而是关心外部世界最终在人物内心呈现出的面貌。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勾起了的人物的想象,这些想象反过来对于外部世界有没有什么更深层的关联。
伍尔夫大胆地对新的小说形式进行了展望。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她强调作家、批评家应该把目光放在当下和未来上,而不要只是盯着过去。她看到了时代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歌颂永恒的文学已经逐渐脱离了现实的人类生活,宏大叙事已经缓缓落幕,现代人对细微、隐秘之物的呼唤却还没有得到文学的回应。她认为,小说就是能承担这一时代任务的文学体裁,因为新的小说形式“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新的小说将同时具有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力量,但“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的标志之一的那种令人惊异的写实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斑点》有诗歌般灵动跳跃的心理活动描写,散文般平凡普通的生活场景,戏剧般出奇意外地对斑点的最终解释;并且《墙上的斑点》不把写实作为写作的核心,相反,对斑点的不确定猜想成了小说最精彩的部分,这表明《墙上的斑点》已经是伍尔夫所期待的回应时代要求的新小说了。
伍尔夫也批驳了爱德华·摩根·福斯特非美学的、模仿论式的小说理论。在《小说的艺术》中,伍尔夫再次强调了小说对于生活的独立性,这是她对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延续上千年的模仿论文学思想的反叛。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有力的一次反叛,但这是对模仿论残余的清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现实主义小说依旧是小说的模范,而现实主义的盛行或多或少带动了模仿论思想的“复辟”。在福斯特眼中,“小说被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她从生活吸取养料,并且必须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来作为报答,否则她就会灭亡”。伍尔夫对此种复刻现实的文学不感兴趣。在《墙上的斑点》中,她用想象使墙上本不起眼的斑点成了串联起散落在人物内心的精彩幻想的桥梁,并宣告把外部现实描写得惟妙惟肖并非小说的唯一出路,事实上也远非最好的出路。
三、《墙上的斑点》—成熟的实验之作
《墙上的斑点》是对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理论的完美实践。具体分析文本,我们更能直观地感觉到这部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更能认同它是一部成熟的意识流小说。意识流作为一种文体,已经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应用。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小说呈现破碎、无序的特点。如果我们用一种亵渎的方式简化一下小说的内容,可以看到小说没有情节,只有话题的串联,可简要概括为“墙上的斑点是什么—城堡与骑士的幻觉—对斑点的猜想—肖像画—房子以前的主人—分别的想象—对斑点的猜想—人类的无知与生活的偶然—丢失之物—生活的比喻—来世与投生的想象—对斑点的猜想—想要静静地思考—自我恭维的愉快想法—正统事物的无趣—对标准的反叛—对斑点的猜想—关于古冢、古物收藏家与箭镞的想象—知识、学者—可爱的世界—对斑点的猜想—对惠特克年鉴的等级性的反感—斑点作为现实的具体的物的安全感—与木头有关的想象—斑点的揭示”。猜想墙上的斑点是什么可以看作“主要话题”,但它与其他“次要话题”并无轻重之分。小说并没有遵循线性的故事发展模式,这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
其次,小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反模仿论、反镜子说的。“我”有能力主动搞清楚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却没有行动,因为了解并描写墙上的斑点的形状、颜色、质地以及它是否是钉子、花瓣或者蜗牛并不重要,或者说这与无边的漫游、遐想同样重要。理念的床存在与否无关我们按自己的想法画出自己的床,甚至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小说写道:“我本来可以站起来,但是,即使我站起身来瞧瞧它,十之八九我也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一旦一件事发生以后,就没有人能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了。唉!天哪,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准确!人类是多么无知!”
再次,小说表达了对琐屑事物的关心。书写内容深入到日常生活中难以觉察到的细微事物,并赋予它们从未有过的价值。小说拓宽了视野,抓住了生活不起眼的一面。但我们知道,主体与客体不是截然分开的,主体的存在需要其他物的证明,正是许许多多不起眼的生活细节证明了我们自身的存在和独一无二性。在《墙上的斑点》的主人公看來,小小的斑点给了她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我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我们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往往这样,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它证明除了我们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事物。”
最后,小说成功实践了对心灵的关注。用伍尔夫的话说,这是一种精神主义而非物质主义式的写作。她试图探寻最隐秘的、最幽微的内心活动,并用文字表达出来。从整篇小说看来,伍尔夫对“可以说的东西”并没有说清楚,因为对于一只墙上的蜗牛她做了太多与之无关的猜想,并认为“十之八九我也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同时,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她也没有保持沉默,在感叹思想的不准确和人类的无知后依然想要追问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
综上所述,《墙上的斑点》虽为伍尔夫早期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实验之作,且为短篇小说,但已是成熟的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已在《墙上的斑点》中得到了圆满的呈现,尽管在技巧上它并非达到了巅峰。正如罗伯特·汉弗莱在《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所言:“《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都是意识流流派中的姗姗来迟者,都不是典型的意识流作品。”《墙上的斑点》作为意识流小说,其最大贡献在于实践了伍尔夫想要以小说语言的形式向所谓“不能谈论的东西”开口的小说理论,是一次成功的文学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