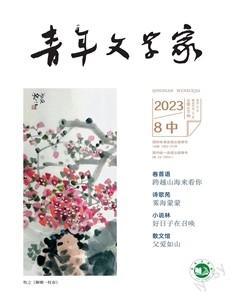论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的代际传承
钱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传奇性的作家。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张爱玲的创作生涯和研究历程可说是大起大落。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连载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名噪一时。1955年,她移居美国后,她的小说就鲜少被提及,逐渐沉寂。20世纪60年代后,张爱玲的作品重新在海外华人市场中受到欢迎。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再发现,使得“张热”现象逐渐出现,张爱玲的作品受到读者和市场的追捧。
细观张爱玲在国内的接受程度,可以说离不开海外汉学界的推动,其中又以夏志清首开生面,填补了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对其的描述空白。一时间,人们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研究进入国内视野,既有像夏志清一派对张爱玲的高度赞美,也有对张爱玲的作品思想进行大力批评的学者。
在此之后,李欧梵在研究中则关注到张爱玲创作的现代性问题,将研究目光关注于张爱玲创作中的日常生活问题以及电影化风格,将张爱玲的“传奇”风格与都市生活化相联系。
对张爱玲的研究至王德威时,王德威则将目光重回张爱玲的文本和创作立场,尤其重视张爱玲小说中的“鬼话”风格和重写题材。王德威不但将眼光重回文学史,更将张爱玲的地位提升至“祖师奶奶”级别。
从以上三人各异的文学视野中,我们不難发现他们对张爱玲的共同的高度关注,其中存在着代际传承关系,大大提高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经典化。
一、对张爱玲的发现与推介
1957年,夏志清发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夏志清在文章中对张爱玲的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是夏志清研究张爱玲的最早发声。其后,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首先以“作家作品论”的模式高度赞扬了张爱玲,并把张爱玲纳入文学史。夏志清的主要观点是他肯定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技巧,推崇其“苍凉美学”,尤其称赞《金锁记》和《秧歌》,大力表彰张爱玲对意象的使用。他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中特别阐释张爱玲对色彩、嗅觉和音乐的敏锐,而小说中意象的丰富,更是在中国近代小说家中首屈一指。
在夏志清的写作中,一方面,他的批评基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尊重女性、重视道德;在方法上又善于旁征博引,以比较的方式提出新见。另一方面,他受到写史题材的限制,虽然提及许多西方作家以作类比,但理论使用频率不及后来的李欧梵与王德威。夏志清受欧美新批评学院派的影响,更多地采取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小说细节,后来这一传统也被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继承。
张爱玲是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描述篇幅占比最大的一位作家,也可以说是对其评价最高的作家。可以说,“张爱玲在夏志清的新文典中占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她是夏志清理想化的文学纯洁的典范”(张英进《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
李欧梵的研究则超出了文学史的范畴,总体围绕着他自己的核心概念,即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他把张爱玲放置在了一个“现代性”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随后进行的一系列关于张爱玲的日常化书写或电影化风格几乎都是为这一套“现代性”理论进行服务。李欧梵也关注到了张爱玲小说创作与上海都市文化的紧密相连,基于此,李欧梵通过张爱玲小说作品中展示的日常生活碎片来构建张爱玲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重要的联系。李欧梵以张爱玲的《封锁》为例,引述学者周蕾的文章说明了“传奇”与都市生活的关联,即在《封锁》这一故事中,如果没有现代文化物质—电车的存在,这个故事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实际上,李欧梵之所以如此关注作家与都市之间的联系,归根结底仍然是在于都市与现代化之间难以分割的关系:这种日常生活碎片本身所展示出的都市生活殊异于中国早期的封建宗法制村镇书写模式,从而显现出现代性的典型性,从李欧梵的分析中可见张爱玲文本中确实存在着强烈的现代性特质。
对张爱玲的高度关注延伸到王德威的文学研究中。王德威再一次把目光放到了文学史的构建中,他显现出与夏志清同样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努力,但在王德威的文学版图中,他将张爱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他将张爱玲谱系化的尝试,可见其将中国文学版图化的野心。他认为,张爱玲的“招魂”在其生前与身后,均不乏知音与后来者,这些知音与后来者就是“张派”传人—白先勇、施叔青、钟晓阳、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袁琼琼,以及阿城、王安忆、叶兆言、须兰等人。诸多重要作家都被王德威归类到了“张派”的文学谱系中,王德威在意的是他们与张爱玲在气质和神韵上的相近和相似。
除此之外,王德威格外注意张爱玲的“重写”现象和“鬼魅叙事”,他认为张爱玲“看到现实中双重或多重视景,似曾相识又恍然若失,既亲切又奇异,既‘阴暗又‘明亮。由是参差对照;轮回衍生出无限华丽蜃影;却难掩鬼魅也似的阴凉”,以及当主流意识形态信奉历史线性进程的必然,张爱玲却“以‘流言代替‘呐喊,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以“卷曲内耗的审美观照”(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颠覆历史线性进化史观。王德威在《魂兮归来》一文中认为,鬼魅叙述的传统从古流传而到现代,此一传统则戛然而止,随后却卷土重来,张爱玲的鬼魅叙述实际上就是卷土重来的一个代表。
二、对抗传统宏大叙事的另一路径
梳理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文学研究成果,尤其是相同的对张爱玲的高度关注与推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关系。从夏志清开创的对张爱玲苍凉美学的肯定背后,是其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感时忧国”的某种否定,他以“纯文学”批评的姿态来对抗功利主义文学,而这一传统显而易见地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研究中继承了下来。
他们统一的审美趣味在反抗国内的重写实传统,并且试图确立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李欧梵注重的张爱玲的日常化书写不但符合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细读,更是与夏志清对抗宏大叙事的意图不谋而合。而王德威对张爱玲重复代替创新,回旋代替革命的肯定,言下之意也不言而喻。
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之间除了存在对抗宏大叙事的共同大方向外,在文学批评方法上也存在很多的相似点。夏志清受欧美新批评的影响深重,因此他的文学批评多文本细读的同时又将中国文学纳入了世界的版图中,这正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点。此后,李欧梵和王德威也将这种世界视野继承了下来,在论述过程中经常将笔下作家与西方经典作家进行比较,虽不能完全摆脱“以西典律中国”的惯性,但仍然能提供新颖别致的观点。
同时,他们三人都偏好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和解读。在夏志清的小说史中,虽然囿于文学史文体的写作限制,他仍然使用了许多理论。而受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热潮的影响,李欧梵和王德威的研究中更是出现了大量理论,以至于出现了一部分理论先行的批评声,譬如清峻就曾经表达过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对他们所操持的“先进理论”显得太过自信,“忽略基本的史实分析,或许因急于推翻某种成说,于是‘搅扰群书以就我疏于历史复杂性的辨析……这种昧于历史或‘六经注我式的批评策略往前再走一步便成了艾柯所说的‘过度诠释”(清峻《昧于历史与过度诠释—近十年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倾向》)。由夏志清所開启的“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在经过了几十年的众声喧哗后,似乎已经形成了另一种权力话语,而李欧梵和王德威是否受到这一“影响的焦虑”则是值得讨论和思考的。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中存在着非常典型的“道德视景”,强调个体的人性和道德。综观《中国现代小说史》,道德的提及频率十分频繁,他非常重视作者的道德视景,批评带有典型的人文主义批评精神;但在西方理论热潮的快速更迭下,这一特点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展现得格外典型。
这样看来,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对张爱玲的重新解读,实际上体现出海外华人学术界迫切并强烈地希望出现一种异于国内传统宏大叙事的新的范式,这一核心由夏志清创立,经过不同的发展却始终不改其背后底色。在文学批评方法上,他们都受到西方批评界文本细读传统的影响过深,醉心于文本阐释甚而造成一定的过度诠释,作家与作品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阐释个人理论的工具与武器。
夏志清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由于在耶鲁大学的研究院跟随新批评派的大师布鲁克斯等人学习,加上其兄长夏济安的影响,形成了西方中心的文本细读模式,是标准的学院派。李欧梵书写过自己的求学经历,夏济安是他以前大学时的老师,教英国文学。李欧梵和王德威都出身外文系,追溯他们大学外文系的传统,由傅斯年创立了一种自由主义的人文教育,此后夏济安到此大学执教,创办了《文学杂志》,大量译介西方作品和理论。这一时期的文学传统对当时的许多作家和学者产生了影响。王德威也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影响:“我觉得传统是有的,但是到了我已经是最后,我抓住的是传统的尾巴。”(王德威、李凤亮《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所以说,无论是接受的教育还是文化上的影响,他们之间似乎都存在着一种代际关系,由夏志清开创而进一步发展和衍生,乃至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学研究范式和趋同的审美趣味。
三、双重身份与徘徊的边缘性
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和创作者、研究者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形成的学术研究范式中,有着共同的对抗宏大叙事的传统,其一原因在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环境较为相似,都受学院派传统影响,强调学术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从而排斥文学与政治的过密联系,这种“纯文学”的审美标准既有其优点也遮蔽了部分视野。他们的客观的“纯文学”立场,多少有“何不食肉糜”的超然姿态,当抗拒和摆脱宏大叙事成为一种“影响的焦虑”后,就容易产生一种“误读”,在这样的境况下,产生隔膜和生疏也是在所难免的。
再者,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同时将眼光置于张爱玲身上,选择以张爱玲为基点进行自己的文学批评,也在于张爱玲与他们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从个人经历、双重身份到中西徘徊的边缘姿态来说,我们不能忽视其中的共同性。回顾张爱玲的回归以及随后而来的“张热”现象,我们无法忽略其后海外华人(尤其以夏、李、王为典型)批评家的大力推介和研究作用。
因此,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选择了对抗国内宏大叙事的另一原因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在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后,他们试图寻找不同于国内的本土的文学批评的尝试,而作为同类的张爱玲以其文本的多样性和极高的文学再生空间成了最好的诠释对象,“一位抗拒时代潮流的独行人,这等才女才可能对那个时代提出终极概括,其意义绝非一群二流作家能比拟,他们不过是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张英进《从反文典到后文典时期的超文典:作为文本和神话的张爱玲》)。
当然,虽然本文主要论述了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对张爱玲的研究和关注,及其存在的代际传承关系,但仍然必须明确海外汉学和国内学界对张爱玲研究的多样性。夏志清的评价标志“张学”的某一高点,也成为之后研究张爱玲的某种蓝本,同时亦有可能造成某种权力的遮蔽。但总的来说,从个人身份或徘徊的边缘姿态出发,海外华人批评家似乎在心声上更能与张爱玲共鸣,他们的热情推介也对研究张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热”现象已经持续数十年,但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海外华人学者,都仍以不同的角度对张爱玲进行再解读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