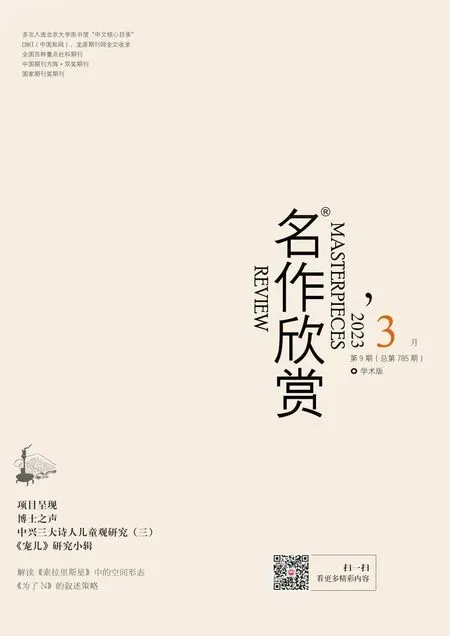利特温采夫《少不入广》与俄侨“回归者”的东方理想
⊙陈扬阳[中山大学,珠海 519000]
⊙李暖[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少不入广》(Молодым не ходи в Гуандун)是当代俄罗斯作家根纳季·利特温采夫(Генадий Литвенцев)于201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以道光年间的中国广州为背景,记述了鸦片战争始末。小说曾获巴若夫奖(Бажо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2018)提名,并被收录进小说集《在地球的另一边》(На обратной стороне Земли,2021),获2022年德国国际文学大赛俄语作家“年度优秀作品”奖。小说集聚焦东方历史和旅华俄侨生活,编织出一个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多元文本,把中国嵌入当代世界的文化纠纷和俄罗斯人内心世界的戏剧冲突当中。
利特温采夫1946 年生于哈尔滨的一个俄侨家庭,1956 年随父母回到俄罗斯,但他始终视中国为故乡,对中国和东方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中国主题以及俄侨旅华史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例如,小说《燕子的梦》(Сон ласточки)讲述了俄侨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里的生活,以及卫国战争余音下俄侨回归祖国的历程,主人公在历史变动中靠着信仰、记忆的支撑,维护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根据当代批评家尼科诺娃的观点,利特温采夫属于典型的俄侨“回归者”(вернувшиеся)一代,他们大多是俄侨后代,于20 世纪末回归俄罗斯,作品多回忆他者语境中的俄罗斯生活,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归国者文化浪潮;其中,相对边缘化的东方俄侨后代积极参与着当代俄罗斯整体文化场域的重建,对保存民族记忆和再现流亡精神体验做出了不同于欧美俄侨的独特诠释。在上述背景下,《少不入广》几乎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尝试。正如尼科诺娃指出,作为回归者文学的一部分,它思考的主题并非流亡生活碎片或侨民家族历史,而是一个帝国长期停滞的开端;它反思中国历史灾难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是当代俄罗斯历史遭际的影射。
《少不入广》的标题化用自中国谚语“少不入川,老不入广”。“少不入广”的说法最早见于清代江左樵子《樵史演义》,意指广州富庶繁华,风月之盛,易耽于声色;沈复《浮生六记》中也提到:“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
在利特温采夫笔下,广州是另一种精神气质的象征,他借主人公之口提到:“广东人开朗而欢乐,同样的外表,同样的五官,但精神气质与我们大不相同。节日期间,年轻人盛装打扮,穿着彩色丝绸的袍子,还有灯笼、龙、风筝,整座城市在五颜六色的火光下绽放异彩。难怪中国有这样的古话:‘少不入广!’这里有太多诱惑,令人忘记故乡。”
广州形象影射了利特温采夫心目中理想的东方世界。在他看来,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整体,对异质文化怀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俄侨在中国比在西方更能体会什么是精神自由,中国城市的独创性、韧性及其对传统的忠诚使几十万侨民得以建立自己的社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动荡带来的文化断裂,在东方保存了一座“基捷日城”,一座“漂浮在异国他乡的孤岛,就像山涧中的鲑鱼逆流而上”。作为“回归者”,利特温采夫反而对东方怀有比对俄罗斯更深的乡愁,并从双重文化故土的根脉中看到了俄罗斯与东方的深刻联系。“为故乡做一些事情”是《少不入广》的直接创作动机,作者意在向俄罗斯人揭开中国历史富有戏剧性的几页,让同胞更好地读懂这个“逐渐成长为强大的现代性力量”的国家,同时也指出,这代表了俄罗斯“转向东方”(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策略下的精神向度和文化转向。
利特温采夫指出,之所以选择将鸦片战争作为小说的背景,是因为鸦片战争代表着东方文明的一个“轴心时代”,意味着边界的打破、非自主选择的激烈对抗和变革,因此,这个故事的核心意义在于异质文明的冲突。文化的首次冲突是通过酒的意象来诠释的。主人公心目中的饮酒文化是“像李白一样举杯邀明月,沉浸在静思和无言的喜悦当中”,但这一观念受到英国烈酒的冲击,这种“盛在大杯子里的朗姆酒很烈”,“把杯子端到嘴边时,我闻到一股强烈的未知的气息,从第一口开始,我就喉咙发紧,流出了眼泪”。古诗词的意境与烈酒未知的气息构成鲜明对立,前者象征着一个精神深邃、沉浸在催眠的梦境和往昔荣华中的封闭世界,后者则象征着未知的恐惧和现代性的攻击。
小说以文化冲突和解体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在迷惘和自省中徘徊的“东方英雄”。小说副标题为“鸦片战争灾难札记,儒生李文华编”(Записки о бедствиях Опиумной войны,составленные Ли Вэньхуа,конфуцианцем),假借翻译文稿的形式,为文本虚构了一个“真实”的起源,在文体上显然借鉴了西方传奇故事,并与清代散文的第一人称叙事有机融合。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中,第一人称叙事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时代变迁和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进程十分缓慢。作者指出,他想从一个中国青年的视角审视这段戏剧性的历史,特别是展现他的内在认知,反思东方古老生活方式中的爱欲、家族关系;通过碎片化的史料文献与东方文人个体经验的融合,以俄语为媒介,复活中国古典文学的修辞、格调和文化记忆。主人公李文华是宁波一个七品官员之子,“文华”意为“饱读诗书”,寄托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准则和精神取向,因此他的讲述很少关注生活细节和家庭日常:“让我和同伴感到亲近的不是游戏和童年的恶作剧,而是对导师真挚而深刻的崇敬以及对智慧的渴望。我们夜以继日地阅读古代先贤的作品,纸是耕地,笔是犁铧,夏聚流萤冬映雪。”主人公的个性觉醒通过《山海经》《列子周穆王》《道德经》等文本呈现出来,并逐渐汇入残酷的历史灾难当中,通过南柯一梦的故事暗示了东方理想的危机。尼科诺娃认为,叙述人的特殊身份使这篇小说的讲述不同于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等作品中对鸦片战争的书写。《少不入广》通过主人公的先贤崇拜,为这段历史设置了一个多义性的东方智识框架,用主人公的话来说,点燃了一盏“长明灯”,在它的照耀下,东方社会和家族面对现代性冲击,呈现出绵延的整体性。
因此,这篇小说书写的并不是“长明灯”的熄灭过程,而是时代之子面临文明崩溃不断反思、探寻的过程,亦即“东方英雄”艰难缓慢的成长历程。利特温采夫采用小人物大历史的情节架构,让主人公的精神转变与鸦片战争的历史转折有机契合。例如,主人公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意外得知鸦片运输路线,决定面见林则徐,“我觉得我的时间到了,我明白自己应当做什么,尽管我在这座城市是个外来者,除了头脑一无所有,但如果能够勇敢坚韧,就可以做些什么”。第二天“我穿上崭新的天青色长袍,戴上一顶朴素的游子帽,向城市中心出发”。主人公认识世界的语言媒介也随之多元化,在林则徐销烟和《四洲志》的编写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翻译角色。而主人公英雄理想的破灭与林则徐的流放并行发生,这期间,主人公再度陷入精神危机,由文化翻译转向文化失语:“我在广州游荡了大约一年,但情况很糟,我看不清那段时间,不想回忆自己是怎么度过的。那时候我仿佛看到这座城市的大火和许多人的死亡,超越了可见的生命界限,进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被腐朽和寒冷所笼罩,像一个影子一样行走,很少思考,什么也不渴望。”通过这样的叙事节奏,作者发现,几千年来,民族性格的变化、个体精神成长与叙事方式的变化一样艰难缓慢,这似乎构成了一种东方特质,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更有助于反思俄罗斯自身的文化问题和精神困境。
尼科诺娃曾对《少不入广》做出这样的评论:“我们已经熟悉的是20 世纪俄侨家族的‘奥德赛’故事,而19 世纪的鸦片战争与作者的侨民经历并不相干,它的出现是由今天的主题和难题所决定的。”作为“回归者”一代,利特温采夫始终关心俄罗斯往何处去的问题,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的走势。在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取代苏联解体时弥漫于俄罗斯社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要重新寻找俄罗斯思想,尤其强调弥赛亚主义和个体情感的道德意蕴和创造性。这一“文化转向”可用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来解释。自由主义始终存在“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洛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它建立在自由与规则、制度的辩证关系之上;另一面则是“生命与自由”价值观及其暴力实现方式,亦即在极端情形下,对生命和自由的追求需要暴力、流血和牺牲。而更多时候,历史证实了经济自由主义与暴力的兼容性,尤其是在西方,硬币两面的冲突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加速了西方的变形。因此,俄罗斯社会逐渐转向自身,寻找与西方不同的世界观传统。
在这个问题上,利特温采夫是“转向东方”一派的支持者,他认为,尽管对于俄罗斯而言,中国是一个形而上的谜,一个由刻板印象组成的幻象,但中国向来不会强行输出自以为正确的文化装置或精神毒品;东方文化不可能在岛屿上躲避欧洲的强制整合,总是被迫与之发生冲突,甚至不是为了保持文化身份,而是保持“人”的身份。而20 世纪90 年代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弥散于俄罗斯各个领域,其直接后果恰恰是人的迷失。对此,越来越多的俄国知识分子诉诸哲学和宗教传统,尝试在公共意识中重建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多向度的关联,尤其是传统、民族和个体认同之间的关联,塑造理想化的个体形象。例如索洛维约夫哲学中的“道德行为力人格”(личность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действующей силы),这对应着儒家哲学中的“君子”。
利特温采夫对鸦片战争的描写正是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冲突和西方中心主义解体过程的映射。利特温采夫在作品中提到鸦片战争的恶果,其一是《南京条约》的签订,它代表了西方殖民的新模式;其二是和约签订后大量鸦片的涌入及其造成的社会堕落、死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现代性恶果对人自然天性的毁灭。例如,在林则徐与英方谈判的过程中,主人公见证了一场关于“世界法则”的辩论。英方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与先进文明完全匹配的文化输出:“某种商品如果有需求,那么世界上的任何边界、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有需求就会有供应,这是世界法则。”林则徐从自然与人性出发,予以反驳:“你所说的需求是否包含在人的本质当中?或者它蕴含在自然之中?或者蒙受天福?不,任何活的生物,任何未被损害的人都厌恶有毒的烟雾。……也就是说,这种需求是通过欺骗和胁迫人为灌输的,违背纯粹的本性。”
此外,作者借林则徐之口指出:“这次持剑犯我国门的是一个未知的敌人,不懂宇宙的法则,不懂共同的语言,因此无比危险。”由此可知,利特温采夫思考的最主要问题不是东西方冲突是否可以避免,而是文化优先性以及文化互渗的可能性问题;他渴望寻找一个能够克服未知的敌意、具有包容性的法则和共同语言。利特温采夫认为,英国对中国南方的入侵不能用东方文明的“落后”来解释,恰恰相反,自给自足的东方文明是在暴力冲击之后才陷入长期停滞的。他的结论与罗伯特·赫德的观点不谋而合。赫德从西方优越性的成见出发,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社会不需要西欧的精神价值和技术成就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它只是在用另一种文化价值来进行自我衡量。在利特温采夫笔下,这场历史冲突处处充满了类似的“惊讶”,冲突双方不断发现对方的“他者性”。譬如,小说中的英国人查理认为,“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我们仍将彼此视为野蛮人”;中国知识分子也对西方人发起同样的质疑:“蛮族缺少什么——智力、教育还是教养?”
“我”和“非我”的对抗是利特温采夫所遵循的主要历史逻辑,作品中随处可见“他者即仇敌”的诠释。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当代俄罗斯社会学中出现的一个新词——“消极身份”,这种身份认同建立在“自我-他者”“我-非我”绝对的二分法基础上,而非共同的信仰、观念之上,往往出现在社会动荡的语境下,是生活方式解体、道德失范的表征。利特温采夫同样发现了这一趋势,对他者的古老恐惧在当代俄罗斯公共意识中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公众恐惧非我、走向封闭的同时,也依赖非我获得身份认同;这是社会对变化的自发反应,如今正逐渐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要行为策略,因此,非我形象是当代大众理解社会现实的主要工具,也隐含着应对危机的出路。《少不入广》为非我隐喻提供了可依托的形象体系和戏剧化的历史场景,探讨在个体与国家、传统发生断裂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如何述说文化走向真空的过程并重新进行身份的自我辨识,尤其是被迫向“消极身份”转变。
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最终章对乍浦战役的书写:“我跑到甲板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整个战场上都是来自天朝帝国的队伍,从他们的外表和庄严的音乐来判断,手拿长矛和梭镖的战士不是在准备一场战斗,而是在准备一场表演,要么震慑敌人,要么使对方趋向和平。一些人穿着精美的镇江彩绸长袍,游行,转身,塑造复杂而有节奏的形象。另一些人则用古老的武术倾泻出沸腾的力量和愤怒——他们挥舞着剑,大声呐喊示威,旋转跳跃,朝我们的方向进行威胁攻击。持盾牌的展示了高超的剑术,将彩绘的盾牌露出并举起,摆出梅花落的仪式。”而英国人用自己的现代文化逻辑做出回应,“英国士兵只知道两三种最简单的刺刀作战技术,但他们以严密的队形行进,机械得像发条一样射击和刺杀”。尼科洛娃认为,经过这一幕,“人在文化中实现自我”的古老真理得到了视觉化的强调。在这段场景中,中国抗击侵略的战斗被诠释成东方理想的精神仪式,一场悲壮的文化展演与温和的劝服,使主人公发起这样的思考:“胜利和失败有什么不同呢?”
由此可知,尽管《少不入广》书写了国家主权的丧失和传统文化的解体,与当代回归者俄侨作家的失乐园主题有诸多契合之处,但利特温采夫始终站在文明瓦解、理想崩塌的角度来思考历史问题,小说的时间指向当代和未来,借一个中国文人形象,向整个现代文明和文化战争发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