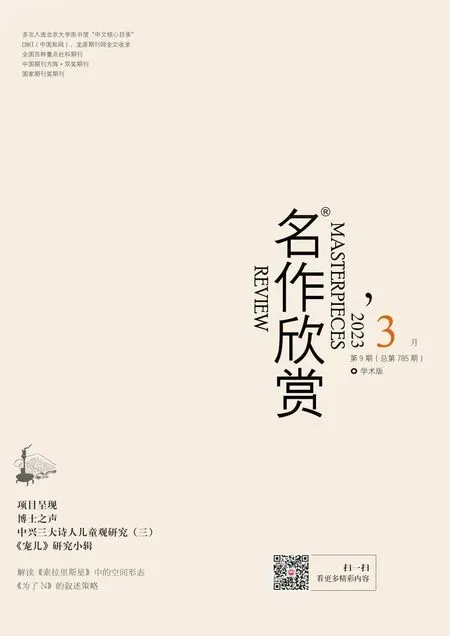一个关于生和死的故事
——川端康成《秋雨》解读
⊙梁艺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1800]
作为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其文梦幻朦胧、心象纷呈,本文以《秋雨》为例,借助“火影——山茶花——秋雨”这一意象结构,将其独特的人生观借极具象征性的语言表现出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
一、抗争下的悲剧命运——渺小而倔强的火团幻影
在搭乘快速列车途经红叶山的川端康成心中,主人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幻影——“天空还是一片蔚蓝,却已微微现出了暮色……红叶的寂静,从高处笼罩着我,渗透我的身心。莫非要让我早早地感受到日暮之将至?”不难发现,这片暮色可能是亲眼所见,但更可能是众多凋零的红叶从天而降,使得衰飒哀戚的红棕色自上而下地感染人的心境。这一切可能是暮色,但更可能是红叶的幻影。而凋零的秋叶也在意义上成为暮色的象征物,是一切即将衰败的代表。
而在这样悲哀的情境下,在漫天凋零的生命中,作家又看到一群闪闪烁烁的火团,毋庸怀疑,这更是幻象,“我的眼睛深处,映出火团降落在红叶山上的幻影”,这“仿佛不是在降落火雨或火粉,只是小小的火团在溪面上闪闪烁烁”。同样,这些火影也是红叶的幻影,是红枫叶快速闪动后在作家眼中弥留时残留下来的幻影,造就了这火团的模样。他们是极悲哀的,降落时太过渺小,连痕迹都不被人发现,结束时也杳无踪迹——“那小团的火球落在蓝色的溪面上旋即就消失了”。但也有过刹那光华,以幻想的形式出现的火苗,也会在溪面上绽放出微弱的火光,它们正恰似一个个即将凋零的生命倔强地发出濒死前片刻的光芒,终于在狭窄的天际间“流淌出了一条火河”,一条被无数卑微的悲剧拼尽全力绽放光芒所攒成的河,即使最终以死亡为代价,以湮灭不闻为最终归宿。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幻影。但为何明明火车只经过漫山遍野的红枫叶,在“我”眼里却平白生出衰凄的暮色和渺小而倔强的小火球的幻象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川端康成的重要身份——日本新感觉派的探索者。新感觉派在文学观念上,以主观为锚,以感觉为线;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自由联想,使用“心象的罗列”,萦绕着一种朦胧缥缈、难以捉摸的气息。所以川端康成多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将人物的意识流动展现出来,更将人物心灵与客观外界的交流互动呈现出来,而《秋雨》正是将个体潜意识泄露出来,将“火影”和“暮色”的幻象呈现出来。但《秋雨》在半梦半醒之间潜意识的泄露绝不是毫无依据的,而是一种真实情感的表达,是在现实中偶有所感才生发出的想象。那这如“小火球”般渺小而不屈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吗?结果又究竟如何呢?后文随即就从幻象引入现实世界,揭开幻影生成的原因。
二、相似命运的串联者——过去飘落的山茶花
在十五六年前的“我”做手术的医院里,先天心脏病的孩子们很多,孩子们总在东奔西跑、嬉戏喧闹,仿佛病症是虚假的想象,但现实总有噩耗来临——一个生来就没有胆液输送管的女孩子,那个穿山茶花和服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姑娘,在手术后静静地入梦了。
她身上穿着的山茶花是很特别的,在日本文化里,意蕴特别丰富。“山茶花,在古代日语里,经常被写作‘椿’。‘椿’就是山茶花,‘椿’正如其字形所示是春之木,乃宣告春天来临之木。在大地万物归于沉寂的冬季,傲然开放的山茶象征着春天的新生活力,将带来春天的气息。”①据方爱萍在《论日本的山茶花文化及审美意识》一文中所说,山茶花凋落的姿态,并非落英缤纷、铺满一地,而是毅然决然坠落枝下,毫无贪生之念,这又正象征着日本人一种豁达无畏的生死观。而综合来看,一个悲哀美学盛行的国度,一个以“死亡作为最高的艺术”并当作“绝美的意境”来描绘的作者,面对美妙却衰败的山茶花,面对“即便鲜活如此,也要死去的‘死亡之美’”,是多么的欣赏和偏爱。但在《秋雨》中,山茶花的内涵绝不仅是这样,小姑娘穿着山茶花的和服离去了,但是多年后的顽强不屈的律子却依旧穿上了。我想这绝不是暗示律子的死亡,而是生命的延续和继承,律子以昂扬不屈的神色穿上和服,就像穿上一种“新生的意味,一种面对与抗争死亡的勇气”。
因为律子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脆弱不堪却奋起挣扎,最终才得以摆脱痛苦命运不断生存下来的姑娘。正如上文那个离去的小姑娘一样,生命就是这般无常而虚无,转瞬就可以消失。这样的悲哀是普遍存在的,正如蜿蜒在峡谷的火河,微小而悲剧的生命体数不胜数。每一个患先天心脏病的孩童,正如那一株株小小的火球,随时都可能消逝,随时都要在薄薄的暮霭中被“蓝色的水面”吞噬。但是这位女孩子,倔强不屈的脸庞,和着迸发着强烈光芒的双眸,默默抗争着命运,仍然存活的现实证明了她迸发着的顽强的生命力。律子作为一个异质化的存在,在摇摇欲坠的生活面前,摆脱了只能在临行前迸发光芒的命运,最终竟真的争得一线生机。在听闻小姑娘手术死去后,律子就展现出一股执拗的态度,“不愿做手术,要回家,不愿做手术,要回家。谁劝说她都不听”,这种态度不是律子的胆怯与逃避,而是她面对不幸命运时的坚决抗争和求生的决心。所以幻影中的暮色和小火球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了,正是“我”前往京都去探望这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体,所以眼前才不由自主地营造出暮色中苦苦挣扎而不得的小火苗,才幻想出渺小却不屈服的重重幻象。而在山茶花的串联下,抗争性更强的物象“秋雨”随机接替幻象“团火”再次出现。这种物象与幻象、眼前之景与意识之流交织的笔法,正是新感觉派表现力的重要来源。
三、生命的交响乐——激荡的秋雨物象
在幻想与往日回忆的交织中,“我”徘徊沉浸于朦胧的梦境,忽然,“雨敲打在客车车窗上的声音,把我惊醒了”,幻影随即消失了,一片风雨交加的秋雨把“我”的心绪引向新的思考。
单看这一场敲击车窗的秋雨,不难发现所有的雨点都有着相似的命运安排——雨点被命运裹挟着,一次又一次地敲击着车窗,所有的“打在窗玻璃上的雨点”,都“一滴滴地顺着窗玻璃斜斜地流落下来”,恰如生老病死般,是人的宿命,无法抗拒,难以挣脱。但细看来,有的雨点总是“流着流着,短暂停住,接着又流动起来。流流停停,停停流流,显得很有节奏”,它在流动与停息间交替,正像极了生命的进程,时而得意快走,时而失意停滞。而有的雨点们“后面的赶超前面的,上面的低低地落到下面,画出一道道交错的线”,也像极了人世间起起伏伏的浮生百相。在短暂的停滞与长久的流动中,在交错的线条与流动的节奏中,秋雨在视听上共同奏响生命的乐章。
而秋雨和前文幻象中的团火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幻象与现实的交叉口,“我觉得火降在红叶尽染的山上的幻影,是静谧无声的。然而,敲打在车窗玻璃上流动着的一滴滴雨点的音乐,却又变成了那降火的幻影”,可见二者实际是相互交融的一物。将秋雨和团火比照来看,如果说团火的幻影是生命力的赞歌,那眼前秋雨叮当作响的姿态便是生命力的交响。他们共同为压抑痛苦的命运所笼罩,小火球周遭是压抑凄清的暮色和随时吞噬火焰的冰蓝水面;而秋雨中交杂的是乒乓作响的狂风和命运的枷锁一般的“车窗”,生命周围总是困苦而绝望的。
而“小火球”与“秋雨滴”又一同构成微弱生命的象征。他们以极为对立的身份——现实与虚构、有声与无声、冰蓝与火红、冰冷与炽热,共同肩负起渺小生命力的顽强抗争。而相悖的含义系于一体构成极大的张力,以火团的绚烂易逝与秋雨的凄冷顽强,暗示着当年正处在童稚时光,却又身患疾病的律子,也暗示着每一个本该光芒万丈的时光里备受折磨,却苦苦支撑的人们。
但秋雨又是不同的,它有着更顽强的韵味。作为生命的交响乐,它是有声的,它更是抗争的,她为不屈的生命而高唱,它为不屈的命运而击打着车窗,而并非如“小火球”一般转瞬便被吞没在水面。那二者的转变点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律子顽强地活着,律子以“不和悦”的眼眸射出“强烈的光芒”,她为生存大胆放弃手术,这种种的一切,都使得她的命运不再像火苗般无声无息地消逝,而是像秋雨一般,摆脱转瞬消逝的命运,击打出命运的破阵曲。同时,这场秋雨也接续起当下律子的心境——“翌日,依然秋雨绵绵……原来律子正用不和悦的目光,凝望着站在被秋雨打得朦朦胧胧的玻璃窗前拍纪念照的新郎新娘。”摆脱当年生存的困境,现在的律子依旧保持着“不和悦的目光”,依然对生活报以抗争的态度,以倔强和不屈服面对着种种不幸。可以说律子的命运自少时便呈现出一以贯之的特色——痛苦与抗争交织而生,但又时刻反抗着,挣扎着摆脱火苗的命运,表现出与天意抗争到底的态度,这种独特的生死观在川端康成的笔下是极为少见的。
四、独特的生死观——异类的《秋雨》
在文学创作技法上,川端康成作为日本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摆脱了西式现代派晦涩难懂的时空错杂的意识流技巧,而将意识流与日本传统文学相结合——借助自然物象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又将自身与自然合一,进而将人物感情世界寄托于自然之上,将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紧密融合。
《秋雨》延续“火影——山茶花——秋雨”这一思维脉络,将流动的思绪展现出来,既表现了人物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又使小说结构工整,毫无时空错乱之感。同时,川端康成更明晰地表达出内心世界对于外界万物的感动,用极具象征的语言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用“火影”与“秋雨”共同展现渺小而抗争的生命体,再以“山茶花”这一绚丽而脆弱的意象进行串联,将真正意义上摆脱不幸命运的“秋雨”承接出来,构思精巧,以景物式的象征传递出作者对于人事无常、生命璀璨的理解,极具新感觉派的美学韵味。
在文本美学思维上,川端康成没有陷入“二战”之后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崩塌的狂潮,而是借助古老的东方禅宗文化对人类心灵进行叩问,表现为一种人生无常、命运难以把握的感伤与无奈,是一种东方式的禅宗的传承,但《秋雨》的价值观并不止于此。
作为“物哀美学”的继承者,“虚无与无常”的美学思想贯穿川端康成创作的始终。②同时作者在童年时期多次目睹亲人离世,甚至被称为“葬礼上的名人”,题材上也格外倾向于虚无与死亡,在作品中往往展现出“死生循环”“将死亡变形成一种美的化身”,甚至是一份“最高的艺术”的特征。如此看来,一种悲观式的死亡在川端康成的作品里出现仿佛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不妨回到物哀美本身去看《秋雨》的生死观。“物哀”就是日本民族对自然风物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同形关系、感应关系的一种审美概括。③“物”就是自然风景、自然风物;“哀”则指由自然景物诱发,或因长期审美积淀而凝结在自然景物中的人的情思。“确切来说,是多半倾向于感伤、孤寂、空漠而又有所希冀的一种朦胧的情感、意趣和心绪。”④所以这份“哀”并非中国式的悲哀与凄惨,而更多是由心底生发出的一份哀怜、一份凄美和一份朦胧的希望。继承物哀美的精神传统,《秋雨》一文不仅将众多渺小脆弱的生命体普遍性的悲剧展现出来,一种无法与命运抗衡的世事无常的宿命感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将一个即将陨落的生命因抗争而迸发出奇迹的光芒的故事讲述出来,将生命生生不息、挣扎中存活下来的温情呈现出来。《秋雨》在生死面前,不像《雪国》中叶子的死,被认为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是“内在生命在变形,在转变成另一种东西”;更不是《千只鹤》中太田夫人死后,菊治和文子都认为她变得更美,真正成为“美的化身”;而是对面对死亡始终“绷着脸”“不和悦的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的律子时赤诚地赞扬她“这孩子很有出息”。这份对年轻生命陨落的悲伤和顽强生命力的赞美敬畏互相交融,共同组成日本“物哀美学”的传承与新变。所以我想《秋雨》是川端康成作品家族中的一篇异类,但也许更是“物哀美学”的传承。
五、结语
《秋雨》借助“火影——山茶花——秋雨”这一结构,将心灵幻象与自然物象结合起来,将过往经历与当下现实融合起来,用极具象征性的语言表现出自然界的生命和人的宿命——用“火影”与“秋雨”共同展现渺小而抗争的生命体,再以“山茶花”这一绚丽而脆弱的意象进行串联,将真正意义上摆脱不幸命运的“秋雨”承接出来,体现出对脆弱的生命只能在濒死前以凄美的姿态绽放光芒这一行为的感伤与赞颂,更表现出对渺小而虚幻的生命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这一行为的感动与敬畏,非常有代表性地展示出川端康成新感觉派和日本物哀美学的双重文学身份。
①方爱萍:《论日本的山茶花文化及审美意识》,《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②④ 吴舜立:《自然审美: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吴梅芳:《论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意象》,《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