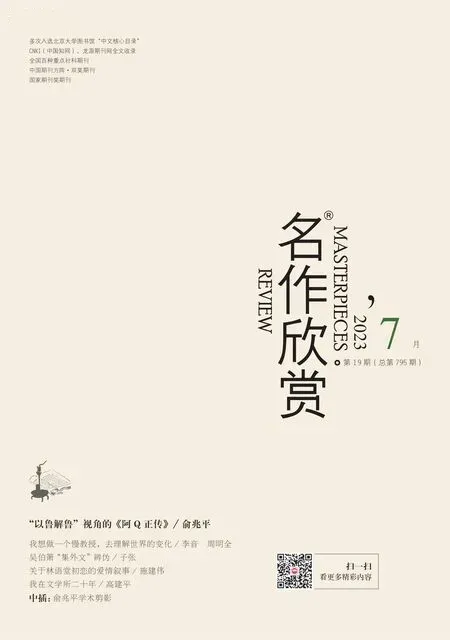吴伯箫“集外文”辨伪
浙江 子张
一
吴伯箫散文,在作者生前编集正式出版的有《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和《忘年》七个集子。其中《烟尘集》实际上是一部自选集,前后共出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三个集子的选集另加一篇《记乱离》,第二个版本增补了《出发集》的选篇。1982 年出版的《忘年》集补入了20 世纪30 年代和40年代的旧作八篇。吴伯箫去世后,其后人与相关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两卷本《吴伯箫文集》,除按出版先后为序收入上述散文集的全部作品外,又在每个集子后面追加“集外”作品,还收入了吴伯箫唯一一部译诗集《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将吴伯箫早年编订的第一部散文集《街头夜》重新做了集拢并收入了文集。
文集不是全集,即便是全集也未必没有遗漏,绝对的“全集”几乎是没有的。对照两卷本《吴伯箫文集》目录和作者生前所述,至少有一篇《山桃花》仍未收入文集。
在1978 年撰写的一篇自述中,吴伯箫谈到这篇《山桃花》:“……这前后写了《向海洋》《书》《忘我的境界》等几篇散文,也写了暴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后四篇集印时都不收入。”①
原来不收入集子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属于“暴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但三四年之后,《忘年》集出版时,《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说日常生活》已赫然在焉,而独独没有《山桃花》,甚至到1993 年两卷本文集出版,连30 年代为《羽书》集漏收的《天冬草》都以“集外”形式收入了,而《山桃花》仍然缺失,原因何在呢?
对吴伯箫集外文的追索,最早就是由对这篇《山桃花》所抱的神秘感开始的。但直到21 世纪初年,才在北大图书馆找到延安《解放日报》影印本,搜索到该报署名“吴伯箫”“山屋”的创作和译文,其中有散文《山谷里的桃花》一篇,而并没有《山桃花》,根据其发表的时间背景以及与《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说日常生活》诸篇的关系,可以断定吴伯箫所说的《山桃花》就是这篇《山谷里的桃花》,时日久了作者记不准确也是正常的。
近年为了编撰吴伯箫年谱,在检索相关民国报刊文献的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不少署名“吴伯箫”或“吴伯萧”的各类作品,既有散文,也有小说和学术性论文。但是,惊喜过后,经过一番仔细甄别、辨析,即发现这些作品、文章尽管均置于“吴伯箫”或“吴伯萧”名下,实际情况却是有真有假,而且假的居多。本文拟围绕这些署名“吴伯箫”或“吴伯萧”的各类作品尝试进行甄别,以见出哪些是真品,哪些属于冒名之作。
二
兹将近年自民国时期旧报刊上搜罗到的署名“吴伯箫”“伯箫”“山屋”或“吴伯萧”的各类作品罗列出来并试做一番真假判断。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吴伯箫”与“吴伯萧”并称于此,缘于一个由来已久的错误,即“吴伯箫”本名在作品发表或出版过程中,常常被责任编辑误署为“吴伯萧”,特别是作为吴伯箫第一本得以正式出版的散文集《羽书》1941 年问世时,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恰恰就是“吴伯萧”。这么一来,一方面“吴伯萧”几乎就成了吴伯箫的另一个笔名,另一方面后来也就成为冒名者盗用的一个名号。在冒名者眼里,得之于《羽书》封面上的“吴伯萧”反而正是其要冒充的真作者。此种误会,当然会使人产生无可奈何之感,但既然要辨识真假吴伯箫,就理所当然需要将署名“吴伯萧”的篇目纳入。
已发现的1949 年前“集外文”篇目如下:
1.《说踽踽独行》,散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青岛《青岛时报》副刊“明天”1934 年12 月18 日第11 版。
2.《牢骚语》,散文,署名伯箫,刊载于北平《鞭策周刊》杂志1934 年第1 卷第17 期。
3.《绿的青岛》,散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济南《青年文化》杂志1936 年第3 卷第3 期。
4.《致萧乾》,书信,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作家行踪》专栏第438 期,1938 年11 月11 日。
5.《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通讯,署名吴伯箫、卞之琳,刊载于延安《文艺战线》杂志第1 卷第4 期,1939 年9 月16 日出版;此文另刊载于延安《文艺突击》杂志新1 卷第2 期,1939年6 月25 日出版,署名卞之琳、吴伯箫。
6.《展开战地的文艺工作》,通讯,署名吴伯箫、卞之琳,刊载于浙江温州《游击》1940 年第3 卷第4 期,第1—3 页。
7.《青菜贩子》,抗战故事,署名吴伯箫,刊载于延安《大众文艺》第1 卷第6 期,1940 年9 月15 日。
8.《山谷里的桃花》,散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延安《解放日报》副刊1942 年4 月27 日第四版。
9.《新型音乐的体认》,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济南《大风》杂志1942 年第17 期。
10.《伟大的子产》(上),教育小说,署名吴伯萧,刊载于南京《教育建设》1942 年第1—2 期。《伟大的子产》(下),教育小说,署名吴伯萧,刊载于南京《教育建设》1942 年第5 卷第3 期。
11.《关于我国票据法之商榷》,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中国经济评论》1942年第6卷第2期。
12.《察哈尔农业调查》(附表格),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中国经济评论》1943 年第7 卷第1 期。
13.《漫谈华盛顿·欧文》,随笔,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小说月报》杂志1943 年11 月15 日,11 月号第38 期。
14.《顔李之学》,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经纶月刊》1943 年第4 卷第1—2 期,第133—136 页。
15.《齐城漫考》,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经纶月刊》1943 年第4 卷第1—2 期,第137—142 页。
16.《漫谈“大观园”》,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万象》1943 年第3 卷第5 期。
17.《漫谈〈离婚〉》,论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万象》1944 年第3 卷第7 期。
18.《热肠篇》,散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万象》1944 年第3 卷第9 期。
19.《漫谈史剧》,论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万象》1944 年第4 卷第6 期。
20.《云南的下层》,报告文学,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1 卷第1 期(创刊号)头条,1944 年1 月1 日出版。
21.《红嘴乌鸦》,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1 卷第2 期(2—3 月号),1944 年3 月出版。
22.《疯》,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1 卷第3 期,1944 年5 月出版。
23.《狼狗》,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2 卷第1 期(革新号),1945 年3 月出版。
24.《蝙蝠》,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副刊》1944 年第3 期。
25.《荒》,小说,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风雨谈》第9期头条,1944年1月、2月合刊,春季特大号。
26.《下乡》,小说,目录署名吴伯箫,文内署名吴箫伯,刊载于上海《风雨谈》第16 期,1944 年12月、1945 年1 月合刊,小说狂大号。
27.《热肠语》,署名吴伯箫,刊载于北平《吾友》杂志1945 年第5 卷第9 期。
28.《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步:社会的研究》,论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前锋》杂志1945 年第1卷第1 期。
29.《赵尚志同志》,人物传记,其“传略”部分作者白和,“轶事”部分标明:李延禄讲,山屋整理,刊载于《东北文化》第1 卷第1 期(创刊号),1946年10 月10 日出版。
先后看到如此多的集外文,特别是还有那么多的小说、论文,的确有些莫名的兴奋感,所谓莫名,其实也就是某种潜意识的期待心理,即希望它们是真品。对一个已然基本完成的作家形象而言,突然增加出数十篇风貌不同于既往的作品来,意味着什么,当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经过最初的那种兴奋,当沉静下来仔细阅读这些时间跨度颇大、文体不一、发表地区也很不同的文本时,疑问就慢慢产生了。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1938 年的战时背景下,吴伯箫经过带学生流亡、遣散学生、只身投军的短暂过渡期之后,最终去了政治色彩截然不同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延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那么,上述发表于战争期间的上海、北平、济南、南京等地报刊上的“吴伯箫”作品,会是身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的投稿吗?
其次,文体的差异。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所用文学体裁的疑问,虽说吴伯箫早期尝试过小说的写作,也试图将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融入散文写作中,但如发表于上海《文潮》和北平《风雨谈》上的诸多小说作品,其内容与吴伯箫侧重的题材差异甚大,两相比较就能感觉到绝非同一作者所写;二是文体风格方面的疑问,吴伯箫是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作家,其散文写作的个人风格很容易识别,而这些小说以及另外发表于《万象》《经纶月刊》上的学术性文章的写法,与吴伯箫那种鲜明的文体风格同样存在很大差异。
最后,上述发表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小说、论文,往往在文字末尾有一个“历下(或济南)讝顔斋”的落款,如果知道吴伯箫已经身在延安的事实,再看这个落款必会产生更大的怀疑,何况吴伯箫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与其品性毫不相符的书斋名。
故而,综合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角度检测这些不同体裁的“吴伯箫”名下的作品,基本的真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为什么最大的疑问是身在延安的吴伯箫不可能向沦陷区或国统区的报刊投稿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令吴伯箫深铭于心的不愉快回忆,即散文集《羽书》稿酬被冒名者冒领一事,这件事又会牵出另一些与冒名有关的事——不只吴伯箫散文在沦陷区遭到剽窃,还有公然冒充吴伯箫的人以吴伯箫的名义在沦陷区接待慕名而来的访问者。
本来《羽书》在上海出版时,人在延安的吴伯箫并不知情,更不可能收到来自上海文生社的样书与稿酬。但在1949 年7 月北平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负责出版《羽书》的巴金却告诉吴伯箫不但有稿酬,而且还应济南“吴伯箫”的要求寄了第二次。实则这位济南的“吴伯箫”是一位名叫吴丁夫或吴鼎甫的不知名文人,就是他在1942 年10 月因剽窃《羽书》集内《灯笼》一文发表于北平《吾友》杂志而遭到读者举报,也是他顶着“吴伯箫”之名在济南接受过一位叫张金寿的文人的访问,关于这两件事可参阅笔者相关文章②,此处不赘。
现在提这件事,则是因为在前述吴伯箫“佚文中”恰恰有多篇与这位济南冒名的“吴伯箫”有关,有些文章是剽窃加改头换面,有些文章是冒名之作。而判断的依据就是前面说的三条:或者文章出现在沦陷区、国统区的报刊上;或者存在较大的文体差异;或者于文末落款“历下(或济南)讝諺斋”。
依据这三条,笔者认为前述二十九种“佚文”为剽窃加改头换面和冒名之作的分别有第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篇,29 篇中有20 篇属于伪作,只有9 篇才是吴伯箫本人或吴伯箫与他人合作的篇目。
三
20 篇伪作,情况多有不同。先说发表地区及其政治背景,总共有17 篇作品分别发表于上海七家杂志,其中《中国经济评论》上的两篇都是专业性很强的经济类论文,《小说月报》上1 篇介绍欧文·华盛顿的随笔,《经纶月刊》上2 篇文史类论文,《万象》上4 篇文史类论文,《文潮》和《文潮副刊》上共1篇报告文学、4 篇小说,《风雨谈》上2 篇小说,《前锋》上1 篇社会政治论文。另外3 篇作品分别为论文、小说、散文,也分别发表于济南、南京、北平的刊物上。而20 篇作品的发表时间均在1942—1945 年间,其中1943、1944 年最集中,1943 年5 篇,1944 年9篇,而这几年吴伯箫并没有离开延安一步。更重要的是,从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特别是经历了1943 年边区教育厅“审干”、西安国民党“追悼”活人事件之后,吴伯箫不只在思想认识和写作倾向上有了根本性改变,个人精神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在如此严酷的背景下,吴伯箫怎么可能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向上海、南京、济南、北平的杂志投稿呢?在吴伯箫晚年,当谈及1943 年《羽书》中的作品在沦陷区被人剽窃的事情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再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在敌伪侵占北平的时候,在北平的文艺刊物上用我的名字发表收入《羽书》的文章,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这种怪事是解放以后才听说的,听了令人哭笑不得……”③看来,《羽书》被剽窃的事吴伯箫是后来才知道的,至于上海、南京、济南的刊物上这些冒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文章他是否知道,吴伯箫没说。
20 篇伪作中的专业性论文和小说、报告文学,因为与吴伯箫喜欢的体裁、题材、文体风格差异太大,也很容易断定不是吴的作品,拿最接近的报告文学《云南的下层》来说,如果所写不是云南,而是吴伯箫去过的任何地方,尚有某种可能,但吴伯箫那时候并未去过云南,即使是听别人说也不会记载得那么详细,更何况篇末还有一个“北雁南飞·于讝諺斋”的落款呢。
还有两篇标题、内容都极接近而实为同一作者所写的《热肠篇》和《热肠语》,一个发表于上海《万象》杂志1944 年3 卷9 期,署名吴伯萧;另一个则发表于北平《吾友》杂志1945 年5 卷9 期,署名吴伯箫,发表在《吾友》上的《热肠语》甚至还配发了作者照片,标明“吴伯箫近影”,但没有照片还好,有了这张照片反而更见出此“吴伯箫”绝非彼吴伯箫,而是不折不扣的冒牌了,因为“近影”根本不是吴伯箫的,而是一个着长衫、戴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由发表此文的《吾友》的杂志,倒一下子提醒笔者,这个冒牌的“吴伯箫”极有可能就是剽窃《灯笼》的那位吴鼎甫!再对照《吾友》读者来信和编辑部启事,就更是百分之百确认了。编辑启事《一年来的抄袭》云:“吴君寄本社之稿除已刊之《灯笼篇》外,尚有《黄雾之花》一篇未刊,所用稿纸印有‘丁夫自用原稿纸’字样,题上用有‘丁夫’二字之小章,署名下有‘吴鼎甫’之方印,文末又有‘吴伯萧’之方印。”④
也就是说,这个济南的冒牌吴伯箫同时有三个名字:吴鼎甫、吴丁夫、吴伯萧,如果加上1944 年发表《热肠语》用的“吴伯箫”,就是四个名字了。至此也就大致能够断定,凡以这四个名字在沦陷了的上海、北京、济南、南京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亦即济南的吴丁夫或吴鼎甫,包括张金寿《北行杂记》中写到的那个“吴伯箫”也应该是这个人。
20 篇伪作中,文末标注“历下(或济南)讝顔斋”者,有《伟大的子产》《齐城漫考》《顔李之学》《漫谈“大观园”》《漫谈〈离婚〉》《漫谈史剧》《察哈尔农业调查》《热肠篇》《云南的下层》《红嘴乌鸦》《荒》《下乡》12 篇,未标注者有《新型音乐的体认》《关于我国票据法之商榷》《漫谈华盛顿·欧文》《蝙蝠》《狼狗》《热肠篇》《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步:社会的研究》7 篇。未标注“讝顔斋”有没有可能会是另一位吴伯箫或吴伯萧呢?我的看法是至少《新型音乐的体认》《漫谈华盛顿·欧文》《蝙蝠》《狼狗》《热肠篇》5 篇不会,因为《热肠篇》与《热肠语》实际是1 篇,《蝙蝠》《狼狗》与以吴丁夫名字发表于《文潮》上的小说《探监》《生路》风格相同,《新型音乐的体认》《漫谈华盛顿·欧文》与落款“讝顔斋”的文史随笔写法也很接近。即使专业性甚强的另外2 篇,笔者的判断是同为此人所写,理由是《关于我国票据法之商榷》与《察哈尔农业调查》均发表于同一杂志,署名相同,且《察哈尔农业调查》文末注明“卅一·九·初·于济南讝顔斋”。
四
抛去20 篇伪作,另外9 篇署名吴伯箫或伯箫的文章,乃是真正的吴伯箫集外文了。依据是:
《说踽踽独行》《牢骚语》《绿的青岛》三篇分别发表于抗战爆发前的青岛、北平、济南的报刊上,这与吴伯箫彼时散文创作、发表高峰期的总体情况吻合,那时候吴伯箫由北平到青岛、济南工作,《羽书》中的所有散文均写于彼时彼地,除了《大公报》,一般也多在北平、青岛、济南的报刊上发表。《说踽踽独行》一篇本是应《青岛时报》副刊“明天”编辑约稿而写,这有责编在“编后”中的说明为证⑤。而发表在北平《鞭策周刊》(1932 年第1 卷第17 期)上的《牢骚语》竟然是前述伪作中《热肠篇》和《热肠语》的“母本”!即是说,在真吴伯箫的《牢骚语》发表12 年后,冒牌的吴伯箫(吴伯萧)才将这篇《牢骚语》改头换面分别投给了上海的《万象》和北平的《吾友》,而且竟然一路顺风,没有人看出任何破绽,盗名欺世一至如此,看来世人也真太麻木了。
至于《绿的青岛》一篇,经与《羽书》集里《岛上的季节》对照,发现它们乃是同一篇散文的两个有所不同的稿本,《绿的青岛》很可能是最初的文本,而《岛上的季节》只保留了青岛四季的内容,删去了《绿的青岛》前后各一页多的篇幅,又将四季的内容分了节。这当然也可以确定是吴伯箫本人的作品。
然后就是抗战时期的5 篇和战后的1 篇。《致萧乾》原载《大公报》副刊《文艺·作家行踪》栏,来自于编辑萧乾引述的吴伯箫来信,吴、萧二人的作者与编辑关系早在战前就存在了,这封信来自吴伯箫当无疑义。难得的是,此信虽然不属于散文作品,却披露了吴伯箫在安徽参加广西军和去延安的一些信息,为了解吴伯箫到延安的主客观原因提供了细节性内容,还是重要的。
《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展开战地的文艺工作》两篇跟《绿的青岛》和《岛上的季节》的情况相似,也属于同一篇文章的两个不同稿本,《展开战地的文艺工作》只是《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的部分内容,从文章发表的杂志判断,《展开战地的文艺工作》很可能是《游击》杂志编辑从《文艺突击》或《文艺战线》上节选的,原作者未必知情。这种情况在吴伯箫也常见,不少文章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载,甚至被剽窃,比如1939 年上海《火花月刊》上《踏尽了黄昏》一篇就是编者转载于《大公报》文艺栏的,而1940年北平刊载的《山屋》《马》,分别署名柏萧和吴伯萧,恐怕就和《灯笼》一样,是被冒名者剽窃的《羽书》集内作品了。需要说明的是,《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是吴伯箫与卞之琳合作的,无论发表还是转载时都是二人共同署名⑥。
《青菜贩子》刊载于延安的《大众文艺》杂志第1 卷第6 期(1940 年),讲的是东北牡丹江一带游击队抗日的故事,和发表在《十月文萃》上的《大院套》应该是同一系列,从发表地、内容、语言风格综合看,判定为吴伯箫作品应无问题。
至于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散文《山谷里的桃花》,也就是吴伯箫自己误记为《山桃花》的那篇,只要跟吴伯箫同时期发表在《延安日报》上的《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说日常生活》略加比照,就感觉得到那种浓烈的个性色彩非吴伯箫莫属。吴伯箫之所以迟迟不收入集子,大概还是觉得此文过于个人化了吧。在笔者看来,此文虽然写在延安,写的人也是从山东长途跋涉到延安的革命者,而情调却更像吴伯箫早期的散文,那种抒情调子的缠绵也的确是吴伯箫散文中少见的,因为这可能是吴伯箫散文中唯一正面讨论他的爱情观的一篇。吴伯箫后来(1969 年10 月)写的个人检讨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⑦。
最后一篇人物传记《赵尚志同志》,实际上分“传略”和“轶事”两部分,“传略”作者白和,“轶事”为李延禄讲,吴伯箫只是这一部分的整理者,那时候吴伯箫已在东北大学,又兼任《东北文化》的编委,尽管只是整理,却不会是假的。
五
现在能确认的吴伯箫集外文,皆为1949年前的,限于目前旧报刊资料数据的局限,也许仍有遗漏。另外,1949 年后的集外文也已找到一些,但本文暂不加以讨论。
最后再对20 世纪40 年代敌占区何以会出现触目惊心的吴伯箫作品剽窃和冒名情况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集中甚至大量出现这种情况,或许跟下述背景有关:
第一,是在剽窃与冒名者看来,吴伯箫正具备被剽窃和冒充的条件。这和吴伯箫在文学上已达到的造诣和已具有的名声、地位有关,因为在战前,吴伯箫是在一定范围内与何其芳、李广田齐名的散文作家,有“散文三杰”之称,但又并非如周氏兄弟、朱自清、徐志摩那样的一线名家,刚好处在有资格被剽窃和冒充的位置上。在30 年代前半段,吴伯箫的散文陆续被收入若干种散文选本,如《岛上的季节》被选入姚乃麟编《现代创作游记篇》(上海中央书店1935 年4 月版),《马》分别被选入海之萍编《春风》(现代小品文选,长春益智书店1935 年7 月版)和孙席珍编《现代中国散文选》(下卷,北平人文书店1935 年版)。这从40 年代《羽书》被剽窃后遭到读者“举报”和冒名发表作品的刊物上对“吴伯箫”的推重也可以看出来。如上海《文潮》创刊号(1944 年1 月1日出版)以头条发表署名“吴伯萧”的“报告文学”《云南的下层》时,同时在“下期预告”中又有关于吴伯萧“万字中篇小说”的预告,可见是隆重推出。而且,该期《编后》还有一番特别说明:“吴伯萧先生是北方名作家,以前在大公报与李广田、何其芳齐名,有散文三杰之称,承他远道惠稿,并担任特约撰述这篇所写云南现状绘声声影,惟肖惟妙。”⑧再如张金寿《北行杂记》中写到在济南专访吴伯箫一事,用了“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⑨这样的说法。
第二,剽窃与冒名者熟悉、至少了解吴伯箫在山东时和去延安后的情况,利用吴伯箫不易知情也不易“投诉”的空档骗取稿费,蒙混发表个人的作品。从现在了解的情况,这位吴丁夫(或吴鼎甫)应该也是一位中学教师,又在济南,他的文章有不少涉及教育题材或主题的。吴伯箫战前也曾在济南乡师和山东省教育厅工作,加之文名甚大,吴丁夫(或吴鼎甫)作为不知名的文人,在得知吴伯箫去了延安后乐得盗名欺世一回,有这种心理动机总是可能的。特别是战争状态中,生活条件不好,如果腿又残疾,骗取稿酬贴补家用就更有可能了。延安“审干”后,西安报纸上和其他地方出现了吴伯箫死亡的消息,或许就会更加强化此种行骗动机。
自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种剽窃和冒名顶替都是无聊、可耻的,正如当年《吾友》杂志上的读者来信所云:“但是,我应该奉劝吴鼎甫先生,不要为了原作者不会登报声明,而冒名顶替,偷他的文章已经够了,但偷他的名字,未免不近人情,生财之道是很多的,千万不要发昧心财,其实千字二元的收入,能值几何呢?请不要成名心切,想列入作家之林,还是关门读书,以待来年吧?”⑩
①吴伯箫:《吴伯箫——答〈调查提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 年第1 辑,北京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0 页。
②子张:《吴伯箫〈羽书〉剽窃案及其他》,《文艺报》2018 年4 月20 日。
③吴伯箫:《〈羽书〉飞去》,《忘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年版,第126 页。
④编者:《一年来的抄袭》,《吾友》第3 卷第2 期(1943 年),第14 页。
⑤吴伯箫《说踽踽独行》篇末注明写作时间为“廿三年十一月底,稿。”原载《青岛时报》“明天”副刊,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一版,编后云:“……这次承张春桥,臧克家,黑丁兄远远寄稿子来,伯箫,林麦兄百忙中写了一篇散文一首诗给我们,还承亚平兄介绍许多诗歌。这里我谨向诸位道谢。”
⑥只是在不同刊物上署名先后有不同,发表于《文艺战线》时署名顺序是吴伯箫、卞之琳,该杂志创刊于延安(实则先后在重庆、桂林印刷出版,夏衍为发行人),周扬主编,卞之琳为该杂志编委,其长篇通讯《晋东南麦色青青》正在该杂志连载,第4 期除了这篇二人合写的文章,同时就有卞之琳这篇通讯的一部分,从署名的前后顺序判断,应该是卞之琳投稿。而稍后在《文艺突击》发表时,署名又变成“卞之琳、吴伯箫”,则或为吴伯箫投稿,特意将卞之琳放前面。
⑦吴伯箫在1969 年10 月24 日写的《检查我在文艺工作上所犯的错误的罪行》里面说:“《山谷里的桃花》,写了同一个从山东根据地到延安的女同志见面,虽然写了一点从她口里听到的山东根据地抗战的情况,主要表达的是个人感情。在《解放日报》发表以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就说我写作态度不严肃,胡乔木也在一次小会上指名批评我是‘个人表现’。”
⑧《编后》,《文潮》创刊号,1944 年1 月1 日出版。
⑨张金寿:《北行杂记》,《杂志》第15 卷第2 期(1945 年)。
⑩ 方坪:《关于〈灯笼〉的“谜”》,《吾友》第3 卷八号,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第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