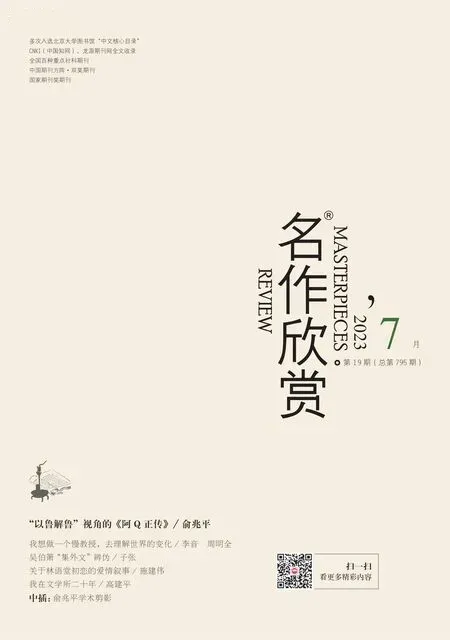论张中民底层叙事的审美向度
河南 郑积梅
底层叙事主要是从文学作品所表现客体对象的层面而言的,学者王春林认为:“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数量庞大的群体,生活每况愈下,有的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以这样的社会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充分地透露出一种对底层人群的悲悯与同情,通过文学性的笔触强烈地呼吁全社会都应该来关注这些弱势人群的文学作品,即是我们这儿所谓的‘底层叙事’了。”①底层叙事在中国有着悠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诗经》中的《国风》开始关注底层民众,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更是妇孺皆知。21 世纪以来,对底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命运描写,成为一个鲜明的文学现象。
河南作家张中民有过短暂的记者生涯,记者的职业操守也深深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那就是在作品中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底层叙事”是张中民小说创作的是一种标志性表现。“从根本上说,文学创作正是映现着作家思想认识立场的文化想象行为。”②张中民底层叙事关注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乡村弱势者、城市异乡者和城市空心人。
乡村弱势者:在孤独的时间中不可承受的生命之痛
“乡村是中国文学表达的起点,更是新世纪文学表达的重头戏。”③中国是传统的乡土中国,对乡土的关注其实就是对生命之根的关注、对中国国情的关注。“乡村现实的问题既是广大乡村的问题,也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直接相关。”④
考察张中民小说的底层叙事,不难发现乡村特别是乡村中的弱势者已经成为他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严肃的小说作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⑤张中民直面乡村弱势者,特别是空巢老人和残障人,体察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内心世界的疾苦,他的长、中、短篇小说几乎都以乡村弱势群体为写作对象,以此把脉各种弱势群体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感受,体察他们在孤独的时间洪流中不可承受的生命之痛。
张中民把庞大的空巢老人群体作为关注对象,而且以此为契机,引发全社会都来关注这类弱势群体。中篇小说《老人和狗》描绘出了一个乡村空巢老人的身心困境,小说从一个老人和她养的一只名叫花妮的狗相依为命切入,着力呈现空巢老人孤独无助、老无所依的生存状态,儿孙回家团聚的渴望只能在梦中实现,小说以一种内在式体验和悲悯的情调直抵空巢老人心灵的空间。小说最后老人与狗双双去世的悲剧,使得空巢老人精神的苦难与肉体的疼痛直抵人心。人与狗的对话似乎增加了小说的荒诞性,这恰恰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乡村生存的无奈。短篇小说《回家》选取大年二十九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叙述在城市打拼事业有成的刘宁回家看望母亲,并最终决定抛开外在人事的纠缠留在乡村陪母亲过年:“马上要过年了,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候,我应该留下来陪您才是!什么公司合同,什么董局长,什么小蓉,所有这些统统都没有我在老家陪您重要!想到这里,他突然临时做出一个决定:我今天不回城了,留下来陪母亲过年!”作品借由“这一个”空巢老人生活的方式、生存的状态,还原了广大中国现实的乡村生活面貌:一个空巢老人独守荒凉的乡村老家。张中民的叙事实践不仅揭示了这些空巢老人的生存境况,还挖掘了空巢老人内心的孤寂和苦闷,全息式地呈现出空巢老人群体的生命图景。作家凭借道德良知和悲悯情怀,展露他们的心灵世界,挖掘他们在孤独的时间中不可承受的生命之痛,给读者带来心灵的强烈震撼。
文学承载着关怀个体与现实的功能,“叙事不仅是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它也是一个人的在世方式;也就是说,叙事不仅是一种美学,它也是一种伦理学”⑥。空巢老人现象无论在社会学层面还是文学层面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残障人也是乡村弱势群体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群体。张中民常常凭借乡村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想象,深入残障人的心灵世界,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的痛楚。短篇小说《大头男孩》和中篇小说《和哑巴说话》《天堂里有没有爱情》都以聋、哑、瘫等残障人为写作对象,并通过多种文体以悲悯的情怀来审视残障人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渴求。《大头男孩》中的乡村男孩大头意识模糊,思想单纯,常常被同龄人欺负,孤独的他心里满是委屈和愤怒。在八岁那年又目睹父亲的惨死,大脑就更经常处于混沌状态。高耸入云的水塔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小伙伴们的疏离与排斥让他对高塔充满了渴望,加之因饥饿导致的对缺失父爱的渴求,让一个小男孩在一个浓雾的清晨试图攀上高塔,最后失足从高塔坠落,造成鲜活生命的死亡。小说娓娓道来,像一曲爱与美的挽歌。《和哑巴说话》中的李林、赵现、王五和刘艳梅都是勤劳善良的乡下孩子,仅仅因为是先天或后天的哑巴,就遭到来自乡邻孩子的嘲讽排斥甚至恶意捉弄。李林只有在自己喂养的几头牛那里才能感受到温情与爱。虽然口不能言,但他们聪明伶俐、心灵手巧,有着正常的是非观念与对爱的渴求,最终奋起反击无端的伤害,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天堂里有没有爱情》写的是养母的固执与偏见造成哑巴养子黄金龙与没有血缘关系的既哑且瘫的妹妹金凤的爱情悲剧。作家把黄金龙的微妙心理、苦难生活,以及单纯而朴素的人生追求表达出来,那个叫爱情的东西,在天堂村里演变成了一出血腥的悲剧。三篇小说都是以悲悯的情怀对个体生命疼痛的展现,对弱势群体命运疼痛的吟唱,对人尊严的强调和对爱与同情的呼唤。
作家“直面底层,直面苦难,并不仅仅限于悲情苦境的平面描述和悲剧展览,而是要反思悲剧何以发生,挖掘苦难的根源”⑦。探讨弱势群体的存在意识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书写弱势群体人生体验的疼痛感,挖掘弱势群体在疼痛的感受中隐藏的人性的复杂,这是张中民底层叙事的原始动力,也是作家底层叙事的主体。残障人生活的乡村人性复杂的一面,被作者生动地展现出来,有力地揭示了残障人生存的疼痛与命运的悲剧。
城市异乡者:在流动的空间感受身心的痛楚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与乡村成为中国明显的二元结构,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代表着文明、富足、时尚,大量的农村人口怀揣梦想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异乡者”。张中民敏锐地关注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重要历史景观,以城市异乡者为写作对象,展开城市异乡者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空间的书写。他以具有穿透力的眼光俯瞰社会世态人生,叙述城市异乡者在城市流动的空间中谋生或打拼而体验到身心俱痛的故事。
短篇小说《相遇》中的货车司机是中国无数个城市异乡人的缩影,他们在不同的城市里游移做最苦的活,跑最远的路。短篇小说《陈亮,快跑》,因为贫穷到广州谋生的陈亮每天凌晨两点半起床开始一天打三份工的生活,这三份工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在订报纸的老太太眼里,他就是一个打工仔,甚至都没有和城市人申辩的资格。虽然在城市娶了娇妻生了儿子,但妻子要给儿子买进口奶粉和购房的要求,对一无文凭二无特长的陈亮来说压山很大,为了赶时间多挣钱,马不停蹄一心快跑的陈亮遭遇了车祸。中篇小说《窄门》讲述“我”——一个城市异乡人在流动的城市空间遭受的身体癌变和承受的精神孤独。“我”住在一个嘈杂的、不见天日的地下室,找不到工作的焦虑让“我”染上了烟瘾,巨大的烟瘾又侵害了“我”的身体,没钱支付住院费用。朋友的屡屡帮忙,才使“我”得到在书店整理图书的工作机会。机缘巧合,“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曙光微现的时候,“我”却被告知已是肺癌晚期。“我”作为一个城市异乡人,其实是现代城市精神病学的标本。长篇小说《向南方》和《远方有多远》算是城市异乡人在城市“追梦”打拼奋斗的姊妹篇,在追梦大潮中有人溺水,也有跳龙门的弄潮儿。上部《向南方》叙述姚远作为城市异乡人在南方城市的奋斗及失败的经历,是溺水者。下部书写姚远的奋斗及成功,是跳龙门的弄潮儿。“追梦”一直是古往今来文学中的经典主题,现实中充满了复杂和无奈,梦想遥远,奋斗不止,但现实冲击却连绵不断。最终姚远的梦想在忍辱负重中取得成功。这样的成功者在众多的城市异乡人中终究是凤毛麟角。姚远在初入城市时,他的居住状况和求职经历都与《窄门》中“我”的情况相差无几,这会让读者记忆深刻。“我”、货车司机、陈亮还有姚远们“都是这茫茫人海中的蚂蚁”,他们都是现代城市社会典型的心理镜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作家在不同的小说中反复书写城市异乡人的生存状况和挫折遭遇,表现他们在城市的一种漂泊无依感、一种陌生感,他们是疼痛一族。“他们的痛,不是单向度和单层面的,而是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上,在人心的每一个细胞里,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灵魂的深处,来自心灵的深处,所以真实、悲切,有强大的灼热感和穿透力。”⑧
城市空心人:生活重压下承受精神的孤独
张中民将笔墨突向当下生活,以现实主义的勇气直面被城市时尚风光遮蔽的那些苦寒、低微的人与事,捕捉生存在城市各种角落的城市空心人的痛苦经历,俯瞰了这些弱势群体在都市生活的艰难处境,他的底层叙事再现了城市空心人生存的窘迫和精神疼痛的现实图景,写出了一种当下的、具体的个人经验,对社会矛盾进行反思与追问,呈现出文学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的焦虑、尊严与担当。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缺陷,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其信息获取能力、储存能力、管理能力和数据智能分析能力远远超出传统数据库,具有数据规模大、运算速度快、数据类型丰富、数据价值高等四大优势[2]。
《万家灯火》以房地产开发商何晓鹏开发纺织厂地块与纺织厂退休工人老常的日常生活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老常住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盖起来的老式筒子楼,面积只有五十多平方米。住在这幢旧楼里的老常,像只寒号鸟那样一直在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微薄的退休金抵不上物价的飞速上涨,柴迷油盐的日常生活开支都用铅笔头在孙子用过的作业本背面记录下来,老常变成了斤斤计较的人,退休工人的窘迫生活在他一笔一画的记录中展现无遗。《空山》也与地产开发相关。从市纺织厂退休的王余在退休之初觉得自己像是走到了世界的尽头,惶恐不安,无所适从,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跑着找工作,可是到处碰壁,自学成才成了策划师,也为一个即将倒闭的企业策划获得成功。生病的母亲需要吃药花钱,上大学的女儿需要各种费用,为了从地产商那里得到足以改善家庭生活的200 多万策划费,王余不得已同意剃度出家,本来还想着酬金拿到手后再想办法还俗,没想到空门一入深似海,佛法学得入魔,他看淡了人世,最后彻底遁入空门,世上再无策划师王余。金钱的巨大压力是造成王余一波三折起伏人生的因由。《相遇》表达的是金钱对人心的异化,小说中的赵寻也是一个城市空心人。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到城市工作有权之后收受贿赂,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出狱之后为了生存做起小生意。小说开头详细书写赵寻从较高社会地位坠落,褪去了身上的光环,沦为城市普通一员,为了省钱甚至连公交车都不坐,还和货车司机就运费搞价还价。权力给了他金钱,满足了他的虚荣心,金钱也害了他,最后他还是活成了金钱的奴隶。《身体里的蛇》里资深小职员孙亮潜意识中总觉得家里马桶里有蛇吐出一条索索而响的红信子向他发起攻击。小说开篇引用冯至的一首诗:“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呵,不要悚惧。”马桶里怎么会有蛇呢?是城市生活的孤独寂寞分裂了孙亮的精神,臆想中的蛇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几篇小说篇幅不长,但写尽了底层小人物不堪的遭遇。叙事的夸张变形有着魔幻化、寓言化的现代审美气质,颇有卡夫卡变形计之意味。
张中民的城市空心人写出了人性深度的复杂性,是读者考察人物、环境、民生、时代精神风貌等的窗口与渠道。同时,张中民的底层叙事在烛照城市空心人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侧面。
文本外的作家:悲悯情怀下对底层群体的文学救护
张中民通过底层叙事完成了对生活的提炼和变形,为读者营造了过目难忘的底层生存镜像。在“娱乐至死”的当下大环境中始终保持对底层题材的专注,张中民的坚守无疑是极为难得的。张中民写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底层群体的生活镜像及心灵脉动,挖掘出他们身体及精神上的疼痛感。“揭示生活中的苦难,往往能给人以直接和强烈的痛感,它能激起人们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还能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因此,书写现实生存之‘疼’自有其意义。”⑨
张中民的语言虽平淡朴实,但都是有情怀、有爱、有色彩的文字。《老人和狗》《回家》中乡村里母亲遥望的目光日益黯淡,《窄门》《陈亮,快跑》《向南方》中城市异乡者的追梦之路艰辛坎坷,作家渴望“哑巴”和“大头男孩”们不再遭受伤害,城市真正能成为城市异乡者的乐园。作家的底层叙事有哀伤,但不喧嚣、不爆裂,更没有咬牙切齿,但却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在读者心上,弱势群体真正的生活,在作家悲悯情怀的观照下,如同显影液里的相片,慢慢浮现出清晰的影像,一张一张排列得庄严肃穆,成为这个时代存在过的、无法湮灭的证据。
张中民的小说重构了当下弱势群体的生活,这种底层叙事以最鲜活的面貌将底层人群的生活、命运、挣扎和归宿描述得淋漓尽致,直面现实书写当下,写出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作家的底层叙事呈现出鲜明的道德同情和社会批判特征,这也是对底层群体的一种精神抚慰。为弱势群体鼓而呼的写作选择,是对弱势群体疼痛的文学救护,是对一种精神力量的寻找,使文学真正回归到对人类生存的“诗意栖居”的关注上来。
①②王春林:《新世纪长篇小说中底层叙事的四种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年第8 期。
④贺仲明:《让乡土文学回归乡村:以贺享雍〈乡村志〉为中心》,《扬子江评论》2019 年第1 期。
⑤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版,第218—219 页。
⑥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 页。
⑦刘川鄂:《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作家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 页。
⑧彭学明:《在疼痛中苏醒和超越:深圳打工文学初》,《理论与创作》2009 年第1 期。
⑨周哲、贺仲明:《“疼痛”的揭示与“温暖”的烛照:东紫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7 年第2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