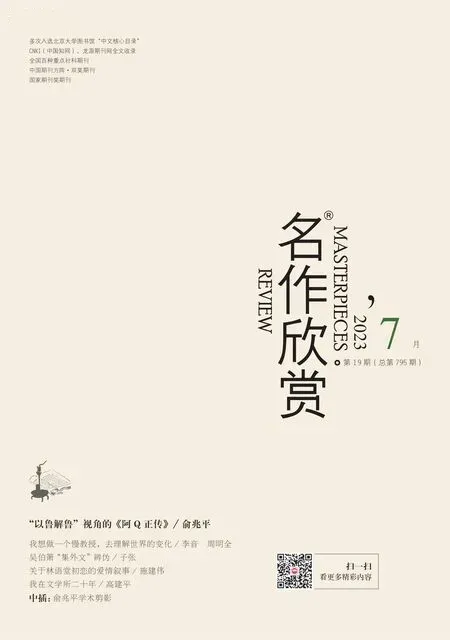生命诗学视野下的李白研究
——读詹福瑞《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河北 陈玉强
詹福瑞先生研究李白,经历了两次顿悟。一次是不惑之年读李白的《将进酒》,悲从中来,怆然泣下,从而顿悟李白的生命意识;一次是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顿悟生命的本质在于存在的瞬间性与消亡的虚无性,从而理解了展现生命短暂之痛的李白诗。这两次顿悟奠定詹先生《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11 月版。下文所引出自该书者,随文标注页码)的基本研究路径,即文本悟入与哲学阐释。
《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詹福瑞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出版
这一路径与“以还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路径不同,是从文本细读中直接触及并阐释李白诗歌的生命内涵,“既要从个人的生命悟入,更要依赖于读书,尤其是西哲的书”(第582 页)。然而,生命悟入岂是易事?“生命,不论古今,无论中外,都是一个微妙的、难以勘透的问题。”(第580 页)詹先生这部书,从不惑到耳顺,写了半世,用功最著,这其中包含持续的学术积累和人生渐悟的过程。
詹先生将中外生命哲学的要义融入对李白的阐释中,使此书具有明显的生命诗学视野。按照学界的界定,“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文学形式是主体生命扩张、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生命本体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 年版,第8 页)。詹先生探讨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就属于典型的生命诗学研究。
尽管郭沫若早在1920 年已揭开文学抒写生命的本质特征,《生命底文学》一文呼吁“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然而检讨百年来的生命诗学研究,成果远谈不上丰硕。詹先生指出:“很明显,生命意识已经消失于当代熙熙攘攘的众生之中了,忙于世俗生活的人们已经麻木,谁还去关心生命为何、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哲学很少研究人的终极之问,文学亦舍弃了这一重要传统,关于生命的研究内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只在少数著述中才见涉及。”(第580 页)
少数几部涉及生命诗学的著述,大都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例如吴投文对沈从文生命诗学的研究、陈超对当代诗歌生命诗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家,尤其对李白的生命诗学阐释,学界是有缺失的。詹先生的这部书弥补了这一缺失,通过研究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为学界建构了生命诗学视野下中国古代经典阐释的新路径。
生命意识研究何以是可能的
“生命意识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第582 页),较难把握。作为研究方法的生命诗学首先要在逻辑起点上回答:生命意识研究何以是可能的?詹先生指出:“研究文学中的生命表现,应是文学研究的基本之义。”(第580 页)
其一,生命时间具有客观属性。生命在时间里发生、展开、终结,生命意识的本质是时间意识,只有从时间里才能窥得生命的本质。詹先生引用叔本华之语“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第213 页),在哲理上可以佐证“李白对个体生命本质的体认,是通过光阴而获得的”(第14 页)。生命意识之所以可以被研究,正是因为其底层的时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
其二,生命意识具有历史属性。李白是肉体性、精神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的历史存在,他的生命意识是从其所处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受唐代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属性。
其三,生命意象具有客观属性。詹先生对李白诗歌中的逝川、石火、春荣、飞蓬、逆旅、过客、春殿、古丘等生命意象有精彩的探讨,揭示了其中包蕴的生命意识。而这些生命意象是客观存在的,故而其比附、隐喻的生命情感空间,也是可以被感知的。
其四,文学具有不朽的永在性。詹先生指出生命的本质是“瞬间的存在而终归虚无”(第14 页),但李白抒写生命并不是为虚无辩护,恰恰相反,他是以文学反抗虚无。李白创造了承载生命之思的杰出作品,揭示了生命的虚无之痛与超越之途,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而具有立言不朽的永在性。
詹先生以生命诗学为研究视野,对李白生命意识的研究,首先是以生命意象为核心的内部研究,其次站在中西生命哲学的高度对之加以审视,又具有外部研究的特点,跳出了以往作家思想研究的俗套,开辟了李白思想研究的新格局。
揭示李白生命意识的内在构成
李白没有提出任何生命哲学的理论,“但是,他通过个人的感受、体验和艺术表现,不仅触及个体生命本质问题,而且极为深刻”(第14 页)。李白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在他对生命瞬间性、虚无性本质的焦虑与反抗上,他的生命之悲与乐、功业渴求与英雄情结、孤独与崇高、逃逸与解脱,均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一方面,生命的瞬间性、虚无性必然引发李白的焦虑,在诗文中体现为生命短暂的悲叹。詹先生精当地指出:“惊惧时光的飞逝,嗟叹生命不永,是生命意识在李白作品中至为突出的表现。”(第160 页)另一方面,由于生命短暂,终归虚无,李白又努力追求生命价值的生成。“李白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认,给其心理带来巨大的焦虑,同时也为其人生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动力”(第14 页),詹先生研究了焦虑与动力双重驱动下李白的生命意识。
李白的生命意识具有复杂性,他对现世乐与身后名,时褒时贬,有一些矛盾的表述。李白《少年行》“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否定身后名,肯定现世乐,对徇节徇书以追求身后名的行为表示不屑;《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江水亦应西北流”,认为现世乐不长久,转而赞赏“屈平词赋悬日月”,又有“身没期不朽”(《拟古》其七)的一面。
如何阐释李白的这种矛盾呢?詹先生认为,现世乐与身后名在李白思想中是并列的。其一,李白接受的文化本身存在矛盾。“造成矛盾的原因,不在李白,而在于他所接受的文化。”(第240 页)在生命目的的认识上,儒、道重精神,《列子》重感官,造成了思想的对峙与分裂,“李白接受的就是这种分裂、多元的思想”(第240 页)。其二,李白人生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心境,导致不同的生命意识。“李白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境和心境不同,他的诗中故而出现了或高扬功名或高扬感官快乐的矛盾”(第240 页),整体上呈现出早年求富贵、晚年求身后名的特点,当然其中还有更具体、更复杂的原因。
事实上,李白以快乐主义的生命观弥合了现世乐与身后名的矛盾,将“现世乐与身后名和谐地统一为一体”(第235 页)。詹先生指出,李白“否定功名富贵与肯定身后名的立足点正是在现下的快意之上,而且是无待,即没有任何负担的快乐”,“携妓纵酒与兴酣草诗,都是逞一时之快。这种诗酒生活,既可以释放受到现实压抑的情感,又可以留下诗文传世”。(第239 页)
也就是说,李白对身后名的理解,不由循节循书而来,而是由其笑傲诗坛的诗才而来。进而言之,他追求的不是道德不朽,而是诗文不朽。在李白看来,现世乐是荣身乐命,身后名是基于快乐主义的诗文不朽,二者本质上并不矛盾。
李白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放在当世,因此他的功名心甚强。“崇拜英雄,建功立业,追求声名的不朽,这是李白为个人生命找到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李白诗歌的主调,是李白作品中最能感发人的意志的内容之一。”(第15 页)然而,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又催生了李白强烈的孤独意识,加重了他的焦虑。“李白一生的主要困扰是强烈的功名心与怀才不遇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加深了他生命苦短的焦虑,造成心灵的极大困扰。”(第16 页)故而李白诗文常常抒写孤独无依之悲、孤芳自赏之傲,赋予其文学以悲感与崇高感。
李白有两种解决焦虑的途径,一是以诗文不朽作为生命不朽的快乐之源;二是推重精神自由,沉入审美境界,超脱现实不快。詹先生指出:“李白习惯于求助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放旷,以此来达到一种快乐的生命状态。”(第16 页)詹先生由李白的游仙诗、饮酒诗探讨李白心灵的逃逸与解脱,由李白的山水诗探讨李白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揭示了李白复杂的心路历程。
李白生命意识研究的多维路径
“就李白说李白,无法说透李白。”(第581 页)因此,詹先生跳脱出来,从哲学、历史诸层面,探讨李白的生命意识,建构了生命诗学的四个维度:哲学之维、历史之维、审美之维、现代之维。
其一,在哲学维度上,梳理中西生命哲学理论,揭示李白生命意识的本质、渊源,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高度。詹先生认为先唐生命哲学是李白生命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儒墨的轻生观、老庄的重生观和列子的厚生观,此三者都影响了李白的生命意识”(第18 页);以西方生命哲学为参考,“找到了李白关于生命本质和价值的内在逻辑,就使李白生命意识的各个方面得到了贯通”(第581 页)。
其二,在历史维度上,注重探讨李白生命意象的历史渊源,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厚度。例如,詹先生研究李白“石火无留光”(《拟古》其三)的石火意象,先梳理李白之前《关尹子》、汉乐府、《抱朴子》、曹植对石火的用典,再阐释李白石火意象的独特性,认为喻指生命短暂的石火意象包蕴着生命稍纵即逝的本质,比源出孔子、喻指时间持续逝去的逝川意象更强烈、更震撼。
其三,在审美维度上,抓住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象进行审美分析,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深度。詹先生以研究对象映照自身,将自身对生命与诗艺的理解,作为文本悟入的契机,剖析李白的时光流逝之叹,写得极为精彩。
其四,在现代维度上,探究李白生命意识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和人文价值,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温度。詹先生对李白的研究不仅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而且站在贯通古今、会通中西的现代立场上,阐释李白对于当下的价值,其功于李白研究甚大,对当代文化建设亦有意义。
李白生命意识研究的价值探讨
詹先生此书不同于以往从道德层面塑造李白的成果,他从生命意识这一根本层面阐释李白,探讨李白的生命意识与当下的关联,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自古以来,对李白的快乐主义不乏偏见,詹先生为李白辩护,认为李白追求及时行乐的“内在思想基础是其对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外在原因是社会对其追求思想的阻碍,使李白追求生命价值的努力遭受打击,其生命力受到挫折,此时的及时行乐就是执着于生命的矫激行为”(第233 页)。李白及时行乐的目的,并非颓废的发泄,“是以最强调的形式指出生命的顽强性”(第234 页),是“他挥发生命力的表现”(第14 页)。
詹先生进而指出快乐是生命的目的及人类的权利,“其实快乐是生命的唯一或曰终极目的,它合于生命的本质,无论是追求物质的快乐,抑或精神的快乐”(第14 页)。为了说明这一点,詹先生广引中西快乐主义生命哲学作为佐证。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纷扰都是恶,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端和终点,它是首要的和天生的善;中国儒、道重精神快乐,《列子》重感官快乐,也是对身心快乐的肯定。
詹先生认为李白诗文中及时行乐的思想也不出快乐主义的范围。追求身后名是延长生命的一种精神上的价值追求,追求现世感官快乐是尽可能占有生命空间的一种物质上的努力,“两者同样都是面对生命苦短的现实而自然生成的提高生命质量、增加生命力度的行为方式。追求快乐行为,合乎人的本性,因此也是合理的”(第232—233 页)。詹先生举德国思想家霍费尔的观点,认为追求快乐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夺取人的快乐,是对人的原始权利的侵犯。
总之,詹先生这部功力深厚的李白研究专著,哲思与文采俱佳,学理与情怀兼备。从李白的快乐主义生命意识中发掘与当下的关联,探讨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可见詹先生的李白研究寄寓着一种深刻的情怀,即对人的生命权利、快乐权利的肯定。詹先生此书既弥补了李白研究的短板,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开辟了生命诗学研究的新路径,又将研究结论指向当下对生命意识漠不关心的普罗大众,展现了詹先生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