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说儒》中的民族意识
刘舒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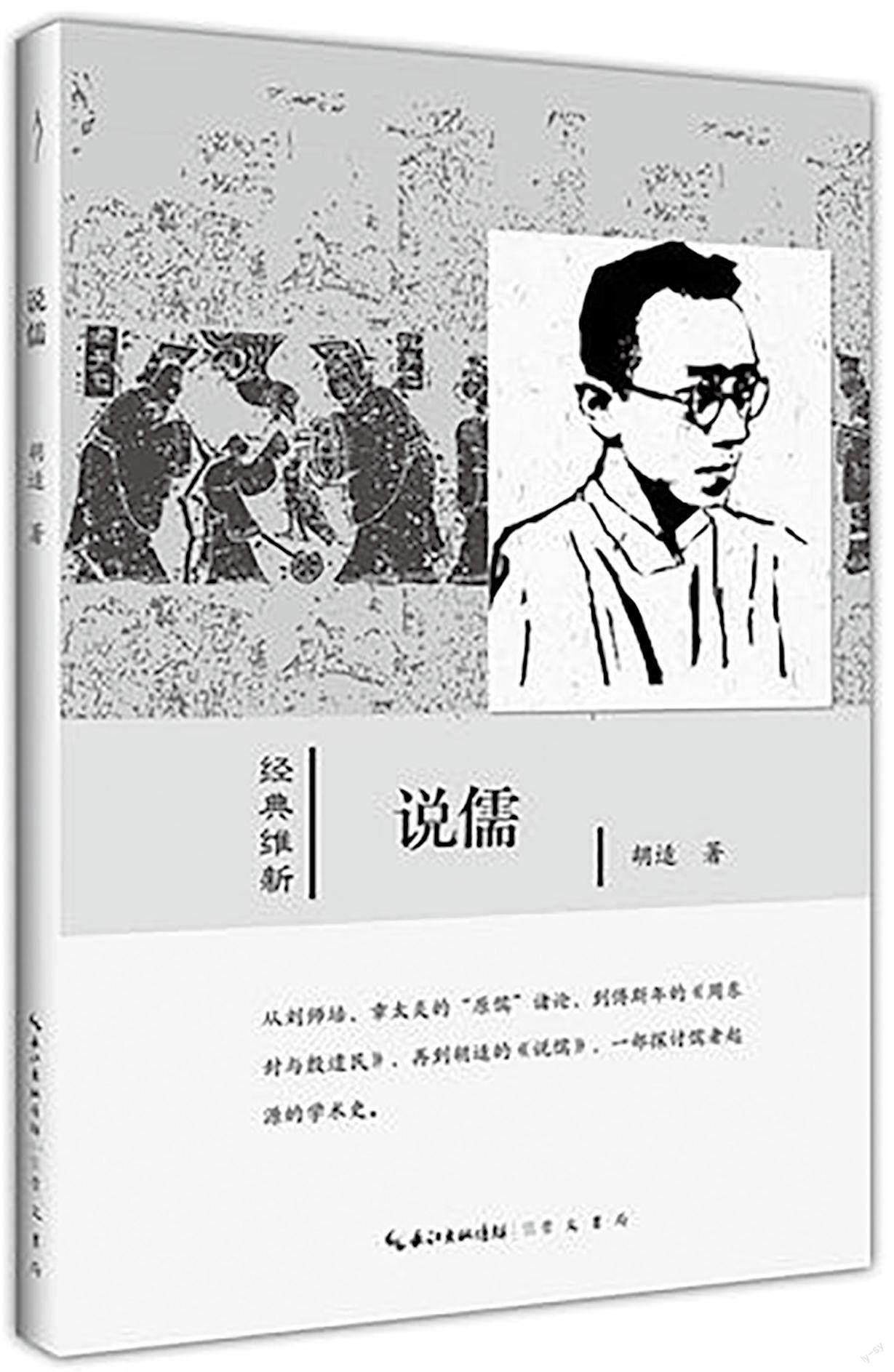
《说儒》是胡适儒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看,他也是“全盘西化”口号的支持者和奉行者。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胡适对于儒学也应该是持否定态度的,就会有失客观。胡适作为新旧文化交替潮流中的一份子,必然有着其复杂的一面,这也影响到了胡适的文化观点和学术观点。自《说儒》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其争论不断,由于一些的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后,《说儒》研究才真正谈得上步入了学术层面。本文拟就《说儒》如何体现民族意识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粗略分析和探讨。
一、胡适与儒学
(一)胡适的生平概述
胡適的性格特征和生平思想与儒学密不可分,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方面,其思想深受传统旧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胡适又是新思想的先锋人物,他在不断的求学和探索中,积极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
胡适对于儒学的看法的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少年时代受父母教诲,像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尊孔尊儒。胡适出生于绩溪,绩溪多商人,经常往来于大城市,因此受大城市风气的感染,胡适父母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胡适读的第一部书便是其父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师》:“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其母虽是小脚女人,但也跟随丈夫的教育理念,注重对胡适的培养。从小受儒学启蒙,也为胡适后来思想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代的留学生活,使胡适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促成了他儒学思想的转变。在国内就读期间,他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笔名“胡适”中的“适”就是来源于《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凭借其出色的国文成绩,胡适借读于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开始了留学之旅。留美回国之后,胡适思想变得激进,其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他开始批判孔子和儒学,也赞成“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是随着新的社会矛盾凸显,胡适对于全盘西化、全面否定儒学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和纠正,从更加理性、客观的角度看待儒学,《说儒》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多诞生于这个时期。
晚年的胡适,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思想观念,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儒学倾向。
(二)胡适与《说儒》
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实验主义是20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随着西学东渐逐渐传入中国,影响了近代一大批知识分子。而当时进化论思潮的流入也不容小觑。进化论是中国近代的主潮。胡适用进化论的思想来探讨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律例是不断前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来假设、推测一个事物的可能性,再用以上求证之方法,来检验这个事物是否有实用之处,结合“历史的态度”分析这一事物形成的背后原因,来评判一事物是否为真理。
据此,我们也可以窥探胡适《说儒》的基本演绎模式和写作动机。结合具体文本,我们发现胡适经常使用“大胆假设”“猜想”等来陈述观点,有的观点尽管没有诸如此类的词语,依然有作者直接推测的意味。此外,胡适还大量运用了实验主义方法溯源儒学以求得儒学真面貌。他的《说儒》一文阐释了儒的起源、儒的生存原因以及孔子与儒的关系,包括孔子为什么可以成为儒的领袖、为什么可以复兴儒等。可以说,《说儒》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研究学术问题的一次具体尝试。然而这种方法论也为《说儒》带来了非议,一些细节的考证并不严谨。比如胡适把儒与殷商联系起来,认为儒服就是殷服,但是冯友兰等人就认为不能把个案扩大到整个群体,“儒家拥护传统反对变革者,故其言服亦不随潮流变革”。
另外一个方面是胡适“历史的态度”,胡适治学并不仅仅是研究儒这门学术问题本身,其目的是要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态,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这就是胡适《说儒》中暗含的民族意识。除此之外,随着沸沸扬扬反孔反儒运动的落幕,胡适也对这股思潮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进行了反思。胡适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儒,为什么儒能够经久不衰,他想厘清这些问题。因此,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如果紧揪着胡适的政治立场,而否定说儒的时代价值,是不正确的。《说儒》更像是我们研究当时人们思想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儒、对于时代格局交替的迷茫和徘徊,而且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内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声音——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二、《说儒》中的民族意识
(一)从社会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待儒的起源
在对儒的古义的论述中,作者大胆推想最初的儒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殷服,行殷礼,并且通过丧葬礼仪、服饰等方面论证这一观点。暂且不论这些论据是否经得起推敲,我们发现作者一直想把读者的注意往殷、周两种文化的冲突上面引导,强调殷文化是儒文化的发源中心,而殷和周分别是强大的统治者和不屈的被统治者。
胡适把周民族比作“东胡民族”“西来民族”等被殷民族仇视的群体。“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形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这里作者并不是有意强调周民族的残酷,因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作者是想强调殷遗民在被压迫阶层是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生态的,那就是通过儒的文化力量,也就是文中所说,“殷商民族文化终究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
作者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几个原因。首先,殷在东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口众多,文化潜在势力强大,并不是武力征服可以付之一炬的。其次,尽管周对于前朝的文化是嘲讽、看不起的态度,但是殷礼和殷制自身的优越性已为周统治者所用,不得不吸取殷制的长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殷民族“团结力”的中心——宗教以及“儒”这一新兴的阶级与职业。作者把“儒”这个行业塑造成一个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是不卑不亢、高风亮节的群体。他们虽然被压迫、被奴役,但是依旧背负着殷礼“保存者与宣教师”的身份。
“希腊的知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败罗马帝国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士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这里不难看出胡适对于文化的重视,从胡适的政治运动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想办法挽救中国的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陈词滥调,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他还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希望能够合理改造中国文化。他以为,在那个动乱年代,只要民族文化得以振興,人民得到自信,就能谋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从民间角度建构儒的形象
往往我们提到儒,都是“饱读诗书”的“圣人”。但是《说儒》中却从职业以及儒的现实谋生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姿态进行反思。作者解构了儒的形象,认为儒以及“儒教教主”孔子有失百姓的期待,不能为后者所理解、接受。他说儒的古义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这里就说明了儒的职业。他又说“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他的弟子则多是治丧相礼的职业中人”,不能完全跳出“因人之野以为尊”“既须靠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节气了”,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讲,你既然领别人的工资,靠别人吃饭,尊严和气节自然要放在一边了。这毫无疑问说明了儒家文化与百姓知识的断裂,儒的哲学思想过于深奥,不要说普通百姓了,连孔门弟子子路也难以理解。再者,儒家所宣传的思想和民众的诉求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只有王室、贵族才会讲究这些治丧礼仪。《说儒》中对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读是“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这都说明了儒的非民间和精英化。但是,文中作者并没有责怪民众,批判民众,而是反省自身的缺点,以谋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集合点。
胡适提出这样的观点有着现实原因。就社会环境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主权被掠夺,胡适认为民族文化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需要缩小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才能调动更多革命力量参与战斗,因此塑造了一个民众期待的儒,成为一种理想;就自身而言,民族危机加重,他有着被排挤在中心之外的失落感,觉得“多数青年人不站在我这一边”;就学术环境而言,晚清在“欧风美雨”等新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经学、儒家、诸子等传统文化都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推动疑古运动大兴,章太炎等人对疑古派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股思潮不利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建立。胡适以“科学方法论”自居,倡导“求是”,对疑古思潮的勃兴产生重大影响,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也对自己的方法渐生疑窦,并且进行了反省与重新思考。
(三)有意神化孔子形象
作者根据犹太民族历史和基督教创教史,结合《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有意建构出一个中国式的“悬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孔子就是那个应运而生的“救世圣人”。作者首先列举了一系列古籍来论证这个预言在当时的真实性,如《玄鸟》篇中的“武王”、《左传》等等,并且把孔子之后的一些思想与这个“预言”结合起来,说他有强大的自信心,“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将孔子去世之前的慨叹说成“自信为应运而生的圣者绝望的叹息”。
这里作者描述的孔子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年轻的时候就被预言选定为圣人,孔子也以“仁”为己任,孜孜不倦心怀天下,相信自己受命于天。其实仔细考证,会发现作者的论证有很多模棱两可之处,比如他引用的《玄鸟》就没有讲述预言。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引用都是不可靠叙述。首先《论语》就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对于老师说的话难免有记录偏差,其次还有孔子去世时《檀弓》的记载,很可能是旁人为了迎合这个预言和夸大艺术效果所捏造的,所以上文“绝望的叹息”论就十分可疑。胡适也在等待那个“救世圣人”,他通过塑造一个神化的孔子来告诉民众: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来救我们于水火之中。至于那个人是谁,胡适也属于困惑阶段,或者说,不一定要是“人”,也许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来引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
三、结语
自《说儒》发表以来,争论不断。笔者认为,对于本文的探讨不应该拘泥于胡适的政治立场的细节考证,而应该更加深入地挖掘胡适这样写,这样说的内在动因和历史意味,从而窥见当时社会对于儒的基本看法和具体期望,辩证地看待《说儒》的历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