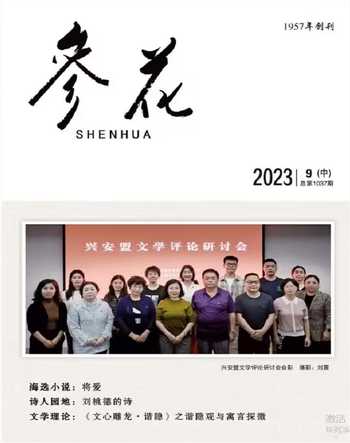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是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之一。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于1847—1852年陆续写成的《猎人笔记》是其成名作。之后,《猎人笔记》被翻译成中文,为广大中国作家熟知,萧红就是从其中汲取营养的。本文从作品取材与情感基调、民俗风情与风景描写、叙事策略与语言应用、人物形象与作品主题四个方面出发比较,探讨《猎人笔记》对萧红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
一、作品取材与情感基调
萧红与屠格涅夫均是取材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甚至直接取材于本人生活经历的作者,他们笔下的人物都饱含作家的体验、感受和同情。屠格涅夫的母亲习惯控制孩子,要求他们对自己百依百顺,为此常常采取极端方式。并且母亲脾气极坏,即使仆人犯了一点小错误,也会被母亲残酷地流放。看着母亲冷酷样子长大的屠格涅夫,在创作中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题,创作中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他曾说:“我的自传,就在我的作品中。”屠格涅夫的小说大多以他的个人经历为素材,所反映的大众生活生动而真实,因此,别林斯基称“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的呼兰小城,从小就看着农民辛勤劳动,她对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在《夜风》等小说中,就有对农民的描写,这不能不被看作是萧红自身经历的投射。另外,孙犁曾说:“萧红最好的作品,取材于童年的生活印象……萧红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不大,她的作品,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文学的味道。”萧红常以童年时期在呼兰小城的生活作为背景,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在《呼兰河传》中,呼兰小城主要有两条大街,东二道街上有火磨、农业学校、高等小学、碾磨坊、豆腐店、机房、染缸房,西二道街上有一个学校。另外还有一条最有名的十字街,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还有拔牙的洋医生。此外,还有“我”的家。在“我”眼中,院子是很荒凉的,没有什么显眼的装饰,东边堆着朽木头,西边扔着乱柴火,左门旁有一大片旧砖头,右门旁晒着一片沙泥土,墙角还放着碎了的大缸、破了口的坛子、腐朽的猪槽子和生锈的铁犁头。至于“我”的家,也是很荒凉的,祖父和祖母住在西屋的两间房,父亲和母亲住在东屋的两间房,一进大门,东边是租给养猪户的三间房,西边是装粮食的三间房,中间有个大门洞,还有三间破草房,三间碾磨坊。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唯一充满吸引力的就是神奇的后花园与储藏室。后花园是“热热闹闹”的,五月里就开花,六月就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倭瓜会顺着墙头长到院子外边去,开出一朵大黄花。到了六月,后花园就更加热闹了,这里有蝴蝶、蜻蜓、螳螂、蚂蚱,柿子和茄子都结了果子,花园里的花长得比人还高。储藏室则成了“我”探险的地方,随便打开一只箱子,花丝线、绸条、荷包都搭配得十分好看;还有些桌子带着抽屉的,抽屉里边有铜环、木刀、竹尺、观音粉。后来,“我”把储藏室的五个抽屉都拿空了,红玻璃的小灯笼、印帖子的帖板、戴缨子的清朝的帽子、鹅翎扇子,對“我”而言,这些都是新奇的玩意儿。后花园与储藏室成为“我”童年时期快乐与美好的所在地,因此,“我”会说:“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是另一个世界了,绝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原型是萧红继母的异母妹妹开子,萧红叫她“开姨”,当时家里为她定了亲,对方给了几万吊的彩礼,可开姨看不上那家人,转而暗恋翠姨的堂兄,一个洋学生,开姨整日郁郁寡欢又无法开口,又被认为大逆不道,后来得了肺结核。
两位作家相似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作品的情感基调都是荒凉的,具有苍凉伤感之美。《猎人笔记》中的“莓泉”一节,弗拉斯因儿子死了,长途跋涉去向主人请求减租,却被怒斥一顿,“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年轻漂亮,但人们说她长得高大,不知羞,说她不像媳妇,还将她抬进装满热水的大缸里去。
二、民俗风情与风景描写
《猎人笔记》描写了猎人狩猎的故事,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国的农村生活。而萧红的小说展示了东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从多个角度全面描绘了呼兰小城的节日盛况,包括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跳秧歌是在正月十五,在农闲的时候,趁着新年,男人装扮得滑稽可笑。呼兰还有放河灯的习俗,在天完全黑了的时候,河灯就要下水了,河灯数目之多,大概有千百只。野台子戏也是在河边唱的,若是秋天收成好,就要唱一台子戏,感谢天地;若是夏天大旱,人们就要求雨,下了雨,到秋天还要唱戏还愿。野台子戏一唱就是三天,光是搭戏台就要三五天,看台要搭出去十几丈远。四月十八办娘娘庙大会,男女老少都来“逛庙”,尤以女子最多,庙会一般到下半天就散了。从书中这些多样的节日习俗可以窥见呼兰人的日常生活,感受丰富多彩的节日韵味。除此之外,萧红居住的呼兰小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古老边城,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生活的痕迹,尤以满族文化元素最为丰富。《小城三月》中翠姨的母亲就是满族人,十分注重婚丧嫁娶的礼仪传统,因此,文中出现了她来接翠姨回去整理嫁妆的场景。
屠格涅夫擅长写景,他能够刻画出瞬息万变的大自然,有着“文学中的风景画大师”之称。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无论是白云、田野、火光,还是朝霞、山谷、云雀,都以一种生动、灵性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猎人笔记》中“树林和草原”一章,屠格涅夫生动描写了草原日出的画面,如“朝霞发红了”“金黄色的光带扩展在天空中”“于是徐徐地浮出深红色的太阳来”这种描写就具有生动的画面感,并且融入了作者的主观体验,构成了一个经过加工的“人化了的自然”。屠格涅夫的这种写景手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生活的同时,又能将自己浓郁的抒情情调融入作品之中。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也有丰富的景物描写,如“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种有灵性的自然描写笔法,彰显了萧红小说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为萧红的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抒情气息,也体现出了萧红最本真的“女儿性”。
并且屠格涅夫与萧红对景物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体现优美的自然环境,而是以乐景衬哀情。郁达夫曾评论过屠格涅夫,说他最善于用人景反衬的写法。在《猎人笔记》中“树林和草原”一节,作者特意刻画了这样一幅情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穷人拖着疲累的步子走着,主人坐在六匹马拉的大马车上,一个仆人侧坐在马车后的脚蹬上,泥污一直溅到他的眉毛上。这种生机勃勃的草原同疲乏的农民形成了鲜明对比,美丽的自然风光又同落后的农村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呼兰河传》里,热闹的后花园反衬着冷清清、黑洞洞的磨坊,富于生机的花朵反衬着冯歪嘴子未老先衰的生命,花开得越红、越旺盛,越是反衬出小团圆媳妇等年轻美丽的生命陨落的悲哀。屠格涅夫和萧红都善于借助景物描写表现他们的批判态度,自然之景与生活之景形成鲜明对比,传达出他们的反抗之声。
三、叙事策略与语言应用
《猎人笔记》在叙事上采用时间叙述和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我”这个猎人的角度来描写景物和塑造人物形象,这种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可以使读者专注情节,“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观察者。萧红在小说创作中继承了这种方式,但更多地是有所超越,虽然《小城三月》的开头和结尾都发生在春天,但是故事的主线是通过翠姨买鞋、订婚、恋爱、抗婚、求学、病死等人生片段串联起来的;《生死场》仅有“十年”和“年盘转动了”两章标题隐含时间,而“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分隔开举行仪式的场所;《呼兰河传》有叙述人称的变化,前两章运用第三人称叙事是为了将呼兰的全貌进行客观展示,第三章之后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是为了寄托“我”对呼兰家乡的怀念之情。可以说《呼兰河传》中的“我”与作家本人有重合的部分,但不能完全代表作家本人的情感态度,只能被视作作家想要描绘的理想的“我”,这种多重视角的转变,以“我”的儿童视角赋予了作品更多的真实性与灵动性。
在屠格涅夫与萧红的作品中还出现了大量方言。方言的使用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同时拉近了读者与作品中人物的距离,使人读来亲切可感。在《猎人笔记》“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一节中,叶尔莫莱问阿丽娜“你丈夫是哪儿人”时,阿丽娜并不理解,只有使用俄罗斯方言“你丈夫是什么地方人”这种说法时,阿丽娜才能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叶尔莫莱和阿丽娜的这段对话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十分贴近读者的日常生活。萧红小说中对方言的使用是为了真实地展现朴实的北方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习惯,北方人经常吃的是小葱蘸大酱、苞米芸豆粥,并且“若外加上一块豆腐,那真是锦上添花”,“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没有吃过的人,不能够晓得其中的滋味的”。作者在创作中思念故乡和回忆童年时使用方言,营造了回忆的氛围,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定地区的农民生活。
四、人物形象与作品主题
屠格涅夫与萧红都是通过描写人物形象引出作品主题的,尤其是劳动人民和妇女的形象。《猎人笔记》中的霍尔外表普通、身材矮小,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工作積极、思维敏捷,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一直认真生活,努力攒钱盖房子,争取摆脱他人干涉,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冯歪嘴子是萧红笔下少见的正面男性形象,他直面女人难产的情况,妥善处理丧事,全心抚养孩子,萧红对他的担当决断表现出支持与赞美。
《猎人笔记》中的阿丽娜是美丽纯真的女仆人,诚实勤劳,有了心爱的人,跪在主人面前,希望被允许结婚,却被当作“忘恩负义的家伙”对待,之后主人立刻剃掉了她的头发,给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送回乡下。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命运大都坎坷,《渺茫中》的母亲在丈夫变心后独自抚养孩子;麻面婆不仅要在田间劳作,回到家中还要烧饭洗衣;小团圆媳妇被撕了衣服,扔进水中折磨;翠姨爱而不得,失去青春生命……这些女性人物的悲惨命运都源于萧红自身的生命经历。
屠格涅夫与萧红都选择了以劳动人民生活为题材,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屠格涅夫后来在《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想时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1935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后,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到了《呼兰河传》中,人们的意识更加淡薄,只是继续着自己卑琐平凡的生活,这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世界,“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大泥坑子的出现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却固执地相信它具有一种神秘力量,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麻木的生命状态。
在散文《无题》中,萧红提出了她对屠格涅夫的评价,针对当时有的人认为“屠格涅夫好是好,但生命力不强”的观点,萧红认为,“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别的作家们他们则不同……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有慢慢走到灵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萧红欣赏屠格涅夫在展示灵魂时倾注了强烈感情,因此,她在回望故土乡民时,也寄予了温情的关怀。在《呼兰河传》的尾声中,她这样说:“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么样了”“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在笔调上具有屠格涅夫式的温和。
五、结语
萧红并不只是单纯地模仿《猎人笔记》,而是置身于相似的创作背景,加入自我思考,由此化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他们都渴望自由。当然,由于历史、创作背景和文化立场的不同,两位作家在人文关怀上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屠格涅夫坚持贵族的立场,而萧红始终站在大众,尤其是女性的立场上。
参考文献:
[1]陈洁.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女性悲剧意识解读[J].参花(中),2022(12):80-82.
[2]李怡萱.东北情怀与童年经验书写——从萧红到迟子建[J].参花(中),2022(12):77-79.
(作者简介:田静蕾,女,硕士研究生在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