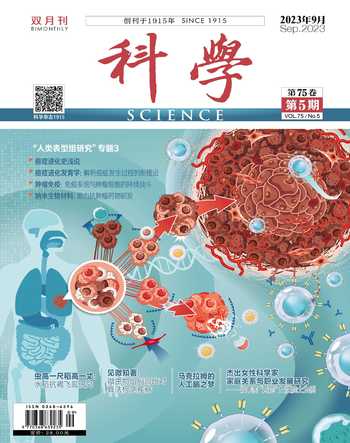癌症进化史浅说
安利伟 周兆才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癌症法》(National Cancer Act),旨在通过扩大癌症研究规模、增加科研经费,根除癌症。在此方案刺激下,癌症成为生物医学领域过去50年中研究最多、范围最广的疾病,有超过至少100万篇论文聚焦癌症发生机制及治疗措施。尽管如此,但根除癌症之路依然漫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癌症是一种古老的进化疾病,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漫长进化过程,是一个体细胞意外突变后不断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求生之路,其内在的逻辑与生物进化的原理极其类似。简言之,癌症是自然选择的最适者突变体。
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的基因组结构是极其完整且稳定的,细胞的增殖活动受到细胞周期的精准调控,不同类型细胞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保证各器官功能的正常运转及维持组织稳态。然而,体细胞会在某些内因(如复制压力)及外因(如化学诱变剂、辐照、紫外线等)影响下,发生染色体基因组的“意外”突变。尽管大部分突变都是同义突变或很快被校正,仍有少量突变发生在染色体关键部分,导致编码基因的功能出现异常,开启癌前细胞的进化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癌是一种概率,患癌是一种坏“运气”。
与癌症相关的基因突变主要分为两类:抑癌基因的功能失活突变(loss-of-function, LOH)和原癌基因的功能获得突变(gain-of-function, GOF)。抑癌基因是一类对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起着负调控作用的基因,它们通过抑制突变细胞增殖并促进凋亡,来保持机体内部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平衡,是体细胞维持基因组稳定性和完整性自设的“警察”。然而,当“意外”突变正好干扰“警察”基因的表达时,其维持秩序的功能受损,进而诱发细胞发生复制周期的紊乱及增殖失控等问题,正常体细胞则有可能变为癌前病变细胞。例如,视网膜母细胞瘤(retinoblastoma, Rb)基因是第一个被鉴定的抑癌基因。正常情况下,Rb蛋白通过调控细胞周期进程保持细胞的正常增殖和分化。然而,当Rb基因发生突变(如甲基化沉默)会使其功能丧失,无法有效抑制某些基因的转录活性,导致大量与细胞增殖相关的基因过度表达,促使细胞不受控制地进行DNA复制,细胞出现异常增殖和恶性转化,转变为癌前病变细胞。又如,TP53基因是目前研究得最为深入的抑癌基因,自1979年被首次报道以来,累计有约3万篇论文聚焦于该基因失调与癌症发生的因果关系。一般认为,正常细胞在受到内因或外因刺激导致基因组损伤时,TP53蛋白能够快速停滞细胞周期、促进损伤修复,从而避免受损基因组被传递到子代细胞。反之,若损伤难以修复则会启动细胞死亡程序,使得机体能快速清除受损宿主细胞。鉴于其在基因组稳定性维持中的重要作用,TP53基因也被稱为“守护基因”。因此,TP53基因的突变与肿瘤关系也最为密切,在30%~50%的人类肿瘤中均发现有不同类型的失活突变,是突变频率最高的抑癌基因[1]。
与抑癌基因的功能相反,正常细胞增殖也需要启动一系列生物事件,包括基因复制、转录及蛋白质翻译等,这些活动需要包括RAS、Myc等在内的基因参与。在细胞的非增殖阶段,这些基因的活性需要被严格“关闭”,它们也是抑癌基因这些“警察”重点监视的对象。这些基因的异常激活会促进不受细胞周期调控的增殖活动,加剧癌前病变细胞的形成,所以它们也被称为原癌基因[1]。例如,Myc基因是第一个在肿瘤细胞中被发现的异常扩增的原癌基因,1982年首次在人伯基特淋巴瘤中被发现。该基因家族编码一类在肿瘤发生和演化中起关键作用的转录因子,促进增殖细胞所需大量蛋白的转录翻译。研究表明约20%的人类肿瘤中存在Myc基因的异常表达,包括常见的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等。与此类似,控制细胞复制的GTP酶家族成员RAS在约30%的人类恶性肿瘤中存在活化突变。
除此之外,某些发生在抑癌基因的突变不仅会丧失“警察”监视功能,反而会被“策反”发挥加速癌症进化的癌基因功能。例如,TP53基因的某些突变不仅使其丧失抑癌监视功能,甚至突变后的蛋白还会获得新的促癌功能,增加细胞遗传稳定性的丧失和肿瘤发生的风险[2]。
尽管体细胞的突变是“意外”的,但基因突变启动癌症进化却是一个有序的过程。2020年,一项研究通过对罹患38种癌症的2658位患者的组织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绘制了基因突变在癌症进化中的分子时钟。发现几乎所有癌症的进化都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有序性,肿瘤的发展遵循着驱动突变或拷贝数变异由罕见至多样化的进化轨迹。例如,抑制基因TP53、APC及癌基因RAS的突变一般发生在进化早期,而包括SMAD4等在内的更多癌基因的突变容易发生在进化晚期[3]。与该结论类似,另一项研究通过谱系示踪技术,也发现肿瘤起始细胞在杂合性缺失TP53基因后会诱导一种可预测、有序、确定的癌症基因组进化,进一步明确了TP53基因突变、基因组不稳定性与癌症发生的关系[4]。因此,癌症的进化起始于“意外”的体细胞突变,但只有遵循进化规律的那些“意外”才能最终生存下来发展为癌。
当癌前病变细胞按照程序突变逃脱抑癌基因监视,获得抵抗凋亡及不受控制的增殖能力后,即为肿瘤起始细胞。尽管解决了细胞内自身的性质问题,外部的身份认同挑战才刚刚开始。当该细胞“举目四望”,首先观察到周围都是曾经的“好兄弟”——正常体细胞,与此同时,正常组织细胞也会注意到这个本该走向死亡的“同类”。于是,一场正常细胞与肿瘤起始细胞之间的生存之战随即展开,细胞竞争也自此贯穿后续整个癌症进化过程。癌症初期,正常体细胞能识别邻近癌变的异常细胞并通过“挤压”生存空间清除它们,整个过程无需免疫细胞参与。这一过程在上皮组织类型癌症如食管癌、胃癌、肠癌、肝癌及皮肤癌早期进化阶段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上皮防御癌症机制或癌症的上皮监视机制[5]。例如,2021年,一项研究通过实验发现化学诱变剂引起的食管部位早期突变克隆约90%以上在3个月内消失,仅极少数突变克隆能在12个月长成较大的晚期克隆并最终发展为癌。其机制研究发现这些早期克隆主要是被周围正常上皮通过细胞竞争方式进行“围剿”清除的,免疫细胞并未被招募及发挥作用[6]。事实上,考虑到体细胞突变及演化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因此,肿瘤起始细胞的数量应该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却只有非常少的起始细胞有机会长成早期克隆,主要障碍就是邻近正常细胞发挥了“监视”功能。

因此,上皮防御癌症机制也是癌症进化首先要攻克的生存难题,即如何在正常组织中建立早期克隆这一“根据地”。目前研究认为,肿瘤细胞一方面利用体细胞晚期突变、代谢重编程、遗传及表观遗传重塑,提高基因转录及蛋白翻译活动,加强对组织内营养物质的掠夺,使得自身朝向更有利于高速增殖的方向进化,通过生存竞争模式反向“挤压”正常细胞生存空间。在提高自身增殖能力的同时,肿瘤细胞也会释放“破坏因子”干扰邻近正常细胞的增殖能力,双管齐下获得生长优势。例如,2021年有研究发现Apc突变型肠癌肿瘤起始细胞通过分泌NOTUM这样一种“破坏因子”,关闭周围野生型细胞生长所需的Wnt信号通路,从而抑制邻近细胞的生长并诱导其凋亡,实现早期肠癌克隆的形成和生长[7-9]。总体来看,营养争夺是细胞竞争胜利的关键,在诱导正常细胞死亡后,肿瘤细胞进一步吸收后者释放的代谢营养物质,以正反馈的形式进一步促进自身增殖。
当肿瘤起始细胞通过生存竞争打败邻近细胞建立早期癌症克隆后,新的难题又出现在面前。首先,随着肿瘤细胞增殖的加快(小兄弟越来越多),光靠克隆周围“贫瘠”的土壤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队伍,如何获得足够营养支撑是驱使癌症下一步进化的首要动力。只有与机体最庞大的营养物质运输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建立联系,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生存问题。然而,并非所有的早期克隆都紧邻血管,如何建立癌症克隆与血液循环系统的联系是进化首要考虑的问题。“要生存,先修路”这一理念同样符合癌症进化方向,即建立肿瘤自身的血管系统,连接血液循环并源源不断将营养物质输送给克隆内部的肿瘤细胞。肿瘤的血管生成现象最早在1940年就已被确认发现。1972年,肿瘤血管生成研究的先驱福克曼(J. Folkman)就提出了靶向血管生成的抗肿瘤思路,成就了后来一系列的抗血管生成药的诞生[10]。经过近50年发展,目前主流理论认为肿瘤的存在诱导了血管生成,肿瘤的生长受周围血管所控制,而抑制血管生成可引起肿瘤的休眠,新血管的生成又促进了肿瘤的生长。此外,血管生成也是癌症从早期同质化的肿瘤细胞克隆,成长为成熟的肿瘤微环境的关键步骤,是癌症形成的重要标志特征。
然而,福祸相倚,肿瘤克隆通过连接血管获得机体营养物质的同时,也会引起循环免疫细胞(免疫警察)的注意,从而开启癌症进化之路的另一场“反围剿”斗争。以巨噬细胞为代表的“侦察兵”——先天免疫细胞会通过血管首先到达克隆部位,一方面分泌大量炎症因子攻击杀伤肿瘤细胞,同时发射救援信号“呼叫”适应性免疫系统,如T细胞和B细胞等联合围剿肿瘤细胞,发挥对癌症早期克隆的免疫监视及清除功能。因此,躲避免疫监视和抵抗杀伤成为癌症进化新的内在驱动力。一方面,肿瘤细胞会学习正常细胞与自身免疫系统的互相识别机制,让免疫系统误判为“自己人”。例如,为防止免疫细胞过度监视造成损伤自身正常组织,正常细胞会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类似身份证),在遇到免疫细胞时,向对方亮明身份以避免被杀伤清除。而肿瘤细胞也利用这套机制通过提高自身表达包括PD-L1,CD47和CD24等检查点分子,分别迷惑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等,从而躲避免疫细胞的识别和杀伤,这一过程称为免疫逃逸机制[11]。与战胜正常体细胞类似,除增强自身躲避免疫识别的能力外,肿瘤细胞也会采用“策反”战略化敌为友,通过直接相互作用或者分泌因子改造免疫细胞。例如,充当“侦察兵”的巨噬细胞会被诱导从抗肿瘤的M1型转化为促肿瘤的M2型,或者杀伤性T细胞被解除“武装”而成为不具有攻击力的耗竭性细胞等[11]。简言之,肿瘤细胞通过武装自己、瓦解敌人这一套组合策略,最终实现免疫逃逸,赢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除免疫細胞外,宿主中包括成纤维细胞、脂肪细胞、神经细胞、间充质干细胞等多种类型的细胞都会加入“围剿”癌细胞的战斗序列。然而,癌细胞均采用与体细胞、免疫细胞斗争的经验进化生存,并充分利用“策反”战略使这些类型细胞转变为有助于癌症发生发展的“帮凶”。此外,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肿瘤细胞还会充分利用血液循环系统调用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外源微生物的代谢物及活菌体等,进一步促进自身增殖、增强进化动力,从而建立起一个涵盖多种类型细胞、连接血液循环系统、具备强大抵抗力和战斗力的生态系统——肿瘤微环境。
当肿瘤微环境完全在原发器官建立完成时,已从最初的肿瘤起始细胞成长为“一方诸侯”的癌症,为继续扩大影响力,需要从原发灶部位启动转移建立跨器官的“新殖民地”——转移灶。转移既是癌症进化的末期事件,同时也可理解为新肿瘤开启的“海外”进化之旅。首先,哪些组织器官适合定植转移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肿瘤微环境部位会释放大量因子通过血液系统转移到各个靶器官,通过对驻地组织细胞进行重塑来建立适合癌细胞生存的转移前微环境。同时,这些先遣部队可能会通过重塑后的转移前微环境释放信号反馈给原发灶癌,启动肿瘤细胞的转移。被选择的肿瘤细胞则会从增殖状态转化为更适合移动的转移状态,从而增强自身的迁移和侵袭能力。这些转移肿瘤细胞从原发灶出发,通过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转运到继发性靶器官定植,这一阶段的肿瘤细胞称为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 CTC)。CTC在转移过程中会遭受血液流动的剪切力、循环免疫细胞的攻击、靶器官“原住民”细胞的生存竞争,它们历经“九死一生”才能在转移器官逐渐建立定居点,完成转移进程。

原发灶的哪些肿瘤细胞更倾向于发生转移是目前困扰科学家的一个难题。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增殖能力强、生存力旺盛的“领头”肿瘤细胞可能会率先加入到转移队伍中去开疆拓土。然而,从进化生物学角度看,这种主动“牺牲”的精神却不一定符合真实情况,尤其考虑到当肿瘤细胞在原发灶已先后打败正常体细胞及免疫细胞后,微环境内部的肿瘤细胞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生存之争,那些“优胜者”细胞是否有需要去开启一场冒险之旅仍有待商榷。近期的一项研究认为,是原发性肿瘤内部细胞竞争的“失利者”,即那些适应度不太好的细胞被迫转移到机体循环中,并在远端器官中定植生长发展为转移灶[12]。由于这些细胞增殖能力弱,它们甚至会在到达转移灶后启动休眠状态,从而保存自身实力并规避“原住民”细胞的竞争和攻击,待到环境逐渐合适时再启动增殖状态。这些潜伏期的转移细胞也是造成转移难以发现及完全清除的重要原因[12]。然而,无论哪种理论,癌症转移都是一场艰难的生存之旅,是癌症进化论的“终极之战”。
2022年,最新公布的癌症标志特征列举了肿瘤的14种典型特征,有助于我们透过癌症表型去深入理解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变化[13]。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包括基因组失稳、抵抗细胞死亡、逃避生长抑制、持续增殖信号及无限复制能力等五大特征,是癌症早期进化用以规避自身抑癌基因及邻近正常体细胞监视、初步建立癌细胞克隆所需要的生存技能;而促进血管生成、逃避免疫清除、肿瘤促炎作用及微生物多态性等特征,则是癌症从单纯克隆到建立肿瘤微环境过程中通过进化获得的技能;激活侵润和转移及细胞衰老等特征则是与癌症转移密切相关的进化标志。能量代谢重塑、解锁表型可塑性及表观遗传重塑等特征则贯穿癌症进化全过程。正如生物进化论所述,癌症进化也是肿瘤起始细胞改变自身获得更强生存技能的学习之旅。

因此,目前的抗癌策略也是围绕对抗癌症进化获得生存技能展开,例如传统的放化疗策略和靶向药物PAPR抑制剂,是围绕基因组失稳特征,选择性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抗血管生成药物主要是阻断肿瘤获取营养物质以达到“饿死”癌细胞目的;包括EGFR抑制剂在内的一系列信号通路抑制剂,均是为了阻断癌症获得无限增殖能力。此外,如今最知名的癌症免疫治疗策略,如PD-L1抑制剂(即人们常说的“O”药、“K”藥)主要是阻断肿瘤免疫逃逸机制,提高机体免疫细胞对肿瘤的杀伤效果。然而,目前这些治疗策略或多或少存在靶向性差、响应率低及易耐药等难题,这也说明治疗过程中肿瘤细胞会进化出新技能以适应更加艰难的治疗环境。
从生物进化本质来看,癌症被认为是多细胞生物如人类高度分化细胞出现的返祖现象,即获得单细胞生物具备的无限增殖能力。从癌症进化的角度来看,如何在进化早期提高对癌前病变细胞的监测及清除,可能是根治肿瘤最好的突破口,也是目前开发癌症早筛策略的立足之本。在此方面,正常体细胞与肿瘤起始细胞的“兄弟之争”是决定癌症进化的关键事件,如何增强正常细胞的增殖能力是癌症早期防御的关键,也是目前科学家在预防早癌中大力推进的研究方向。然而,现实却有不良饮食、酒精、压力、衰老等诸多环境因素,通过损伤上皮组织、削弱其监视和清除早期克隆的能力,导致肿瘤更易发生发展。另一方面,考虑到癌细胞本是机体的一部分,如果能够在实现共存的条件下阻滞其进化转移,也可能是治疗癌症的一种策略。如果癌症进化不可避免,那么减缓其进化速率,让癌症成为一种慢性病,与生物体一起衰老,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思考及应对策略。
(致谢:本文相关研究受到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2020YFA0803200项目支持,韩毅对插图绘制提供了帮助。)
[1]Mel Greaves. Cancer: the evolutionary legacy. Nat Med, 2000, 6(5): 496.
[2]Levine A J. p53: 800 million years of evolution and 40 years of discovery. Nat Rev Cancer, 2020,20(8): 471-480.
[3]Gerstung M, Jolly C, Leshchiner L, et al.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2,658 cancers. Nature, 2020, 578(7793): 122-128.
[4]Baslan T, Morris IV J, Zhao Z, et al. Ordered and deterministic cancer genome evolution after p53 loss. Nature, 2022, 608(7924): 795-802.
[5]Vishwakarma M, Piddini E. Outcompeting cancer. Nat Rev Cancer, 2020, 20(3): 187-198.
[6]Colom B, Herms A, Hall M, et al. Mutant clones in normal epithelium outcompete and eliminate emerging tumours. Nature, 2021, 598(7881): 510-514.
[7]Flanagan D J, Pentinmikko N, Luopajarvi K, et al. NOTUM from Apc-mutant cells biases clonal competition to initiate cancer. Nature, 2021, 594(7863): 430-435.
[8]Yum M K, Han S, Fink J, et al. Tracing oncogene-driven remodelling of the intestinal stem cell niche. Nature, 2021, 594(7863): 442-447.
[9]van Neerven S M, de Groot N E, Nijman L E, et al. Apc-mutant cells act as supercompetitors in intestinal tumour initiation. Nature, 2021, 594(7863): 436-441.
[10]Folkman J. Tumor angiogenesis: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N Engl J Med, 1971, 285(21): 1182-1186.
[11]Hiam-Galvez K J, Allen B M, Spitzer M H. Systemic immunity in cancer. Nat Rev Cancer, 2021, 21(6): 345-359.
[12]Kim K, Huang H, Parida P K, et al. Cell competition shapes metastatic latency and relapse. Cancer Discov, 2023, 13(1): 85-97.
[13]Hanahan D. Hallmarks of cancer: new dimensions. Cancer Discov, 2022, 12(1): 31-46.
关键词:癌症 进化 生存竞争 免疫逃逸 靶向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