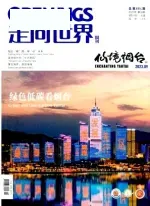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
孙文韬
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作为一种富含文化温情的视觉意象,寄托了古人的家国情怀。关隘、山险遗迹相对应的“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对于不同知识结构和阅历的受众来说有着不同的感受。
“关山意象”接受的不同理解和接受区别造成不同类型的受众。大体分为感动型、震撼型、分析型。其中感动型的受众,相信是感动于雄伟的齐长城景观给人们带来的历史沧桑感,吟诵诗文的兴致极高;而震撼型受众则是对齐长城遗址景观的整体体验较为丰富,对齐长城遗迹景观绘画所呈现的遗迹残缺美,报以认同;分析型则是更加高级的类型结构,其接受群体充满着对齐长城遗迹景观绘画历史的想象和现实的感悟,对齐长城遗迹景观绘画理想化表现有接受意愿。
此种审美的接受体验,要得益于齐长城文献的呈现程度。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表现的不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更是古人精神意念在文化遗产遗迹中的传承发展,是今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心灵景观。从山水画文脉发展来看,五代宋初的山水画大家李成长期居住在山东的营丘,此地地处齐长城遗迹景观密集的鲁中山区,他的山水画在景物表现方面,突显寒林烟树的特点,并且有表现遗迹景观的作品《读碑窠石图》传世。碑碣久远,行人抚古追今。建筑无存而寒林仍在。通过对画面的读解,观赏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心绪像寒林一样,寒而不荒,蕴藏生机。碑石所代表的遗迹景观,透过历史的烽烟、变乱,顽强地守护着文化传承的内核,以待来者。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使得遗迹景观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传播得更加久远。景观地的自然景观风貌,不是一时能够感受到的。所谓“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不同的时令、气候、光照,同一景观地会呈现出不同景观样态。如前文所述齐长城遗迹景观在冬季其荒寒的景象撼人心魄,衰草连天,枯枝老干,与齐长城墙体呼喝应合,为人们诉说千年历史风烟。而春雨霏霏之际,草木萌发,齐兵营四周绿意盎然,促使人们在郊游踏青之际,感念先人。而这一切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感觉体验到的,所以要借助他人的感知、体验数据,那么这些感知体验数据就是非常可贵的齐长城景观的文献。所以对齐长城景观文献的研讨还应该扩展到对其景观四季不同变换等因素上。“关山意象”是文献与画面的互动乃至融合的纽带。对于“关山意象”的探讨、分析,有助于对优秀景观绘画作品的赏读、理解和认知。
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作为一个充满文化温情的系统,包含着人与天地万物的沟通。联系着齐长城文献与其遗迹景观的艺术呈现之间的关联。如果说我们引用阿恩海姆的观点来评述中国古代山水画,是一种力的图式被动解读。如果当代信息背景下的遗迹景观山水画呈现止步于此,只是停留在遗迹景观绘画本身,那么其意义便有局限性。然而,此作品并未止步于此,画面中的山石、树木、云烟都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凝结于画面右侧。这种调动观者视觉先抑后扬的过程宛如戏剧的表现,由创作者与观赏者共同完成画面、构建画面。题跋既是对画面中沧桑建筑的描述,又是以现代人视角,用山水画笔追诉历史记忆的过程。从修建年代、功能作用、施工工艺等多方面描述,将文献中的齐长城和山水画中的齐长城联系起来。遗迹景观的背后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及性格体现,而这种体现则是基于表达者对这种文化和性格的主观认知。

如果离开了表达者的主观认知,那么再好的遗迹景观也会是毫无生命力的苍白状态。当然,主观认知是建立在历史长河中的反复对比、反复甄别、反复反思的理性之上的。齐长城遗迹景观的山水画呈现,是借助齐长城遗迹呈现历史印记,是关于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关山意象”与山水画、山水诗又联系紧密,“关山”题材是山水画主题之一。在传统文化情境之中,文字与图像在对遗迹表达上相迭互映。对于齐长城关隘、山险遗迹来说,山水画呈现更能明确山体景观特点,彰显其文化历史意义。根据阿恩海姆所说“楔形能够产生动力”的理论进行分析,此作品在畫面中部有树木作为画面的支撑,山石旋动起伏于画面左侧,经由层积块垒的山体进入主峰的表现。从画面中可以得知,山石的外部形态,树干的积聚形态,田野的分布形态,山石的累积形态,皆为动感十足又不失稳重的楔形结构。单个楔形形态的张力结构,在不同的物象表现过程中,“异质同构”达到视觉动力接续的目的。

大峰山齐长城遗址公园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齐长城起点附近,齐长城墙体绵延大峰山顶一千多米,临崖览谷,易守难攻。再加上近百间屯兵营房,带给人们巨大的视觉震撼。关于齐长城古籍早有记载,《管子·轻重篇》曰:“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齐长城建于2600年以前,为多代齐王历百年渐次兴建。司马迁《史记·楚式家》中载:“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洲,千余里以备楚。”齐长城西起山东长清县孝里镇南部,向东至青岛小珠山入海。历经千里,绵延1300余峰峦。齐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长城。齐长城在谷口平地为素土夯筑,山岭之上则为石块垒砌,就地取材,方便施工。大峰山齐长城遗址位于长清区孝里镇齐长城起点附近,是集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于一体的遗址景观公园。其景观有全国唯一的保存最完整的战国时期齐长城遗址墙体与阵容宏大的屯兵营。大峰山齐长城是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西段起点流传地。山腰有兴建于金元时期的道观峰云观、齐鲁第一洞——璇玑洞,还有古城门、抗日战争纪念馆。大峰山可谓多重景观演绎历史,一城高悬铭记齐风。不管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还是从东西方的区分来看,景观绘画图像的语意内涵,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意识、声音所映迭。新技术条件下,遗迹景观有其自身丰富的传播管道,不一定非要借助绘画来完成其空间营造与空间体验的要求。但是富有历史沧桑感与绘画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景观这另当别论。景观借助绘画来显图呈像,是将文化遗产景观的视觉文脉最大限度地保留、保护,并为遗迹景观的当代转向传播提供有深度的、有文化温情的遗迹景观绘画图像。山东药乡国家森林公园是1992年经国家林业部批准的国家森林公园。是一处难得的有林场背景的齐长城遗址景观公园。公园最高峰黄尖山海拔千米,山势巍峨,如刃刺天。植被覆盖率高,树木品种繁多,行进于山中树荫繁密。所谓药乡以盛产药用植物而得名,地处泰山之阴,钟灵毓秀,盛产泰山四大名药的何首乌、紫草、四叶参、黄精及赤灵芝等中药材180余种。传说药王孙思邈曾在此地种药采药,今建有药王庙以纪念。该区域位于高耸的黄尖山一带,以齐长城遗迹为主要景观。齐长城是世界长城之祖,是古代齐国连山接海的浩大的综合防御工程。其残存墙体若巨龙起伏于山间谷底,给予后人凭吊历史、感念先人的重要景观。此区为封山育林场所,松树高直挺劲,与长城景观相呼应。秋高时节有红叶漫山遍谷,红叶学名黄栌,在古战场、长城下,大面积红叶景观更添厚重的历史感、沧桑感。虽历经千年沧桑,仍屹然伫立,属于亟需保护的荒野遗址景观,然而现有的文物遗迹保护工作中往往忽视对遗迹景观的当代意义、价值的发现,目前的景观绘画创作往往过分倚重观念的演绎,模糊文化界限,丧失传统滋养,特别是景观绘画创作目前倾向充满制作,崇尚块面笔触,轻视线性表达。齐长城逶迤曲折,跌宕起伏,绵延千里,是齐鲁大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一卷历史,一砖一石,都勾勒出血与火的篇章。此区内林木繁茂,松柏苍劲,景观四时有别。景观特点概括为:古、旷、秀。风门道关是齐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隘,位于莱芜、章丘、博山三地交界处,关口位于高山垭口处,南北有很陡的山坡,无风成三级,大风飞沙石,被当地村民称之为“黑风口”。由山下的三个平原、坡地为主要景观的村庄,到以悬崖、峰峦为主要景观的卧云铺村、逯家岭村,有一条柏油路相贯穿。对外宣传为,一线五村。由谷及岭,由河及溪,山随境转,线状分布。山水画呈现的视域范围加大,使得山水画的散点呈现特点得以发挥。
卧云铺人用的石头大都取材于村顶的山石,叫“十八行子”。“紧十八,慢十八”,十八是庄户人家对“多”的统称。不管是山岭上的齐长城,还是古村的住宅,都是先民们开山凿石,用血汗营建的景观。根据石头的大小厚度与色泽硬度,卧云铺的先民们将打磨好的石块称为“十八行子”。石块营建着长城、修补着道路、垒砌着房舍、增添着希望。卧云铺人眼中的景观,是石块搭建的,亲切的称之为“子”。逯家岭村是真正意义上的悬崖村庄。在村庄里,可以直接眺望齐长城遗迹。此处齐长城遗迹景观绘画呈现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齐长城遗迹与传统民居村落相得益彰,为遗迹景观山水画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首先,齐长城遗迹景观山水画呈现,寄托了古人的理想和追求。齐长城是古老的遗迹景观。在这遗迹景观之中,我们可以感到历史的苍凉和时光无情。任何伟大的景观,都在建成的那一天起,走向衰亡。这是无法阻止的自然规律。在遗迹景观的山水图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追溯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思古之幽情。而即便是荒野一般的遗迹景观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功业遗存。家国情怀,是我们在遗迹景观绘画中感受到的深层寓意。
其次,齐长城遗迹景观的山水画呈现,是今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心灵生活体验之所。“关山意象”的达成也基始于齐长城遗迹的物质遗存和“关山”题材山水画呈现的精神传续。
视知觉形式动力理论也为我们理解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提供了方法基础。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是不断演进嬗变的。从初始形态的地图呈现发展至山水画呈现,在北宋形成经典样式与成熟图式,进而在明清之际注重笔墨语言内美的发展,笔墨的情思灌注与视觉形式张力日益丰富。这一趋势也反映在现当代对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上。
《齐长城寻踪之大峰山》,就是以山水画方式记录大峰山齐长城遗迹景观的分布特点,样貌特征。结合山脉、丘陵及齐长城自然景观与历史典故,将山顶的齐长城遗迹与山腰的峰云观等古建筑,组织在游移变动、层迭互联的山水画格局中,共同营造“风云变幻,亘古如兹”的齐长城遗迹景观氛围。齐长城沿线古道众多,犹以济左走廊、博池古道等历史悠久、古迹众多的道路闻名遐迩。关隘、古道与古民居是相依伴生是齐长城遗迹景观的组成部分。“古道关联着山顶的齐长城和山脚下的古民居。古民居又是许多节庆民俗活动的背景、舞台。齐长城起点附近的方峪古村、莱芜茶叶口镇的齐长城一线五村、淄川涌泉等古村落皆为遗迹景观与山川景色并美的绝佳去处。”这对于山水画创作来说,表现题材是极为丰富的。笔者作品《齐长城寻踪之博池古道》,就是以淄川齐长城遗迹景观中颇具特色的齐长城博池古道、涌泉民居为表现对象,描绘夕照中古道隐现于齐长城遗迹景观之中。昔日古道的功能已经从货物商旅的通途转换为旅行揽胜的幽径。
齐长城遗迹景观山水画呈现的空间形态,值得我们去深入理解、研究。齐长城遗迹景观永恒的生命力,需要后人,不断探索、印证、发展、完善。遗迹景观绘画呈现的画面中,空间形态总是丰富而齐全的分布于画面。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观察得知,城市、田园、荒野在和谐宁静的氛围里,向我们诉说着遗迹景观的变迁。城市象征文明在画面远方。田园在文明与荒野之间。而在洛兰笔下的经典构图里,近景总是点缀罗马建筑的残垣断壁,中景出现罗马乡村的明丽静谧,远景群山连绵。遗迹景观的空间形态,从近景的残缺暴露状态,到中景的完整和谐状态,再到远景的空无荒蛮状态。有序的空间形态过渡,将深刻的景观审美意蕴涵于其中,奈人寻味。遗迹景观经典的空间形态,同样存在于东方景观绘画中。传五代董源《龙宿郊民图》、北宋郭熙《早春图》、南宋马远《踏歌图》都有一致的空间形态表述。近景为田园乡村,茅屋篱舍的形态,渔人农人的生产生活,富裕而安定;中景为皇家宫苑,有烟云围护,山水相临;远景是空蒙的山色。在帝国都城的郊野,在帝王勤勉的统治下,呈现百姓安居乐业、政治清明的景象。不管是由城市观看田园,还是由田园观瞻城市。不同的视角,都是全面表現多重空间形态。这给予齐长城遗迹景观绘画呈现的实践以极大的启迪。
齐长城遗迹“关山意象”山水画呈现的艺术语言本身具有承传性特点,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语言不断“因、革、损、益”的发展,有艺术语言内部的“动力”诉求。随着时代发展,现实语境的变革也使得景观绘画外部承载“变革”诉求。而时代的快节奏发展,无法等待遗迹景观绘画呈现自身艺术语言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外部变革的诉求,使得遗迹景观绘画呈现失去了往日的依托,无法正常在自身艺术语言的追求中,因循过往、革除弊端、损其残缺、益之发展。在时代背景之下,联系与遗迹景观绘画呈现相近学科,共同寻求跨界合作“多点互联”式的创新,才能更加适应如今的现实语境。
当今,图像信息已经充满了人们的视听空间,现实语境是极其激烈的图像话语权之争。遗迹景观绘画呈现汇集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心灵景观,根据时代面貌重新考虑遗迹景观的文化意义。新时代的背景下,遗迹景观绘画呈现应依托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再现,充分体现心灵景观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契合,突现“人”在遗迹景观中的价值意义。“天地仰生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文化根脉在“生生不息”的增长。生成图式的创作过程是建立在预成图式创作过程基础上的。比较显而易见的是遗迹景观绘画构图的多变。以建筑景观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绘画,偏重屋宇的稳定。遗迹建筑的立面与画面边角往往是垂直关系,在绘画中的生动性就有损失了。斜向、曲向等形线语言的介入,才能使遗迹景观绘画呈现生成图式。从对遗迹景观的形貌观察做起,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齐长城遗迹的墙体、关隘。人们体验与观察的视角发生转变,从远距离观看转向为多角度审视,从单一的突显遗迹景观到多义表达呈现遗迹景观中人格意识的存在。

齊长城遗迹景观山水画是心灵景观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契合。景观绘画的主旨是在创造人的心灵景观的外显,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内求。景观绘画的创造,就是在自然与人之间构建精神的景观。分析“意境”这个词汇,来解释说明景观审美的二重结构,借助景观人们将自然与人相联,借助景观绘画,人们将“意”与“境”相联。清代著名山水画理论家笪重光在其著作《画筌》中强调“意之所至”与“实境”“真境”“神境”相联系,既非客观真实的再现景观事物,也非主观随意的表现景观事物。主客相融、思与境偕,方是景观绘画的入境创造,才谈得上作品为观赏者提供视觉上的入境体验。
The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Qi Great Wall relic is the fusion of spiritual, natural and cultural contents. The main idea of landscape painting is to manifest the innermost thinking of people, which tallies with their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s of nature. The creation of landscape painting is to reproduce the landscapes in a professional and compliant manner. The phase of “artistic conception” can exemplify the dual structure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If we say that, the landscape connects nature and people, then the landscape painting gives aid to mix the spiritual and the solid. Neither duplicating mechanically nor reproducing arbitrarily, it’s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for creating the brushwork and giving 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