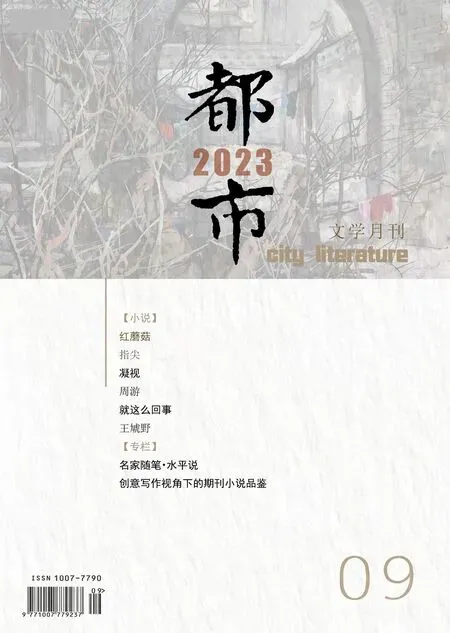三缺一
文 燕青
1
看着郝仁两手倒腾着手机,弓着背,吧嗒着个拖鞋,从卫生间出来,转向卧室,又穿过客厅到了阳台,贼头贼脑地盯着母亲的卧房,轻轻一叹,又杵到了厨房。勤就觉得自己的脑袋又大了:“哎哎哎,你能不能别晃悠啦!舅又不是第一次来。去去去,这一会会儿,来来回回快二十趟啦。”
“哎,轻点、轻点、轻点。”郝仁见勤把南瓜剁得咚咚响,赶紧拉着媳妇的衣角,“哎,轻点、轻点,让舅听见,还以为是咱们不想收留他呢。”
“就他事多。”勤嘴一撇,“你也知道你舅是个刺头啊,一年到头不知来多少趟。每次都好烟好酒供着,鸡鸭鱼肉吃着,走时,还大包小包拿着,就这也听不到他一句好。”
“他就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嗯,细想想,也是个可怜人。”勤把南瓜块放进盘里,又弯腰从柜子里抓出一把细粉条,郝仁可不干了:“宽粉宽粉!我不爱吃细的。”
“爱吃不吃,就你舅,”勤睕了他一眼,“顶天立地一颗牙,牙下能过万千鸭,你确定要给他吃宽粉?”
“忘了忘了,”郝仁一拍额头,“媳妇,还是你心细啊。”
“别贫嘴了,剥葱捣蒜去。”
郝仁拿葱蒜,还不忘问面和好了没。
“误不了你的事。”勤叮叮咚咚一阵响,油锅哧哧啦啦满屋飘香,“你确定还能去?”
“那有啥,舅有老妈陪着,况且,这小酒一下肚,村里的事哗哗哗给你往出倒,你再给他泡上壶好茶,他还能顾上我?”
郝仁麻溜地把酒瓶、酒杯、碗盘、筷子摆好,吆喝老母亲和舅舅吃饭。
“哎哟哟,这勤媳妇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在屋里就闻见香了。”六十多岁的舅爷搀着老姐姐的胳膊,直夸勤做的饭菜香。
“香就多吃点,你一个人,一天到晚就是瞎对付了吧。”八十岁的老母亲半天没夹住块猪头肉。
“姐,来来来,张嘴。”郝仁舅舅夹着一块颤颠颠的猪头肉,起身就往姐姐嘴里送。
老姐姐直摆手:“我不吃我不吃,我是要给……”话没说完,滑溜溜的猪头肉已经被弟弟喂进了嘴。
“用勺子吃吧,”勤白了郝仁一眼,“勺子呢?”
老姐姐把勺子给弟弟递过去,“多吃点,勤专门给你做的,软软糯糯,”又把半盘虾酱豆腐扒拉到弟弟碗里,“吃完饭,让仁儿带你去镶个牙。”
郝仁一听,正夹着菜的手微微一定,勤扑哧就笑出了声。
郝仁就当是没看见勤幸灾乐祸的样子,镇定地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咿咿呀呀哼哼了半天,“舅,下午排满了,明早再去。”
舅舅没意见,满嘴行行行。
勤憋着笑,眉毛直跳,五十多岁的人了,糊弄起老人来,脸不红心不跳,看我怎么揭穿你。勤身子一动,郝仁赶紧就喊,面软乎点啊。勤眼一瞪,牙还没全露出来,老太太朝郝仁碗上一敲,悄悄吃你的吧,这还要你告?勤朝郝仁挑挑眉,咋的,哼!
面刚进锅,郝仁就拿着漏勺满锅搅,“再等等”,可郝仁实在是等不上了,桌上的手机不是振动就是哇哇直唱。老太太眼一瞟,郝仁赶紧解释,“舅,您慢慢喝,我下午要去开个会。”
“咋不接电话?”老太太筷子一指,“就在这儿接。”
“接接接,这就接,”郝仁一脸的正儿八经,“哦,知道了,车马上就到楼下?”
“去吧去吧,工作要紧。”红光满面的舅爷倒是痛快,可牙口不争气,门牙缺岗,老牙松晃,吃个东西还得打对半天。
老姐弟俩一个走风漏气地说着,一个耳背打岔地应着,勤坐旁边笑着。只有郝仁连吞带咽,三下五除二吃完就拽了一张纸巾,急匆匆跑了。勤急急忙忙跑到茶几旁,拿上新沏好的茶追了出去。
2
还没进屋,郝仁就听见王继光喊各就各位,然后就是“吱”“滴溜溜”紧随其后的报数声,郝仁进门先丢骰子。对面又粗又壮的王继光把椅子往桌前挪了挪:我就不信,你能丢个12?话完骰定,12!
郝仁坐庄。落座、整牌。今天的牌出奇得顺,起手就自绝一门,将有搭子够,出了三张牌,就听口了。他抿了一口水,靠在椅背上,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郝哥这是偷吃杏了?人们这门还没绝完了,你倒上架了。”上手的张小猛是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可也不能怕点炮就拆搭子呀。”
王继光大手一挥,还没张嘴,下手的吴德回过头,对着身后坐在沙发上钩帽子的女人慢言细语:“何仙姑,没听见王继光嚷嚷好半天了,你咋还没给他把水杯端过来?”
“来了来了,”被称作何仙姑的女人应着,提了一个大玻璃茶水壶挨个给大伙续水,到王继光跟前时,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站着。吴德一双绿豆眼直滴溜:“咋的,这光哥身上有蜜呢?”
正捏着一张牌提起来插进去,扒拉开又放整齐的王继光顾不上吴德的调侃,他眉头紧锁,自言自语:“我和他绝的是一门牌,这张?舍不得,那张?也不安全。”
“哟哟哟,照三家,照三家,这一家就照不住了?”吴德这薄嘴唇吧啦吧啦,激得王继光恨不得把牌塞进他嘴里。
王继光直起身来,仔细看了看郝仁面前的几张牌,他把面前的几张散牌插进去,又把两搭万子牌端出来,挑熟张打。
何仙姑也不急,等王继光喝完添满后,才提着壶,给里间那桌续水去了。
郝仁看着王继光的这一操作,心里也是暗暗佩服,“照三家”这个尊号,真不是浪得虚名,他一贯是照庄家管旁家,一人看三家,别看粗喉咙大嗓门,可一打起牌来,比那张飞穿针还要仔细。赢他一回钱,那是老虎嘴里拔牙——难了。不过,下了牌桌,但凡谁开口想整两口,光哥不论输赢,家里、饭店任由哥们挑,大餐、小菜随便点,白酒、啤酒管够。
这下轮到张小猛犯愁了,“这张牌不保险。可咱也是七对一上一听呀,总不能怕点炮就弃胡吧,一家上架正常打。”张小猛搓着手心里的2 筒忐忑不安,这张牌是郝仁一上架就接上的,按照常理,这张牌的点炮性是非常大的,可自己的牌面也很大。就在张小猛犹豫不定的时候,吴德又在催牌了。张小猛一个不耐烦:“催啥催,2 筒。”
郝仁也不说话,牌面翻起。
卡2 筒的龙!
大家瞠目结舌,好家伙,一上来,就是一条龙。
“催催催,歇心了吧。”张小猛对着吴德就是一气,“打牌就安安静静打,你催催催。三年还等不上个闰腊月,我就不信你没有出牌要想算的时候。”
王继光抿着嘴,把握在掌心里的一张牌轻轻混进牌里,正想推牌时,何仙姑瞅准,抓起来一看,2 筒,她什么也没说,眼角斜了一眼王继光,厨房里的水壶嘘嘘嘘叫着,何仙姑赶紧灌水去了。
“千刀万剐不胡第一把。”面对张小猛的一顿猛喷,瘦吴德也不接茬,他眯着眼睛,一吞一吐,四五个烟圈就连绵不断地晕化开来。
郝仁抽了一下鼻子,可他没有发作。这里,谁都知道郝仁前几个月刚做了个小手术,不能闻烟味,所以,王继光、张小猛他们几个都是不吸烟的,今儿,这吴德是怎么了?
张小猛刚要开口,郝仁左手碰了他一下,摇摇头。王继光看看郝仁,看看张小猛,又看了看吴德,他咳嗽了一声,吴德还是揭牌、碰牌、出牌、吸烟吐圈,照旧。王继光把椅子往后推了推,重重咳嗽了几声,瘦吴德还是照旧。
“老吴,”王继光扣倒牌,一脸的平静,“咱能不能不吸烟?这郝仁兄弟……”
“没事没事,”郝仁见涉及自己,赶紧出来打圆场,“一半支没事,少来点不碍事的。”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人家还不嫌呛,你咋倒有说头了?”吴德斜眼喷出一口烟,“噗”将一口痰吐到地上。
听到动静的何仙姑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哎,大兄弟,你这就不好看了吧,不要说是为郝仁兄弟,就是为了你自个,大家伙劝你少吸烟也是好心的呀。你说你,不听劝就算了,这怎么还往地上吐痰呢?”何仙姑说着,转身便要去找笤帚。
“哟,吴科长,你怎么也来这低俗场所,不务正业来了?”里屋的几个看打麻将的女人不知道啥时候也出来了,“大波浪”红姐应该是和吴德熟络的。
吴德先是一愣,嘴角一扯:“娱乐娱乐,消遣消遣而已。”
“哟,我可记得,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何仙姑拿来扫帚,张小猛地抢过来扔到吴德面前,说道:“让他自己扫,公共场所不能随地吐痰,更何况这是家里,吴哥,你这是要恶心谁了。”
“要你管?我想吐就吐。”吴德看着这么多人针对自己,“你们仗着人多欺负我。告诉你们,老子也是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人,呸。”
吴德低头吐痰的脑袋还没有抬起来,就被一巴掌甩得连人带凳子跌在地上,水杯咣当落地,吴德的手恰巧又按在了玻璃碴上,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号叫声。
众人一愣,都不知道王继光啥时候出的手。
“我忍你好多次了,既然你屡教不改,那我就帮你长长记性。”
“两个奸夫淫妇,你们以为你们俩眉来眼去的,老子没看出来?”吴德指着王继光和何仙姑,一脸的狰狞。
“你你你,你!血口喷人!”何仙姑浑身发抖,俊俏的脸上血色全无。
王继光又一脚踹过去,吴德捂着屁股蛋哭爹喊娘。
郝仁要去拉王继光,被张小猛一把拽住:“死不了。嘴上缺德没个把门的东西,就应该好好修理修理!”
王继光身子一晃,脚还没有抬起来,吴德那边又号叫了起来:“杀人了!杀人了!”
刚刚被吓愣的女人们,也都缓过劲来了,她们捂着嘴巴,一阵偷笑。红姐拍着何仙姑的肩膀,瞪了眼坐在地上号叫的吴德,拉着她坐在沙发上:“和这种吃人饭不办人事的东西生气,不值当。”
有人摁住王继光,有人接过扫帚,有人扶起凳子,还有人蹲下拣大块的玻璃碎片,就是没人去扶哇哇叫的吴德。
“滚!”怒气难平的王继光,一声暴喝,吓得吴德抱着脑袋就跑。
“好了好了,继续玩吧。”红姐轻声细语,那几个女人也小声议论着,各自归位了。
“你说你们咋就把这个瘟神给招惹来了呢!”红姐直皱眉头。
“那天三缺一,李大爷看见他在楼底下溜达,就叫上他来凑数。”何仙姑直抹眼泪,“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啊。听李大爷还称他是什么科长、股长来,又看他穿戴得齐齐整整,还觉得他不赖。今天,是他自己来的。”
“哼!人模狗样、欺软怕硬的缺德货,靠着自己手里有点小权,克扣底下人的工资,自己买楼买车,女人都换了好几个了,到头来,还不是一个个的从他手里撬钱?”红姐拍拍何仙姑,又看看大伙,“郝仁兄弟,今天手气不错?来,我上。咱们是继续还是重新开始?小猛子,看姐今天咋收拾你!”
“你们两个是‘鬼见愁’,不能放一块。”
张小猛虽然被红姐收拾得够呛,但他年轻气盛,脖子一梗:“来就来,谁怕谁。”
郝仁忙摆摆手:“重来重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刚才就算是练手热身吧。”
3
刚刚安顿好这桌,门外噔噔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不用看,一定是高志远。何仙姑赶紧把靠墙的麻将桌拉出来,将四把铺着厚垫子的靠椅摆好。这两桌,前后错开,专门窝在客厅与厨房中间,厨房的玻璃推拉门一关,对流风吹不着,并且一年四季开着灯。两人之间,再放个小凳子,让老人们放杯子。这下,挂包包、放水杯的地儿全有了。岁数大了,就喜欢热热闹闹,可一打开麻将,却又喜欢安安静静,你说让他们去卧室里吧,嫌憋屈,去客厅吧,不是说风大,就是说人来人往,晃得人眼乱。时间长了,何仙姑才明白,这些老人是嫌看的人指手画脚,甚至是怕旁观者看上自己的牌去偷告别人。
高志远进了门,背着手,先左右打量了一番,听着何仙姑热乎乎地喊了他一声叔,这才点点头,心满意足地往靠墙的位置走去。放水杯,脱外套,套在靠背上,落座后闭目养神,两三分钟后,喝水、续满。这一套流程,就算是他来迟了,也是不慌不忙,全部走完。
何仙姑总觉得这高志远一定是领导当惯了,总感觉这个精精瘦瘦的寡言老人有一股君临天下、不怒自威的气势。刚才若是高志远在,那吴德说不定连个屁都不敢高声放。想到这里,何仙姑郁闷的心情,霎时就晴朗了一些,脸上的笑容,也跟着灿烂了一些。
李家奶奶、王叔,一个个自带装置都来了,高志远抬起手看了看表,又伸长脖子往门口瞧了瞧,闭上了眼睛。这时,楼道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高志远还是没有睁开眼睛。
“老哥们,真早啊,看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吧,三缺一,开吧开吧。”这张大炮真是个爽快的主儿,一进门就往空位上扑。
高志远继续闭目养神,李奶奶、王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搭话。这张大炮耐不住了:“嘿,高哥,开吧。”
何仙姑赶紧过去拉着张大炮的胳膊:“张叔,您真是我的福星啊,您看,我这晾衣架不知道咋回事,升降的时候总卡,我数来算去,咱这里,只有您这个大能人能解决这个大难题。”
张大炮一听,心里美滋滋的:“啥毛病能把咱大侄女为难成个这。”
张大炮在阳台上忙乎时,门口来了一位齐耳白发六十左右的老奶奶。她一进门,李奶奶就招手:“李老师,这里。”
被称作李老师的老奶奶点头微笑,刚一落座,高志远就接过她的水杯,和自己的放在一起。
“李老师,这段时间不走了吧。”李奶奶边揭牌边问。
“嗯,亲家去了。”李老师人柔话也软。
“该上学了吧。”
“开了学,老大家的升三年级,老二家的幼儿园大班。”
两个女人一问一答,两个男人就静静听着。
叮铃铃,手机响了,“李老师,手机,手机响了。”
李老师手忙脚乱想掏出手机,可越着急越掏不出来,往起一站,咣当,把李奶奶的包给碰地下了,急忙弯腰去捡,李奶奶拍拍她的手:“接电话吧。”
李老师滑开手机,屏幕显示是大儿子的来电,让她下个月去北京住一段儿时间。老年手机,音量大,李奶奶听了,是好一阵羡慕啊。
“李老师,您看您多福气啊,北京、广州两头跑。”
半天没见李老师回话,李奶奶也没放在心上。
“哎,李老师,该您了,碰还是揭了?”
高志远时不时歪头看一眼李老师。总觉得李老师今天有点奇怪,怎么一到了她这里,总是卡牌。
“噢噢噢,轮我了?”李老师咬了咬嘴唇,歉意地冲大家一笑,“对不起啊,没看见。”
李老师三心二意,不是误了碰牌,就是点炮,半个小时不到,一锅就塌了。李老师算了账,匆匆离去。高志远望着离去的李老师,屈指在桌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
“完了?好利索啊,这是快锅啊!”从阳台上回来的张大炮,大咧咧一坐,“来,再开一锅。”
老好人王叔,是怎么都行。高志远拿起水杯,说家里有事,也走了。
“有事?他能有啥事?就一个姑娘,还是嫁的万儿八千里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能有啥事?在这里,喝水有人倒,说话有人听,既过手瘾,还能解闷。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不知道这些人每天都胡思乱想些甚。”张大炮一脸的鄙夷,“要不说,文化人,难弄。”
“刚才听李老师的儿子让他去北京?”
“去就去,北京,首都,好地方啊。我要有个儿子让我去,我连做梦都能笑醒。”
“瞎嚷嚷个啥呀,这是大儿子的电话,大儿子是在广州,你说,这大儿子咋能安排李老师去二儿子家住呢?”
“就是呀,这老大怎么能安排李老师去老二家住呢?要去北京,也得是二儿子打电话或回来接呀。”旁边看打麻将的阿姨也插了一句。
“这李老师也真是个硬气人,一个人把两个小子都供到研究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结婚生子,又卖了老家房子,轮流给看孙子,现在,孙子上学了,这颗心也终于能掉进肚子里安稳了。”李奶奶叹口气。
“就是就是,咱们这几十年的老邻居,终于能看见她过几天好日子,享享清福喽。”
俩老太太就着这话题,又忆起了没拆迁时,大杂院混住时岁月的艰辛与喜乐。哪家孩子调皮捣蛋,谁家娃读书认真,数来算去,还就是李老师家俩小子最有出息。虽说男人死得早,她一个民办教员拉扯两个半大小子难,但看看现在,那些苦罪也值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说了,哎,小仙哪,有人没,没人的话,我就和老伙计们下两盘棋去。”王叔举起水杯,何仙姑赶紧过来给填满水。“等等吧,陈姨一会就到。”
4
趁等人的工夫,张大炮跑去客厅看郝仁那桌去了。李奶奶调转椅子,转过身来,背对着门,从包里掏出钩了一半的帽子。她是个闲不住的“巧手手”,年轻的时候,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人,一年四季的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出自她的精打细算,裁剪衣服,缝缝补补,毛衣毛裤,纳底做鞋。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就算做下这些东西也没有人穿了,她就与时俱进,钩织些小东西,一是打发时间,二是锻炼手指,生怕自己得了老年痴呆。这不,何仙姑的帽子,就是跟着李奶奶学的。钩了几针,李奶奶才想起何小仙说前几天钩的桌布,有几个花错了,拆了可惜,将就吧,碍眼,就搁在柜架上,等有时间了看看能不能补救。
“人老了,记不住事了,趁现在想起来了,赶紧看看。”李奶奶自嘲地推开椅子,探身去柜子上够那块桌布,回身落座,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把正搬着椅子的张大炮吓了一大跳:“哎呀呀,我的老姐姐,你咋能,我我我……”
张大炮就像是被定了型一样,愣在了原地,王叔赶紧把地上的李奶奶扶起,又踢了张大炮一脚,张大炮这才回过神来,放下椅子,和王叔一起把李奶奶扶起。
“老姐姐,伤着了没?”王叔他们想往沙发上挪去,李奶奶摆摆手,原地站立了几分钟,这才一步一挪往沙发那里去。
郝仁他们也撂下麻将,前来问询老奶奶的情况,张小猛拿起手机,准备拨打120。何仙姑吓得说不出个囫囵话来,看着老奶奶自己坐在了沙发上,这才吐了一口长气。王继光边拿包边找车钥匙,蹲下身子,要背着李奶奶去医院。
“不要不要,缓缓就好。”李奶奶直摆手。
“那,给我你儿的号码,来我给他打个电话?”
李奶奶一听,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行不行,打了电话,以后就不让我出来玩了。”
闯了祸的张大炮蔫头蔫脑的,颠来倒去就是一句话,我就没看见老姐姐在跟前。
红姐不放心,拉着老奶奶走了两步,又慢慢转了一圈,确定没有伤着骨头动了筋,一屋子人这才全都出了口长气。
陈姨来了,红姐又从里屋拉出一个嗑瓜子的大姐,替了李奶奶。
毫无悬念,张大炮一把没胡,完美塌锅。
输了钱的张大炮,一反往日不坐塌椅子不离座的劲头,低眉顺眼坐在茶几旁的小凳子上,不喝茶,不说话,更别说嗑瓜子、嚼花生了。
“他张叔,玩去吧。我不碍事的。”老奶奶笑眯眯瞅着张大炮,“是我自己不注意的,别往心里去啊。”
“不了不了,让别人玩吧。”张大炮不敢直视老奶奶,他耷拉着脑袋,全然没有了往日那种不服输、不气馁、不挽回局势不罢休的豪迈劲儿。
何仙姑也心里发虚,要不是因为给她拿桌布,李奶奶也不会摔倒。再者,不管什么原因,事是出在她家里,她后怕呀。所以,何仙姑再三询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老奶奶压低嗓门和她说着悄悄话:“闺女,别声张,万一传到孩子们耳朵里,我以后估计出门就费劲了,别说打麻将,就是连教你钩织也不行了。”
5
众人散去之后,王继光迟迟没有离去,他左手搓着右手,右手按摩着左手,踢着脚尖:“今儿,让你受委屈了。”
何仙姑摇摇头,寡妇门前是非多,一想起早上大伯子骂她克夫的电话,何仙姑心里的那个委屈随着眼泪唰唰地就又下来了。好几年了,男人的意外,是她能预料到的吗?人们为啥总爱翻旧账啊。
“要不,你就随我回村里,或是咱换个地方吧?”王继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何仙姑的脸色。
何仙姑不说话也不点头,只是盯着雪白的电视墙发呆。
“咱俩,你没男人,我死了女人,一不丢人,二不偷情,光明正大,谁也说不得长短。”看着低头不语的何仙姑,想着她憋屈而又没地方去说的苦衷,王继光的直脾气又上来了。为了这个打小就一块长大的妹子,他可是放下了村里的煤摊子,专门撵到这又窄又小的老式楼房里来了。他的小仙,二十年前就错过的小仙女,这次是说成啥也不能放过的,就算是让他上刀山下火海,他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可任凭王继光说破了天,何仙姑就是不说话。王继光再说,何仙姑就抹眼泪。王继光走了,何仙姑盯着门口,还是抹眼泪。
6
因为答应了要给舅舅镶牙,郝仁打完麻将赶紧联系医生朋友,过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既是确保不影响明天下午的活动,也是怕勤捉住他自编自导的那个假电话的茬儿。
第二天上午,郝仁和勤带着老母亲,给舅舅花最大的价钱,预定好最好的牙,然后一家人在外面吃了饭就赶紧回家。昨天,大家三缺一等他,他决定今天,一缺三,等大家。可他刚下了楼拐过弯,就看见张大炮坐在远远的树荫底下,伸着脖子在西南向的巷口张望。
郝仁摇摇头,自嘲道:“自觉自行早,还有更早人。”
一进屋,郝仁又愣了:“哟,高大爷,今儿没午睡?”
“嗯,”应了一声,高志远又转过身,看着窗外。
郝仁也见怪不怪,高志远永远都是一副冰棍脸,用红姐的时髦话来说,是生人勿近、惜字如金,用张大炮的话就是“干吗老甩着个脸子,别人又不该你一块钱,况且,多说一个字会死啊?”不过,这话是高志远不在场时,张大炮拍着桌子豪气十足地说的。把这俩老头丢在街上,估计是你看不上我,我也瞧不起你。说也奇怪,这两个冤家,还偏爱往一个桌上凑。张大炮那大口袋里,今儿装个山楂棒,明儿是一把炒花生。一不胡牌,就叼一根山楂棒,有时一着急,还能把椅子往后一推,直接站起来,看看上家,瞅瞅下家,遇上李老师,会温和一笑,若碰到是高志远,要么把牌一扣甩一句:“稍安勿躁”;要么眼一瞪,张大炮立马就乖乖坐下,嘿嘿一笑。
郝仁摇摇头,今儿这是怎么了,平常都是在家午休好养精蓄锐的老人,为啥都早早地来了?张大炮更奇怪,这大热天的,来了怎么不上来呢?一点钟的太阳是最毒的,平时手不离瓶,嘴不离水的人,今天不怕中暑?
撩起大卧门帘一看,呀!小哑巴来了。“嗨!”
正低头看手机的女人一回头,冲着郝仁眼一眨嘴一咧,一脸的清纯。郝仁心里直嘀咕,这个清清爽爽的女人,会在麻将桌上偷牌换牌?门帘一动,郝仁还没有看清是谁,帘子已落,人也进了隔壁小卧室里了,紧接着,挪椅搬凳的,女人叽叽喳喳的小碎声隐隐约约,像是在打电话招人。郝仁转身还没走到客厅,何仙姑从里边出来:“要不,你凑一把?”
郝仁一指小哑巴,“那不就是一个现成的?我还是等等小猛子吧。”
“嘘,”何仙姑把手指竖起来,指指小哑巴,又冲着小卧努努嘴,直摆手。
郝仁一笑,进屋凑摊子去了。
中途,郝仁去卫生间时,看见高志远也不嫌小猛子他们吆三喝四地吵,还在阳台那儿瞅着窗外,没见张大炮,也没见李老师,更没见老奶奶。郝仁一看手机,三点半。哟,估计这桌夕阳红今儿是没戏了。
7
这几天,高志远都是简单对付几口之后,就早早来到何仙姑这里。有时候太早,高志远就一个人干坐着,不喝水也不说话,伸着脖子望向窗外。高志远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要坐到这里,为啥要瞅窗外。放暑假了,孩子们都被大人关在家里睡午觉,老头老太太也不急着送孩子、做饭,一日三餐慢慢就变成啥时饿了啥时吃,就连绿化带里的大槐树们,也是懒洋洋地举着枝丫,耷拉着脑袋,心不甘情不愿地杵在大太阳底下,无言地进行着集体罢工。倒是西门角落里的几丛月季,躲在背阴处,深绿色的叶子舒舒展展,碗口大的花朵正生机勃勃地展示着自己的美丽,丝绒般的大红沉稳厚重,胭脂样的绯红鲜艳活泼,黄蕊红瓣小俏皮的应该是芍药。高志远闭上眼睛,仿佛隔窗都能闻见它的甜味,这种景色既像是他没离休前办公室窗前的小花圃,又像是爱人在世时老院子里一年四季的争奇斗艳,可似乎都不像,倒让他想起是李老师身上那股淡淡的体香。高志远正要深吸细闻,忽的,李老师又不见了。高志远一惊,不仅屋内没有李老师,就连往日热闹的小区,此刻都是静悄悄的。高志远稳了稳神,下意识地回头,总感觉有一双隐忍着委屈和无奈的大眼睛在看着他。那是李老师的眼睛,难道她遇上什么大麻烦了吗?有谁能知道她的近况呢?该死的大喇叭张大炮也不见了,和李老师做了多年邻居的李奶奶也不来了,向何小仙打听吧,他又张不开那个口。其实,这个时候,他是非常羡慕张大炮的,直肠子、大嘴巴,想到啥就是啥,要是张大炮就在眼前,不论张大炮提啥条件,他高志远都答应,哪怕日后成为张大炮茶余饭后的笑料,只要能打探见李老师的情况,他也认了。
高志远第一次感到深深的失落与挫败,那个领导着千儿八百人,运筹帷幄,意气风发的高志远不见了,精气神刹那间就像是被人抽光剥尽一般,他提着杯子,有气没力地走了。
一连几天,高志远都是心神不宁地在窗户边坐坐,又失魂落魄地离开。
这天,李奶奶来了。
过了一会儿,张大炮也来了。
高志远眼睛发亮,蹬蹬蹬走到老位置,外套挂妥,水杯放好,身旁照旧留了一个空位。
张大炮眼巴巴地瞅着李奶奶,铁盆似的大屁股只挨了椅子的尖尖:“那个,他奶奶,你这胳膊腿脚没事吧。那天,我确实是没看见……”
“没事没事,害你多想了。”李奶奶笑眯眯的。
“那咋好几天没来,害得我天天在楼底下瞅你,生怕有个三长两短,”张大炮一脸的不自在,蒲扇大的手掌在大口袋里掏呀掏,“给。”核桃、花生、巧克力,当然,还有他的山楂棒。
李奶奶两手直摆,张大炮长胳膊一伸一绕,就把她的包捞了过来,一股脑儿全塞进李奶奶的小包包里。
高志远也不管张大炮怎么折腾,他还是抻着脖子往门口张望。
“哎,他高爷爷,”李奶奶摸着面前的麻将牌,看了高志远一眼,张了一下口又闭住了,深深咽了一口口水,那个麻将牌是左手倒右手,右手再扣倒,两个手指头快把麻将牌给搓得掉皮呀。
“嗯?”高志远抬腕看看手表,继续朝门口瞅。
“那个,那个,”李奶奶还没说完,张大炮急了:“咋回事,有事赶紧说,害得人们跟上你干着急。”
李奶奶低下头:“李老师应该是不来了,咱再凑个人吧。”
“不着急,再等等。”高志远还是瞅着门口。
“干啥去了,咋不来了呢?不是说亲家去看娃了?哦,你看我这猪脑子,那天,李老师接到电话说是儿子让去北京住,享清福去了。”张大炮拍着自己光秃秃的大脑袋,“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啥也记不住。小仙哪,看看里屋谁在呢,让出来凑一把。”
“小哑巴在了,行不?”
一听是小哑巴,张大炮手一挥,“去去去。”
“不是去北京,回老家了。”李奶奶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老家?李老师老家不是早就拆迁了?她回去住哪里?和谁住呢?”高志远这下子总算是听明白了。“不是去北京?咋又回村里了?”
“在北京的是二儿子,大儿子在广州。大孙子上小学,用不着李老师接送了。二小子家亲家母去了。两个孩子,住的都不宽敞,大儿子让去二儿子的家,老二媳妇嫌李老师光照护老大的家,重男轻女,不应承。”李奶奶用手背抹了一把眼角的泪珠,“你说,这李老师守寡硬撑的,把两个小子培养得有出息了,现在,又落得个这下场。”
啪的一声,张大炮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大腿上,“像这些白眼狼,当初就不该供他们上学。这要是换成俺孩,看我不剥了他的皮,扔到茅坑里!”
“怪不得那天李老师接了个电话,脸色就不好,三把两把输了牌。”王叔不知道啥时候来的,也在愤愤不平。
高志远哆嗦着手,连杯盖子都拧不开,王叔叹口气,把盖子打开,轻轻放在高志远跟前:“这李老师一个人怪可怜的,要是想不开可咋办呀?”
高志远抿了一口水,抓起衣服,铁青着脸走了。
“不说了,来来来,咱再凑个人。”王叔笑着吆喝何仙姑,但眼睛却是盯着张大炮,“你这老小子,舍得露面了?来我看看你给咱老姐姐带什么好东西了。”
“这这这,”张大炮显然是没有提防王叔会问得这么直接,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东西不东西吧,沉甸甸的,提过来,还得拿回去,怪麻烦的,这样吧,折成现金吧,准备出多少钱,三百?五百?”王叔看着张大炮的大脑门子上细密的水珠子,心里那个爽呀,简直比就着瓶嘴咕咚咕咚灌上两瓶冰镇啤酒还痛快了。
张大炮左手背一抹大脑门,右手捏着裤兜,嘴巴眉毛都快拧巴成一个肉球球了,“我不知道今天老姐姐过来,明天,明天,明天我就把钱……”
“好了好了,别逗他了。”李奶奶眼睛快笑得眯成一条缝了,“别往心里去啊,他这是拿你寻开心哪。”
“明天明天。”张大炮讪讪一笑。
“不要等明天,待会不论输赢,你,仙客来定一桌,请老姐姐吃饭,咋样?”王叔摆出一股没有结果就誓不罢休的架势。
“行行行,没问题。”张大炮尽管心里是肉疼,但他还是一个劲地点头应承。
“打住打住啊,说说笑笑就行了。哎,仙啊,咋的,还有没有人来?”
“就是就是,你看,咋打个麻将,还是三缺一。”张大炮擦着快要流进脖子里的汗附和道。
“放心吧,过不了几天,咱这老人组说不定就会把你开了呢!”
“为啥?凭啥?”张大炮立起眼睛瞪着王叔。
“老高干啥去了?”
李奶奶也是个通透人,双手一拍:“哎呀呀,这感情好,我咋就没看出来呢!”
“啥好不好的?”张大炮还是一脸的迷糊。
“就你那糊涂样,等着被我们开除吧。”
“为啥要开除我?哼,没了我耍不成,玉米面捏人人。”
“好好好,离不了你。小仙,赶紧的,不行,你凑一个吧!”李奶奶笑眯眯地给这两个老小孩打着圆场。
“来了来了,”大嗓门王继光应着,从何仙姑手里接过大水壶,顺便把何仙姑黏在脸蛋蛋上的一缕头发给挂在耳后。何仙姑脑袋一偏,秀气的脸上飞起一酡红。
8
回到家,郝仁照例把输赢和见闻说给勤听:“哎,那个小哑巴是咋回事?真的会偷牌换牌?”
“看见那小模样心疼了?”勤柳叶眉一挑,“明天开始,你在家,我去玩。”
“行行行,你去你去。这几天,委屈你了。”
“你舅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的一半天吗,这都已经十来天了。”勤一肚子的不高兴,“这才几天,就被小哑巴勾魂了?”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这脑瓜里整天净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勤掐了郝仁一把:“大实话。听说那个小哑巴是个外县来的保姆,给五十岁的主人生了个儿子,男主人出事了,女主人就把她赶出了县城,并让她永远不要回去。”
“敢情这电视剧也不是瞎编的。”
“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你不能和她坐一桌。年纪轻轻,干点啥不好,要是我姑娘,看我不打断她一条腿!”勤指尖一拧,郝仁龇牙咧嘴:“你掐我干啥?”
“赶明儿问问你舅,这次,是要干啥。”
提起舅舅,郝仁就觉得脑袋甚至是头发丝都疼,年轻时,放着公家的铁饭碗不端,找了个农村没工作的,不顾家里人反对,要死要活跟人家结婚;结婚后,又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和单位的一个女工不清不楚。最后是彻彻底底成了三无人员,工作、老婆、情人全没了。在农村,吃不下苦;在城市,又没能力,一晃到了六十岁,隔三岔五就来郝仁家混吃混喝。你说你来就来吧,偏偏还要挑三拣四,要不是郝仁会哄媳妇,一般人家的媳妇妇早就扛着炒瓢,把他从家里拍出去了。可要赶他走吧,又过不了老娘那关。说到底,舅舅再不成器,也是这个世界上老娘最大的牵挂了。
一提舅舅郝仁就心烦,“洗澡去喽。”看见歪在床头的勤一脸的苦哈哈,“舅舅为难你了?”
勤举着手机:“这个家伙,最讨厌,每次都坐我上家,专打生张发碰,害我一张牌都不上。”
“那还不简单,你坐他上首啊。”
“我也想啊,可每次他都比我进得快。”
“你出去再进来。”郝仁撇撇嘴,这傻媳妇,除了实在还是实在。
卫生间的门被敲得砰砰响,郝仁赶紧关掉水龙头。
“没用的,他还在我上首。”
“笨蛋,”松口气的郝仁拿出洗发液,“那就再出去,重新进。”
“不顶事,这次我都跑出楼门了,结果回来,他还在我上首。”勤着急的,现在三缺一,人一齐,就自动开始了。
“你跑出楼门口干吗。”
“你不是让我出去再进来嘛?”
郝仁这下有点哭笑不得,他擦干净手,顶着满头的泡泡,边操作边讲解:“不是让你跑,是让你点退出,然后,再选择加入。是指程序,笨蛋。”
脑门被弹了一指的勤,看着自己的新位置,也不和他计较,冲郝仁吐了个舌头,跑进卧室去了。
换了位置的勤,果然是手气逆天,一局十二把,胡了八把。心情大好的勤不仅不提舅舅回村的事,而且还张罗着给舅舅找个老伴。勤指尖在郝仁胸口画着圈圈:“你舅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人,没坏心眼。”
“是是是。”
“我看,全是咱姥爷家全家害的。”
“好好的,咋就扯到咱妈家人头上来了?”郝仁侧过身来,两人面对面。
“年轻时,想干啥就干啥。等老了,想干啥干不了啥的时候,你姥爷姥姥在干啥了,你那几个姨姨干啥了,咱妈又干啥了。”勤扑闪着大眼睛。
郝仁一阵无语。
舅舅是姥爷的老来子,十亩地里一苗谷,稀罕得很,宝贝得很,要太阳不给星星,可到头来呢。哎!宠子如杀子,慈母多败儿,现在,说啥也迟了。
“明天你领上好好洗个澡,理理发,买上几身新衣服,下午,是下午吧?”
“什么下午?”郝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别打岔,新牙。”勤睕了郝仁一眼,“瞧你那记性。别说,你舅舅换身行头,假牙一安,说不定还是很帅气的。”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家的舅舅。外甥像娘舅。”郝仁得意地挑挑眉。
“臭美吧你,早知道你有这么个扶不上墙的阿斗舅爷,我是宁当尼姑也不会嫁给你的。”
“这小嘴叭叭的,两天不打上房揭瓦,看来你是欠收拾了啊。”
这二三十年的老夫妻闹腾起来,一点也不亚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过,闹归闹,勤还是联系了娘家村的亲戚,定好了三天后,领着舅爷去相亲。
郝仁看着打电话的勤,突然想起,两天没和儿子联系了,大三了,也不知道有没有看上眼的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