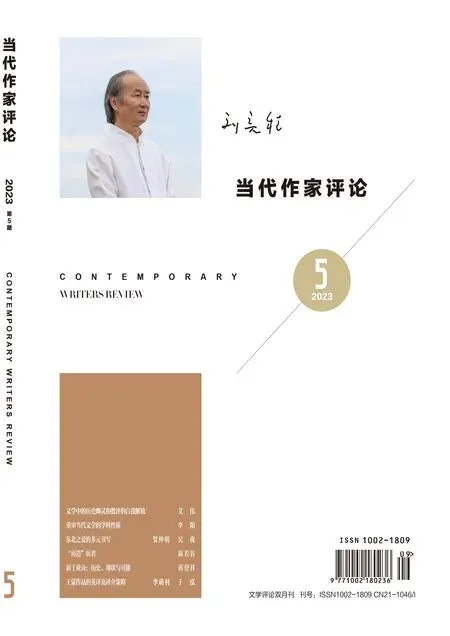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社会主义新人”与少年儿童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的讨论
王一典
叙事类儿童文学都涉及人物形象塑造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塑造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少年儿童形象是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新课题。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1979)中的李铁锚、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1981)中的汪盈、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1982)中的章杰、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1984)中的张光汉、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1984)中的熊荣都是新少年儿童形象的典型。尽管学界对这几部作品中的少年儿童形象多有讨论,(1)见吴翔宇:《新时期儿童文学主体性建构的机制、过程及反思》,《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张国龙:《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旨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李利芳:《〈草房子〉:记忆中国童年情感》,《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却较少将这些作品和与相关批评文章结合起来考察。(2)齐童巍的相关批评文章有涉及,但偏重于叙述,未能对具体的批评话语策略展开分析。见齐童巍:《20世纪80年代儿童小说史论》,第127-1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另外,这些形象一直被看作是新少年儿童形象的典型,却少有人注意到它们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的关系。本文将上述作品中的少年儿童形象,以及当时批评界对它们的讨论,放在“社会主义新人”概念下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少年儿童形象如何借助这一概念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一概念如何影响批评界对少年儿童形象的评价,批评家们采取了怎样的话语策略将原本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形象纳入“社会主义新人”谱系中。
一、“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与少年儿童形象的榜样作用
对少年儿童形象塑造合法性的确认首先来自对儿童文学题材的重新界定。20世纪50至60年代,学界认为儿童文学的题材要广阔,在写儿童生活时要涉及社会生活,学校、家庭、农村等都可写进儿童文学。(3)见陈伯吹:《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文艺月报》1965年6月号;袁鹰:《关于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发言》,《儿童文学论文选》,第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潘旭澜:《更广阔、深刻地反映农村生活——读几本反映农村生活的儿童小说漫想》,《儿童文学研究》1963年第3辑。在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潮的引领下,儿童文学题材问题又重新提上了日程。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李楚城,他从实际生活和教育需要两方面阐明了儿童文学表现儿童生活的重要性。首先,“革命文艺总是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典型形象来实现自己的任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家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时,有时也很自然地接触到儿童生活领域,在作品中出现少年儿童形象。但对于一般文艺作品,毕竟不能在这方面提出过多的要求。然而,对于以少年儿童为自己的教育对象的儿童文学来说,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力反映儿童生活,大力塑造儿童形象”。(4)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其次,从教育需要出发,延续“十七年”时期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逻辑,“要培养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品德,教育儿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遵守纪律,像敢于同敌人作英勇斗争一样,敢于同学习中的困难作斗争,敢于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这一切都应该通过儿童自己的生活的反映,去完成作品的教育任务”。(5)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
另外,儿童文学和一般文学一样要遵循文学的党性原则,但在主题确定和题材选择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李楚城引用并置换了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的部分内容,说明儿童生活尤其是学校生活对儿童的重要性。他提到:“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指出学生应当以学文为主,即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6)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这句话的前半段确是出自“五七”指示,后半段则是根据当时邓小平提出的重视科学、教育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进行修改的。同时,李楚城还将少年儿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的举动与革命年代的英雄壮举相提并论,认为“广大少年儿童就要继承这一革命传统,去跨越学习科学文化道路上的‘雪山’‘草地’,突破‘大渡河’‘金沙江’”。(7)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借助文学修辞,学习科学文化,建设四化的方针任务被纳入了革命解放事业的脉络中,成为少年儿童在新历史阶段的政治觉悟,而学校题材就顺理成章成为儿童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少年儿童形象的刻画也就具有了合法性。而且,既然一般文艺在刻画工农兵形象时会涉及少年儿童形象,那么儿童文学中也不可避免涉及工农兵形象。“作家在塑造各种类型的儿童形象时,不可能不同时塑造各种类型的成年人形象”,(8)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因为“儿童生活是和整个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9)李楚城:《大力反映儿童生活 大力塑造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第1辑。这样,塑造少年儿童形象就与塑造工农兵形象并行不悖了。少年儿童形象在历史题材和当下现实题材中都可以予以表现。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来说,“塑造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新的美的少年形象,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新课题”。(10)周晓:《努力塑造新的美的少年形象——评小说〈勇气〉〈新星女队一号〉》,《人民日报》1982年6月2日。这一课题的提出与当时整个文学界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紧密相关。
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首次从中央层面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创造活动。”(1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8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文章在追溯这一概念渊源时,一致认为其与“十七年”时期文艺界开展的诸如“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以及“先进人物、正面人物和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提倡一脉相承。(12)见康濯:《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有研究者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作为一个由政党意识形态领导人重新提出的价值引导性概念,‘社会主义新人’在政治思想、道德原则两个层面上‘具有比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优秀的道德品质’的要求,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引导期许。”(13)张慎:《新时期文论对“社会主义新人”概念的启用与重构》,《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这种期许在教育功能更强的儿童文学批评中表现更为明显。倪谷音从教师角度观察当下儿童阅读情况后指出:“我还像过去那样,常上图书馆,可翻来翻去,却只见铁木儿、张嘎、海娃、刘文学已长了胡子站在书架上向我这个老朋友点头了。当然,他们仍然是今天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但毕竟是以前年代里的事了,似乎缺乏新鲜感。”(14)倪谷音:《请多塑造富有时代精神的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之后,作者又以两件真人真事为例,说明学习科学、钻研科学是这个时代孩子特有的精神面貌,因此希望作家多写些献身现代化的人物故事。新时期的少年儿童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但也不能低估“四人帮”迫害给少年儿童造成的严重影响与毒害,如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讲究实惠、只顾自己等。基于此,作者“希望作家能有针对性地写些作品,以帮助小朋友讲道德,明是非,这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我国文明程度,和促使孩子们健康成长有莫大的关系”。(15)倪谷音:《请多塑造富有时代精神的儿童形象》,《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贺嘉也指出:“在注意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各种各样’的少年儿童形象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塑造闪烁着共产主义精神的当代少年儿童形象。”(16)贺嘉:《塑造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形象》,《光明日报》1981年5月26日。因此,儿童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塑造一是为了展现新时期儿童的正面形象,二是通过榜样对儿童读者发挥道德教育作用。这两个目的决定了儿童小说创作中作家价值立场和少年儿童形象的精神面貌。
二、工作方法与思想立场:对张莎莎和章杰的不同解读
首先引起批评界注意的是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小说塑造了爱独立解决问题的李铁锚和爱向老师报告的张莎莎两个形象。小说发表后,“编辑部先后收到来信近四百封,除少年读者外,还有教师、家长及其他战线上的一些同志”。(17)《少年文艺》编辑部:《〈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刊登以后》,《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在读者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同时,作者及专业批评家们也对小说发表了看法。王安忆先后在《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研究》上发表创作谈。她在谈到对两个人物看法时,王安忆认为:“并不是仅仅缺少工作能力的同学,而是另一个,是另一个。我觉得张莎莎这样的同学更应该写,因为这个人物反映出了问题,这问题或许还值得我们思索。而铁锚呢,我也不反对他能有点涵养,能够依靠老师,注意分寸,可当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也不否认他,并且不希望他和张莎莎俩‘取长补短’。总之,他们两个人绝对不是两个极端,不可能同时回过头来面对面走几步,求得统一。”(18)王安忆:《我的一点体会》,《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
王安忆突出两者的不可调和性,是对部分批评家将张莎莎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工作方法的否认,张微就是其中代表。他在细读文本基础上认为,张莎莎和李铁锚并不是对立关系。李铁锚勇敢、正直、憨厚,真心帮助同学,长大了会是一位富有革命正义感、乐于助人、勇于担责的青年,是建设“四化”的接班人,但是作品中张莎莎几次报告的事情都有其合理性,“动不动报告当然不好,但应该培养和提高对干部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19)张微:《为张莎莎说几句话》,《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张微还认为张莎莎打报告恰恰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因此李铁锚和张莎莎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集体、为他人着想,只是在工作方式上有所差别而已。
钱景文的思路与张微基本一致。他认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处理上,作者也是郑重的。李铁锚是肯定的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拔高他,把他写成完美无缺,高而又高的神童……正是因为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先进人物,使孩子们读来感到非常亲切,可以学习。”(20)钱景文:《良好的开端》,《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而对于张莎莎,钱景文认为:“作者对她是批评的,但也并不是说她什么优点也没有……另一种孩子事事向老师汇报,这是几年来在老师的各种鼓励下形成的‘习惯’,是社会思潮对他们的影响……作者并没有把张莎莎这个人物写过头,对她批评也是善意真挚的,是从教育广大少年儿童出发的……在儿童文学中,我们提倡塑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形象教育少年儿童,但也并不排斥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有时,犯错误孩子的教训,对少年儿童来说更有教育意义。”(21)钱景文:《良好的开端》,《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4辑。较之张微,钱景文并没有为张莎莎做太多辩护,而且也承认张莎莎的做法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但他更多将张莎莎看成是一个可以被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在成长进步的学生,与李铁锚一样,张莎莎也可以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因此,李铁锚和张莎莎从不同方面给予读者教育意义,两者也不是对立的。
综合张、钱二人的论述,李铁锚和张莎莎是完全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和王安忆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这主要因为双方对小说立意有着不同理解。王安忆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联儿童小说《古里亚的道路》和身边许多张莎莎式的人物。王安忆认为张莎莎问题的根源是“四人帮”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破坏,对民主作风的糟蹋,而儿童也和成人一样受到影响。可见,王安忆并非只是要创作一篇学校题材小说,而是要从学生问题和教育问题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可以归入反思文学之列。而在张微和钱景文看来,这篇小说就是反映教育问题的学校题材小说,李铁锚和张莎莎的优缺点都是学生正常反映,不能与那些思想受到严重侵蚀的小干部相提并论。张微在文章中还特别列举了几条这类小干部的特征来与张莎莎作区分。这样一来,张莎莎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教育方法和学生工作方式的问题,而不涉及思想立场问题。这种将作品与社会政治问题划清界限的做法,是批评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整个政治社会环境不甚明朗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的讨论会召开之时,关于歌颂和暴露、“歌德”与“缺德”等问题的讨论刚刚平息,因此批评家们对这类敏感问题采取审慎的态度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小说中情节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也为批评家淡化李铁锚和张莎莎的差异提供了空间。首先,虽然王安忆的本意是借学生反思社会,但小说故事基本发生在校园里,人物也以少年儿童为主,成人在作品中只是陪衬,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这也是后来作品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是正是这样的“瑕疵”让小说能够局限在学校题材范畴中被评论。另外,从两个主要人物性格来看,虽然李铁锚有主见,遇事喜欢自己解决,但他处理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利他的,是为别人着想的。张莎莎向老师“打小报告”的行为更是心中有同学、有集体的表现,何况被她报告的同学确实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张莎莎无疑是在帮助同学进步。正是在这样逻辑下,李铁锚和张莎莎都被纳入了集体叙事的“大我”之中,成了具有社会正面导向价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尽管《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程度并不强烈。虽然作者提出了谁来当中队长这一问题,但通过批评家们的解读,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何况作品本身的矛盾冲突也并不激烈,但是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的发表却再次引发了文学批评界较为激烈的讨论。主人公章杰个性十足,爱独立思考,为了雕刻的爱好,拒绝参加班集体活动。老师当众表扬同班的方大同见义勇为,他却认为方大同不会游泳却下水救人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小说发表后,批评界针对这两个人物尤其是章杰的所作所为展开讨论。首先是唐代凌在《当代少年的个性是什么》一文中指出:“章杰是个具有思想锋芒的当代少年,方大同只不过是个过于听话、缺乏个性的五六十年代的‘好学生’典型。”(22)唐代凌:《当代少年的个性是什么》,《儿童文学选刊》1983年第3期。这一论断由方大同与章杰两个人物性格的不同,延伸至新中国初期与20世纪80年代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的对立,之后的批评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进行的。李楚城和达应麟的观点相似,两者都认为章杰并不能准确表现当代少年的思想特征。李楚城的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在《祝辞》中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认为这里的“新人”指的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优秀人物。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儿童文学应该努力塑造的当代少年,也应该是少年儿童中的先进分子,是值得广大读者直接仿效的优秀少年形象”。(23)李楚城:《浅谈当代少年形象——也谈〈我要我的雕刻刀〉》,《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1期。达应麟承认章杰“遇事爱思考,敢于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确是他的鲜明个性”,(24)达应麟:《章杰这个人物》,《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1期。也反映了当代少年的某些特点,但是他的立场和角度都存在问题。因此,章杰代表的“只是在少年中那种遇事打小算盘,有浓厚的‘实惠’思想的人”,(25)达应麟:《章杰这个人物》,《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1期。而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对这类少年加以引导。
从上述两篇批评文章看,章杰显然是个需要改造的少年,而方大同才是被效仿的对象。究其原因,方大同代表集体主义,而章杰则代表个人主义,在批评家眼中他俩的对立和冲突本质上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两位批评家关注点都在章杰对下水救人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参加集体活动专心雕塑的情节上,因而就引发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为什么这部分情节会引起批评家们的兴趣呢?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青年出路和价值观是当时整个社会热议话题。《中国青年》在1980年第12期发表文章《“信任危机”与青年》,写出了“我们的灵魂被奸污了”的愤懑,以及青年对政治的不轻信、不盲从的态度。文章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代际肖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是最称心的:热情,质朴,‘党叫干啥就干啥’。八十年代的青年虽然对党也有感情,但雷锋式的单纯却不见了;他们不甘做‘螺丝钉’,想发挥自己更大的才智和潜力,因而他们那个‘自我’更内向、更执着,富于哲学沉思色彩;不安于现状,不承认任何未经实践检验的信条。”(26)夏中义:《“信任危机”与青年》,《中国青年》1980年第12期。转引自沈杏培:《从“边缘人”到“新穷人”:近年小说中进城青年的身份与危机》,《扬子江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与此同时,出现了围绕“雷锋精神”的四次大争议,其中三次发生在1983年之前。(27)见苏颂兴、胡振平编:《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第5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李楚城在文章中提到张华抢救老农的事件就是其中一次讨论的导火线。这些争议由关于雷锋精神的讨论开始,问题的核心依然指向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甚至是20世纪50至6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的对立,唐代凌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对人的价值、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中,“基于发展‘四化’的重要目标……各方话语极为小心回避了具有张扬生命力的‘个人主义’,而采用的策略就是将人道主义纳入到集体当中”。(28)吴晶晶:《新时期初“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研究(1978-1984)》,第56页,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对李楚城和达应麟对章杰身上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指责就在情理之中了。“社会主义新人”事实上是一种权力话语预设的产物,它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划。因此,李楚城和达应麟都将方大同视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而将章杰排除在外。如果说张莎莎和李铁锚的差别还是社会主义新人在工作方法上的差别,那么方大同和章杰的差别则是价值观念、道德品质乃至阶级立场的天壤之别。因此,在李楚城和达应麟那里,章杰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典型的。
相比之下,陈子君的文章搁置了之前讨论中设置的二元对立框架,也没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宏大社会政治问题上纠缠,而是直接从文本入手,认为章杰并没有否认方大同舍己救人的精神,而反对的只是他的方法。同时要辩证看待章杰,承认他爱独立思考的优点,又要警惕他不关心集体和桀骜不驯的个性。(29)陈子君:《谈〈我要我的雕刻刀〉的得与失》,《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2期。陈子君将章杰与方大同的矛盾由立场差别转换为处事方法的差别,以及一分为二分析章杰的话语策略,这与之前张微和钱景文对李铁锚和张莎莎的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子君也未给章杰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而是指出他的独善其身、冷漠和桀骜不驯等性格方面的缺点。
除此之外,陈子君对“听话”这一行为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正确的话要听,也要树立老师的权威性,但是对何为正确,在多大意义上具有权威等问题都没有涉及。另外,《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未及展开的社会反思主题,也在《我要我的雕刻刀》中得到了较充分体现。陈子君不赞同小说将“十年浩劫”的原因归结为“听话”的结论,同时指出“听话”对国家管理的必要性,不能笼统反对“听话”。陈子君采取“文本细读”和“就事论事”的批评方式,将由唐代凌引发的立场、时代对立,转换为处事方法和性格为人的差异。小说的主题也由社会批判反思变为教育观念和方法的讨论。综上,儿童文学界通过窄化主题(社会主题变为教育主题)、弱化矛盾(立场问题变为方法和性格问题)、文本细读(专注作品,避免伸发)、一分为二等批评策略,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我要我的雕刻刀》中的少年儿童形象纳入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谱系中,挖掘形象背后的教育价值和榜样力量,融合个人和集体的矛盾冲突。
尽管评论界对《我要我的雕刻刀》褒贬不一,但它却是这几部作品中唯一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下简称“全国儿奖”)的小说。1986年6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强调:“少年儿童文学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方面,担负着崇高的、重要的职责。”(30)束沛德执笔:《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束沛德:《儿童文苑纵横谈》,第402页,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虽然儿童文学取得明显进步,但在许多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塑造更好地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少年儿童心声,塑造更多闪耀时代光彩的少年儿童形象问题”。(31)束沛德执笔:《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束沛德:《儿童文苑纵横谈》,第402页,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全国儿奖”设立的目的在于“鼓励优秀创作,奖掖文学新人”。(32)束沛德执笔:《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束沛德:《儿童文苑纵横谈》,第402页,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从决议对儿童文学成就和不足的总结,以及“全国儿奖”的设立目标来看,“全国儿奖”入选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评奖委员会认为能够承担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重要职责,并且在塑造富有时代色彩的少年儿童形象方面起引领作用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我要我的雕刻刀》中的章杰便是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典型。因此,获奖不仅从官方层面肯定了作品的思想立场,也在某种意义上平息了评论界的争论,而且奠定了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其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三、现代国家视野中理想人物的评价标准
相比之下,批评界对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中的汪盈形象几乎都给予了正面评价。周晓称她是“振兴中华、为国争光的勇将”。(33)周晓:《努力塑造新的美的少年形象——评小说〈勇气〉〈新星女队一号〉》,《人民日报》1982年6月2日。陈子君称其“天真、纯洁,在生活面前富于自信心,充满了创造的活力,且行动干脆、利落、果断,遇到困难毫不动摇、退缩,勇往直前,反映了我们时代广大青少年的新的气质,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精神气质”。(34)陈子君:《〈新星女队一号〉引起的杂想》,《儿童文学选刊》1982年第3期。
比较汪盈和章杰的性格,两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陈子君描述汪盈的那些特点在章杰身上也同样适用,但为什么批评界对两人的态度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在于汪盈的个人理想和追求与国家命运前途融为一体。在小说中,汪盈成立女子足球队的出发点是男生能干的女生也能干,外国有的中国也要有。这其中蕴含的性别平等、国家富强的价值导向,使得汪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可以说,作品将汪盈爱好体育的个人兴趣与为国争光的主流观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她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也被批评家们解读为国家向前发展的萌芽和火苗。在此意义上汪盈无疑是“社会主义新人”谱系中的代表人物。反观章杰,同样自信、果敢、有创造力,甚至也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芒,但由于他的最终目的与集体(国家)导向存在抵牾,因此招来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以上所提到的几个人物都是20世纪80年代少年儿童形象,对他们的评价也折射出新时期初期文学界的价值立场和伦理观念。在对《我要我的雕刻刀》进行评价时,唐代凌认为方大同身上“更多是50年代的少年儿童特征,而缺乏当代少年的气质。既称之为当代少年,就不应是超越时代的某种优秀品质的化身,也不应是共产主义未来一代的理想的造型”。(35)唐代凌:《当代少年的个性是什么》,《儿童文学选刊》1983年第3期。达应麟则认为:“作为道德观念,有他鲜明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从今天来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标准,与五十年代是一脉相承的。”(36)达应麟:《章杰这个人物》,《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1期。前者是用断裂的角度去看待两个时代,而后者是从接续的角度看待的。如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对20世纪50至60年代相关概念的重构和再造,因此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是建立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基础上的新人形象,社会主义对“新人”形象的方向和性质做出了规定,只有在这一基础上的“新”才是被认可的,才能成为读者的榜样,发挥作品的教育意义。而作品中那些溢出这一框架的特点(如个人主义),就不得不面对来自批评界的诘难或修正。由此可见,作者对少年儿童形象的把握和塑造直接关系到作品命运。因此,在《我要我的雕刻刀》之后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中,范锡林塑造了看似冥顽实则求知欲强烈,又具有正义感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少年熊荣。“较之《我要我的雕刻刀》,应该说,熊荣的形象更显得可爱了,他自信得甚至有些自负,但他没有章杰那种离群和孤傲。”(37)周晓:《为“现代化”型少年催生——读〈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记感》,《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3期。《蓝军越过防线》中的张光汉尽管表现欲强烈,但“勇于承担责任,凛然坚持原则”(38)汪习麟:《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汪习麟评论选》,第385页,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的作风被看作是中国新一代军人精神气质的代表,因而指向关系国家民族的未来,也就自然成为新人品格的典型。
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深刻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初批评界对少年儿童形象的评价。批评界对上述作品的不同态度取决于少年儿童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概念规范。面对作品中超出这一规范的因素,采取必要的策略,淡化负面影响,既是新的历史时期批评界响应国家文艺政策的表现,又是儿童文学所承担的教育引领职责的必然结果。在今天的批评家看来,“1980年代初的儿童文学界及时有力地完成了重塑儿童主体的历史使命。刘健屏写于1982年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是一篇标志性作品。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1981)、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1983)、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1984)、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1984)等都秉持民主开放的儿童观去创造崭新的时代儿童人物形象”。(39)李利芳:《〈草房子〉:记忆中国童年情感》,《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这一论断大体不错,却略显简单模糊。事实上,通过对不同少年儿童形象及其同时期发表的相关批评文章的细读,便会发现这几部常被一同讨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面貌并不相同,甚至在价值立场上南辕北辙,但通过批评话语的阐释、修正以及评奖机制的奖掖,这些形象都被纳入“社会主义新人”框架中,成为可以被并列讨论的对象。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