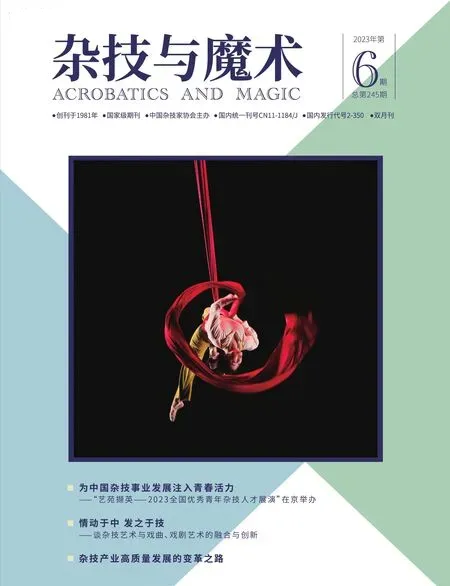情动于中 发之于技
——谈杂技艺术与戏曲、戏剧艺术的融合与创新
文|童孟遥
杂技与戏曲在远古属于是同根同源、花开两枝的艺术形式,汉代初年统称作“百戏”,并在进一步分流、各自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后来,随着时代和审美的进步和变化,杂技在影响戏曲艺术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戏曲、戏剧的浸染。
自2004 年我国第一部杂技剧《天鹅湖》诞生伊始,现代杂技艺术已经逐步发展成一门综合艺术门类。杂技表演从单纯向观众展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向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编排过渡是一个必然趋势。在杂技向杂技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杂技来讲故事”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即如何让杂技和剧情更加贴合,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包括思想、情感、意志及其他心理因素通过动作、表情、神态等直观外化出来,使故事的主题、思想和情感等更加打动人。在戏剧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表达往往受到戏剧情境的规定和制约,而作为心理直观外化的手段——动作,也须以情境为前提条件。特定的情境体现特定的心理内容,而特定的心理内容必须通过特定的动作得以表现。动作体现在杂技和杂技剧中就是杂技动作和技巧,杂技动作所描绘和塑造的人物、行为一般都是可观可感的,先天便具备了一定的叙事性和戏剧性。《毛诗序》尝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推,传递情感时,杂技和杂技剧因为本身艺术特点的限制,不能“形于言”,但是它的故事内涵、人物情感可以依赖于身体和动作语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传达。而这也是杂技剧探索成型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内在原因之一。
现代杂技艺术已经开始重视情感张力和人物交流的角色化表演,故而杂技编导和演员在二次创作时可借鉴戏曲、戏剧等其他艺术的表情达意手法,把角色的内心情感外化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现代杂技要慢慢通过借鉴戏曲和戏剧的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出传统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内蕴和精髓,讲好故事。
一是对戏曲戏剧形式、技艺的直接借鉴,包括对于戏曲戏剧的剧种特征、服装造型、舞台装置、表现手法、手眼身法步等外在形式和程式动作的化用,以及不同剧种中的生、旦、净、丑等行当部分绝活儿和基本功(踢枪、耍叉、变脸、把子功、云手、圆场等)的移植和借用。戏曲中的国粹京剧影响范围最大,且因历史发展的缘故保留了一部分的杂技技艺,与杂技属于源接近关系,所以现代杂技中的戏曲元素有一多半来自于京剧。譬如在第26 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上荣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的杂技《俏花旦——集体空竹》就融入了大量京剧元素,包括京剧服饰、音乐、身段、动作,女演员身穿改良版的京剧花旦服饰,头戴盔头、帽插雉翎,集体表演杂技抖空竹的抛耍扔接,既保留了娇俏灵动的花旦形象,又完成了较高难度的杂技技巧表演。此外,该节目的整体舞台构思、舞美风格及表现形式,也借鉴了戏曲舞台的虚拟性特征,采用了简练写意与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舞台天幕上悬挂的京剧脸谱,直接揭示和展现了人物的身份、节目的主题及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背景等虚拟信息。《俏花旦》依靠表演内容和表演形式呈现出传统优秀文化的多元融合。济南市杂技团的杂技剧《齐风鲁韵粉墨》同样是以“杂技+京剧”的形式,将杂技形象与京剧经典折子巧妙结合,文武戏皆备,大胆借鉴戏曲服饰、技巧、身段等元素来充实和突出杂技技巧,体现了杂技艺术本身的技巧创新和发展。
除了京剧外,现代杂技剧还融合了汉剧、川剧、滑稽戏、皮影戏、舞剧、芭蕾舞剧等戏剧元素。由上海杂技团和上海市马戏学校联合创排的杂技剧《战上海》在敌我追击的紧张氛围中,出人意料地插入了一段滑稽戏表演:一位反串的老太太佝偻着身形,迈着颤巍巍、慢悠悠的步伐,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看似无意却数次间巧妙地搅乱了敌动队的追捕节奏,给予了地下党人脱身间隙,也及时抚慰了观众的紧张情绪,大大丰富了剧情的趣味性和可看性。武汉杂技团创作演出的《寒梅疏影——杆上技巧》在节目编排上也是把汉剧、水袖、圆场、戏腔等戏曲元素穿插进了杂技技艺中,集力量与柔美于一体,而且该节目创意还源于武汉市花——梅花。主道具地桩是一棵粗壮的梅树,枝干等可360°旋转,演员在梅树上进行倒立、平衡、托举、单手支撑等各种力量展示,配合灯光的星星点点洒映,颇有几分梅花盛开时“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画意境。北京杂技团的儿童杂技剧《涿鹿之战》更是直接融合武戏、皮影戏等多种戏曲元素,剧中有一段类似京剧经典桥段《三岔口》的无对手、暗室打斗的场面和用凳子叠成的房子投影类似皮影戏的桥段,都是非常具有创意且十分贴合剧情的演出样式。
二是对传统戏曲、戏剧叙事美学的创新表达。传统戏曲、戏剧故事类型丰富全面,几乎囊括了爱情故事、家庭纠葛、历史传说、神怪故事、公案传奇、武侠豪情等题材,人物形象更是千人千面,大可成为杂技故事的重要素材库。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倾力推出的杂技剧《化·蝶》即是在剧情与技艺之间,精准找寻到了一个戏剧表达和技巧呈现的对接点和平衡点,在充分发挥杂技本体的艺术魅力之余,更能够增强杂技表演带给观众的情感冲击力。该剧以“蝶”从生而受限到挣脱桎梏、自由飞翔的一生为演绎媒介,运用杂技本体语言叙事,根据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设置人物的戏剧行动,巧用杂技技巧完成性格描写,动情讲述了梁山伯、祝英台二人的爱情和成长。最后男女主角的“肩上芭蕾”是华彩之笔,是跨越生死、追求自由的灵魂与突破极限的身体的交相重叠,如梦似幻。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一直是传统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热衷的表现题材,花木兰自强不息、个性开朗的经典女性形象也流传至今。重庆杂技团的杂技剧《花木兰》以此为故事原型,除了塑造花木兰的鲜明性格外,还以木兰为叙事中心,依次展现了一幅或闲居乡野、恬淡悠然,或英勇无惧、杀敌报国,或凯旋而归、喜庆欢欣的人物群像图。在剧中,角色和情节是展现杂技的重要推手,杂技演员充分运用杂技语汇塑造人物,因剧情变幻而营造出乡居、战斗、凯旋、庆功、成亲等舞台场景和戏剧氛围,将杂技技巧作为演员表演角色的基本舞台手段,使杂技从纯技巧性表演转换为对角色塑造的艺术性表演。
儿童杂技剧《涿鹿之战》中出现的“风伯”“雨师”的形象来自于志怪古籍《山海经》中的“风伯御风,雨师行雨”的记载,人物造型也结合了脸谱、靠旗等京剧元素,将马、人、神大战的戏剧性场面表现得惊心动魄又机警有意趣,呈现出一种属于中国戏曲的独特的故事表述和审美节奏。剧中还借鉴了新舞剧的表达形式,以肢体动作为表演强区,以幕布文字作为补充说明,身体表达、情绪抒发与节奏推进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叙事张力,营造了紧张混乱又壮阔宏大的戏剧氛围。但是,该剧主创们并不只是抒发壮美的情绪,更有种种或松弛或无力或沮丧或温馨的柔和甚至低沉的情绪。比如,小石头回忆与父亲嬉闹玩耍的点点滴滴时,观众可以共情家庭的温情和父子情的深重;当战马牺牲自己救助小石头时,观众立时能够移情自己豢养的宠物伙伴,感受小石头的悲恸伤心……这些对比强烈的抒情桥段和场景,有效提升了现代杂技的叙事能力,也营造了观众共情的剧场空间。
三是戏剧精神、审美理念的有意识的融入,诸如道具、场景和角色特质、故事情节的设计等。究其实质,戏剧其实是对社会生活、政治历史、人情世故和世俗观念的表现、发掘和思索,戏剧精神也就是人的精神。人创造了戏剧,戏剧也在创造着人。人的戏剧审美心理定势制约着戏剧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戏剧精神又不断地丰富、充实、调节着人们的戏剧审美心理。而不同的戏剧所采用的具体讲述方式,不过是戏剧精神的一个表现载体而已。
戏剧精神、戏剧情节的植入必然会增加杂技的故事性,杂技技巧也相应地会被赋予更多的精神内涵。但是在杂技和戏剧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受戏剧表现形式的束缚,在小细节、小情感,特别是刻画人物个性方面,无法像经典戏剧、优秀戏曲那样以人物关系、人性展示、矛盾冲突来表达主题和理念,所以杂技剧在融合戏剧精神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其中的平衡点,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在技巧和主题上推动两者优势互补、技艺交融,最终实现点石成金、技艺双绝的艺术效果。
不少成功优秀的杂技剧在融合戏剧精神和审美理念、将戏剧精神植入杂技创作时,往往从角色化、心理化、情节化和意象化这四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为杂技与戏剧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开辟新道。
其一,塑造人物,趋向角色化。以往的杂技剧如《战上海》《渡江侦察记》等,更多是表现英雄群像,而现在的杂技剧已经有塑造人物、表现人物鲜明个性的探索和尝试。云南省杂技团创作的杂技剧《聂耳》描写了天才音乐家聂耳短暂但灿烂的一生,体现出了聂耳活泼灵动、敏感浪漫、热爱生活的多面人物性格,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其二,心理外化,感受人物情绪。杂技演员借助动作、道具、场景、音乐、音效等方式,抒发人物内心不可诉诸言语的各种情绪,呈现人物形象,实现动作向情感、情绪的转化。《聂耳》中有一段精彩的斜坡个人倒立撑技展示,演员的身体语言与人物情绪息息相关,双腿和身体由扭曲不平到大开大合的变化,同时联合手臂力量的支撑,将聂耳从一开始的纠结复杂、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的豁然开朗、自我振奋的思索过程明确无误地呈现出来;《花木兰》结尾处借一袭华美的、铺满全场的大红嫁袍,彰示了花木兰与爱人喜结连理的喜悦、战场厮杀苦尽甘来的欣慰、众人诚挚的祝福等多重意蕴。
其三,注重情节推动和杂技技巧展示的协调统一。笔者认为,杂技艺术创作需要结合剧情去铺排、解构、重构乃至创新杂技技术。比如,由宜宾市酒都艺术研究院原创的杂技剧《兵工厂》中有一段兵工人制造兵器的特写:火箭道具被一分为二、一左一右撑到了半空,杂技演员在连结左右齿轮的绳上表演走钢丝、倒立等技巧,这种独到的创意,不仅合理适时地展现了技巧,还切实展示了兵工人专注研发兵器的工作和精神状态。而《聂耳》中码头工人躬身推车、监工用鞭子抽打工人搬运到零星反抗再到齐心协力维护自身群体的觉醒和变化,这之中除了甩鞭有杂技含量,其他更多偏向舞台戏剧性表演,但能合理交代剧情,没有为了刻意展示杂技技巧而牺牲剧情,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四,富有象征意味的重要道具和主旨意象的设置。《化·蝶》主创借助“蝶”之意象,将梁祝二人的生死爱情与美丽蝴蝶的孕育、孵化、破茧、化蝶的自然过程紧密贴合,以蝶喻人,以人映蝶,多层次、多角度回溯化蝶的始终及爱情的归宿,阐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寒梅疏影——杆上技巧》中的梅树和梅亦是揭示主题和背景的关键道具和意象,梅树是支撑的道具底座,梅则是整场演出的灵魂和气质的阐释,疏影横斜,清冷坚韧又超然脱俗;江西省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山上那片红杜鹃》中的“红杜鹃”也被寄寓了深沉的象征意味,它既实指红土地上耀目灿烂的杜鹃花,也是千千万万投身革命、为革命而献身的女红军战士们的美好化身。
笔者认为,仅就目前的中国杂技和杂技剧而言,扬自身惊险奇绝的传统性技艺之长、补戏剧舞台叙事之短,是未来新杂技的重要变化和发展趋势。戏曲、戏剧元素被大量吸收和运用于杂技舞台,都可看作是艺术表演和创作领域的新范式。戏曲、戏剧及其他更多艺术元素的不断融入,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正因戏曲戏剧等元素在新杂技语汇中的合理使用,才能够衍生出新的情感张力,扩张出更深厚的表现空间和叙事空间,创作出更多有杂技、有主题、有人物、有情节、有意境的综合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