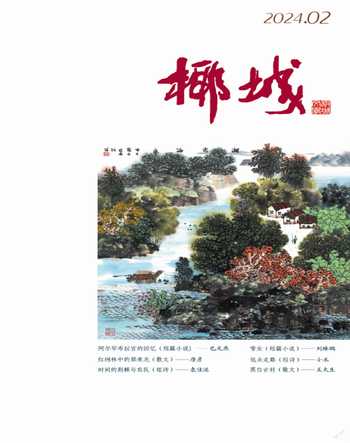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短篇小说)
巴文燕
他仔细端详她,目光炽热,像暗夜里发现目标的探照灯,全然笼罩着她。起初,她还算从容,很快就不堪重负,败下阵来。其实也无所谓,她想,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
他可能感觉到了她的不适,收敛了光芒,说,你知道吗,我是从徐思那儿得到你的电话的。她一时没反应过来,表情有些茫然。他又说,我找徐思也找了好久。她似乎终于听清楚那个名字,从他嘴里冒出来,有点奇怪。她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张薄而有棱角的脸,晃荡在混浊的深水,随着回忆的张力,拍打长满墨绿色青苔的河岸。
徐思在哪儿?她问。
在施秉,他说。
施秉是县城的名字。
他在政府的宣传部工作,全县所有的标语和宣传画都是他写的,他画的,还有各种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电线杆和树之间,飘来飘去。
他还弹吉他吗?
不太清楚,应该还弹吧,他那么喜欢。
他结婚了吗?
他愣了一下,说,他没有结婚,这你应该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沙发上挺直自己的腰,下巴微微往前戳。多少年了,虽然容颜渐衰,但身形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坐她对面,中间隔着一张质地精良的玻璃茶几,茶几上有骨瓷的茶壶、茶杯。这是一家五星酒店,他选的是一间商务套房,有着精致的客厅和宽大的浅蓝色落地窗。此刻,隐蔽在云层后面的太阳,像一位垂暮的老人,懒懒地仰卧在山的起伏处。一簇簇薄灰色的水汽,擦着湿漉漉的街道和人群,跟在夜色的身后,缓缓升起。
他踞身过来,手肘撑在大腿上,脸凑近她,说,说说你吧。
他与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她以为他会是一位油腻的中年大叔,可没想到他还那么年轻——还是记忆中的模样——这怎么可能呢?有一刹那,她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她做的梦越来越多,有时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
我从未停止过关注你。
那为何还要通过他,徐思,才能找到我?
这个有些复杂……他脸上并没有尴尬,一如继往,殷切地注视她。她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轻笑,想,又在撒谎。我没有撒谎。他好像能看穿她的心思。她狐疑地乜他一眼,换个话题:你为什么没变?
你也没怎么变。
不,我老了。
你越来越有味道。他的声音还是那样缓慢,音量恰到好处,因而更好地诠释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你从未像此刻这样迷人。后面这句口气格外真诚。可她听着直打冷颤。前些日子,就有一位年轻、帅气的男子,向她表达同样的意思,并热烈地向她表白,希望往后余生能照顾她。她当时的反应,就是直打冷颤,她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好奇怪。可此刻是他啊,这不是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吗?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她曾经无数次梦见他。尽管,每一个梦,都有着挥之不去的铁锈味儿,就像被摘下来的玫瑰,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彻底死去,尖刺还粗壮起来,演化成生铁,长满深黄色的锈粉。
这个梦可真有意思。
很多很多年过去,只要一想到他,就会陷入记忆的迷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可以抽离。比如谈一场无望的恋爱,比如来一场没有目的的旅行,再比如加班加点地工作、沉浸于某本读不懂的书,或是聚会、喝酒……时间是假模假式的良药,原本异常清晰的线条,在不断的冲刷浸蚀、来来回回中,渐次模糊。但只要稍稍拔拉,大厦般冰冷的雕塑,就会从鲸落变成翱翔的飞鱼。
灰扑扑的街面上,自行车前后轮在他稳健的双腿下,徐徐前行。
她双手扯着他衣襟的两侧,隐藏在他的阔大的背影里,就像躲在一个灌满蜜糖的地窖(冬暖夏凉)。那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施秉家家户户冒着炊烟,忙碌着为年夜饭作准备,而他载着她,穿行在小城的街道上。
街道空旷,灰白,难见一个人影。
坐在他身后,冰冷的空气被隔绝在外,金色的白光在灰暗的建筑物之间呼啸,无论她的眼睛瞟向哪里,两侧脸颊都有刚刚熟透的苹果在炸裂。她那时也还从未谈过恋爱,浸没在忐忑又幸福的梦境中。那刻,她以为这将是她一生的开始,哪怕一生都在这条寂静、枯涩的街道上徘徊,也无所畏惧。
事情并没有按照她以為的那样发展,整个冬天,他踌躇不前,忽冷忽热。好的时候,她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冷淡时,她只剩下一口气,欲断未断地等待他的召唤。这让她痛苦不堪。无处可往的时候,她独自去小平房听徐思弹吉他,她总是请他弹《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她就是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心中升腾起对他难以释怀的情愫。徐思一味地满足她,一遍又一遍,指法越来越娴熟,越来越老道……起初,她的眼里渗着泪水,后来,她凝视屋顶一束灰黑的蛛网,在废旧宫殿的余晖中,细细琢磨,它是如何死去的。
在她那口气几乎断掉的时候,他又来叩响她的门扉。他俊朗的身型、迷人的微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的阳光,容不得她丝毫的拒绝,一切又重新开始——如此陷入无休止的轮回。
有个冷夜,他们并肩站在她家屋顶,眺望这座不大的南方小城。那时县城还没有多少高楼,她家所在的这幢六层楼的房子,鹤立鸡群。他们越过高高低低的屋宇,鸟瞰半个城池,远处,一簇簇只剩稻茬的荒田、倒圮的油菜花地,结满了薄冰;荒芜的棉花垅畴,长出不知名的蓝色小花,一眼望不到边,在冷风中挺起它们纤细的脖颈。再远处,就是潕阳河了,它在山脚下、田地间,迂回出一条亘古的线条,漫向遥远的归宿地。
她从小在潕阳河边长大,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夏天,潕阳河就是孩童时代,她和小伙伴们嬉戏的天堂。无论如何她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这条古老的河水,牢牢禁锢,令她想逃脱又无处可逃。
寒风愈来愈紧,她禁不住瑟瑟发抖,禁不住向他靠过去,他搂住了她。外面的冷和他环绕的暖,令她浑身颤抖,来历不明的火焰在她年轻的身体里噼啪作响。她终于仰起纤长的脖子,迎向他。有一瞬间,她置身于赭红色的宫殿里,身体通透,里面灌满露珠、云雾和漫天星辰,她以一种赴死的决心,让自己镂空如宫殿中央繁盛的花园。然后,然后她的耳膜传来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女性的名字,是从他的嘴里呼出来的。她就像被子弹击中般的跳开。黑夜包裹了所有的真相,她看不清他的脸,更看不清他的眼睛,她感受到巨大的羞辱。
她以异常冷静的口吻请他离开,既然不爱,就不必再纠缠。
那一刻,她像个慧剑斩情丝的侠女,她这个双子座真是当之无愧。他试图解释,但无从解释,证据确凿。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跨越一座山峰。那一刻,她看见少时山峦深处的那座宫殿,如蜃楼般冉冉升起,像一面古代的战旗,在小城的上空叭叭作响。
很长时间,她独自站在屋顶,将自己交托给寒意,既敌亦友,与它们频频对弈。她的皮肤、心脏和血液,都打上铅灰色的补丁。她深信不疑,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光芒会刺穿这冬日的阴霾,亮出它绚丽的彩虹之剑。当时,她是那样想的,坚定得不能再坚定。可是,当他再次出现,以温煦、谦和的姿态,还有脸上淡淡祈求、讨好的意味,她听见线头断裂的吱嘎脆响,刚刚缝合的伤口,支棱起菱形小嘴,嗷嗷待哺。
她仰着溜长的脖子,对着空气嘘了一口,说,你没必要骗我,而且,现在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意义了,他说,这也是我回来找你的原因。我早知道,故事不会这么轻易结束,她说。嘴角微微下撇,像是对自己的不屑,也可能是对他的。
其实我一直在等你,等你来找我。
我知道的,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来?
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想多看看你,看着你生活,或者看着你过完这一生。
如果那是你的愿望,那你是不是来得早了点,你看,我还不是很老(她刚刚还在说她已经老了)。她低头从左到右,扫了眼自己的身体。她穿了件浅蓝色的麻质衬衣,很垂,敞着扣,莫代尔质地的纯白背心,双乳在内衣的支撑下,显出恰到好处的盈满。
不早不晚,他说,刚刚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脖颈处衬衣的领子还是那样,白得发蓝,白得耀眼。
她有点恍惚。
桥上,全是白色的衣领,整洁的,坚挺的,将他的脖子裹得严严实实。脖子的主人双手惯常揣在裤兜里,双腿站得笔直,眼睛在远处的人间灯火漫游。潕阳河就在脚下,潺潺的,流向幽深的暗夜。若隐若现的小城,溢出暗蓝色的光,昏黄,若即若离。很久以后,天空飘起了雪花。那些有着透明绒毛的精灵,围绕着他们,跳起舞来。翅膀是抒情的旋律,陨落的同时,又渐次复活。浸着她的脸颊,浸着他泛着幽蓝白光的衬领。她被晃得痴迷,忍不住踮起脚尖,他揽过她,热烈地吸吮……
你为什么总是穿着白衬衣,好几次我梦见你,都是白的,全身都是白的。梦醒来,我就想,下次一定让你换一件,蓝色的,或者灰色,我后来很喜欢蓝色,你看,我这件衬衣就是蓝色。我知道,他如暖阳般的微笑,分明是位谦谦君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就是知道,你知道的。
她讨厌他说话的口气,那么肯定,不容置疑,跟从前一样。那时她愚蠢地快乐着,心甘情愿臣服于他的霸凌,而今时非同往日,她已不是从前那个怀春的少女。她想起忒修斯之船,漫长的航行之后,此船还是彼船吗。她倏地把杯子重重地放在茶几上,发出咚的一声。他赶紧伸過手去,把杯子摆正。抬头问她,然后呢。
什么?她还沉浸在愤懑的情绪中。
然后我穿蓝色衬衣了吗?他的嘴角有些调皮的意味,无视她的态度。
还是白衬衣!她瞪他一眼。
他又笑了——他笑起来真好看,就像电视剧里帅气又惩恶扬善的男一号。你知道我喜欢白衬衣。她确实知道,他喜欢白衬衣,大冬天的,里面也是件白衬衣。她隐隐记起,她还拿她仅有的积蓄给他买过一件,但未见他穿过。那时,县城大礼堂舞台上简陋的舞池,白衬衣总会散发幽幽的蓝光,吸引所有女孩子的目光,他随便向哪个女孩伸出手去,对那个女孩来说,都是过后向小姐妹们炫耀的谈资。凭着他俊朗的外表和莫名的文艺气质,他所向披靡,哪里受过什么挫折。倒是她,常被他晾在一边。她却不以为然,坐在一旁,看着他的美好,她有一种置身事外的空性体验。有时,也当作是观看一场精彩的演出。她假装看不见那些和她一样贪恋的女孩。
如果没有徐思那个小平房,我们很难见面,我们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好过。此刻她就是不想遂了他的意。
我已经原谅你了,他说,你不用害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我才不怕你呢。她的嘴真硬。
很多很多年前,即将大学毕业的那个冬天,在家乡的小县城,她遇到了他。很平庸的开始。那时的文艺气息浓厚,人们不是写诗作文,就是喜欢弹吉他,年轻人喜欢聚在一起听歌、弹琴,有时也聊聊文学、朗诵朗诵诗歌什么的。他们就是在那样的场合认识的。怎么说呢,她看到他的瞬间,就被迷住了。首先他很帅,气质文雅,最致命的是他眉宇间莫名的忧郁,符合她内心对男朋友的所有向往。而她坐在木椅上的恬静,像树下一枚搁浅的贝壳,在清风中传出悠扬的波浪声。那个夏天,他和她经常挤在那间狭窄的平房里,听徐思弹吉他,《爱的罗曼史》《悲哀的礼拜堂》《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忧伤、空旷、深邃的古典音乐,让她萌动的心愈演愈烈,直至不能自已。
有个晚上,她印象深刻,整夜她低着头,盯着三尺开外那双泛黄的皮靴。阿尔罕布拉宫细碎、瑰丽的音符,在她耳边缠绕,富丽堂皇的幻境将她笼罩……直到那双鞋的主人站起来,开始移动,她才从那起伏的迷雾中醒来。她昏昏沉沉抬起头,他正瞅着她,嘴角挂着自信、恬静的微笑。他们一起走出平房,他送她回家,而徐思,则止步在平房的转弯处。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他们弹吉他的人,在路的尽头,站了多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方小县城的夜晚有着幽长的阒寂。木电线杆子下粗上细,顶上悬挂昏黄的路灯,隔很远才栽一根。灯与灯之间,足有几十米是黑暗的边城……边城的最顶端,是完成无数人宿命的潕阳河。
谁知道呢,后来,她赤脚站在潕阳河的狭窄的岸边,某个高处,晨露包裹她的双脚;脚趾间刺骨的凉意和无所依傍的湿滑,沿着两腿传导至她的后脖颈;有一根神经触突异常清薄、敏锐,在有着无数蜂窝的虚空中左冲右突。她竭力握紧那根神经,感受着倒挂的荒诞和虚无。她的脚掌抓牢地面,十个脚趾杂乱地搓揉,像踩在滑板上。细长的草叶在她脚下倒伏,躺成一片湿润滑腻的尸体……为了控制住即将倾圮的身体,她的双手抬起来,慢慢展开,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最后,如一只怪鸟的羽翼,扇动着冲向天际。
他突然站起来,绕过茶几,挨着她坐下,伸手把她的左手握在掌心。她明显感觉到心脏像只跃动的小鹿。她很讨厌这种感觉。她真想把那只鹿的头砍下,当球踢,踢得远远的。那只鹿侧身望她,一会儿,跳着脚跑开了。她能看见,在林子深处,它和同伴们迅速集结。她用了点儿力气,才把手抽出来。说,你不用这样,好像很爱我的样子。
我是很爱你。他说。
她睨他一眼,屁股往右移动半尺。
他的双手悬在半空,举起,又放下,无处安放的样子。
或许这种爱跟你理解的爱不太一样,但确实是爱。他用食指轻轻挠挠太阳穴,接着说,我的身体是仰面倒下去的,你还记得吗,当时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你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听到“啪”的一声,掉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比山还高,像一道白色的幕墙,挡住了你和这个世界。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她蹙着眉,牙齿紧咬。
不,你听我说完。他的眼神有她从未见过的坚定。我刚进到水里的时候,确实很害怕,那种怕是难以形容的,心想,完了,彻底完了。早忘了什么是恨,只有恐惧,无尽的恐惧。可就在最后的时刻,我释然了。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体验,如释重负,懂吗,如释重负。
她茫然地注视他。
就是所有的牵绊,焦虑、恐惧,活着的那些烦恼、忧虑,全都没有了,瞬间消失。我感觉自己是一片羽毛,一片自由自在的羽毛,想去哪儿去哪儿,任何时间和空间。什么爱啊恨啊,简直觉得是小孩子过家家般的可爱和悲凉。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轻轻抖动。
诗人说,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他是对的,只有脱离时间的桎梏,我们才能获得自由。你以为你推我那一掌是将我置于死地,却无意间助我脱离了时间的控制,我得谢谢你。
她的嘴角有掩饰不住的不屑。她想,也许这又是一个梦,不用那么当真。她后来习惯了被梦带走。有人说那是梦魇,但是,只要突破那个界线,也无外乎就是梦中梦而已。
你是来带我去天堂的吗,还是去地狱?
他愣了一下,突然迸发爽朗的大笑,他一边笑一边站起来,走到窗前。云层后面幽凉的热度,已经彻底滚到这个星球的另一端。透过浅蓝色的玻璃,她看见纷飞的雪花,它们在半空中抱成团,欢欣鼓舞地洒向大地。它们永远无法理解暗夜的巨大悲伤。他的笑声消隐于其中。
那对蔽天的翅膀,是徐思帮着收拾的。
你怎么长了这么一双翅膀,好大啊,徐思惊异于翅膀的巨大,仔细端详它们。她整个人缩成一团,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乱蓬蓬的头埋进羽毛深处。染上污泥的翅膀斑驳而破败,像飞行着穿越了整个冬天。
她的声音在急促的鼓点上跋涉:我不知道,不知道……那水太深了,太绿了,碧绿碧绿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绿的水,一眼望不到底,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她喘着游离的气息,让人感觉随时都会窒息。
徐思抚摸她湿漉漉的头发,说没事的没事的,真的,没事的。
翅膀太大了,抵到了屋顶,灰尘和蛛网裹在上面,他不得不站在琴凳上把它们扒拉过来,小心收拢在她身体两侧。他把毛巾浸进热水里,拧半干,小心擦拭她的翅膀,动作轻柔。在他虔诚的呵护下,翅膀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消隐不见,她原本白晰的手臂露了出来。有几根残留的羽毛,根扎得太深,吉他手取下琴弦,缠在羽毛上,刚好六根。你的琴……怎么办。他说没事儿,你什么都不用给我说,我都知道的。他坐下说,我弹琴给你听吧。
他双手环抱无弦吉他,灵动的十指,将红色城堡演绎得柔肠寸断。
她在阿尔罕布拉宫那间废弃的屋子里,沉沉睡去。
等她醒过来时,两条手臂干干净净,只有几道凹陷的暗红色印痕。她叫徐思的名字,没人答应,无弦吉他斜靠在黑色的谱架上。
那个冬天可真冷啊,她一个人奔走在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都没有他的身影!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可以随时把声音传至某个人的耳朵,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她無助地去到那间小平房,吉他手裹着一件黄色的军大衣,照例在弹吉他。她问吉他手,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吉他手茫然的表情,眼神游移,她冲着他尖叫,声音把空气撕成碎布条,有着烙人的焦糊味儿。
你知道,你一定知道他去哪儿了,你们是那么好的兄弟。
不,我们不是兄弟。
我不管,告诉我,他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她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像个垂死的病人,说,你知道的,你告诉我好吗,求求你,我有很急的事要找他,特别特别急……
我不太确定……
她的十指在他的手臂上,像榨干的琴键,飘着最后一根稻草。
吉他手刚把话说完,她兀地站起来,冲向门外,冲向车站。
那个冬天太冷了,下起了百年难遇的凝冻,班车都停运了,铁轨上也是厚厚的冰层,仿佛整个世界被寒冷封印,不能挪动须臾。凭着意念,她终于找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请求师傅将她送达三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面包车司机只是碰巧路过,自然是不敢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中冒如此大的风险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居然被说动了,亦或许是最后一刻,徐思递过来的那一摞钞票?
面包车喘息着缓缓爬行,路面飞舞碎屑般的雪雾,冰凝在车轮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她仿佛又听到吉他手的弹奏,把她带进雪的宫殿,王的宫殿,那或许是阿尔罕布拉宫最初辉煌的模样。那时,吉他手紧紧握住右上方的一个把手,冰冷的车上,他的手心浸出一沓沓的汗来。
三十公里的路,爬行了四个小时。
他们到达一个有着很多木楼的小镇,在其中的一幢木屋,白衬衣走了出来,看到她和徐思,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他并没有请他们进屋,而是走过去,拉过她的手就往镇边上走。在一个干涸的低凹处,她所有的仇怨化作润泽的溪水。他告诉她,这里就是他的家。她问他为何不告而别。他说不想让她知道,他其实是来自穷乡僻壤的一个穷小子。这有什么呢,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贫穷,甚至是灿烂爱情的精美点缀。她心疼起他来,望着远处冷峭中破败的乡村,她想,她愿意为了他生活在这里,生儿育女。在那样的向往中,她有了告诉他的勇气。但是,她感受到他的怯懦和犹疑——他抱着她的双手松驰了下来。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结婚,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去医院……打掉,你不用担心,我,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她迫不及待地在他的脚下垫上几块砖,她想免除他所有的为难和自己的不堪。然后,她看见一个红衣女子朝他们奔跑过来,徐思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
你太可恨了,那里根本就不是你的家,而是你女朋友的家,说女朋友不太恰当,那不过也是你的一个玩物而已。哦,对了,你的家究竟在哪儿?她也走到落地窗前,望着外面的纷飞的雪花,声音像是柔软的棉布,在玻璃上滑动,凉嗖嗖的。
我的家就在施秉,我和徐思是一起长大的兄弟。
你待他可不像兄弟。
确实,我对不起他。他侧过身来继续说,我这人特别会装,装帅,装文艺,装女人喜欢的模样。我对谁都没有用过心,包括我的父母,我的亲哥、亲姐,我都没有用过心,我只是一味的索取,占有。
对我自然也不会。她心想。
他好像能听到她说话,说,是的,我对哪个女人都这样。他平静的口吻,没有歉疚的意味,她想表达对他的不满。但他接着说道,我那时真是没心没肺啊,仗着别人对自己的好,左右逢源,树上开花,真是活该。
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所以,其实我特别感谢你。
什么?
感谢你有力的一掌,机缘巧合,让我提前感受到真正的自由。不,那是自由都难以形容的感觉。他转过身来,想拉她的手,再次被她避开。
无论他是如何想的,并以什么样的身份找到她,她都难以接受。他看出她的惶惑,说道,你不用怀疑,你现在看到的我,既是我也不是我。從那天起,我就停止生长了,我俗世生命的全部,停留在落下去的那一刻。这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你以后会明白的。
即便经历了那样的不堪,她还是请求再见他一面。她写下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请徐思转交给他。她无视吉他手的劝阻。他们约好在潕阳河一个偏僻的角落见面。那里人迹罕至,被茂密的枊枝、荆棘、矮树丛遮蔽,只有施秉的老渔家,偶尔去那儿钓鱼。那是一个死水般的深潭,施秉人都叫它龙潭,运气好的话,能钓起七八斤的大鱼;运气不好,一个小虾米你也休想抓到。还有传说,龙潭里有一条青龙,一年出来一回,出来一回就得死一个人。
他姗姗来迟。
你为什么选这里,他问,你不怕啊?
她说,孩子,没了……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沾着青苔的鹅卵石,朝安静得有着一层薄雾的潭水扔过去。
如果是这事儿的话,我马上走。他说。
她凝固在那儿,像贴在宫殿门扉上半裸的妇人,在细雨中微张着苍白的嘴。他走到她面前,狠狠揽过她,说,不过,我觉得这里很适合做那事儿。他的眼里全是欲望。那一刻,她在想自己真贱,每一次,都是更深的伤害——不乱刀砍死你,你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刀光剑影。一念之间,她决定把这些伤害全都还回去,她要为那个逝去的生命讨回公道,为自己讨回公道。她长舒一口气,提出到潭边的一个高处,那儿有一个溶洞,溶洞前有一块厚实的草地。她说,人在上面,翠绿的潭水在下面,行事定会有种奇幻的效果。他露出灿烂的笑容,拉着她就往那个高处跑。
几分钟以后,她眼睁睁看着他下坠的时候,一道彩虹在天边升起,刺穿了冬日的阴霾,随着他的身体,一同落入无尽的梦魇。
如果你是来复仇的,现在就开始吧。她对他说。我给你说了那么多,你怎么还没明白。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只是来看看你,来向你说一声抱歉,对不起!尽管他一直是温和的、谦逊的,但当他说出这句话,她还是有些意外。她本能地表达,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
是我错在先,对不起!他再次说,面向她徐徐弯腰,郑重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她有点不知所措。她怕自己再次陷入圈套。然而,他的眼睛是那样明亮、平静,是她见过的,也是她没有见过的。
他们并立在落地窗前,久久不言。
绚丽的雪花,时不时跑到温暖的光晕中,它们有时缩成一团团光的边角,跳动着桅子花的幽香,晃若虚幻的春天气息。
为什么才来?
其实我就缓了几天,但也挺久的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真的该走了,就像徐思那样。
你不是说他在施秉吗,整个县城的标语和宣传画都是他写的,他画的,还有各种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电线杆和树之间,飘来飘去……
是的。
可是,他不是和你一样,也……死了吗?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不是吗?
那个吉他手的面孔,终于从水里浮现出来。清瘦,白晰,嘴角挂着轻笑。他弹奏吉他的时候异常严肃,表情冷峻。很少言声的喉咙,有时也会发出沙哑的吟唱,旋律却十分准确,转换起伏,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是,她似乎从没有认真观察过他,她只关注过他的十指,他的琴声,他小平房里日日蕴积起来的黏稠的氛围,直至他为她处理好硕大、肮脏的翅膀。她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也就在那个时候,她清晰地看见另一双翅膀,在她和吉他手的肩胛处升起,穿墙破壁,飞向远方。
他把她安抚好,把无弦的吉他搁在黑色谱架上,就替她自首去了。他声称是自己不慎把他的兄弟推下龙潭。警方勘察了现场,确实没有发现打斗、挣扎的痕迹,调查俩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罅隙和仇怨。在那个没有手机,连座机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当然更不可能有无处不在的监控探头,警方相信了吉他手的自首。而她一直处于惊惧当中,没有半丝半毫的勇气站出来,走到大庭广众之下去澄清事实。
我没见你之前,徐思就告诉我,他喜欢你。
她望着窗外灯火阑珊的巨大迷宫,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他。
世人永远梦不见那些安静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