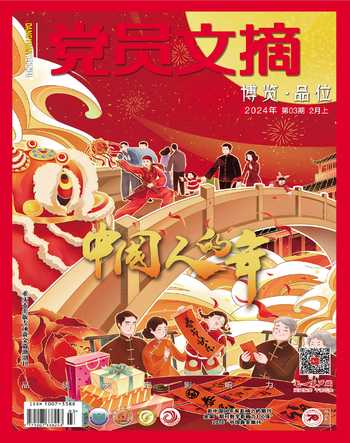被“遗忘”的黄文弼:沙漠中“一个人的考古队”
倪伟

“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袭老羊皮。”在一首赠诗里,语言学家刘半农如此勾勒好友黄文弼在沙漠戈壁中的寒酸模样。
1930年,37岁的考古学家黄文弼终于结束3年多的西北科考,从新疆平安回到北平。他启程的时候,满口牙齿尚健全,回来时已经掉了几颗。
“黄先生此行3年余,经历许多艰难辛苦,成功而归。”在北大为他举办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激赞道,“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从此,黄文弼被认作“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
此后30年,黄文弼辗转于北平、南京、西安、城固、成都、峨眉等地,完成了新疆考古成果“三记”“两集”的撰寫,为新疆考古揭开了序幕。
丈量万里山河
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扩张,激发了西方人对于世界未知领域的科学探险兴趣。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西北文物大量流失,其中,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及西域楼兰古国的文书、简牍、佛像等,被西方和日本探险者一箱箱、一车车运到海外。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准备发起他的第四次中国西北行,却遭遇北平学术界的群起抵制。斯文·赫定审时度势,与中国学术界代表坐下来谈判。由北大国学研究所等十余家学术单位组成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达成19条协议,约定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中,专事考古的学者是黄文弼。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考团从北平出发,前往内蒙古。
1928年初,黄文弼率领一个小分队,前往新疆开展工作,队伍里只有他一位学者。在外国探险队肆意发掘、盗扰的遗址之上,黄文弼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掘,是吐鲁番交河城的一处古墓葬区。他按照墓葬区的分布,分区域有序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800余件、墓表120余方,以及大量其他随葬品。
1930年4月,黄文弼抵达罗布泊北岸。4月23日上午,他派出两支猎户组成的小队出去探寻古迹,自己留在驻地工作。当天下午狂风骤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晚间,大风未息,驻地的帐篷几乎被摧毁。黄文弼听着狂风呼号,担心没带皮衣的猎户小队,一夜惴惴不安。
次日上午,大风停了下来,但尘沙未减,寒冷异常。一队猎户终于安全回归,而另一队的猎户拉亦木却始终没有回来。傍晚,黄文弼远远瞥见一个骑着马的人,身披大裘,戴着皮帽,猎枪横陈在马背上,手执缰绳,从帐篷前徐徐经过,正是猎户拉亦木。黄文弼在考古报告中罕见地喜形于色:“余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

黄文弼在整个罗布泊考古中最著名的发现,就在拉亦木到来后。
那是一处汉代烽燧亭遗址,只剩西墙的墙基和3根直立的木柱。黄文弼在芦苇草中捡到了数十枚木简,根据木简残文,此地名为“土垠”。土垠遗址一共发掘出70余枚汉简,比国外探险者在新疆发现汉简的时间早很多,是在新疆发现的最早一批汉文简牍。
离开罗布泊后,黄文弼继续前往塔里木盆地,在盆地中考察了一年半,调查遗址百处以上,还新发现了大量古城。
1930年9月,完成所有任务后,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回到北平。他带回了煌煌成果,仅新疆的采集品就有80余箱。不仅如此,整个西北科考团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地质学家袁复礼在北疆发现了恐龙化石;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和“小河公主”;中国现代学术界“四大发现”之一的1万多枚“居延汉简”,也出自西北科考团。
这一次考察,奠定了黄文弼终身的学术方向。此后,他于1933年、1943年和1957年重返新疆。他在新疆境内的总行程超过38000公里,天山南北几乎所有古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穿越塔克拉玛干
自从离开北平,黄文弼就踏上了风餐露宿的苦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壮举,是他凭借简陋的装备和物资,竟然成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据《汉书·西域传》及《水经注》记载,塔里木盆地南部有一条“南河”,最终汇于罗布泊。“南河”后来消失在沙漠中,为了探寻这条古河道的遗迹及变迁,黄文弼决定做一次冒险。他由盆地北沿的沙雅,穿过茫茫沙漠,到达盆地南沿,用时1个月零6天。结束之时,对于旅途的艰难与惊险,他只淡淡记了一笔:“辛苦备至。”
翻开黄文弼的日记,则能具象地体会到所谓“辛苦备至”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进入沙漠时正值风沙凶猛的春季,时不时就起风沙。最严重的时候,“走沙扬尘,十步之内,即不见人”。黄文弼一行几乎每天都会迷路,尤其是至克衣河的400余里中没有任何水草。他们一路走,一路向遇见的猎户、村民询问古代遗址,“沙漠湖滩,有古必访”,结果采集到许多陶片、铜钱、古文书残纸等古物。
“南河”追踪之旅,黄文弼根据现存的断续的河床痕迹以及沿河遗存,判断其断流发生在公元5世纪至8世纪之间,这为该地区古国和丝路兴衰等课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证据。
从田野回到书斋,另一段更漫长的苦旅在等待着黄文弼。他要将所有考察的成果写成报告,为学界共享。但彼时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只能在颠沛流离中笔耕不辍。1939年至1942年间,他奔波在川陕两地,一边教学,一边继续新疆考察报告的撰写,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旦给予他时间和安稳,他便爆发出惊人的学术能量,《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相隔不到4年先后面世。1958年,当《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出版时,黄文弼新疆考古的代表著作“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全部完成,历时26年。这位倔强而坚韧的学者,终于在纸面上将万里足迹重新走过。
日本艺术考古学家前田耕作曾说:“黄文弼为了把案头的金石学转换为富有生机的田野考古学,已经苦苦行进了4万公里。把这样一个黄文弼从尘封了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就相当于把偏向西面来看中亚的观点,摇摆到从东面来观察。”在他看来,黄文弼以一己之力,将新疆乃至中亚考古和历史,变为中国的学问。
黄文弼的生命止于1966年,享年73岁。
2012年,黄文弼后人将其生前使用和珍藏的图书文献,无偿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成立了“黄文弼中心”,将“黄文弼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作为重点科研项目。研究者们正分类整理西北科考团中方成员未经公布的大量文献,重新打捞那些尚未被充分利用过的学术资料,让那次科考成果在百年后最终完成。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