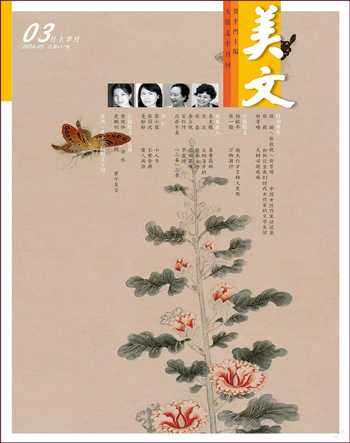罗盘经
一
没有机器响的日子,宁静的村子显得无比的空旷和低碳,童年的夏天,仰望头顶永远是瓷蓝瓷蓝的天空,因为有抽水机的弥散而充满了响亮的意趣。
“Z”字形的摇把由慢到快,循序渐进旋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轰、轰、轰……”随着一股黑烟腾空而起,很快飘散在田野上,抽水机开始欢快地把歌声送往田间地头,为小麦、水稻或棉花伴舞。村背埠头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我并不反感站在抽水机旁彼此说话听不清楚,傻傻地在那里看师傅怎么加固螺丝、添柴油、上皮带,怎么把机器弄响,听抽水机声是我小时候借助耳朵贴近机械化生活的唯一途径,单调、不知疲倦的抽水机给了我比家乡的小河还长的想象和日出日落一样简单的开心。
摇摇把也是一门学问,弄不好会反弹到自己,机器歇下来,趁师傅不注意,我也会使出吃奶气力学着师傅的样子用力去摇,才明白自己表演了一幕蚍蜉撼树。至于为什么要把水从小河里引入高处修筑的渠道,是我当年一直不关心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跳进渠道的水里嬉戏,去体验冲浪的感觉,更好奇的是水怎么从管子里出来,我的快乐却往往由于抽水机师傅莫名其妙的呵斥“想死啊——”而化为泡影。抱起湿淋淋的衣服,走了一些路,转过头,我会不知好歹对着远处的师傅扔下一两句粗话,甚至捡块小石头朝抽水机的方向以抛物线的方式示威,然后撒腿就跑。
过了几天,我没心没肺忘记了对抽水机师傅的无礼,又无忧无虑过来看他熟练地抡起摇把发动机器,可恶的师傅总会扬起那钢铁摇把凶狠狠地瞪我一眼,心情不好时还会拧我耳朵报复我,质问我上次为什么骂他,我就学语文课本上刘文学的样子宁死不屈,把师傅想象成偷摘生产队地里辣椒的地主。更多的时候,他也就做做样子而已。在村里,师傅比较受人尊敬,况且我们村只有一台抽水机,它离村庄有一里多路,搭建了简易的棚子遮风避雨。抽水机一般还难得响,我总盼望一身油渍的它响起来,寂静的村庄会因为它的响声而明媚、生动、饱满起来。现在终于明白儿时的无知,抽水机一响就意味着干旱或内涝,队长的眉头就会皱起来,担心收成。看来,抽水机连同师傅的地位比它的响声高。到了冬天,抽水机派不上用场近乎冬眠,怕有梁上君子的惦记,生产队里会派强壮劳力将抽水机抬进队屋保养,来年春天再弄回埠头草棚里,日夜守护着全村的丰收。
抽水机师傅和我同村,同姓,他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乡村,开拖拉机的、碾米机的、抽水机的,还有进合作社(就是商店)当营业员的,印象中大都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子女。我那時也就十岁左右,成天就知道浑玩,书包、书本是放学路上很不错的武器。但是,对类似于抽水机师傅的职业我是又敬又畏,甚至把想当一名拖拉机手的理想写进了作文,那个摇响机器的勇猛连贯动作我用成语“一气呵成”描述还得到老师的夸赞呢。
那个时候,农村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东西就是三机四机的,比如拖拉机、碾米机。假如在村子里来了辆绿色吉普车,总给人一种不太现实或者不真实的感觉。我姑夫在景德镇市直机关做事,逢年过节,就会调部车过来看我奶奶,村里人都觉得很新奇,纷纷过来看车子、凑热闹,当时我也觉得特别神气,以治安巡防队员般的警惕性忠实地守卫吉普车,不许邻家孩子接近去摸去碰。那几天,我很山大王,同伴们都比平时听话,但这种良好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就被乡村的无聊乏味冲淡。一年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过年,儿时最向往,有时,妈妈手里的活忙不过来,会叫孩子们到合作社打瓶酱油,或称几斤盐,我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干,其后就用几个剩钱买糖果或几卷纸炮回去,妈妈是不会吝啬的。怀揣纸炮,会有一大帮伙伴围绕,此时我很有号召力。找来尖石头一锤,“叭”,脆亮的响声连同自己的喜悦一起在伙伴们周围炸开,享受到的是乡村孩子那最淳朴的几分刺激带来的快乐。
其时,印象中最深的还是碰上谁家宰杀“年猪”,可兴奋坏了以我为首的一帮凑热闹、瞎忙乱的小家伙,从捉猪时起,便围着看大人如何绑、杀、烧开水褪毛、取猪头、倒悬在木梯上、剖肚翻洗大小肠……整个过程我全看个彻底,大人们也不责骂,要在平时,早把我们轰散开。捡起猪脚趾壳,装些案板上的碎肉,放在烘桶里煨,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肉让人垂涎三尺,我半生不熟地吃起来,便觉得是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了。其实我家在村子里地位并不高,一是论辈分偏低(本是好事,瓜瓞绵绵),几乎逢人都要喊叔叔、爷爷、太公的,甚至躺在摇篮里的孩子我也要喊他“毛叔”;二是家里阶级成分偏高,还好属于贫下中农队伍(是中农),没有影响升学,也没有给我平时的生活带来阴影,现在想来才清楚毕竟在那时中农也是团结、争取的对象。
还有一个和别人家不一样的是,我家居然没有放养生产队里的耕牛。像一个没有恋爱经历的孤独孩子,我站在栎树下发呆,很羡慕不少伙伴放学回家骑牛出去到村前的草洲放养,炊烟飘散时分,在夕阳里他们带着饱满的神情、拖着老长老长的影子缓缓而归。这个“牧归图”已深深地烙进我的脑海,多么的诗情画意啊,而听得最多的是大人的软硬兼施:“不好好读书,放牛种田去!”我常常纳闷,放牛——那么美好的事,怎么被当作吓唬人的代名词了。那时,我显然没有听过贺绿汀创作的驰名世界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但我特别陶醉那样的情景意境,这是与我的儿时生活息息相关的啊,遗憾的是我只是当了一名临渊羡鱼者,以至至今我也没有掌握骑牛的本领,虽然在读师范时学会了吹一手漂亮的竹笛,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当一名优秀的牧童了,只能选择到舞台上演奏陆春龄的《小放牛》,而那种原生态的味道怕是永远也无法通过笛孔表达出来。
对啦,说到草洲,那是鄱阳湖的温床,那是我从小摸爬滚打的家园。那里生长着两样植物,遍地都是,挖出来,洗干净取根剥皮,可以生吃,味道甜,有点粉,学名我叫不上来,土话分别叫做“叽葛哩”、“老虎姜姜”。“叽葛哩”像微缩版的葛,开紫色的花,皮是褐色的;“老虎姜姜”则像葱蒜,开白花。它们与红遍初冬的蓼子花都是隔着季节的邻居。更多的时候,我的眼睛比鄱阳湖畔无边的草洲空旷,面对没什么零食吃没什么玩的偏僻乡村,我们只能选择泥巴水草为伴。因为有“叽葛哩”“老虎姜姜”的点缀,草洲给饥饿的岁月带来了许多欢笑,它们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那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当年,我羡慕死了城市的公园,每天面对的是毫不起眼的草洲。而今,草洲拥有一个时髦诱人的名词——湿地。有的地方开始建湿地公园,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带之不走的草洲资源吸引游客。草洲还是那个草洲,居然换个叫法身价倍增也能卖钱了,就可以理直气壮叫旅游了。
我一直没去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没有资格养耕牛,难道是照顾我家没有剩余劳力吗?还是妈妈为了考虑我们学习而拒绝了生产队的安排?现在妈妈年岁大了,我想当时应该是有很多原因生产队才不给牛让我家养吧,事过境迁,何必再去勾起老人家对那段酸楚往事的回忆。不过,除了缺穿少吃,我并没有感觉受到什么偏见和歧视,我还是很喜欢、留恋在老家的日子。
记得我家菜园离村庄有一里多路,妈妈弄农家有机肥抬去园里时,总要我在前面搭把肩。一路上,我也和母亲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交流学习体会,母亲的表扬会让我欢喜老半天。这是我唯一乐意参与的家务活,到了菜园扁担一放就可以在山水田垄间去放牧一颗稚嫩的心灵。那个时候,渴了,蹲下去掬一捧田沟里流淌的溪水喝,绝对不用担心是否有农药、除草剂的残留。这是乡村留给我最沁人心脾的回忆。
二
记忆里散落的家园,有一缕浪花是为哥爷跳跃的。
总是不经意会回一趟老家,没有特别的安排,也不一定是特别的日子。自从奶奶不在了,每次回去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看看哥爷,轻轻地叩开一幢虚掩的小木屋,那是哥爷的住所。
哥爷乃二伯,就是我父亲的二哥。也不知家人为何把“哥”“爷”二字搭配在一起赋予二伯,颇具诗意化的称谓,就一直这么叫着,未去细究。哥爷也乐呵呵答应着,一脸的快慰。
哥爷,拥有一副瘦瘦高高的身影,却不失挺拔,尤其那微笑的嘴角显得那么的和蔼可亲,成为我少年时动人、温情的细节,多年来一直印在脑海里。
哥爷出生于1929年(己巳年),祖父为他取了个挺文化的名字——尊圣,圣人乃儒学鼻祖孔子也。听祖母说过哥爷小时候并不“尊圣”的趣事。那时大家庭还算殷实,到了启蒙年龄,送他进私塾读书,几天下来,哥爷说什么也不愿去学堂了。或许哥爷天性就对封建伦理道德有叛逆反抗精神,老先生摇头晃脑教念“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文字时,野性的哥爷早已坐不住了,憧憬着投身山林湖泽放逐天真的童心,为此没少领教戒尺的力量。祖母那个气呀,逼哥爷一天捡两畚箕猪粪,以熏醒他回心转意走入正道,年少的哥爷居然爽快答应,雀跃而去。哥爷是受不得私塾的诸多羁勒的。
然而,奇怪的是,我小时候,倘若侄儿辈的人完不成作业只顾疯玩,他会大吼一声:“不好好念书,跟我捡粪去。”我们就会乖乖地端起课本装模作样念几句。
年轻时哥爷结过一次婚,生一子——我的堂哥,因故不久二婶改嫁了。哥爷是个老实厚道人,从此一直孤身鳏居,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
患难之际,哥爷对我们家挺好,帮把手搭把力是家常便饭。母亲每每回忆起往事,常常对我们说:“对那段艰辛的岁月,你们什么都可以忘记,唯独不能忘却哥爷对我们家倾注的一片真情。”六十年代后期,父母从油墩街镇搬回老家,父親要到二十几里外的一所中学教书,许多农活、家务杂事全部落到母亲的肩上,从未抓过犁耙的母亲默默承受起了一切磨难,一天下来常常是疲乏困扰、头晕目眩。哥爷非常怜惜他的弟媳——我的母亲,尽力帮我们家干些诸如挑水、担柴之类的重活脏活,以减少母亲的劳动量。在哥爷的帮助下,我们家终于从风雨飘摇中走了过来。印象中,父亲每次从学校回来,买了什么好菜,总少不了要我们去喊哥爷来尝尝或留给哥爷一份。后来,每看到饭桌上摆出红烧肉、米粉蒸肉,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哥爷来。
哥爷后来随堂哥去邻乡鸦鹊湖垦殖场当农工,也常常回村。八十年代初,我还在读初中,那年到垦殖场去看哥爷,当时他为普田畈小队经营几亩菜地,就一个人支个茅屋吃住在菜地旁。我就是那时才认识圆圆的包心菜、吃上甜甜脆脆的包心菜的,看着哥爷在一大片包心菜地里劳作,觉得哥爷会种包心菜真了不起,在那物质贫瘠的年代,层层叠叠的包心菜卷起了少年的我对哥爷的又一层敬意。离去时,哥爷让我带了两个回家,背着沉沉的包心菜,我一路兴奋,想着明日家里升起的炊烟一定更加生动。
那年,少不更事的我还想证实一下祖母讲的关于哥爷小时候不读书的故事。问起哥爷时,他布满皱纹的脸抽动了一下,浅浅一笑以掩饰内心的无奈、苦楚,久而无语,接下来鼓励我好好学习,不可步他后尘。后从父亲处得知,等到哥爷幡然醒悟想要读书时,家境开始破败下去。我真后悔那次莽撞不经意触动了哥爷的心。其实,祖母讲那故事的用意是教育孙辈要好好念书。我等几个孙儿还真没辜负祖母的良苦用心,只是委屈了哥爷,成为大家族反面教材。好在哥爷自己也常常奚落自己,心甘情愿以此警醒后辈。
几年不见,时间的风霜悄悄染白了哥爷的两鬓。哥爷识不得字,话语也少,却特别喜欢听收音机,一部破收音机伴随哥爷几十年,信息、政策、时事新闻、戏曲、生活常识、评书联播等,他都收听。哥爷耕作之余,能有此爱好,生活过得异常的滋润、充实、有趣。
借着从窗户上透进来的光线,我看了哥爷的陋室,收拾得还算井井有条。
哥爷对土地特别有感情,先后在田头地尾、荒山草滩边边角角开垦出十几块大小不一的耕地种植农作物,日子就这样在锄头的刨挖下变得生动、丰满起来。有时,我会让哥爷带我去那一块块寄托哥爷晚年生活情趣的荒地看一看,居然被哥爷伺弄得很肥沃,很茂盛,四季青青,花香馥郁。望着自己用锄头蘸着汗水写出来的作品,哥爷笑出了孩子脸。哥爷宛如一个在大地上行吟的田园诗人,让身心放牧于荒岭僻野,心境散淡如菊,悠然为人处世。
有一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祭祖。哥爷询问起我的情况来,他教导我要珍惜自己的工作,别弄丢了。哥爷还一本正经告诫我不能贪污、受贿,说那样会坐班房甚至打头的。这些想法,想必都是收音机告诉哥爷的。淳朴的哥爷如此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因为我这一介书生无职无权,与腐败基本无缘,只是难为了哥爷一份牵挂、叮咛。我便把头点得像熟透的稻穗一样,让哥爷放心。
吃过午饭后,我要哥爷陪我去祖母、祖父坟茔前尽点孝心,在湛蓝的天空下,哥爷银白色的头发格外醒目。祭过坟,该与哥爷告别了,望着哥爷并不起眼且有些佝偻的背影,我的眼睛微微湿润起来……当再次见到哥爷时,哥爷居然问堂哥我是谁,苍老的话语、无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有一种预感在蔓延,那一刻,我想也许留给哥爷的时间不长了。一“想”成谶,只过了大半年时间,突然一天,我接到堂哥语速平静的电话:“哥爷走了,有空回来送一送。”哥爷的葬礼按照老家风俗进行,庄重热闹,三天后安息在小村南面下岸一高地上。
而今回老家,我还会去看望几眼那陪伴了哥爷最后岁月的平房屋,在屋檐下静静地站立,望着紧闭的前门耳门,透过窗户看到屋内墙壁上的蓑衣,摆放在墙角的锄头、扁担、畚箕等,眼睛微微湿润起来,缓缓转过身,踽踽独行村头田间,去寻找哥爷近九十年的风雨足迹。在我的老家,多少老人都是和哥爷一样走过了平凡的一生,然后变成一个个隆起的小土堆,最终淹没在岁月的草丛间。
回想我们的一生都是循着故乡所指的命运和路径,哥爷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冥冥之中的罗盘经的指向?
(责任编辑:庞洁)
石红许 江西鄱阳人。散文见诸中高考语文试卷、各种文学选本和文学期刊。著有散文集《河红万里》《风语西河》《山河新雨》等。曾获刘勰散文奖、中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奖、首届中国红高粱文化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