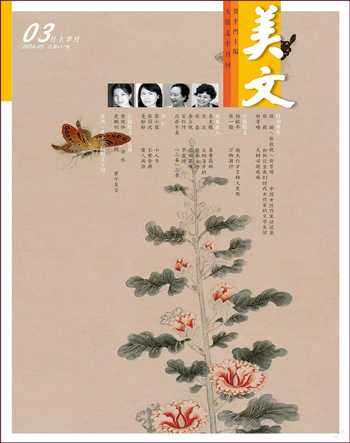并未逝去的诗:意大利语版《中国农民工诗人》序
[意大利]朱 西 著 [意大利]乐安东 译
朱西(Giusi Tamburello) 博士,意大利汉学家。1980至1983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先后执教于意大利莱切大学、巴勒莫大学等多所大学。翻译并出版过芒克、多多、根子等中国诗人的诗集和高晓声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并有大量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文章发表于欧洲、美国和中国各刊物。
乐安东 (Antonio Leggieri) 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汉语教师。研究领域包括幽默、中国古典笑话集、比较叙事学、翻译学等。白先勇的《台北人》由其首次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出版。
2023年,由我主持翻译和主编的意大利语版《中国农民工诗人》出版,中国学者当中的吴思敬、张志忠等也都应邀参与到了这项工作当中。与此同时,由马丁·温特(Martin Winter)和科妮莉亚·特拉夫尼切克(Cornelia Travnicek)编辑的德语版同名图书也已出版。主持这项工作,让我意识到东西方文学研究的“不同步”。因为,农民工作家和诗人在中国已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已经慢慢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而在意大利、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汉学界,它却仍是一个热点领域,还不断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出版。在一个如此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我在想,近年来,国外的学术界对农民工诗人的诗歌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工诗歌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出现和发展的,它能够对研究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状况和文学发展状况提供参考。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取得了非凡的技术成就和工业发展,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然而,不应忘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曾经为中国的巨大转型与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些工人原是农民或农民子女,他们离开农村原籍,前往工业大幅增长的沿海城市寻找工作和财富;他们当中很多是年轻人,在高中甚至大学完成学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为了寻找机会,改善生活条件,迁移到国内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他们背井离乡,离开原来熟悉的村庄、家庭,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面对城市环境的新情况、新节奏和新奇之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个性。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开放之后,便开启了国家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使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性工业基地”,而且也使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状态演变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世界的国家, 至少在许多科技发展的领域是这样。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变也造成了多方面的不平等,因此,不平等成为了所有农民工诗人的第一个共同点,他们在诗歌中描述了迅速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不平等,以及所带来的疲劳和痛苦。这些诗歌曾经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中国学者多集中于发现农民工诗歌的主题、节奏、隐喻等方面跟过去的中国诗歌的不同之处,外国学者则利用农民工诗歌揭示其背后的故事,并带来新闻舆论的关注。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山西大寨村在一个深谷的地理区域,在没有政府经济帮助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建立了高效的灌溉系统并生产了丰富的作物。几乎同时,在黑龙江大庆市发现了石油,该地区变成了工业生产区。两个区域都产生了模范型代表人物。所以,当时的中国政府号召,农业学习大寨的生产模式,工业学习大庆的发展模式,即“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大寨人和大庆人当时的热情,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句中,都有尽情描述,比如,“照在麦田上的红色阳光”,“隆隆作响的机器”,“钻井队钻出珍贵石油的声音”等等,这些诗歌使人们感受到,工人和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站在历史变革的主导地位。大寨在干旱丘陵地区建起农田和大庆在寒冷中创造油田,这两类带有史诗性的模范案例,都被纳入到后来农民工诗人的诗歌中。
中国人从当代历史书籍上,大致都能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随后的“十年文革”,但作为汉学家向外国人(包括自己本国的意大利人)介绍这段历史就相当困难和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改革开放时代的农民工诗人代表了中国历史脉络上的一个极其非同凡响的阶段,他们凝视现实但放弃幻想,审辩式、批判性思维变得更加强烈和微妙。我一直认为,有必要去了解历史的事实以及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从“朦胧诗歌”到“伤痕文学”,再到“寻根文学”,最后到前卫的实验文学以及最近几年轰动一时的科幻文学,也许可以看到文学试图与历史达成的某种“妥协”,以便寻找或重建某种新的平衡。如果说农民工诗人一方面仍然代表其上一代所塑造的主人——工人和农民,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只是大批工人和农民的一部分——从农村到大城市寻找工作的那一部分。因此,他们是移民,但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实际上从自己国家的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工人在原籍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被转变为沿海地区大工厂的工人,因为沿海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前沿。他们肩扛行囊,打开它即能在任何地方睡觉,甚至是在户外也能过夜;他们来自生活环境穷困的农村地区,他们的口号就是适应,以便赚取一些钱来支撑与他们分离的家庭中的老人和孩子;他们在工厂里保持着带有疏离感、孤独感的单调工作节奏,因为疲劳,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常常就是直接的受害者。然而,他们被剥削的状况、被压迫的情景,他们的疲劳、孤独、拼命工作后依然经济拮据,最终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要通过文学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在难得的休息或闲暇时刻,他们将文学作为慰藉或者逃离疏离感、孤独感的方式:当代中国农民工诗人的诗歌就这样诞生了。阅读他们的诗相当于进入农民工工作的工厂,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作为读者,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诗歌了解并思考他们的世界。一句又一句、一节又一节、一页又一页所展开的主题,将声音、气味、情境都描写得如此细腻、深刻和丰富多彩,让读者立刻沉浸在工厂的一种工业复调之中,这种复调看起来和感受起来都是全新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工诗歌深深地吸引住读者、抓住了讀者的心,并使读者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事实上,诗人们在不断致力于追求社会理想时,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疏离状态,他们只是借闲暇时间进行描述和表达。相反,只有我们读者在阅读农民工诗人的诗歌时,恰恰才会感受到这是一种疏离状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被理解为对工人的剥削,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人与客体及与他人关系的疏远或疏离。尤其是,我们从农民工诗人的诗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工与他们的雇主的关系非常紧张。即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厂也具有以劳动剥削为动力的特征。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也毋需回避的问题,至少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处于初级阶段时是这样。在那时的工厂里,雇主千方百计地减少成本提高收入,对利润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工人命运的关注,而女性农民工在此环境中更要付出高于男性的劳动强度甚至接受一些屈辱的条件。虽然中国在各个领域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但实际上农民工诗人的诗歌所反映和凸显的他们的状况,与全世界所有工厂工人的状况是那么接近,那么相似。这也许解释了外国学者对这类诗歌始终饱含兴趣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农民工诗歌的发表和出版,政府意识到工厂在用工方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在法律层面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例如,维护工人的权利,保证医疗和预防疾病,建立随迁农民工子弟学校,同时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这些,也都使得西方学者在农民工诗歌中发现了大量新词和新用语,使他们有兴趣通过农民工诗歌研究中国社会语言是如何变化的。
我主编的意大利语版《中国农民工诗人》是从“艰辛的工厂劳作”这样的主题开始,然后过渡到“城市和乡村之间”“男女的生活状况”“家庭关系的维持”“期望与失望”等。这些主题,在把握个人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同时,也通过诗歌语言表达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在城乡、男女、家庭等各种关系中的游移、摇摆与不安,也有艰难的选择、决断甚至绝情,这种描述是现实主义的描述,是痛苦情感的抒发和百感交集式的表达。因此,在这些诗歌的诗句中,我们发现了乡村自然的文字,这些文字一再出现,描述了农民工们怀旧和思乡的背景;我们读到了因生产线事故而遭受伤害的暴怒言词;我们也看到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理想的诗句……这一切组合成了农民工生活的交响诗。
意大利语版《中国农民工诗人》收录了二十四位农民工诗人的诗歌,主要由诗人郑小琼推荐,但首先出现的是杨克的名字,随后陆续出现的是郑小琼、谢湘南和许立志等。郑小琼1980年出生于四川南充。 2001年3月,中专毕业后到东莞打工,被称为第三代打工作家。2018年秋天,我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时间再次静下心来关注并研究她。此前,我在各种会议上见过郑小琼,并发表了一些关于她的文章,比如2019年罗马出版的《当农民成为工人》等,因此,算是已经认识和了解她。《作品》杂志创刊于1955年,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曾获广东省十大期刊、广东省优秀期刊等奖项,杨克曾任社长兼总编辑,郑小琼任副总编辑,他们都为许多农民工诗人作品的发表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他们两位诗人特别重要。当得知我要将农民工作家的诗歌翻译成意大利语并将与德语版同时出版时,郑小琼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将她发表于《作品》上的诗歌收入了进来。
我一直认为应该用单独章节的篇幅来专门研究一些诗人,特别是杨克、郑小琼、谢湘南和许立志等,随后尽可能按主题划分其他诗人的作品。当然,并非这里研究的每个诗人都只写一个主题。事实上,所确定的各种主题经常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相互交集。我们所作的尝试只是提供一个框架,在突出各种主题的同时,传达反映生活现实的诗歌灵感的复杂性。按照这样的主编思路,意大利语版《中国农民工诗人》前两章分别介绍了杨克和郑小琼两位诗人,两个人的创作生涯都是从工厂开始的,他们是那些凭借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工人身份成长为诗人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一方面,它表明在当代中国,诗人仍然有着高于工人的声望,而就农民工诗人而言,即便他们并非专业从事创作,他们也通过发表诗歌引起的关注而使自己改善了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他们既为其他同样写作的同事树立了榜样,也为不写作的同事打开了传播空间,让大家了解当时中国工厂的工作现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切,并实施法律和健康方面的保护。本书另外还有两整章专门讨论谢湘南和许立志。谢湘南的诗代表了前述几个不同的主题,也显示出其灵感来源的多样性。专章讨论许立志是为了向这位年轻的农民工诗人致敬,他在24岁时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极端的选择给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或者说空间,但任何解释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或过于简单化。也许,只收录其诗歌而不作评价和解释最好。
随后的章节在同一标题下包括多位诗人,这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诗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而是因为他们的诗似乎更凸显其所在章节的主题分类。如此操作下来,在“告别村庄”一章中就收錄了彭争武、张守刚和女诗人刘丽华的诗;在“城与乡”一章中,收录了李长空和刘洪希的诗;在“工况”一章中,收录了阿鲁、池沫树、黄吉文、蒋明、柳冬妩、罗德远、孙海涛、许强、周启早的诗;在“职场事故”一章中,收录了郭金牛、程鹏、何真宗的诗;最后,在“年轻人失落的梦想”一章中,收录了方舟、徐非和邬霞的诗。由于农民工诗人的诗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也在社会层面上产生了反响,所以在“打工诗歌,农民工的诗歌”一章中提到了诗歌研究者对“打工诗歌”和“农民工诗歌”的讨论和定义。在“工人诗歌的共鸣”一章中,还引用了英国诗歌以及意大利诗歌的文本,这些诗歌文本既描述了工业革命诞生时期的社会生活,也描写了英国和意大利整体工业发展的道路,所以也有学者尝试将中国农民工的诗歌嵌入其中,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工作经验往往是全球性的。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在主持翻译和主编这项工作时所做的一些技术处理。当我必须重复一些中文单词时,它们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斜体书写,第二次以及随后出现就用圆体书写。因此,这些单词在诗歌的原文中并不一定是斜体的。在翻译中文的拟声词时也是用斜体书写的。通常,对于汉字的音译,我用汉语拼音的形式呈现,将现代汉语的发音转录为拉丁字母。然而,为了减轻阅读负担,只有一个单词对主题的描述起非常重要作用且去掉声调会造成误解时,才保留表示汉语声调的变音符号。在翻译中,以小写字母开头是为保持汉字的统一性,这也因为中文原文诗歌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往往非常有限。在中文中,“省”一词表示与中央政府直接相连的次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我均统一将其与意大利语中的“区域”(Regione)概念相对应。有些传记资料非常难找到,郑小琼给予了很大帮助,对其所作出的非常宝贵的贡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这些诗人的传记中,我还特意表明了每位诗人职业发展的路径。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