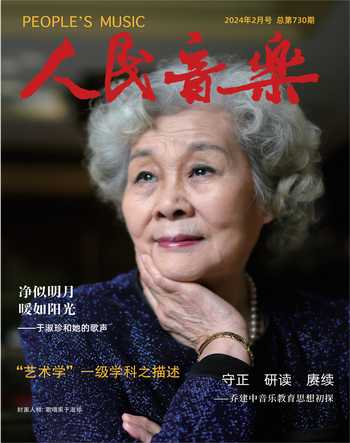新疆少数民族器乐系统性传承研究
王翩


中国器乐艺术与中国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等民间音乐形式相互交融,与民俗文化密切关联,反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独具风格特色。新疆作为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核心区域,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其保护与传承推进文化润疆工程,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提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強化‘非遗系统性保护”,旨在改变碎片化、局部的保护模式,以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整体性、发展性的眼光布局“非遗”保护,实现“非遗”传承的当代化、生活化、常态化、完整化。目前学界已经围绕系统性保护的理论内涵、系统性理论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①,并在部分地区个别领域中作案例探析②。
少数民族器乐传承的经典模式分为自然传承、院校传承和“非遗”传承三类,每一种类型都牵涉民间-文化持有者、高校-学者和国家-政府等不同维度、不同角色、不同身份人群间的合作与角力③。在“非遗”保护理念下,少数民族器乐艺术传承多元主体“如何系统运转”,就成为一个值得再思索的话题。本研究聚焦新疆少数民族器乐传承实践,从器乐艺术保护中各主体及其职责入手,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器乐艺术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探索系统性保护实效提升路径。
一、谁将可为:器乐艺术保护理念的历史演变
20世纪20—40年代,刘天华、杨荫浏、延安“鲁艺”师生等人先后开展局部民间音乐记录整理。1949—1963年,全国性民间音乐普查记录,整理工作分省、市、区地开展。1979—2009年,分省、市、区地编撰全国性“十大文艺集成志书”。2000年至今,全国性的“非遗”保护工作正式启动④。
2000年,昆曲在中国政府的组织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在中国从宣传普及转入具体实践。此后,古琴艺术(2003)、新疆木卡姆艺术与蒙古族长调民歌(2005)接续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在此背景之下,回答民族艺术传承“谁在保护?为谁保护?保护什么?怎样保护?”之问,一时成为民族音乐艺术研究集中关切的问题。
为此,《音乐研究》专门组织音乐学者与教育者先后开展两期“专题笔谈”,相关成果刊于2006年第1、2期。这次专题讨论的若干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也有不少基于音乐艺术特性发出的思索、提出的担忧,对今日探究包括少数民族器乐艺术在内的音乐艺术传承仍有启迪意义。不少学者立足音乐文化传承特点,强调民族音乐艺术的保护要突出民族自身的主体地位。萧梅提出,“无论是学者或是政府在当前的‘遗产保护工作中,都不能取代少数民族自身在其音乐文化中的主体性”⑤。及至十余年后,萧梅针对“表演者的主体性”等问题再分析,反思表演者的当代处境⑥。
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拓展“谁来保护”的主体范围,呼吁器乐艺术文化生态建设。文化生态学理论最早由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J.%H.%Steward)在《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强调文化在演化的过程中适应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并受该特定环境的改造重塑⑦。樊祖荫提出:“要特别重视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主体———传人及班社和整个文化环境的保护。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扩大传承面,让各级学校的艺术教育承担起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义务。”⑧尽管仍强调民间艺人的主体性,但该说已将音乐艺术保护的主体扩展到学校乃至整个文化环境。
项阳则回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经验,从中国音乐文化自身发展规律与特性出发,指出深刻烙印在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内核之中的“变”与“不变”。他认为,“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其本体中心特征(律调谱器)依然存活在民间。体现在为神奏乐和为人奏乐的两种形式。在传承过程中,何以变,何以不变,值得认真探讨。总体说来,以敬神为主要奏乐目的者,音乐传承相对变化较小;服务于人的音乐则变化较大”⑨。
具体到新疆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保护实践,与新疆木卡姆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相当时期,毛继增正主持开展国家重点项目《新疆传统音乐文化实录》。他认为,面对民间艺人群体数量萎缩的现实,新疆艺术学院创建的木卡姆表演艺术班,培养的学生“不是木卡姆表演匠人,而是木卡姆的表演艺术家,木卡姆文化的管理者、传承者、保护者”⑩,有效解决了传承的后顾之忧。
可以看到,21世纪之初学界对“非遗”保护责任主体的认识处于探索与争鸣状态。对“谁来保护”的讨论,更多地从音乐文化自身特性出发,强调民间艺人的主体性。而对政府、社会力量如何参与音乐艺术传承保护,尚有一丝“观望”姿态,甚至部分学者对“非遗”一词的认识与使用仍较为谨慎。
随着“非遗”保护研究与实践的深入推进,政府主导下的音乐艺术保护工作,从“要不要”的争论转向“要且如何更好”的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建设也不断深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2012)、《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批复》(2016)、《关于实施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2017)、《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17)、《关于“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通知》(2018)等文件、政策纷纷出台。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首次以“两办”的名义印发的有关“非遗”保护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
二、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的各方职责
厘清各级保护主体的职责所在是探讨新疆少数民族器乐传承的前提与基础。其中,政府、社会、公民各方的权责划分可从非遗相关法规中得以一窥。
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开启法制化保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2010)的出台,推动具体艺术形式保护有法可依与规范管理。其中,自治区条例强调“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规定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职责划分,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是非遗保护中承担的法律职责最为集中的部门。除认定、考核、监督、奖励、扶持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与非遗项目外,还承担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活动,挖掘、整理、开发、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健康的民俗活动表演项目等职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规定:“自治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木卡姆艺术流传地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木卡姆艺术保护和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木卡姆艺术传承机构,具体承担木卡姆艺术的保护工作。”
“非遗”传承人是承担“非遗”保护、展演与研究的核心群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8)中均强调,“非遗”传承人需要承担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实物与资料、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公益性宣传等职责。而相应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亦明确指出“非遗”传承人有从传承、展示等活动获得有偿回报的正当权利。
目前新疆尚未出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规。就笔者目之所及,当前地方政府中仅有通辽市专门出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通辽市蒙古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8)。该条例指出,政府更多承担机构管理、政策制定与执行、资金扶持等职责,市、县、旗级人民政府文旅部门作为执行者,承担音乐文化的调查整理、传承人的管理、传承传播效果评估等事项。该条例没有详细罗列“非遗”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但规定了传承人如未能履行相应职责则将限期整改甚至被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从其惩戒性规定反观之,通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责规定包括办学传艺、配合非遗调查、参与评估、保管器物资料、公益宣传等。
学校、社区、利用公共财政运行的单位团体、公民、法人等其他组织,在“非遗”传承保护中扮演辅助角色。该群体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应当为“非遗”传承保护提供诸如场地、宣传、资料保存等保障,具有鲜明的鼓励性而非强制性。除了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权限所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务”,为文旅结合、“非遗”与经营性活动相结合提供法律支持。
三、新疆少数民族器乐“非遗”保护的地方实践与再审视
(一)何以可为:新疆少数民族器乐传承资源空间特征
文化演化的过程适应其所处的特定环境并受该特定环境的改造重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性知识存在内在联系,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而如何提升少数民族器乐保护与传承实效,则必须回到具体的地方现实与社会文化情境之中。
1.地理空间特征
在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新疆地形地貌为绿洲、沙漠、山区、草原等所分割,呈现“三山夹两盆”的地形特色,又以天山山脉为中轴,分为北疆和南疆,吐鲁番、哈密一带又称东疆,成为东疆、南疆、北疆三大区域。新疆地貌复杂的特征,形成绿洲与草原地带文明相互接触又相互竞争格局。
新疆“非遗”类型齐全,拥有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共575项,国家级128项,自治区级447项。其中,传统技艺类最多,共160项,约占总数的27.83%。传统音乐类处于第二位,共102项,约占总数的17.74%。从空间分布来看,喀什地区拥有的自治区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最多,且为南疆地区的非遗项目聚集度最高的地区;位列第二、三的分别为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东疆的哈密市。从音乐类“非遗”项目的内容看,喀什地区不仅有诸如木卡姆、赛乃姆等器乐艺术,还涉及维吾尔族乐器制作技艺、塔吉克族乐器制作技艺等外延项目。
新疆少数民族器乐“非遗”项目的空间分布与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特点相一致。自治区共有56个民族成分,其中世居民族有13个,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等。超过一百万人口的民族有4个,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和回族,超过十万人口的有2个民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伊犁州直属县(市)是新疆哈萨克族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该地区的自治区级音乐相关“非遗”项目则有哈萨克冬不拉艺术、哈萨克六十二阔恩尔、哈萨克铁耳麦、哈萨克库布孜等四项。同时,因与俄罗斯接壤且俄罗斯族人口较为集中,该地巴扬艺术一项入选第三批次自治区级“非遗”。
2.经济社会资源耦合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器乐的文化特征与空间分布往往带有鲜明的民族交流融合特点。不过,当前“非遗”传承下的器乐保护更多的地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新疆各地州入选的“非遗”项目数,与当地的一般性公共支出显著相关。
在学校教育中,高等学校更多地承担起艺术研究的职责,而少数民族器乐传习的职责则更多地落在自治区属、地州属的中高等职业院校身上。在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音乐艺术较多的地方,其自治区属职业院校开设的民族器乐专业亦较多,二者呈显著相关(P=0.018<0.05);而在列入自治区级“非遗”项目的音乐艺术较多的地方,其地州属职业院校开设的民族器乐专业亦较多,二者呈边缘相关(P=0.077<0.1)。如果说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保护之下,入选保护名单则意味着财政、政策等资源倾斜的话,藉此获得相当资源的地方政府则更有意愿和能力通过地方职业院校开设专业教育,扮演好传承者的角色。
(二)“非遗”视角下新疆少数民族器乐保护的再审视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遗保护模式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力并易形成规模优势。对边疆地区而言,政府主导型保护模式为植根基层的器乐艺术文化提供托底保障。政府“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不是事无巨细地直接“干预”,而是借由平台搭建、资源协调、政策导向、支援帮扶等服务型组合政策,营造从增进了解到增进保护自觉的社会舆论宣传,带动全社会的关注,真正实现民族文化保护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过,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器乐的类型、空间分布分析及其与自然经济社会资源的耦合分析,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器乐传承仍有诸多可资深化之题。
1“.政府主导”政策导向与不均衡的地区财政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是各级“非遗”法规中最基本的保护方针。政府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推动者、引导者、保障者,具体职责由县级政府及其负责“非遗”保护的文旅相关部门承担。地区间的财政差异、教育资源与文化资源差异决定着不同地方的保护力度差异。同时,虽然新疆的“非遗”保护法以及木卡姆保护条例等均提及“鼓励社会参与”,但是社会层面“非遗”保护的内生性机制还未普遍形成,仍需健全自觉保护、自觉传承的长效机制。
2“.非遗”法规与保护政策对少数民族器乐保护的作用
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往往强调“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由是最终获批列入保护性项目往往来自少数民族高度聚集地区或具有深远民族历史文化的经典项目,如新疆木卡姆艺术、俄罗斯巴揚琴、哈萨克冬不拉等。除获批自治区级乃至国家级保护的器乐项目外,散布在民间未获专项扶持的器乐占绝大多数。而未能列入代表性“非遗”保护名单的器乐则呈现出更为自发又更依赖民间与社会力量的传承特征。
3.少数民族器乐“非遗”项目与学校教育资源的错位
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性的“非遗”学科以及理论研究体系尚未成熟。对于中小学学生群体,虽然部分学校开展普及性的民族器乐教学展示等活动,但这并不属于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程,也未形成统一教学标准。对于普通民众,受制于时间与学习渠道的缺失,除在特定的场合或活动中接触“非遗”,很难获得比较系统的培训与教育机会,“非遗”传承主体仍属特定人群。而对于采用传统“师徒制”传承方式的从业人员以及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学生,虽其实践经验相对丰富,但学术水平及文化修养有待提高。
4.少数民族器乐表演研究中心与原生社会的空间关系
少数民族器乐艺术保护尤其要关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民间生活”和“传统文化固有的传承方式”。在新疆,由于高等学校、艺术研究机构、大型舞台表演机会集中于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等城市,从研究、高等教育、展演乃至档案资料保存等方面服务民族器乐艺术传承的活动已经远离其原生社会空间。为此,需要建立可以联络各方的交流平台,并为保留原生器乐艺术社会空间做好系统记录。
新疆的少数民族器乐艺术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历史交流中多元共生,美美与共。系统性保护少数民族器乐艺术需将“非遗”法规中的“整体性”原则落到实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强调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在新疆地方条例中,则将保护内容细化为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和民间美术、民俗活动、手工艺技能、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相关资料、实物和场所等。维吾尔木卡姆保护条例不仅强调木卡姆是《十二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各种木卡姆艺术的总称,在内容上也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目前“非遗”保护工作机制下,即便个别器乐艺术入选保护名单,其他器乐艺术仍可以通过大型曲目创演、基于民间文化综合性的特点,开展协同保护,从而构建起以“非遗”项目为牵引、辐射相邻器乐与相关空间的“大非遗”保护工作体系。
结语
20世纪中国器乐艺术成功转型为“一门相对独立又颇有成就的现代表演艺术类别”,这得益于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系设科、表演的舞台化、优秀的演奏人才、丰富的表演曲目、专业作曲家的深度参与。自2000年以来,在“非遗”理念下,昆曲、古琴、木卡姆、蒙古长调等从地方走向区域性领域,又从区域性领域走向全国性领域,最终走向世界领域。彼时学者展现出的拥抱、接纳,抑或观望、沉思,本质上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接触“异者”领域时或新奇、或不安的情状。但地方性音乐艺术的“走出”,并不是单向路径,而是在“走出”的过程中也将新领域的目光引回本地。实践表明,这种“走出”与“引回”以和平友好为底色,社会多元力量的综合参与为民族器乐带来活力。
少数民族器乐艺术的系统性保护工作, 是文化传承自身的发展规律与传承特点内在要求。文化传承“是类型的而非个性的,是反复的而非一次性的,是集团的而非个人的,是基层文化而非上层文化”,“作为一种音乐体裁, 器乐本身既有其本体样态与逻辑,也与其所生存的整体文化语境相伴生,同时具有艺术性与文化性。”由是,新疆少数民族器乐传承保护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创造并完善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少数民族器乐文化传承的机制与路径,充分调动各社会部门、团体的力量才能使“非遗”保护的效益最大化。
——以新疆莎车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