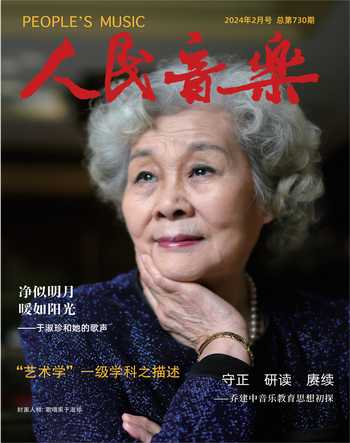坚守文化本色拥抱科技发展
李文浩
2023第三十届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以下简称“中国国际乐器展”)于6月29日—7月2日在北京举行,其间举办的“首届中国民族改良乐器精品展”活动,成为本次展会的“点睛之笔”。这是中国国际乐器展成立三十年来,首次将目光聚焦在“民族改良乐器”领域,为沉寂许久的“乐改”工作重拾焦点,活动由“成果评选”“精品展”和“论坛”三个部分组成。
来自全国乐器研究及演奏领域的多位业内专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包括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乐器(科技)专家委员会专家丰元凯、韩宝强,器乐科学专家付晓东、卞留念、高舒,扬琴演奏家黄河,打击乐演奏家王以东,弓弦演奏家宋飞、高扬,吹奏乐演奏家杨守成等。由国内民族乐器厂家、个人工坊、院校乐器工程教研系(组)等多渠道选送了百余件民族改良乐器,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最终评选出82件亮相第三十届北京国际乐器展。
本届精品展中的乐器大多来自民乐制造厂家和各领域专家合作的成果,从形制、材料、发音、构造等方面入手不断创新与突破,兼顾传统美学与当代审美,生产出诸多满足不同市场需求的民族乐器系列产品。例如,北京乐器研究所选送的复原乐器“筑”,北京钧天坊古琴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选送的“大鹏式-青鸟古琴”和“蕉叶式-青云古琴”,北京吕建华民族乐器文化有限公司选送的“高分子聚合二胡弓毛”,沈阳音乐学院弘韵箜篌乐团选送的“昂首凤式双排弦踏板全转调箜篌”,雷琴传人丁宝春选送的“雷胡”,湘西山里人民族演艺有限责任公司选送的“便携式拆装型民族大鼓”等乐器。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乐改”的国家在场,当下的“乐改”更为“遍地开花”,民族器乐在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发展成为促进各地、各厂家“乐改”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到现代传播途径。
一、“乐改”百年西学之路
回顾20世纪的中国“乐改”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其中以20世纪初“中国音乐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争鸣为开端,掀开了近代民族乐器改良的新篇章。当时出现了三种“乐改”观点:其一以匪石1903年提出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为代表,认为“中国音乐改良的结果就是达到西乐的程度”,持这种“西化论”的音乐家在当时还包括萧友梅、青主,他们在《对于大同乐会拟仿造就乐器之我见》《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等文章中都对各自的观点进行过详述;观点二,以郑觐文为代表,他反对以西方音乐为标准作为国乐改良之策,在创办“大同乐会”的过程中,试图从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中建立现代国乐,通过复兴古乐器尝试探索民族化的交响道路;观点三,以杨荫浏为代表的中西互鉴的国乐改良观,他主张在国乐改良的道路上结合前两种观点有选择性地取舍与批判。①事实上这三种观点都是基于20世纪初叶中国处于“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尽管当时“乐改”大方向还是以“西方”标准为依据,但并未触及中国音乐的本质。
第二次“乐改”高潮出现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尤以1954年在国家支持下成立的“乐改小组”为代表,“乐改”也由此从民间转向官方。彼时学术界依然对“乐改”存在上述三种观点。中国艺术研究院民族器乐理论家李元庆在1954年提出从音域、音量、音律、乐器规格标准化四个方面分析当时中国民乐的缺点以及改良途径。②这在实践性和落地性方面找到了“乐改”的突破口,成为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乐改”的主要方向。随着在1970年代前后“民族化”的深入,涌现出了像402扬琴、36簧加键笙、低音加键唢呐等具有时代性的“乐改”成果并达成行业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不乏昙花一现“乐改”成果,如今难觅其踪。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民族化的西方作品和西方化的民族作品创作热潮带动了“乐改”的第三次高潮。③例如刘文金的《长城》、关铭的《兰花花》等民族交响新作品,也包括谭盾的二胡与扬琴二重奏作品《双阙》、何训田的二胡与交响乐队的《梦四则》等先锋派作品,这种“西化”的民族艺术创作趋势,将“乐改”引入西方音乐语境之中,民族乐器的制造也围绕“交响化”而展开。民族乐队各声部系列化获得较大发展成熟,如弦乐器系列(高胡、二胡、中胡、大胡),弹拨乐声部阮系列(小阮、中阮、大阮、拉阮),管乐声部笙系列(32簧高音加键笙、中音笙、次中音笙、抱笙、排笙)和唢呐系列(高音唢呐、中音唢呐、次中音唢呐、低音唢呐),使乐队更加体现大型化,立体化,声音效果更为丰满,厚度增强。极大地满足了专业作曲家对音域、音响、调式乃至配器方面“交响化”的要求。
二、走出西方语境
诚然,文化和科技是推动“乐改”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21世纪全球音乐朝着多元化发展,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走出西方强势文化的遮蔽,以一种自信、自觉的姿态展示东方音韵。20世纪90年代后,“乐改”工作从官方再度转向民间,向常态化、个性化、群众化的方向发展。本次论坛云集了制作、教学、演奏、理论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研讨论题包括回归中国音乐文化语境坚守文化本色、推动民族艺术多元化发展、科技与“樂改”等内容,阐明“乐改”工作肩负双向推动西方与民族、传统与流行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关于回归中国音乐文化语境坚守文化本色。对民族艺术的思考就是一个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尊的过程。④以此观点投射到“乐改”工作之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尊”还远远不够。斫琴师王鹏在会议上呼吁,要从民族乐器制造中体现出中国音乐文化的魅力与精神内涵。付晓东提出:“需要在理念和哲学层面对当今‘乐改目标形成共识,现今的很多做法真是走偏了。如果古琴朝着大音量发展,增大音量就会缩短弦的持续震动,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古琴演奏中的‘一唱三叹的腔音演奏技巧就会因此消失,这是民族艺术的‘本,我们不能舍本求末。”关于“乐改”中的“本末”问题,论坛主持人韩宝强也曾撰文呼吁“乐改”各界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命。⑤
关于推动民族艺术多元化发展。基于世界多元文化格局趋势,宋瑾曾提出在各个民族音乐的发展中,“西方化”“民族化”并非对立,二者反而呈现和谐发展,甚至是相互促进的关系。⑥民族乐器改良的“两条腿”发展模式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与会专家提出,在“乐改”道路上,一条腿站在“传统”之上,比如独奏和室内乐要保持本色,坚持以弘扬和传承中国音乐文化内涵为前提;另一条腿要站在时代文化当中,加大对民族交响乐队的改良,不仅将定音鼓、大提琴、低音提琴等西方乐器融入民族交响乐队,还可以在民族乐队“和声化”方面做进一步提升。
关于科技与“乐改”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乐改”已经走上一条与时代同行,拥抱“科技”的道路。正如本届评审专家委员会组长丰元凯所讲,在科技的带动下21世纪“乐改”具有跨领域、多元性、综合性的特点。⑦中国音乐学院师生在展会现场展示的70“智慧型乐器博物馆”就是很好的实例。这是以“数字穿戴技术”搭载乐器学领域知识的数字化平台,具备虚拟全景体验、虚拟仿真、智能交互、乐器科普与专业研发等功能为一体的线上乐器博物馆,收录有周代乐器筑、篪,曾侯乙墓编钟、编磬等数百件中国古代乐器。通过科技手段大胆创意,让中国古乐“复活”于当下,彰显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历史的博大精深。
三、从思维到实践的统一
本次论坛对当下“乐改”的具体实施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共识,比如:加大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加强跨领域制作、创作;推动新型材料的使用;加快便携式的民族乐器的研发。这些具体、细化的工作建议凸显了当下“乐改”跨领域、多元性、综合性的时代特点,专家们呼吁要尽快将现阶段达成的“乐改”共识铺设到全国,建立更为科学的执行标准,带动全行业良性发展。
主办方、与会专家、展商代表等强烈表示,当前亟待建立集信息、服务、引领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服务性平台,要将民乐制作、教学、创作、科研、理论等多个环节纳入其中,结合当代科技、材料学、行业标准、知识产权、市场营销、音响工程等各个相关因素有机融通,共同协作。此外,还要在保护、推广优秀的乐改成果的同时,对“乐改”中不良现象进行批判和纠正。
论坛再次聚焦民族乐器制造的“标准化”问题。众所周知,建立与推动民族乐器的制作标准与规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之所以工作难度大,制定“标准化”背后的确存在复杂因素。高舒说:“现行乐器制作标准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国家在2000年后出台的行业标准,都把强制性转化为推荐性标准,也就是建议化标準,而且每两三年就会修订一次,标准是在一定框架下由制作者灵活掌控的。”成立于1956年的北京乐器研究所乐器标准化中心已经制定了多项民族乐器的“行标”“国准”,但行业专家依然表示“标准化”工作依然艰难,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黄河认为:“民族乐器一直在改良的路上,不仅扬琴,还有其他乐器,还没有完全定型,没有完美,但在某些工艺上,是可以依靠科学技术,以标准化、规范化制造民族乐器。”王以东以民族打击乐专业为例,呼吁建立打击乐制造统一标准,当前各自为政的乐器制造标准导致在演奏符号、记谱方式等方面也出现多种形态的连锁反应。这种由“标准”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其他民乐专业中同样存在,制定、推动、实施与修订“标准”已成为当下“乐改”工作的重点、难点之一。
结语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走过了一段崎岖的“西学东渐”之路,经历了国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探索。守住文化之“本”,我们既要回归到中国音乐语境之下取其精华,保持与挖掘本民族音乐文化个性与特色,体现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觉,更要胸怀世界多元文化的大格局,以时代为题,以科技为舟,在与世界互鉴中制定行业标准,让民族音乐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讲述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