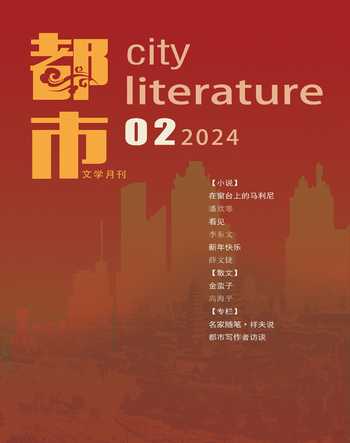孤 独
一连几日,我总能碰见那个老太太,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晚上。
按理说,这也没什么可令人诧异的,邻居嘛,难免出出入入碰面,见了面寒暄一两句,互相问候也是理所当然。但不同的是,她总给人一种神出鬼没的感觉,就像是冷不丁有个人从身后拍了一下肩膀,让人猝不及防。比方说有一天晚上,大概十点多光景,母亲正在厨房的水池边低着头专心地洗碗,我和父亲还有妻子在客厅逗女儿玩,这时,窗棂外倏地飘来一个身影,隔着纱窗定定地看着母亲,母亲低着头,没有发觉。看了一会儿,那身影突然忍不住开口说:“还在忙啊?”母亲手里的碗在惊慌之下掉进了水池,她自然吓一跳,可想到这瓷碎声是自己亲手炮制,又有几分气性无处撒的委屈。缓过许久,母亲抬起头,见她还在,只好客气地和她说上一两句话。事后我问母亲:“认识她吗?”母亲摇了摇头,转而继续说道:“应该是楼上的,这个老太太经常突然出现,还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很奇怪。”
她身上种种的怪异举动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起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洗完澡后,我趴在楼道的窗台口抽烟纳凉。正看着一棵树有些出神,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在休息啊?”我的身体不由得抖了一下,烟灰像枯叶一样落到大腿上,扭过头一看,正是那位老太太。她身材臃肿,粉色斑点的连衣裙似乎快要遮不住鼓起的肚子,一头花白短发,耳垂肥厚,目光如炬,像是蹲在寺庙里的古佛雕塑。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在这寂寥的夜色里,让我有些不寒而栗。我说:“在这儿吹吹风,奶奶,这么晚了,您怎么还没休息?”她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我,说:“出去散了散步,这就上去睡觉,这就上去。”说完提着一只白布袋子,一步一顿地消失在黑暗中。
我抽完最后一支烟,哈欠连天地也回去睡觉了。
在一个周末晌午,我又碰到了她。那天吃过午饭后,我出门扔垃圾,刚推开门,炎炎热气就奔着脑门子直往上扑。我一溜烟蹿到楼下,隔老远儿看到那个老太太两只手小心翼翼地端着盘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正慢吞吞地挪步。我面向她走去,靠近了发现原来是一盘菜,盛得满当当的快要溢出来,她的两只大拇指迫不得已嵌进了菜里。我忙说:“奶奶,我帮您端吧。”她微微抬起头,认出了我,连说“好,好,谢谢你小伙子”。我接过她手里的菜,并肩和她走着。我问她:“还没吃午饭?”她抬起胳膊擦了一下额头的汗说:“在食堂吃过了,打包一些回去,热一热晚上吃。”这时我才想起之前小区开了家食堂,专门给上了年纪的老头儿老太太做饭,每个月固定交些钱就行,给一张电子卡,饭菜油少,盐少,干净卫生,很适合需要养生的老年人。我又问她怎么不用饭盒装,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记性太差,忘记放哪儿了。
老太太家住四楼,等到了门口,我看到一块“光荣之家”的金黄色门牌赫然悬在门楣。
我把菜交给她,说:“您休息吧,我先下去了。”
老太太说:“进来吃块儿瓜吧,说说话聊聊天也好。”
正好我心里还存有几丝疑惑,就跟着进去了。
刚推开门,一股浓烈的大衣柜子味霎时淹没了我的鼻子,一直等到气味消散,不适才稍稍减轻了些。走到客厅,我瞥见正中央的白墙上挂着两张相片,老太太招呼我坐沙发,旋即转身进了厨房。我身上泛出一阵冷意,也起身进了厨房,倚着门框劝她:“您别忙活了,我坐一会儿就成。”她说:“不打紧的,吃块瓜落落汗。”于是我跟着老太太又折回到客厅,她递给我一瓣西瓜后,背过身子不紧不慢地擦起相片下面的供桌,我这才仔细地观察起来,左侧的相片是一位年轻军人,右侧是一个小男孩儿,六七岁的模样,笑得俩深酒窝,满脸稚气。两张相片均用棕色木质相框裱着,都是黑白底色。虽是黑白底,却难掩军人眉目间的英气。照片下边挨着一张四四方方的木头供桌,桌上摆了一只锃亮的香炉和几小碟果盘,里面放着苹果和橘子,香炉里插着几根未燃的沉香。这时,老太太转过头来,一脸慈祥地说:“吃瓜吃瓜,不用等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别过头四处打量,款式老旧的茶几,几处掉漆的暗褐色的柜子,破皮多处的沙发,无一不彰顯着时间久远的痕迹。柜角处直棱直角,并未粘防撞贴。老太太擦完桌子又重新添置了水果,才安心地坐下来。
“我记着你有一个女儿吧,小伙子?”
“嗯,对。”
“我应该见过你女儿,就前几天在社区公园,你一只手推着婴儿车,一只手牵着你女儿,那天你穿的也是这身衣裳,你女儿穿了一件白色碎花裙子,是吧?”
“没错奶奶,是我,您记性真好。”
“唉,不行,老喽……”她爽朗地笑起来。
“我看见你牵着你女儿走路,她那么小,走路也走不稳,一晃一晃的真是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她几岁了?”
“刚一周半,个子偏大,走得还不太稳当。”
“真好啊,真好……”她喃喃自语道,慈祥地看着我,像是认识了我很久。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太阳慢慢转了过来,被阴暗潮湿的楼道蚕食多半的阳光透过窗户暖烘烘地倾泻进屋子,屋里顿时燥热起来。
“今年夏天真热。”我开始没话找话。
“是呦,一年比一年热,等着,我去开下空调。”
说罢她慢腾腾地四处转悠起来,嘴里念念有词:“哎?遥控器呢?遥控器放哪儿了?”
“没关系,奶奶,吃块儿瓜一样凉快。”
忽然,她一拍额头,感叹:“瞧我这记性。”
她拉开茶几下层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只黑白难辨的遥控器,连着按了好几下,都没反应,接着打开后盖拿出电池重新安进去,又按了几下,挂在屋顶一角的空调这才不情愿地运转起来,沉闷的响声像是人在打鼾。
“估计是接触不好,空调也旧了,我一个人,也懒得修。”她指着空调说。
“还是得定期清洗过滤网什么的,要不然会吹出灰来。”
“就这么凑合着用吧。”
“那可不行,这样吧,等哪天我找个清洗师傅过来洗一下,天热了经常要用,可不能耽误。”
“好,好,那麻烦你了,小伙子。”
老太太感叹着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干什么都有专门的人服务。我们从如今人们便利的生活聊到了大锅饭,联产承包责任制,筒子楼,最后又绕了回来。
“现在你们年轻人,压力大,得学会开导自己。不过,话说回来,以前的人压力也不小,像我那时候结婚呦,都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现在呢,听说要车子、房子、票子。”
“怎么样,还打算再生一个吗?”
“暂时没这打算。”
“也好,也好,蛮好的,一个蛮好的。”
“您的儿女呢?”我忍不住问道。
她抬起头看了眼墙上的遗像,慢悠悠地说:“唉,就剩一个女儿了,在国外。”
我心中不禁有些自责,连忙和她道歉。
“不打紧的,不打紧。”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我拿起两块儿瓜,将其中的一块儿递到她手上。
“这瓜真甜。”我说。
老太太似乎没听见我说话,一双眼睛像是蒙了层雾,半晌才说:“七六年大地震,儿子跟他爸一块儿走的。”
她将干瘪粗糙的双手放在膝头,肩膀好似也塌下去了一截,望着窗户,用饱含回忆的语调说:“小勇出生那天呦,下大雾,外头啥都看不清,后来听人说那天外边还出了车祸,就在不远的地方。接生婆让我不停使劲,不停使劲,嗓子也喊哑了,最后好不容易出来,不哭呦,都吓坏了,拍了好久才哭出声。他们抱过来让我看,小家伙的眼睛睁不开,扯着小嘴巴一直号,全身湿漉漉的。后来呀,他老是哭,一哭哭半宿,怎么哄都不行,我就请了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他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还说他命苦,让我在小勇枕头下放一把剪刀。我信了他的话,就把剪刀放在小勇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都放。你说也怪,一会儿就不哭了,一觉睡到天亮。剪刀锈了就换一把新的,那么些年过去了,也数不清到底锈了多少把剪刀了。我啊,就眼巴巴地盯着他,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摔倒了就哭,看见我就笑……唉,一转眼,快五十年了呦,过得真快。”
老太太说着,眼泪顺着脸颊的皱纹流了下来,像是河水顺着七拐八拐的河床奔流。
我的心像是被揪成了一团,又涩又紧,便岔开话题,和老太太聊起了其他事情,直到她听着咿咿呀呀的越剧靠在沙发上迷糊着了,我才站起身,对着客厅的遗像鞠了一躬,轻掩上门走了。
外面的热浪像汹涌的海水般一波接一波翻腾,拍打在我脸上,直把我拍回现实世界。我看着周围,感觉像是匆匆过了几十年一样,仿佛《述异记》中误入仙地的王质不知时间已过百年。
后来我跟妻子说起了这事儿,妻子恍然大悟般感慨,怪不得她隔三岔五老找人说话呢,那天买菜还逮住我一直说个不停,原因在这儿啊,接着轻轻叹了口气,这老太太挺可怜的。
日子不紧不慢地向前一步步走着,我的生活与以往相比也并无差别,但和老太太聊天时的情景却像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旋涡般搅动着我的思绪。我还从没想过,如果一个人临到了了,落到孤苦伶仃,心里会有多失落,没人聊天,没人陪伴,尤其是住在像我们这样的老小区,房客们换了一拨又一拨,邻里间交情也淡,顶多碰了面打声招呼,有的连招呼都不打,谁关心你心里想什么?连个贴心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去年年底,我的姥爷和姥姥相继过世,碍于工作和路途的原因,我未能回去吊孝。听母亲讲,姥姥在最后撑不住的时候,躺在床上,干眨巴着眼说不出话来,眼泪沿着眼眶流出来,只能用手指轻轻比画,使不上劲儿。我听了心里直发酸,并因此对死亡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宛若一条裹缠心头的水蛇,让我久久不能入眠。有时即便睡熟了,脑中也会冒出些奇奇怪怪的梦,在一条昏暗逼仄的小巷子里,道路泥泞不堪,空中不停飘着细雨,四周不断散发着霉味,巷子尽头的光忽明忽暗,始终看不太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促使我一直不停地向前走。梦醒后,第二天上班时,总感觉脑袋昏昏沉沉,整个人精神委顿。我不由得开始思索人活着的意义,对于个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太过庞大和缥缈的话题,但我仍努力想弄明白。
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见天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让我结结实实地尝到了苦头。起初,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病了,妻子见我彻夜失眠,催促我去挂一个心理科看看,说有病就去治,别整天没个精神。刚开始我还挺不乐意,我有病没病自个儿还不知道,用得着别人指指画画?见沟通未果,妻子转而去寻求母亲的帮助,母亲的话不容违拗,我只好在网上预约了一个心理医师,年龄不小,看简介很专业。周末那天,外头一直下着小雨,我撑着伞,踩在一块块淋湿的青石板上,一时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医院里到处都是焦急挂号的患者家属和眼神呆滞的病人,一路小跑的、到大厅咨询台咨询不明白的、拉住志愿者问东问西的、取药处窗口前排队探头探脑的,各色人都有,慌乱得像是马上就要到世界末日了。
那天,医生先让我在一台电脑上做几套题,我打开一看,全是些关于心理问题的题目——会经常感到沮丧吗?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晚上大概几点入睡?诸如此类。我心里很抵触,可还是硬着头皮老老实实答完了。拿到结果后医生眉头紧蹙地盯着电脑,头也不回地又询问了我一下大致的状况,接着转过屏幕让我看,七个选项中五项显示重度抑郁,我有些震惊。医生伏在桌子上,在一张单子上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我心虚地问他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他边写边让我别担心,说顶多是有些焦虑,吃点药把心放宽就好。
出了医院,我的手上多了一大袋子药,随着走动,袋子里的药“砰砰”乱响。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空一片暗青色。我鬼使神差地想到了25岁的海子携着四本书卧轨自杀,那四本书是通往天国的钥匙吗?我想我大概真的是病了。我使劲拍了拍脑袋,似乎这样做就能把这些乌七八糟的念头从脑中拍出去一样。
一天洗衣服,妻子从我的裤兜里搜出了确诊单,一脸严厉地推到我面前。我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我放宽心,别太当回事。妻子没言语,转身蹲坐在矮凳上,默默择起了芹菜,我挨着她坐下。她嘴里嘟囔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们房子买了,工作稳定,有爸妈帮衬带女儿,吃喝不愁,还有什么让人烦心的呢?”
是啊,还有什么烦心事呢?我也没想明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日子越过,里邊儿模棱两可的答案就越多,有时当间还会冷不丁冒出一个东西别在心坎,像是一根木头楔子卡在机器转动的齿轮中,动弹不得。
之后一连几天,我和妻子都为新房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今天通知业主周末去验收房子,明天又通知要去监督工人修缮地板,后天又收到消息说不交物业费的话物业要扣下钥匙了。每天业主微信群的消息都能把手机震得嗡嗡乱响好一会儿,我不堪其扰,只好把群消息通知关掉,但忙过一阵后又忍不住打开看看最新进度。杂七杂八的事儿容不得我想西想东,只好铆足了劲先处理手头的零零碎碎。
已经好些天没碰到那个老太太了,我这才意识到。她去哪儿了呢?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有点儿担心她了。周六,我和妻子从新房那儿回来,出了地铁站已是华灯初上,街边商铺的招牌流光溢彩。母亲打电话过来说她和父亲正在广场带女儿遛弯儿,我和妻子便匆匆赶了过去。广场上人头攒动,我们循声走去,只见一帮老太太正在一角跳广场舞,一旁放在地上的黑色音箱传来阵阵欢快的音乐。一曲舞罢的间歇,从里头闪出一个人影,朝我们走来,我一看,正是那个老太太。她今儿倒是先认出了我。她伸出一只手高兴地和我打招呼,一脸红光,像是在异国他乡碰见了同胞。
“我这几天一直在这儿跳广场舞。”她满面笑容地说,像一个吃了大白兔奶糖的小孩儿。
我为她这样的变化感到高兴,人嘛,生活总得有个奔头,有奔头才有希望。
她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说,谢谢我那天听她说了那么多话,这么多年,已经很久都没人乐意听她倾诉了。我笑着说,那您以后要是想和人聊天就找我,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她说这几天恐怕不行,太忙了,忙着跳广场舞,忙着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还忙着给小区的流浪猫流浪狗喂食儿呢。说着说着,她眼里闪烁起了亮光。过了一会儿, 远处的同伴叫她,她语带歉意地和我说了几句后,匆匆回去了。远去的背影,似乎看起来也不那么孤单了。
我想,我也该找点事儿做了。我想起上大学时,迷茫的时候晚上就到操场上跑步,两条腿肚子各绑一只沙袋,跑上不知道多少圈,汗水浸透了T恤,等体力耗尽了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塑胶跑道上,喘着粗气,遥望蓝灰色的天空上零星的几颗孤星,它们闪耀着,宛若广袤的夜海中一闪一灭的航标灯。等躺够了起身,发现留下了一个轮廓分明的汗印子,最后回澡房再冲个冷水澡,一身清爽。
婚后琐碎的日子让我把这个解压方式逐渐淡忘了,每天下班回到家,已是人困马乏——地铁站永远熙来攘往,车内永远座无虚席,比肩叠踵的人群无时无刻不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碌,我裹在密不透风的人流里呆若木鸡。一天晚上到家,我刚把包放到椅子上,还没来得及喝口水,父亲穿着一身运动装从卧室里钻了出来。走,跟我去跑步。他一如既往以命令似的口吻对我说,并没打算和我商量。我以加班太过劳累为由予以搪塞,可父亲并没打算放过我,走走走,我这么大岁数还不嫌累呢,你一个大小伙子累什么?换鞋换鞋。我被父亲推搡着出了门。
我不善于当机立断,就算当下做出决定也很难付诸行动,像是必须有一个人在后边推着我走才行。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跑着,刚开始还能想一些事情,到了后来,浓重的呼吸打乱了我的脑子,我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跑完回去睡觉。
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梦,梦见了很多人,朋友、同学、过世的姥姥姥爷,场景辗转一个又一个,他们之间竟意外地彼此熟悉,一旁的我倒成了陌生人。一夜下来,疲惫得像跑了一个通宵。
新房子下来后散了四个多月味道,卧室的木质地板已经重新铺好,书墙、衣柜、橱柜也已经安好,各类家电也添置得差不多。一直挨到十一月份,杭州的天气日渐微冷,院子里随处可见淡黄色扇状的银杏落叶。“货拉拉”的长厢车一路拖着浓烈的尾气驶进院子,两个搬家师傅一老一少,楼上楼下地跑,不大一会儿工夫便累得满脑门子汗。我递给两个师傅每人一支烟和一瓶矿泉水,“不急,歇会儿再搬,怪累的。”老师傅一脸憨笑着点着了烟。聊了一会儿,我好像想起了什么,还没跟那个老太太告别呢。掐灭烟头,我“噔噔噔”上了楼,透过窗户看屋里黑着灯,敲了几下门,没人应声,应该是出去了。我讪讪地离开小区,坐在副驾驶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忽然有点儿怀念,甚至觉得那些平时抠门的小商小贩也变得温文尔雅了。
年后有一次我办事时路过那里,想起搬家的时候没见着那个老太太,连声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心里还有些遗憾。于是我轻车熟路地拐进小区,路过那个之前经常买烟的摊位时,老板一眼认出了我,高兴地和我打招呼:“嗨,挺长时间不见你了,忙什么呢?”
我笑着说:“搬家了。最近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常来玩儿啊。”
和烟店老板分别后,我径直去了老太太那儿,看到几步远的屋里亮着灯,挺热闹,小孩儿兴奋的喊叫声充斥着整个房间。老太太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国了吗?我轻轻敲了几下门,屋里传来一阵声音:“小声点儿,别喊了。”接着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门“吱扭”开了,一张陌生的年轻女人的面孔隔着门缝疑惑地看着我:“你是……你找谁?”
“我是之前住在楼下的邻居,您是老太太的女儿吧?”我说。
“不是,我是租客,她搬走了。”
“那您知道她搬哪儿去了吗?”我注意到,正对面的窗台上,一盆海棠正绽放着粉白的花朵,娇艳动人。
“这个不清楚,好像说是富阳,要不就是加拿大,她说孩子在那儿。”她说。
责任编辑 杨睿姝
作者简介:
蔚飞,本名郭鹏飞,90后,河北蔚县人,现居浙江杭州。作品见于《三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