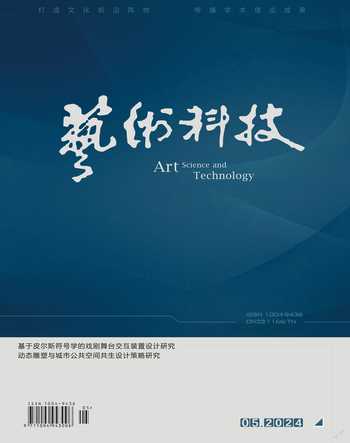琵琶独奏曲《龟兹舞曲》的演奏技法及音乐表达探究

摘要:目的:琵琶这一在西域诞生,在中国发展的乐器,历经千年的变化后,其形制仍保留着品相弦结合的特点,但发音习惯与技法使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许多改变。西域民族音乐丰富多彩,将少数民族特色元素运用到琵琶演奏中,极具民族表现力。文章围绕技法变化进行分析,探究如何运用指法变化进行少数民族音乐元素的琵琶化表达,将理论与演奏实践相结合,为进一步学习和理解乐曲提供理论分析。方法:文章分别从创作背景、技法定义、技法分析、技法选择、技法使用、技法对比、音乐表达等方面进行阐释。从技法运用的角度进行分类讨论,并结合琵琶触弦的发音特点分析《龟兹舞曲》的音乐表达。结果:乐曲中融合了新疆音乐元素,尤其在变化音的使用上,利用琵琶可做保留过程音的技法特点完成“活音”元素的表达,利用琵琶多同音的结构特点完成通奏低音的演奏,利用轮指与内线分挑的方式完成点与线的结合。通过探讨相同指法的不同演绎方式,给予“旧”指法“新”定义,在旧的基础上发现其新的可能性。结论:琵琶凭借自身声音特点以及丰富的技法变化,在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器乐化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技法为手段、音乐为交流方式,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琵琶仍承担着东西方交流媒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龟兹舞曲》;琵琶技法;音乐表达
中图分类号:J6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5-00-03
《龟兹舞曲》是琵琶演奏家、作曲家杨静老师,受邀为电视剧《唐明皇》所作的配乐,作品创作于1993年,运用了唐代燕乐音阶及其调式、调性,乐曲技法丰富,在传统推拉、揉弦、弹挑、扫拂等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新疆风格、通奏低音的演奏方式,利用琵琶实现符合西域音乐特点的声音表达,生动描绘了丝绸之路上龟兹乐舞的形象。
琵琶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技法纷繁复杂。在《龟兹舞曲》中,有运用左手弹奏出的多種类型的推拉音,右手有快速弹挑以及多种类型的轮指,如满轮、勾轮、下出轮等,通过技法的变化得到不同的音色,将人物形象等更生动地展现给听众。使用合理的指法可以减轻演奏者的演奏负担,合理的指法选择是正确表达谱面的第一步,同一乐曲对于相同技法的不同表达以及相似技法的选择,值得演奏者深入思考。
1 推拉音
按弦向右推进,使弦音升高为“推”;按弦向左拉出,使弦音升高为“拉”。右手须标明指法,不标则为虚音。即“推”“拉”音实际作用相同,通过将弦推进或拉出使音升高,二者除方向外并无不同。但在实际运用中,“拉”音的使用频率远高于“推”音,原因有三。第一,对于琵琶习琴者来说,正确的按弦是左手大指在琴背横放起稳定作用,其余四指呈拱形立在琴弦上,除手指前端外,其余部分如手掌应当悬空不贴、靠琴身。这样的按弦姿势决定了手指向内用力的舒适性,并且在日常弹奏中手指更习惯于向内(手掌)方向用力,加重‘拉的动作。第二,由于琵琶弦距的设置,所以“推”容易出现手指碰弦、卡手指(即在某些音高的需求下弦会被推入另一根弦的下方,这是因为上下两根弦的空间较窄导致手不太能够顺利挪出)的情况。第三,对于变音后需要再恢复音高时,“推”后回位手指做保留按弦较困难,更难保证经过音的效果,而“拉”可以更好地控制手指选择是否需要将弦放开或与品相贴。在该乐曲中,作曲家使用了大量的推拉音,但其使用方式略有不同,以下对推拉音进行分类比较。
乐曲在主题部分主要使用了三种类型的“先拉后推”式推拉音。
第一,带滑音的先拉后推式。乐曲一进入主题部分便使用半音推拉音,谱面标记为#G到A,且两音之间带有连音线,意为要求这两个在连接时需要非常连贯紧密,因此在技法选择上,为使两音之间的过渡更为粘连,选择带滑音的推拉音。该类型推拉音特点为,在滑音到A音时不需要右手触弦发音,而是通过滑音的余音保留,这样的方式既能有效呈现出半音效果,又能突出其中新疆音乐的附点节奏特点。但在实际演奏中,在#G音位上先将弦拉出使实际音高高于#G,发音后保持左手持续按音并利用余音保留过程音推回后滑到A音。该类型推拉音的特点是起始音的音高需要介于两音所构成的小二度之间,且不可将中间过程音断开。乐曲在主题部分带有分弦的推拉音都可归于此类。
第二,同品先拉后推式。在同一块品上做先拉后推的推拉音。作品20~27小节,旋律变为更加线性化的长轮段落,骨干音在变化过程中使用了推拉音进行过渡,乐曲中的#G到#F、#C到D,都是在相同品位先将骨干音拉高再恢复的推拉音。同品位的先拉后推式推拉音主要针对由高音到低音的推拉音,通过拉弦做下滑音的音响效果。另外,在第一拍长音换到第四拍时直接拉弦,中间不可以断开,以此模糊手指换音的声音缺口。
第三,同品连续半音推拉音。将标识相同的推拉音连续重复完成,在一定速度下重复推拉固定音高这个动作有可能出现音高不准确、拉出发音不及时的情况。该乐曲对于这类推拉音的演奏要求更高,原因有二:其一,推拉音下方标示有“吟弦”要求(吟弦:按在音位上做左右摇动,发出波音效果),即在拉音恢复原始音高后马上吟弦随即拉音,在动作上要求演奏者更加快速;其二,在实际演奏中,“E→D”三个推拉音,拉出后的实际音高第一、第二个为E,而第三个则需要高于E的实际音高。
三种类型的推拉音在完成时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连贯性,即滑音的连贯性、换音的连贯性、连续拉音的连贯性;二是推拉音的不确定音高,滑音前先拉出介于二度之间的音高、长轮中带有滑音性质的换把模糊了本来的确定音高、同品推拉的不同音高。这两个特点是基于新疆音乐中“活音”/“游移音”的运用,“活音”将调式中的某个音级微升或微降,使两音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大二度小二度等,而是在音程关系中寻求不稳定性,但又在多次不稳定音程的组合下形成该段落的动态稳定。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作琵琶化表达,是琵琶作为非语义性媒介的重要作用[1]。
2 轮指
轮: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弹出,大指挑进,连得五声为“轮”[2]。轮指是琵琶由点到线的重要方式,想要将琵琶这个点状乐器呈现出线条感,轮指几乎起到90%的作用,其连贯性、演奏方式的多样性提高了琵琶对于线条的塑造能力。关于线条的塑造,该乐曲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
2.1 由单弦到多弦
引子部分,使用拂弦拉开音乐的帷幕,在一弦上单音演奏将拂弦带来的浮躁归于平静,后重复单音的同时由单弹变为轮指,逐步由单弦轮过渡为双弦轮、三弦轮、满轮。在引子部分作者将音乐由点到线进行呈现的同时,通过轮的弦数改变增加音响厚度,使音乐由安静至嘈杂,最后使用下出轮击打面板将引子与主旋律清晰间隔开来。单音模拟出沙漠的萧瑟、孤寂,右手上下改变发音位置的满轮,似风声呼啸、黄沙飞舞。
2.2 上出轮与下出轮
上出轮是由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作弹,随后大指作挑;下出轮则是由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依次作弹,随后大指作挑。19世纪早期轮指的演奏技法多以下出轮为主,而19世纪末上出轮的出现,或是受琵琶持琴姿势改变的影响而发展,且多用于浙派(南派)之中[3]。现今,琵琶早已从横抱演变为竖抱,轮指习惯也由下出轮变为上出轮。轮指习惯的改变与竖抱琵琶有很大的关系,在竖抱的持琴习惯下,手指在弦上的发音位置发生改变,手臂位置保持不变时,小指离弦更远、离复手(用来固定琴弦的配件)更近,此位置并不利于手指的发音,靠近复手琴弦震动幅度变小,其发音更亮却也更短,又因小指天生力度偏弱,而这样的位置进一步阻碍了声音的正常发出,此时想要五个手指发音平衡,小指需要勤加训练。竖抱时,上出轮更易发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由食指出发可以更好地给后面的手指提供发音空间,手指在足够的距离下可以做充足准备,发音前的充足准备是正常发音的前提。因此,在竖抱情况下,上出轮的发音相对于下出轮来说更易控制,五个手指发音的平衡效果更易达到,而下出轮因发音空间限制,想要更加连贯还需要通过手腕旋转帮助,此时无法固定发音位置,容易出现由弱到强的音响变化。
在现在演奏的乐谱中,下出轮多与满轮结合一起使用,不单独轮某根弦,尤其大指的“挑”变为“拂弦”。《龟兹舞曲》中也沿用了这一形式。如谱例1所示,图中所框出的和弦音所使用的技法标记为轮指(琵琶技法中没有下出轮的固定标识,一般会直接在轮指处表明或注释),在实际演奏时使用的是下出轮。下出轮与满轮的搭配使用,可以使轮指在保留下出轮强弱变化的同时给手指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发音,使音色更加饱满丰富,让声音的连接更加自然。该部分以下出轮为中间音,前后形成二度辅助或上行级进,从谱例中可以看到,第一个和弦所选择的是三个手指演奏的分音,较传统两个音的分音来说三个音增加了该和弦的音响厚度,其音量也会随之变大,发音后左手进行拉音完成二度级进,因为没有二次触弦而是利用第一个音的余音完成拉音,所以音量随之减小,使用下出轮连接前音不会破坏分音与拉音形成的渐弱保留音音效,弱音进入连接较强的拂弦,再演奏大幅度强音吟弦,也不会显得过分。可见,下出轮的合理运用使得该部分在保持强音量的情况下自然地完成了前后音级的过渡。
2.3 勾轮
勾轮是指大指勾里弦,其余手指在外弦做轮。勾轮是琵琶轮指中较为常见的旋律配和弦音或衬音的演奏方法。长轮段落中,上声部呈旋律线条,下声部伴奏音型保持切分节奏,上声部的三拍长音或一二拍的同音连音线弱化了第二拍与第三拍形成3+1的节拍强弱规律,下声部形成的四拍的切分节奏型强调了第二拍的重音,因此上下声部形成节奏互补。上下声部演奏时,上声部使用线条化的轮指,下声部是点状的勾、挑,在演奏方法上实现了点线的结合。在演奏该部分时,首先应保证旋律的清晰,而后在做大指勾挑时强调第二拍所演奏的音,明确体现出上下声部的节奏填补以及点线的对比演奏。
3 弹挑
进入快板段落,在前半部分选择了通奏低音的演奏方式,将主旋律全部置于三弦低音,除旋律音外,在一弦上运用空弦进行低音伴奏。速度130,标注“meno”,即稍慢一点的、温柔一点的音乐术语提示,并说明:强调旋律音,一弦上的夹弹为铺垫音。从谱面可以看出,乐谱为连续十六分音符演奏,所以在速度上并不会很慢,但音乐情绪在此时还不应过于激动,前部分快板是乐舞进入高潮部分的铺垫,演奏时应当保持旋律的平稳,着重强调旋律音的进行,而一弦的铺垫音则需要轻盈且清晰地演奏。琵琶的音色可以通过指甲的入弦深浅进行调整,入弦浅接触面窄过弦速度快,发音更快,在需要快速弹挑但对于音量没有过高要求时可以使用触弦较浅的方式。入弦深指甲接触面变宽,更易发力,过弦速度变慢,但力度、音的结实程度都随之提升。对于乐曲中强调旋律并伴以持续铺垫音则需要两种触弦方式的結合,演奏者需要快速转换两种触弦方式,以过弦为转换标志调整触弦状态,才可达成旋律与铺垫音的音响平衡。
快板的后半部分速度变为146,力度形成两次大框架上的p-f-ff力度变化,以A为骨干音对其进行上下环绕,音乐情绪随着速度的变化也进入下一个阶段。环绕音类型的快速弹挑是在比拟少女跳舞时旋转的姿态,上行音区的逐级拓宽好比旋转时裙摆的变化,随着音乐的强弱变化,音区一次又一次加高后恢复,旋转幅度加大,裙摆也更加肆意,最后通过“#G-A-B-C-B-A”六音组的无限反复将音乐推向最高潮,六音组谱面所写为四遍组合后反复一次,在实际演奏中音组的反复不受个数限制,凭演奏者当下感受到的情绪而定,在反复同时作渐快渐强处理,最后停留在#G音上模拟出少女在舞蹈中无尽旋转后身影定格,此刻一切归于平静。音乐的停止不仅是旋转的停止,还是少女所演绎的丝绸之路想象的停止,在停止的这一刻将一切激情挥洒出去,呈现出丝绸之路上少数民族热情淳朴的特质,是对舞蹈的热爱,是对琵琶音乐生命的阐述。
4 结语
演奏者是声音的转化师,将音符转化为声音,又将声音形成画面或感受传递给听众。在这个过程中,听众所接收到的音乐是经过谱面技术处理及器乐声音技术处理的音乐,技法的正确选择可以让转化事半功倍。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技法是声音的武器,不同技法的选择是不同的组装方式,如果说作曲家是制造家,那演奏家则是组装大师,只有二者的结合才可以呈现出最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全国民族乐器演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委员会系列丛书编委会.琵琶考级曲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4-6.
[2] 田甜.论20世纪琵琶“轮指”技法的演变[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21,39(3):123-131.
[3] 赵雅琪,汪岷.浅析新疆音乐元素在琵琶曲《龟兹舞曲》中的应用[J].艺术评鉴,2021(12):68-70,74.
作者简介:朱林平(1999—),女,贵州贵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音乐表演(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