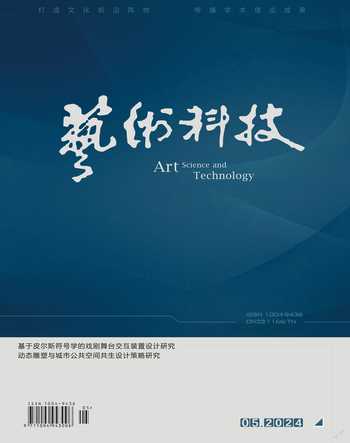张謇戏剧教育思想论析
摘要:目的:文章旨在探索实业家张謇的戏剧教育思想。他于1906年向官方提出设立“戏曲改良演习所”的想法,并于1919年付诸实践,创办了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然而,时人多关注伶工学社主任欧阳予倩的戏剧教学思想和人才培育模式,较少讨论张謇。其实,张謇具备一定的戏剧素养,并非戏剧外行,对中国戏剧教育的发展亦高瞻远瞩,他对戏剧教育的见解和戏剧事业的规划值得人们重新关注与梳理。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回顾张謇1906—1920年的书信,尤其是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交流记录,再次挖掘、整理、概括其戏剧教育思想观念,试图还原其创办伶工学社的本意。结果:通过细读书信不难发现,张謇曾提出过一系列戏剧发展理念,可归纳为以下三大点:在“新”与“旧”的问题上,提出修改旧脚本,培养新艺员;在“树范”与“传承”问题上,意图树立南通戏剧教育地方典范,重用顶尖戏剧人才;在处理“传统”与“现代”问题上,积极发扬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优良部分,同时接纳、借鉴西方戏剧。更难得的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张謇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问题,尤其注重复兴戏曲舞蹈,希望戏曲舞蹈能够流传后世并展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结论:张謇对彼时国家的戏剧教育事业有自己的规划和策略,期冀通过系统化的戏剧教育培养新型戏剧人才,到各地试演,从而达到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作用,充分体现出一个实业家对国家未来的思考与责任。
关键词:改良社会;订旧启新;人才选择;戏剧美术
中图分类号:J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5-0-04
1919年,著名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一所综合性的新型专业戏曲学校——伶工学社,聘请欧阳予倩主持工作,意在打破旧科班的传统教育模式,以科学的方式培养戏剧人才。这是张謇通过戏曲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的一次实践,也是欧阳予倩戏剧教育改革理想的一次尝试。综合来看,学界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欧阳予倩主持下的伶工学社开展,集中在欧阳予倩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伶工学社的兴衰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而很少对张謇的戏剧教育思想给出充分解答。其眼中的中国该如何进行戏曲改良,提出过怎样的戏剧教育思想,希望培养出什么样的戏剧人才,对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又是何种态度,都需要回顾与张謇有关的文献,尤其是从1906—1920年的亲笔书信中窥探一二。笔者以张謇写给梅兰芳的信件为核心,以欧阳予倩、梅兰芳、张孝若的文章为辅助资料,提炼和探析张謇创办伶工学社前后的戏剧教育思想。
1 订旧与启新
为了改变“社会苟不良,实业不昌,教育寡效”[1]715的现状,张謇将戏曲作为改良社会的切入口。这是因为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戏曲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若要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与其“强迫教育”,不如“利导”,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见识“今日之世界”。在张謇看来,改良戏曲是一种简单又便捷的改良社会的方式,“至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倡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1]636。
至于如何改良,通过何种方式改良,作为实业家的张謇,于1919年伶工学社办学之际,给梅兰芳的信中明确提出“订旧”与“启新”两大计划。“订旧”即改正原有脚本,“启新”即培养新的戏剧演员。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想法并非当时才有,早在13年前,张謇写给两江总督端方信中就曾提过类似的建议。信中,张謇列举了法国、日本分别通过上演战败丑剧和宣扬尚武精神以激国民士气之事实,肯定了戏剧的作用与价值。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于“蔽”字,若要去“蔽”,当下最好的方法则是官方设立“戏曲改良演习所”,挑选优秀伶人,传授生徒,到内地试演。如此一来,纵使不能让所有人入学堂学习,也可使人人了解今日世界,起到民智开化,从而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伶工学社的创办其实为张謇早期“戏曲改良演习所”想法的落成,“订旧”与“启新”一以贯之。
与多数戏曲改良倡导者相同,张謇的“订旧”无外乎提倡摆脱封建社会糟粕、转而宣扬民主、爱国,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剧,以增强国民意识。不过,“启新”的概念却相对模糊、摇摆。伶工学社建成后,无论是教学体系的改革,还是人才培养方式,均受到当年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的影响。欧阳予倩的“启新”思想很明确,目的在于破除旧科班的教学模式,培养有知识、有修养的综合型戏剧演员。诚然,从张謇对欧阳予倩的赏识与支持不难看出其“启新”思想,与欧阳予倩有一定重合,但具体要培养怎样的新艺员,又该如何培养,与欧阳予倩观念是否完全契合,还需要回到张謇写给梅兰芳的信中一并探求。
1917年,张謇曾三次在信中与梅兰芳提及自己“养成正当戏剧艺员”的计划。10月20日,张謇提及在京城中挑选聪慧年轻子弟于一处练习的想法,“假如养成三十人,就曾学戏之子弟中,择其聪慧而安祥者,合为一班,即在都中加以训练,延聘一二人为之监督,岁由南通给费以资之”[1]636。信中欲重点培养的“聪慧而安详”的弟子,都是曾接受旧科班教育、有过一定基础的习戏者。五日后,张謇再次致信,提及富连成科班:“倾闻都中本有富连成小班艺亦不劣之说,不知确否。如其不劣,此班可全行移动否?抑可择尤延致否?使仅平平,另谋招练,是何方法?”[1]636当时富连成声名鹊起,张謇意欲仿照,复制其人才培养方式,特征询梅兰芳意见。然而,富连成是按照传统的科班教育模式培养人才,主要训练学员的京剧舞台基本功和昆曲,教学更偏重技艺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其教育理念与日后欧阳予倩引领下的伶工学社有着本质区别。信的最后,张謇还提到“尚拟就南方另养昆曲子弟”的计划,同时希望培养专门的昆曲人才,并于11月16日再度提及拟建五十人昆曲班的事宜。反观伶工学社课程,除了京剧、昆曲外,还开设了音乐、舞蹈、唱歌等艺术类课程,以及国文、算数、地理、历史、英语等基础课程,其目的并非培养传统伶人,而是造就专业的戏剧演员。因此,尽管张謇与欧阳予倩都想通过培养新的戏曲人才的方式进行戏曲改良,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但二者存在很大差異。欧阳予倩有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具体措施,大刀阔斧地“破旧”,积极实践较为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力图培养综合型戏剧人才。而张謇戏曲教育思想的起点依旧是科班基础上的改良,站在实业家的角度积极探求戏剧发展的可变因素,显得较为保守、温和,人才培养目标也不够清晰。
2 树范与传承
20世纪初期,以上海为源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不少戏曲改良社团,编排的新戏也陆续登上舞台。尽管戏剧人才辈出,张謇认为能担任改良大任的人并不多:“近日海上有编改良新戏者,将一切旧社会之习惯贯穿其中,观者往往泣下。然亦仅一二伶人足任改良之选。为今计,莫如即由此一二伶人设一戏曲改良演习所,使之传授生徒,到内地试演。”[1]194当时,张謇推崇的优秀伶人只有一两个,认为由他们传授徒弟,方能扩大影响力,起到改良社会的作用。他曾希望官方能授予“改良传习之伶人”,给他们以特别荣誉,且不能做损害道德及名誉之事,其实为习戏学生树立典范之用意。“将来即等差其传授之多寡以为奖励内地试演,并饬地方官特别犒奖”[1]194,建议设置奖励机制,传授学生专业知识多多益善。
张謇对能肩负戏曲改革的人才十分看重,尽管给端方的信中未曾交代其心中最合格的“改良传习之伶人”,但十年后他物色的人选必是梅兰芳。张謇曾三番五次写信邀其完成“通俗教育,改良戏剧”的夙愿,即使后来与欧阳予倩合作,他依旧没有放弃对梅兰芳的约请,并于信中提及聘梅氏为“伶工学社名誉主任”的设想,希望与之共图戏曲教育大计。张謇对戏剧人才的极度渴求,也反映在其对欧阳予倩的态度上。上文分析过,张謇与欧阳予倩培养人才的思想并不完全契合,但是秉持着“改良社会”的最终目的,张謇依旧将伶工学社章程制度、课程设置等全部交由欧阳予倩负责,以欧阳予倩的新式教育理念进行管理和实践。张謇充分信任梅兰芳、欧阳予倩,十分看重戏剧界顶尖人才立标杆、树典范的社会作用。当梅、欧二人在南通更俗剧院同台献艺后,张謇特设“梅欧阁”纪念此次演出,并亲自撰写名联“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曾解释过:“中国的戏剧界向来分的派别很多,你傾我轧,各不相下。我父也认定中国艺术方面,总得优秀分子集合起来,协力改进,方能昌明,所以我父对于梅兰芳欧阳予倩的各树一帜,都觉得有调和联合、共图中国戏剧改良光明艺术之必要;所以,他在南通新剧场内,建了一个梅欧阁。”[2]443张謇在写于1920年的《梅欧阁诗录序》中亦强调“若梅若欧”人才之难得,他们对艺术的追求自觉摒弃淫邪与浅陋之声,有节有度,鼓舞人心。因此,张謇重人才,更重其影响,他们培养弟子之品质及传承之精神,关乎整个戏剧界、整个中国社会。
人才典范选择完成后,张謇还欲树立地方典范,于南通创办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就是他的一次试验。张謇认为,南通实业、教育、慈善、自治皆成系统,自身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维持戏曲的良性发展,能为戏曲改良提供肥沃的土壤。“吾之伶工学社、更俗剧场,将以为全国之导线也,而亦弟之试验演习场也。”[1]735不难看出,张謇以伶工学社为全国新型专业戏曲学校的先声,并有推广至全国的规划。他在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投入大量财力、精力,并非只想促进南通戏剧事业的繁荣,而是希望借助欧阳予倩等人的专业改革,将南通培养戏剧人才的经验惠及全国,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正因如此,张謇对梅兰芳的加入才抱有殷切期待,认为以他的志向和才能去培养人才,十年后戏曲改良所发挥的优势将福泽全国。
3 美术与通俗
五四前后,关于旧剧何去何从的话题,知识分子曾展开激烈讨论。不少激进派持“全盘西化”观点,提倡新剧,废除旧剧。欧阳予倩在《予之戏剧改良观》中也曾感慨:“试问今日中国之戏剧,在世界艺术界,当占何等位置乎?吾敢言中国无戏剧,故不得其位置也。何以言之?旧戏者,一种之技艺。昆戏者,曲也。新戏萌芽初茁,即遭蹂躏,目下如腐草败叶,不堪过问。舍是更何戏剧之可言?”[3]11在田汉看来,欧阳予倩“否定中国有戏剧和戏剧文学”,存在一定的虚无主义倾向[3]20。尽管伶工学社课程安排和教学内容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欧阳予倩本身还是有所侧重,对西方新事物极为推崇:文化课程设置比例偏高,对传统旧剧进行歌剧化改良,组建音乐班学习西洋乐器等。如此一来,虽然学生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社学员很难在短时间内于舞台表演上做出成绩。曾有人质疑,伶工学社无法像科班一样三个月登台演出,欧阳予倩反驳科班的教学是“用火逼花开”的方法,若要办科班,就不应找他。还有人质疑学社的国文课过多,欧阳予倩认为还嫌少,张謇便对欧阳予倩说:“要他们学成你那样的程度当然不容易。”[4]92由此可见,尽管张謇全力支持欧阳予倩的改革,但未必完全赞同他的做法,二者思想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张謇真实的办学理念值得再次推敲,其对传统戏曲与西洋戏剧的态度也需要作进一步探索。
1920年2月4日,张謇回复梅兰芳信件中有这么一段话:“美术学中有戏剧,与专言通俗者不同。质言之,戏剧美术犹歌舞,舞今所无,歌可以昆曲、二黄骇之。通俗犹新剧,以其本色衣冠而无唱也。沟通此事,期益社会,非熔铸古今中外而斟酌损益之不足以为阶梯。弟之才艺适于美术,予倩则通俗优于美术。”[1]735在信中,张謇提到了“戏剧美术”与“通俗”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以及它们之间定义的区别。王国维先生曾说过:“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5]163那么,信中所提“戏剧美术犹歌舞”中的“戏剧美术”则大体指代中国传统戏曲,而“通俗”强调“无唱”,大体指代西方新剧。在张謇眼中,梅兰芳“美术”精通,欧阳予倩“通俗”在行,各有所专。张謇支持欧阳予倩改革,积极接纳西方戏剧自不必说,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他只想去其中之弊病,精华部分则积极提倡与致力发扬,屡次邀约梅兰芳正是张謇欣赏并希冀传承中国传统戏曲的重要表现。梅兰芳曾回忆张謇原话:“中国的戏剧,尤其是昆曲,不但文学一部分有价值,传统的优秀演技,也应该把它发扬光大,这是我的意见,你们的责任了。”[3]38当然,张謇对传统戏曲的见解绝非随口一提,因为其本身就具备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对于梅兰芳的演出,他不仅写诗称赞,如《观梅郎戏艺有此作》等,还能观其“艺益精进”,对《思凡》《葬花》等演出片段亦作出点评,提出自己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对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舞”尤为执着,他认为“今有歌而无舞,舞但见昔人之赋,而未见昔人之谱”[1]702,势必“复古舞”,但他在看了梅兰芳的新剧后,自觉其表演近古人之舞,因此他寄希望于梅兰芳来南通担舞蹈教学之大任,且预计三年内“可作舞谱”,用以传授新人。众所周知,京剧表演举手投足皆是舞,梅兰芳不仅自身形态优美,他的戏曲舞蹈更是戏曲界的一大突破,展现了中国戏曲舞蹈的极致审美。张謇很早便认识到这一点,希望能发挥其优长,作“舞谱”传世以供后人借鉴,对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具有远见卓识。
由此观之,无论是“美术”,还是“通俗”,张謇皆采取肯定的态度,希望能兼容并蓄,熔铸中外古今,引进相关戏曲人才,吸纳一切有益于戏曲改革的积极因素,为伶工学社所用,从而打造出改良社会、移风易俗的优秀样本。
4 結语
伶工学社的创办并非一时兴起,张謇也并非在南通实业繁荣之后才将目光投向戏曲教育领域,长期以来,他都对戏曲教育事业都抱有很大的热情和期待,并有自己的思考。根据上文分析不难发现,其散落在信件中的戏剧教育观点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能形成清晰的戏曲改良事业规划:建一所新式学校,集结国内有文化有内涵的顶尖戏剧人才,将传统戏曲中的优良部分发扬光大,尤其注重“舞”之复兴,同时也注重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培养新一代戏剧人才,到各地试演,并推广至全国,最终起到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作用。
可惜的是,张謇十分看重的梅兰芳一心扑在舞台艺术上,志向并不在此,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仅三年也因种种原因而离开。张謇心目中的戏剧教育宏图并未实现,伶工学社也在1926年因他的逝世而停办。但不可否认的是,伶工学社存在本身就具备不同凡响的先驱意义,在戏剧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另一角度看,张謇的大胆尝试、对戏剧教育发展的真知灼见,凝练了他从文化艺术角度进行教育救国的思路,体现了一个实业家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思考与责任。
参考文献:
[1] 李明勋,尤世纬.张謇全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94,636,702,715,735.
[2]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上海:中华书局,1930:443.
[3] 南通市文联戏剧资料整理组.京剧改革的先驱[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11,20,38.
[4]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0:92.
[5]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戏曲考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163.
作者简介:刘伊辰(1992—),女,江苏南通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