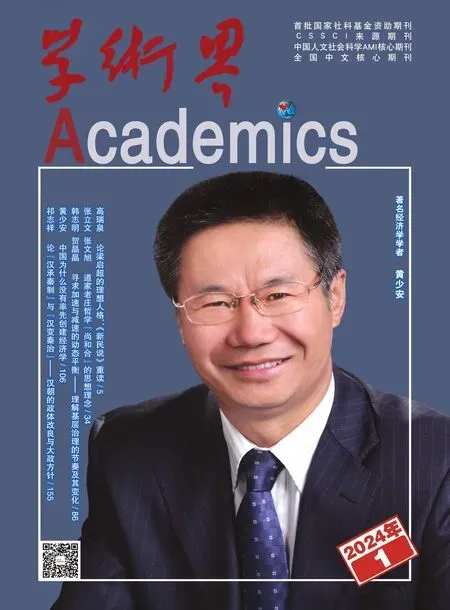严复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
——以严氏《政治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吴汉全
(1.杭州师范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2.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源于戊戌变法前后,有两位代表性的学者,一位是严复,一位是梁启超。〔1〕严复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开创者,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皆有开拓性贡献,而政治学乃是其一生中着力研治的重要学科。1905年夏,严复应上海青年会邀请,就政治学问题演讲八次,系统地表达了严氏的政治学理念及对于政治学建设的意见,并成稿《政治讲义》一书。该著最早以演讲稿的形式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并被《广益丛报》等数家报刊转载。1906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同年4月又再版。《政治讲义》是严氏代表性政治学著作,〔2〕对中国政治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严复的《政治讲义》为中心,同时亦兼及严氏的其他著作,阐发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开创者地位。
一、研治政治学的基本理念
在严复的一生中,思想启蒙、翻译西学著作及著书立说,占据主要的位置。严复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其所担任的官职,尽管不能说都是无足轻重的,但似乎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故而,严复仍然是纯粹的学者,并且亦是从传统学问走出来,进而在西学引领下建构政治学体系的开创者。大致说来,严复研治政治学最突出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进化论为指导
严复是在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进化论的先驱者,其政治学的研究亦是以进化论为指导下进行的,并力求将进化论运用到政治问题分析之始终,从而成就了其进化论的学术观。早在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就介绍了达尔文学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今译《物种起源》)。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篇)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3〕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中,重点地阐发进化论,其上卷第一篇的题目为“察变”,阐发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思想。在严复看来,生物进化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同时亦适用于人类社会,亦即在人类社会之中同样有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他说:“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4〕严复依据自己的看法,在译文中加了许多按语和注释,其所加的“按语”多达28篇,有的按语在篇幅上竟然超过译文。这些“按语”就其内容而言,自然也有对赫胥黎主张的阐释与说明,但更多的按语属于“我注六经”的诠释范式,表达自己对于进化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看法。就严氏翻译《天演论》的目的来看,就在于此著能够“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有助于中国人在进化论指导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自强保种”。〔5〕可以说,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中所作的“按语”,为中国学术界理解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导向。严复不仅通过译著来传播进化论,而且在《政治讲义》等政治学著作中成功地运用进化论分析政治现象,从而构建了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在“学”与“术”分辨中研求学理
严复以现代学科的眼光对“学术”所作出的界定,不同于中国古代学者的认知。中国古代学者论“学”者很多,但大部分叙说的是“学”之功用,且侧重于人身修养,与西人面向自然、面向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也有将“学”与规律的探寻相联系的学者。如邵雍就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6〕从总体来论说学术者,在中国古代亦不乏其人。颜元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7〕章学诚则更进一层,不仅论述学术之功用,认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8〕而且阐明学术有“二途”,“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9〕当然,对“学术”进行学理上的界定而接近今义的,是严复、梁启超等一批受西学科学观和进化论影响的学者。严复在政治学研究中认为,“学”与“术”是不同的,需要加以学理上的分辨。他说:“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10〕在严复看来,中国古人尽管亦有诸多的“谈治之书”,但以今世的科学眼光来看,只能称之为“术”,而不能称之为“学”;尽管如此,“学”与“术”也是相互联系的,两者不可偏废,但“学”对于“术”始终有着支配的地位。他给学术予以定义的同时,阐明“学”与“术”的关系:“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11〕严复正是在“学”与“术”分辨中开启其政治学研究道路的,故而他不仅高度重视政治学学理的抽绎,而且亦特别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三)辨析真伪与发明新知
严复在治学中注重事实真伪的辨析,反对思想言说中的牵强附会,同时亦反对“以今概古”的研究取向。譬如,严复认为古代政治演进中并无民主之事,因而也就不可以现今之民主理念,附会到过往的历史之中。他指出:“古无民主,若希腊,若罗马之旧制,乃以权力之均,不相统属,不得已聚族而为之,此谓合众可,谓之民主不可。何则?以其有奴婢故也。又以知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且既为民主,亦无转为君主之势。由君主转为民主可,由民主而转为君主不可,其转为君主者,皆合众非真民主也。”〔12〕又指出:“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繇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第33页)严复还说,他在街市上见到一本《宪法古义》的书,“意谓凡西人之宪法,皆吾古先所已有者”。对这种“吾古先所已有”的怀古思维方式,严复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大抵吾人本其爱国之意,每见外人好处,总不肯说此为吾国所无,而十三经二十七史皆其附会材料,名为尊我,实则大惑。”(第73页)在严复看来,政治学的研究不能穿凿附会,而要以考镜缘由、探求真知为使命。他说:“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要,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悌,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矣。”(第33页)可以说,学术研究中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反对研究中臆测附会,既注重辨析真伪、分析异同,又力求探源求是、提出真知,乃是严复研治政治学突出的理念。
(四)以科学态度探求“公例”
在西方近代学术界,科学业已拥有话语权势,“科学”与“公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学问不表现为“公例”的,不能称之为科学;而所谓科学,最根本的一条是遵循因果律,并且能在研究中求得“公例”,亦即探求规律。换言之,一门学问能否具有科学的品质而成为科学的学问,就在于能否以探求规律为使命。严复承继西方的科学观,不仅将政治学视为科学的学问,而且也看出政治学要成为真正科学,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指出:“政治之为科学,与他科学不同者,他科学如动植之类,吾辈之治之也,如堂上人听堂下之曲直。而政治不然,吾人身与其利害,而衡鉴易淆,一也。况所治之物,自鸣各殊,而不必皆实,二也。”(第72页)为了使政治学成为严整的科学,遵循“自然律令”,严复秉持进化论治学,力求将进化论与科学统一起来,并认为只有具有科学的态度才能获得“公例”。在严复看来,宇宙间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律令”,研究者必须遵循规律来治学,才能达到“学明”而“术立”、“理得”而“功成”的境界。他指出:“占位者宇,历时者宙。体与宇为同物,其为发见也同时而并呈。心与宙为同物,其为发见也历时而递变。并呈者著为一局,递变者衍为一宗。而一局一宗之中,皆有其井然不纷、秩然不紊者以为理,以为自然之律令。自然律令者,不同地而皆然,不同时而皆合。此吾生学问之所以大可恃,而学明者术立,理得者功成也。”〔13〕自然,研究者在遵循科学态度的同时,还需要在会通中把握联系,抽绎其同,分析其异,这样才能在“公例”之中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对此,严复说:“盖知之晰者,始于能析,能析则知其分,知其分,则全无所类者,曲有所类。……曲而得类,而后有以行其会通,或取大同,而遗其小异,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14〕严复的看法是,学者能否以科学态度来治学,这是与其内在的信念密切关联的。人们之所以尚未认识到公例,乃是因为人们的认识能力尚未达到。故而,研究者仍然要信仰学问有其公例之所在,并在心中始终秉持其自由意志加以追寻。他指出:“群学之有公例,而公例之必信,自我观之,且由心志之自繇。脱非自繇,则自然之用不彰,其得效或以反此。夫人事之难测,非曰此中无原因,乃原因复杂,难以尽知。”〔15〕科学态度和“公例”的理念贯穿于严复的《政治讲义》等著作中,同时亦成为严氏研治政治学的基本理念。
二、对政治学问题研究的贡献
严复在1905年所著《政治讲义》著作,在宣传西方政治学原理的同时,亦结合自己对中西政治及其学术资源的考察而阐发其学术见解,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政治学方面的开山之作。为什么要研习西方的政治学?严复在《政治讲义》中给出的回答是,尽管“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且“《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但“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第7页)严复的《政治讲义》共8讲,尽管关联政治学内容的方方面面,但始终以政治学中的重要问题为纲,并在中西参照、古今会通、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发展状况相结合中展开,其学术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继国家研究的政治学传统。政治学在西方被称之为国家学,研究国家及其权力问题乃是政治学的传统。严复深谙西学,学有所本,尤为熟悉并重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并接受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政治讲义》就主张承继西方政治学以国家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并认为在政制分类的基础上,应该首先以国家这种政治现象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严复是主张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他根据自己的政制分类法,不仅主张研究真正国家、宗法国家、神权国家,而且还提出了“第四种国家”的问题,这样“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一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第32页)严复在国家分类上的重要贡献,是在三种国家之外“别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此第四种之结合,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且“此种国家言政治者,不以为有机体,不以为官品,而以为无机体,而以为非官品之国家”。(第29页)那么,为何要设立这个“第四种国家”的类别呢?严复的解释是:“一缘吾学眼法平等,视一国一朝无异一虫一草,原无所容心于其间。二缘此等并兼力征之事,论其古初,何国蔑有。……即物穷理之事,于物无所爱憎,而所不能不立此分者,因自然演立之国家,与力征经营之国家,必不可等视齐观,并为一谈。故谓前三种为自然国家,谓后一种为非自然国家。”(第30页)可见,严氏独辟蹊径地设立“第四种国家”的类别,主要是依据进化论对于有机体与非有机体的认知,故而在国家类别上又提出“自然国家”与“非自然国家”的两分法。关于国家产生与衍化的历史轨迹,严氏从历史衍化的内在连续性及历史与现实密切关联度出发,有这样的集中性概括:“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特所主有畸重轻,故言政治者,得以分论。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其始也,宗法重于国是,神权隆于政柄。其后也,政权最尊,而二者皆杀,此天演之国莫不然。……虽然,三者而外,有其群之演进,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第30-31页)严复对自己的分类充满自信,认为“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且“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第32页)概而言之,严氏关于国家生成及衍化轨迹的论述,乃是以国家这种政治现象演进的历史(经由“蛮夷社会”至现代社会)为基本脉络,而其所说的四种国家[宗法国家、神权国家、真正国家(亦即军国国家)、第四国家(亦即并兼国家)],不仅有着前后相因、交错并进的演进图式,而且亦有政权与教权的较量,并有着国家有机体与非有机体、“自然国家”与“非自然国家”的分别,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学理与事实的结合中,构建了一幅国家衍化的动态图景。
第二,将国家权力视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严复的《政治讲义》在阐发国家类别的基础上,又循着西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进路,提出政治学要重点研究国家的“权力”问题。他指出:“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由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由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第74页)这就是说,权力的研究不仅需要阐发权力产生、维护、衰亡的过程,而且还要研究权力的载体(即权力之“所寄”)及权力“为公、为私、为善、为恶”等方面功能,同时还要注意权力机关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国家权力的研究中,尤其强调研究与权力相关的“机关”的极端重要性,认为这主要是由“机关”在权力运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同时又是与“机关”所处的状态(即“机关未具”状况及“机关既具”状态)相联系的。他指出:“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有扶倾政府之权力,而又有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当“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洩,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第76页)严复在权力研究中提出机关研究的方向,这在当时对于政治学的发展是有其学术贡献的。
第三,对政治学的本土化提出新的要求。《政治讲义》旨在推进西方政治学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其所蕴含的政治学本土化的学术诉求是特别显著的。而严复对于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有所认识的。他指出:“夫国家最初之义,不过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而已。一群之中,必有出令者,必有从令者。……然则,使所谓国家者,不必如中国之二十余省而暨满、蒙,亦不必如俄国之跨有三洲,如英国之日无停照,但令幅员如古之齐、晋,径在数百里以上,雅里氏之说,不可守矣。顾彼西人又必不肯弃雅里氏之成训,然则一有国家,将必皆为市府,而邦域国家不当有欤?乃物竞之烈,又非邦域之制,不可自存,此真事之两难者也。”(第38页)概而言之,政治学研究中的困难,一是政治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研究者“身与其利害”,亦即政治现象与研究者本身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二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相关原理和主张,与亚氏此后“物竞之烈”时代的政治现象不相适合,但大多数政治学者又“不肯弃雅里氏之成训”。由此,严复结合自己研习政治学的体会,从克服政治学研究的困难和深化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出发,提出几个具体要求:
一是学术分类的要求。严复在《政治讲义》中鉴于中国传统言说系统中范畴含混、指代不清、语义模糊的情况,认为必须遵循西方科学精神而进行分类的工作,这就必须在思维方式上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他说:“盖西学自希腊亚理斯大德勒(亚里士多德)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偭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故五纬非星也,而名星矣。鲸、鲲、鲟、鳇非鱼也,而从鱼矣。石灰不可以名煤,汞养不可以名砂。诸如此者,不胜偻指。然此犹为中国所前有者耳。通海以来,遐方之物,诡用异体,充斥于市。斯其立名,尤不可通。”〔16〕严氏基于科学分类的理念,认为“因科学于物,所据以分类者,应取物中要点为之基”。(第27页)这就看到了归纳逻辑在事物分类中的独特地位,故而他希望研究者在科学精神支配下,注重归纳逻辑在事物认知中的突出意义,这自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变革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从而使政治学等现代新学科有着语义明晰、话语严谨的著述体系。
二是范畴研究的要求。严复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范畴的,认为政治学中的相关范畴及名词,皆应该在科学理念之中而有明确的界定,其语义与应用范围皆不得有所含糊。他说:“夫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不至犯文义违反之条禁。……然此正是科学紧要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第47页)关于政治学范畴界定的重要性,严复在《政治讲义》中还说:“自西力东渐,政论日变,至于今日,其变愈亟。深恐此等名词主义,后此传诸口耳者,必日益多。……但其字既为常用若此,我辈既治此学,自不得不深考而微论之,观其实义之所属。”又说:“我辈所言政治,乃是科学。既云科学,则此中所用字义,必须界限分明,不准丝毫含混。”(第43页)譬如,严复以自由(严氏称“自由”为“自繇”)为例,说明范畴研究的具体路径。在严氏看来,考察自由的含义既需要在既定的学科范围之中,又需要探求其生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语境。就范围而言,自由这个范畴因为是在政治学范围中运用,故而“自不能不先言管辖”,于是就有了“管辖者,政府之专职,而自繇之反对也”的含义,此可见“考论自繇,亦系区别国家,体验政府性情之事”。(第43页)对于自由范畴的适用范围,严复还特别提请研究者注意:自由这个范畴“用之矣,必留神其字义有种种之,必须别析界划清楚,且须证明系政界自繇,而后可用。盖政界自繇,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繇不同。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繇,非政界自繇。政界自繇,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繇主义生焉”。(第45页)就历史背景来说,自由这个范畴因有其生成的历史语境,故而“欲论自繇,自必先求此二字之的义。又此二字名词,用于政治之中,非由我辈,乃自西人,自不得不考彼中用法之如何”。(第43页)严复通过对自由范畴的考辨,认为政治上的所谓自由只是相对的,故“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繇,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而果真是“无政府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事”。(第49页)又譬如,严复又举证亚里士多德的“独治”“贤政”“民主”范畴,说明其含义业已“大异其始”。严复指出,亚氏所说“独治,治以一君者也。贤政,治以少数者也。民主,治以众民者也。三者皆当时治制正体,然亦有其弊焉者。……其为分如此,顾名词沿用,至今有大异其始者。譬如贤政,乃当时最美之制。而法国革命之日,亚理托括,几成痛心疾首之名词。而鄂理加基之名,又置不用,实则今欧洲所呼为亚理托括者,乃希腊所訾为鄂里加基者也。又近世之人,几谓德谟括拉寺为最美后成之制。而在当时,则并非嘉号。今之所谓德谟括拉寺者,乃古之所谓波里地也。其美恶易位,有如是者。倘求其故,自是当日少数贵族主治,以美名自呼,而加主张民权之众以恶谥。称用既久,小民不加深考,循而用之,人意之中,同名异实而美恶乃易位矣。”(第20-21页)严复倡导政治学范畴的界定与研究,主张研究者对政治学范畴进行历史的考释与学科的分析,并认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在于倡导求真务实的良好学风。这对于政治学在中国形成严密有致的话语体系并进至为科学的学问,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是发明新知的要求。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强调政治学研究要努力提出“新知”,并希望研究者具有“质疑”的精神,努力在“黜旧说”中“进新知”,推进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创建。在他看来,学者研究政治学“不止于黜旧说,乃在于进新知”,(第72页)亦即在研究中提出新的见解和新的看法。严复在政治学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提出了“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的主张,并提出了“扶治”这个范畴,认为在“治者”“受治”这两者之间还有“扶治”这个中介。在当时的政治学界,政治治理研究一般皆以“治者”“受治”二分法,且对于专制与立宪之间的区分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即专制权力“自上而下”,而立宪权力乃“自下而上”。对此,严复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专制权力亦是“自下而上”。他说,“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成立。然则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第72页)那么,专制之权为何亦是“由下而成”?严复的解释是:“凡独治之权,未有不赖群扶而克立者。此群扶之力,其士大夫可也,其豪杰可也,其民可也,其兵可也,甚至由于他国之众亦可。如印度国家,其扶立之者,非印民也,乃英兵也。”(第71页)严复又进一步解释道:“一切政府,即在专制,其权力之成,必由群下,不过广狭殊耳。夫政府所建名号,千诡万殊。或国君其视土地,犹私家之视田业;或云天之所立,作君作师;而有符瑞感生,以为天命之据。此其真伪诬信,姑不具论,但名号建矣。而所感召谁乎?必有众也。假有众相与不承,彼又乌从而得力?故名号建于上者,其归顺拥戴存乎下,凡政府皆然。独至立宪政府,其归顺拥戴者,存乎通国太半之民。即不然,亦必有国家思想之众太半归之。”(第74页)严复的看法是,一切政府(亦包括专制政府)的权力都来自“群下”,不独立宪政府的权力为然。严复提出权力皆是“自下而上”并以“扶治”范畴加以解说,这在政治学上是一个崭新的见解。在《政治讲义》的最后一讲中,严复又就“扶治”问题给予总结,认为在政治统治中之所以会出现“扶治”这种现象,就在于治理者“以一身而御众人,其力常不足者也,故其势不能无待于群扶”。这个“群扶之力,必自靖自献而后可”,故而“群扶”的力量很大,对于政府“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亦即破坏政府之权力也”。由此,“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第75页)严复主张政治学研究者要善于质疑前人的学说,并在质疑之中提出新说,推进政治学研究的创新。如他认为:“市府始成,常由宗法”,而不是成于“民约所公立”,不应成为卢梭等“小国分治说”的依据。就此,他指出:“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谓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其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意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第35页)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还质疑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说,认为亚氏在国家的分类上“有独治、贤政、民主等名目”,尽管“此法相沿綦久,然实不可用”。(第18页)严复所质疑的,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亚氏所提出的分类只是应合了当时的政制情形,但现在世界上国家的状况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亚氏三分法中之类型,其涵义已经随历史之衍化而发生变动。严复还列举了神权国家的归类问题,认为“神权政府,所独异之性质,在奉鬼神天道,以统治权”,这在亚氏的分类中就存在问题。他指出:“神权国家,治柄出自教皇。夫教皇治柄,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始行见夺。其中与寻常政府,殊异甚多,而历史中与之相类,可归一门者,亦复不少。若但守三科分法,将此等特别国家,必当置诸独治之列。如此,则其形式功用,皆不明矣。”(第23页)严复在质疑亚氏政制分类的同时,亦提出自己的分类办法:亚氏“之分国家也,以治权操于多寡为起义”,而“吾人之分国家也,以其所由合者为起义”。(第27页)何谓以国家“所由合”的分类标准?对此,严氏以真正国家、宗法国家、神权国家这三种国家形态为例,有这样的解说:“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同保种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第27页)应该说,严复对亚里士多德的政制分类主张提出质疑并进而提出自己的分类方法,因为依据天演之历史进化的理念,并立足于世界上政制衍化的现实状况,因而自有其学术见地。
第四,注重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在严复看来,政治学研究有其“术”之所在,而此“术”在根本上决定于“学”,亦即研究方法之优劣取决于方法论。基于进化论的研究理念,严复在《政治讲义》中主张研究政治学需以社会为立足点,遵循历史衍化的“公例”。他指出,“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此亦即需要以历史演化的见地来研究文明社会之前的“初级社会”,而所谓“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尽管五大洲所有国家“固不必尽由于宗法”,但“由于宗法者为最多”,如希腊、罗马、英国、法国等“莫不皆然”,只是“洎形式渐变,乃忘其本来面目”而已;由此,可得“社会天演深浅之粗分”,即“浅者不离宗法,深者已离宗法”,这并且成为“历史之一公例”。(第24-25页)正是基于进化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严复认为“凡真正国家,将成未成之先,其中常有二种境界:其一家族,其一教会”,出现“宗教宗法二者并行”局面,并且两者“常有倚重之处,此浅演社会之所同者”,只是到了“文明大进之时,国家常无待于二者而自为法度耳”,于此“我辈既以天演术言治,自不能置初级程度不言”。(第26-27页)严复主张在进化论指导下研究政治学,希望在学术研究中努力践行进化论的方法论,因而也就特别重视政治学方法论的建设,并提出具体的研究步骤。他指出,研治社会科学之步骤有四个方面:“(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折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腐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利,四也。”(第12页)根据治学的这四个步骤,严复提出政治学研究“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因为这“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其具体方法是:“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第12页)严氏是在历史衍化的视域之中,提出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分类、探求政府功用、划分衍化阶段、抽绎公例的四种方法,从而使政治学在规律的探索中成为政治科学。
以上,初步考察了严复所著《政治讲义》的学术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严复能够写成《政治讲义》这部政治学著作,并进而构建其政治学体系,大致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多年来翻译西方政治学名著积累了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严复首先是翻译家、启蒙思想家,然后才是著名学者。就严复的学术生涯来看,翻译西方政治学名著、宣传西方政治学思想,乃是严复学术活动中的最主要的方面。在西方政治学著作翻译方面,严复对孟德斯鸠、穆勒、甄克斯的著作予以高度重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乃是西方政治学的名著,严复据英文版全部译出,并取名为《法意》,于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在严复之前,《论法的精神》已有地理学家张相文的中译本,但张译本乃是根据日本学者译本的转译本,且张氏只翻译了该著的前20章(原著31章),故而张译本乃是不完全译本。穆勒的《自由论》亦是西方政治学的名著,此著在中国最早的译本有两个:一是严复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03年刊行;二是马君武译本,取名为《自由原理》,于1903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严复又译出英国学者甄克斯的《政治史》,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严复基于西学本土化的理念翻译西学原著,并在译述中运用“按语”形式表达其对西学的理解,为当时的先进中国人研究西方政治学创造了条件。
二是关注中国政治变革为获取西方政治学的智慧提供了动力。严复是积极关注中国政治的先进中国人,他早年引进的西方政治学说的目的,就在于变革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辟韩》一文中,提出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新理念。如他认为,中国封建统治的“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17〕但在西方民主社会之中,君主与人民之间并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在社会生活中所结成的契约关系。“国者,斯民治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18〕严复的主张是,正是由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故而国家治理及君主的选择皆是由人民决定的,所谓的君主乃是人民依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形成的,并且君主必须具有公心、贤能的品质,而其责任就在于“卫民”。〔19〕因此,如果君主不能担负“卫民”的责任,则人民就可以废除君主。在这里,严复倡导西方政治学所倡导的“主权在民”思想。在严复看来,中国在政治上必须变法图强,积极地采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他提示人们注意,西方社会业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必须认清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顺应历史的潮流。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的开头就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20〕在严复看来,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就必须取法西方、变法图强。他说:“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21〕严复在对中国严峻形势的分析中,强调要研究“西洋富强之效”,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为他日后继续研习西方政治学理论提供了思想动力。
三是政治学之外的学科基础也为建构政治学体系创造了条件。严复不仅通晓西学,而且有较好的中学根底,同时对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诸多学科亦特别熟稔。譬如,严复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学的建立,作出了探索性的工作。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皆是传播归纳逻辑思想,这对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建立有奠基性作用。《穆勒名学》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论述形式逻辑的名著,承继了培根的哲学思想,主张将演绎逻辑置于实验和归纳逻辑的基础上,并加以改造,建立起归纳逻辑的思想体系。这对于严复有较大的影响。严译《名学浅说》是英国思想家耶芳斯介绍形式逻辑的著作,在学术思想上推崇归纳逻辑。严复选择此著而加以翻译,可见严氏有着推重归纳逻辑的思想倾向。严复高度评价归纳逻辑的地位,认为归纳逻辑乃是科学求真的唯一方法。他指出:“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22〕在严氏译本中,“内籀”是指“归纳推理”,而“外籀”则是指称“演绎推理”。在严氏看来,作为事物内在本质的公理、法则即所谓的“公例”,不管是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公例”,还是自然科学中的“公例”,其研求之法只能是归纳法。仅就社会历史领域来看,归纳法就是开民智的有力工具,这对于破除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推崇演绎推理,而这并不是科学的归纳法,“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23〕又譬如,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提倡以“群学”(社会学)来治理社会问题,认为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了社会生活领域,为社会学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氏同时。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凡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精深微妙,繁富奥殚。”“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24〕严复依据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治理就要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主要的措施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25〕所谓“鼓民力”,就是培养人民强健的身体,禁食鸦片、废止缠足,改革旧习俗;“开民智”就是创办新式学堂,废除八股取士,提倡西学;“新民德”就是采用西方的自由平等,代替封建的伦理道德。可见,严复具有较好的社会学基础,并为推进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再譬如,严复在研习《国富论》时深受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影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他在翻译《原富》时,写了约6万字的“按语”,将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合二为一,提出“义利合”的经济主张。他说:“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26〕严复在倡导“义利合”主张的前提下,强调社会财富皆由民力之所生,主张国家要充分发挥民力的作用,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允许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并积极保护个人的利益。在对外贸易方面,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工商业的办法,提升中国输出产品的层次。他说:“中国之往外国者无熟货,外国之来中国者尟生货,故中国之于外国,犹郊野之于都邑,本业之于末业也。斯密氏此书,其所反复于郊邑本末之间者,取易其名,固无异直指今日中外通商之利病矣。”〔27〕这说明,严复对于经济学也是有很好的学术基础的。
严复的《政治讲义》在思想和学术两方面,皆有很大的影响。就政治思想演进而言,《政治讲义》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在政体设计上宣传西方近代政治理论,为建立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民主政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就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而言,《政治讲义》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开山之作,其倡导的进化论政治学的主张为后来学者所承继,而其所提出的政治学本土化的具体要求,亦为此后中国的进化论政治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努力方向。
三、研治政治学的主要特点
严复在20世纪初年是从推进立宪的角度而对西方政治学进行研究的,其在中国建构政治学体系的努力亦服从这个目标。他的《政治讲义》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尽管贯穿着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但从西学东渐的历程和中国政治学起源来看,乃是推进西方政治学本土化的努力,并具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一是政治学研究的经世致用诉求。严复虽是具有西学深厚功底的学者,但亦秉承中国传统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故而特别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他早年发表《论世运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就在于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抨击专制政治,努力为中国政治变革找到新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于1905年在上海青年会所作的政治学讲演,其目的还是期望通过传播西方政治学原理,为当时正在酝酿的君主立宪服务。他在第一次开讲时就说:“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第7页)而严复在八讲之后所作的总结中,亦特别申明立宪政治中建立国会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国会乃是“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故而“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对于国会这个机关,严复分析其作用:“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洩,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第76页)可见,严复这里对国会所作的诠释,是从立宪的根本要求上强调必须有国会这个机关的存在;同时亦在向主张立宪的人士说明:只要设立国会这个机关,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不仅没有“革命”的问题,而且皇室也不会倾覆,这就能破解政治史上的“一治一乱之局”。需要指出的是,严复虽然主张学者集中精力治学,但亦不反对学者为社会服务。在他看来,尽管“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名位上亦有“学问之名位”和“政治之名位”之别,但为学之道在于能将学问运用到社会之中,故而学者在治学之中必须面向社会,善于向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人学习。因为,实际的情况正是,“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而就社会来说,“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28〕这说明,严复希望学者能多多地服务于“农工商”,乃是基于“国治”的目标,其强烈的经世致用理念跃然纸上。
二是政治学研究的西学根基。在传统与西学之间,严复的西学立场是鲜明的。在他看来,中学之八股取士乃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故而主张“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29〕严复的看法是,西学与中学完全不同,西学的优势就在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30〕严复猛烈地批判传统学问,主张治学上以西学为根本。故而,他对于固守传统的“今之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这些人“每谈欧亚交涉之事,动为逞臆之言,以中国旧理例西国时事,无怪其为外人齿冷也已”。他指出,学者在治学上尤其需要了解和掌握西方的情势,并具有较好的西学基础。他的看法是:“夫欲为今世通才,于变端之至,而知所以控御之方,非博读西书,又乌得乎?”〔31〕严复认为,学者欲精通西学需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始基”,而后学问上才可能成为“有本之学”,但中国人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实在很少;尽管十多年来中国人亦“始谈西学”,但“大抵求为舌人,抑便谈封而已”,并且大体上也是“求用而不求体”〔32〕的。严复这里的评论,可以看出其崇尚西学的态度及追寻“有本之学”的信念。
三是历史政治学的特色。严复研究政治学善于从历史沿革中论及政治学的原理,把历史作为理解政治现象的基础,故而其政治学的架构有着历史政治学的倾向。譬如,严复提出的政治学的四个“公例”,乃是从历史衍化中抽绎出的。他指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第17页)事实上,在政治现象及政治关系的研究中,严复亦善于基于历史现象的分析而加以论述,阐明政治衍化中所具有的思想意蕴及其所内含的历史逻辑。譬如,关于国家的目的问题,当时学术界有“抑强扶弱”说、维持“公道”说、“御外存群”说、“扶植民德”说、大众“幸福”说,等等。严复主张,探索国家的目的应紧密联系国家衍化的历史,并将国家置于社会历史的演变之中,从而使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统合起来。他说:“盖国家即有目的,亦是随时不同。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假有以宋、明政策,施之汉、唐,或教英、法,为当年之希腊、罗马者,此其为谬,不问可知。”(第18页)在政治学研究中,为了使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得到有机统一,严复希望研究者能研究政治家,并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第30页)又譬如,严复基于历史上政制衍化的实况,提出亚氏的“旧有分法,实为无当”的意见,但严氏仍从历史演进中充分地肯定亚氏是“政治家所崇拜”的人物,并认为亚氏“其书所立大义,有历古常新而不可废者耳”,同时亦从当时的历史状况进一步肯定亚氏著述的历史合理性,指出亚氏之“分政体为独、少、众三科,当彼之时,自一切征诸事实,不同后世空谈。如专制独治,有北之马基顿,东之波斯。而巴尔干半岛之南,与海中小岛,各各独立国家,政权或操之少数,或散之庶民,是以为分如彼”。(第21页)应该指出的是,严复研究政治学所具有的历史学倾向,乃是基于历史学与政治学关系的学术考量,同时也是从西方政治学史中汲取了思想智慧。他曾说,研究政治学首先需要知晓“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盖二学本互相表里”;正是如此,“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而就政治学演进历史来看,“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第8页)严复研治政治学善于从历史衍化中发明政治学原理,其阐发政治学主张亦强调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证据,故而其建构的政治学体系有着历史政治学的显著特色。
对于《政治讲义》的学术地位,应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中加以认识。中国政治学在清末处于创建阶段,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单篇文章有之,运用西方政治思想批判中国专制制度的文章也不少,而有着较为严密架构的政治学专著却不多见。严复的这部《政治讲义》著作,可算是例外。这同时也奠定了严复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先驱者地位。严复是在中国引进西方政治学的先驱,同时亦是中国创建政治学体系的学者,与梁启超同为中国政治学起源中的关键人物,并且两人在学术思想上皆承续英国功利主义一系,而非法国卢梭激进主义一系。由此,在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将严氏与梁氏作比较,并结合中西政治衍化的状况及其所提供的学术资源给予分析,这对呈现中国政治学起源的面貌是有学术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