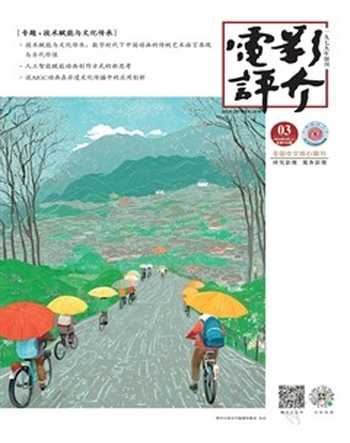舞蹈电影的叙事建构及审美表达
舞蹈是以人体为表现手段来塑造形象和表达情感的综合艺术,电影则是通过银幕和屏幕展示画面,它们都是利用多维时空元素来创造直观的视听体验。舞蹈电影是综合舞蹈与电影两种艺术门类的电影类型,其中舞蹈直接参与电影叙事,推动电影情节展开,或者借助舞蹈来传达电影主题。舞蹈电影中,舞蹈艺术与电影艺术“不是取代彼此,而是为彼此提供新的力量”[1],两种艺术完美结合,通过演员的舞蹈表演和富有旋律、节奏变化的音乐,引领观众深入电影的情节和故事,进而深刻理解电影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深层含义。
一、历史脉络:舞蹈电影的缘起与发展
电影在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动态影像记录方式而存在,这与人类的舞蹈活动紧密相连,将舞蹈作为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拍摄和展示。19世纪末,法国电影先驱者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Lumière,Louis Lumière)用固定机位的摄影机记录了独立发生的事件,其中不乏舞蹈表演的记录,如“《芭蕾舞演员》《爪哇舞》《俄罗斯舞蹈家》《扇子舞》”[2]等。1894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拍摄的《蛇舞》(美国,1894)中,著名舞者安妮贝拉·惠特福德用她华优美的舞姿和飘逸的裙摆展现了多变的造型,这部舞蹈短片也是世界上首部手工上色電影。安妮贝拉的舞裙在红、绿、黄等色彩间变幻,为整个舞蹈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进入20世纪之后,电影逐渐从单镜头式的萌芽状态发展为一种通过镜头调度与蒙太奇剪辑建构复杂影像文本的叙事系统。”[3]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声电影的兴起使得舞蹈可以与音乐同步,相得益彰,在电影中呈现更加精彩的画面。“起初,新兴的声音录制限制了摄影机的移动,于是拍摄舞蹈动作时,摄影机又变回早期电影那样的固定视角。一次早期的有声电影尝试,录制出了一部简单而伟大的影像,即1934年多丽丝·韩福丽(DorisHumphrey)表演的《G弦上的咏叹调》。”[4]20世纪40年代,玛雅·黛伦(Maya Deren)拍摄的《午后之网》(美国,1943)被称为舞蹈电影的雏形,这部短片电影在舞蹈电影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使舞蹈电影开始受到电影界的关注。此后越来越多的舞蹈电影作品出现在银幕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和摄影技术的改进,舞蹈电影进入了黄金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好莱坞拍摄制作了著名舞蹈电影《雨中曲》(美国,1952),这部电影被广泛认为是最精彩的舞蹈电影之一,其一大亮点在于其将舞蹈生活化,用舞蹈来讲述电影故事。舞蹈不仅仅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更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叙事功能。这一时期,中国制作了一批如《宝莲灯》(中国大陆,1957)、《小刀会》(中国大陆,1959)等舞蹈艺术和电影艺术颇为统一的电影。
20世纪60年代,导演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和杰罗姆·罗宾斯(Jerome Robbins)等人通过运用多镜头、特殊效果和音乐剪辑等手法,创作了如《西区故事》(美国,1961)等一系列艺术性高的舞蹈电影作品,这些影片将舞蹈段落整合进全片,并与其他元素同等重要。在这一时期,中国创作了《红色娘子军》(中国大陆,1960)、《蔓萝花》(中国大陆,1961)、《东方红》(中国大陆,1965)等电影。其中,《蔓萝花》根据贵州苗族民间传说改编,填补了贵州舞蹈电影的空白,该剧主题思想鲜明,戏剧情节引人入胜,刻画出了蔓萝等鲜明的人物形象,场面优美,舞蹈语汇极为丰富多彩。此后,舞台表演的舞蹈电影以及专为摄影编排的舞蹈电影得到了发展,也出现了许多关于舞团或舞者的纪录片。中国拍摄了《丝路花雨》(中国大陆,1982)、《孔雀公主》(中国大陆,1982)等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舞蹈电影。
进入21世纪,舞蹈电影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了电影技术的进步与舞蹈电影的发展。《舞出我人生》(美国,2014)在场面、主题、拍摄技巧方面都获得了诸多新突破。部分电影工作者尝试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舞蹈拍摄成舞蹈电影,如欧洲的踢踏舞、日韩的街舞、南美的拉丁舞以及中国的敦煌舞、维吾尔族舞、傣族舞等。不同国家、民族的舞蹈风格和文化元素的舞蹈,通过电影媒介的呈现,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为文化输出的重要力量。舞蹈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和文化传统,增进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理解。从默片时代到数字时代,舞蹈电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也促进了舞蹈艺术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观众对舞蹈电影需求的增加,舞蹈电影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将给人们带来更多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体验。
二、“形”“影”不离:舞蹈电影的叙事建构
舞蹈电影以舞蹈为主题,并直接参与到电影叙事当中。“电影有着它自身的叙事传统,舞蹈电影更是如此,舞蹈为电影叙事服务,是叙事链条中的一环。”[5]“舞蹈在这些电影中并非透明的,而是人物命运、戏剧冲突、个体存在、性格特点都围绕着舞蹈,并通过舞蹈来展开。”[6]在舞蹈电影中,故事情节与舞蹈动作相互融合,舞蹈场景的布置,角色塑造与舞蹈表演之间相互联动,是建构电影叙事的关键要素。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在舞蹈电影中起着推动故事表达,深化舞蹈电影风格特征和艺术表现的作用,给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和深入的艺术体验。
(一)故事情节与舞蹈动作的融合
在舞蹈电影中,故事情节与舞蹈动作相互交织,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展开。“在舞蹈电影的表述过程中往往依据情节的需要,选择适宜的舞蹈风格,并设计相应的舞蹈动作,以此展现电影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与性格特征。”[7]一方面,故事情节为舞蹈动作提供有力的背景和情感基础,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舞者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电影《你美丽了我的人生》(中国,2018)以梦想贯穿始终,讲述了娜孜与凯撒因误会而分手,多年后又因舞蹈再次走到一起,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困难后,他们通过舞蹈找到了力量和希望,舞蹈也成为他们表达自己、释放情感的出口。舞蹈中凝聚着主人公对舞蹈事业热情、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故事情节设计巧妙,观众能深入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主人公在舞蹈中所传达的深层情感。正如贺元在《舞蹈电影的多重审美品读》一文中所言道:“舞蹈电影运用舞蹈动作推进情节,使人物性格与形象更加丰满,从而更为立体直观地展示各个人物,赢得观众的共鸣与启发。”[8]另一方面,舞蹈动作的节奏和表现力为故事情节注入能量,使整个电影更加生动有趣。无论是以优雅著称的芭蕾舞为题材的电影,如《白毛女》(中国大陆,1964)、《中央舞台》(美国,2000),还是以激情四溢的街舞为题材的电影,如《街舞少年》(美国,2007)、《精舞门》(中国大陆,2008),通过舞者的舞蹈动作构成的身体语言与观众进行情感沟通,舞蹈动作以视觉上的震撼力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将矛盾冲突推向极致,并使观众更直观地感受电影表达的主题与情感。在舞蹈电影中,故事情节和舞蹈动作相互交织,共同构建出一个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这种独特的交织方式使舞蹈电影成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式。
(二)舞蹈场景的布置与叙事推进
舞蹈电影中的舞蹈场景起着推动剧情发展和转折的作用。正如伊丽莎白·肯德尔(Elizabeth Kendal)在谈电影与舞蹈的进化时写到“舞蹈场景可以控制影片韵律节奏,并暗示一种对现代性思维的象征”[9]。舞蹈场景的选取、设计和呈现能够有效地传达情感、展示剧情,并提升观众对故事的理解和投入度。第一,舞蹈电影中的舞蹈场景布置在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冲击力,能有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增强其观影体验。选择具有独特艺术氛围的地点来拍摄,例如华美的剧场、宽敞的舞厅或是闪烁着霓虹灯的城市街道,不仅能增添电影的视觉魅力,还能创造特殊的氛围,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故事。在《舞出我人生》(美国,2006)中,选取了舞厅进行拍摄,利用场景中璀璨的灯光和浮动的舞台道具与演员的动作进行融合,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效果。第二,在舞蹈电影中,舞蹈场景布置通过与舞者的肢体语言和舞蹈动作的结合来传达情感,进一步推动剧情发展。“艺术品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它所表现的正是人类情感的本质。”[10]舞蹈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通过舞者的动作、姿态和表情,深入表达角色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舞蹈场景的布置不仅为角色提供了情感表达的空间,还为剧情发展提供了动力。例如,电影《街舞少年》,利用舞蹈作为传达角色深层心理和情感的媒介,特别是在城市贫民区的场景中,主人公威廉斯和他的伙伴们通过充满力量和象征自由精神的舞蹈,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反叛态度。第三,通过舞蹈场景布置推动角色的发展和转变。“在电影中,在进行人物造型设计与场景布置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对场景的合理塑造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11],即改变舞蹈场景的环境和氛围,以此表达角色的成长、冲突和转变。在电影《天使之舞》(西班牙,2006)中,热爱舞蹈的主人公艾米,曾是在街头巷尾秘密练习舞蹈的舞者,逐渐成长为自信的舞蹈家。在比赛中,即使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舞者,她也毫无畏惧,展现了惊人的舞蹈实力。电影向观众展示了舞者追逐梦想、超越自我的奋斗历程。电影通过改变舞蹈场景的视觉效果,如色彩、音乐和灯光,来表达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舞蹈场景的布置与角色发展相互呼应,推动了电影情节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观众对角色的理解和共情。
(三)角色塑造与舞蹈表演的互动
在舞蹈电影中,角色塑造与舞蹈表演之间的互动推进电影的叙事建构。舞蹈是表现人们最强烈感情的艺术。《乐记·师乙篇》曾载“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2]。舞蹈作为一种身体语言,通过角色塑造来表达情感、展示个性和推动剧情发展。首先,在舞蹈电影中,演员通过舞蹈表达情感,使观众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在情感。在《黑天鹅》(美国,2010)中,主人公妮娜通过舞蹈表演展现了她对舞蹈的痴迷,同时也暴露了她焦虑和疯狂的心理状态。演员运用舞蹈来真实地传达角色的情感,使观众能够投入角色故事之中;其次,舞蹈电影通过角色的外在形象揭示人物性格特点和推动故事发展。角色的服装、化妆和舞台设计等外在视觉元素与不同角色的舞蹈风格相结合,突出了角色的个性特征和推动了电影情节的展开。电影《闪舞》(美国,1983)以纽约地下舞蹈文化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通过舞蹈来追求自由和表达自我的故事。演员身穿特色鲜明的街头服饰,如松垮的运动裤和涂有涂鸦的T恤,他们通过独特的舞步和肢体语言来展示个性。这些动作不仅充满创造力和活力,也有助于塑造各个角色的独特形象,加深观众对人物的理解,并推动剧情的进展;最后,舞蹈电影中角色塑造与舞蹈表演的互动是故事线索的重要推进力。在部分舞蹈电影中,舞蹈不仅是角色个性的体现,也常常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在《红色娘子军》(中国,1960)中,吴琼花的舞蹈中充满着坚毅和勇敢,塑造了她面对敌人时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人物形象。电影通过舞蹈展现了琼花从一个只想报私仇的女性成长为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反映了旧社会妇女面对敌人敢于反抗和斗争的精神,从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这些舞蹈表演不仅是舞蹈电影吸引观众的手段,更是角色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象征。观众通过角色的舞蹈表演,能深入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与电影角色建立起情感共鸣。
三、逖“听”遐“视”:舞蹈电影的审美表达
影像美学的应用、音乐与舞蹈的契合以及舞者身体的表现都是舞蹈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些要素相互交织、相互支持,共同为观众创造出独特而美妙的艺术体验。舞蹈电影通过视觉、听觉和情感的融合,使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舞蹈艺术的魅力,并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和情感共鸣。
(一)影像美学的运用
舞蹈电影中,画面构图、光影处理和摄影技术等技术手段通过视觉语言有效地传递情感和表达主题,合理运用这些技术手段不仅有助于展现舞者的才华和创造力,还能创造视觉美感和提升观众审美体验,为观众带来视觉享受和情感共鸣。首先,舞蹈电影的画面构图,通过恰到好处的镜头角度和位置,突显舞者的动作和身体线条。《舞出我人生》系列电影,因其精彩的舞蹈表演和創新的画面构图而闻名。导演安妮·弗莱彻(Anne Fletcher)巧妙地运用各种镜头角度和位置,将舞者的动作和身体线条展现得生动有力,运用特写、追踪和鸟瞰等多样的拍摄手法,使观众在观影中能近距离观察舞者的技巧和动作,感受他们的能量和激情。画面构图还利用对比和平衡等原则,营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有效地增强观影的视觉冲击力。其次,电影艺术本质上是关于光与影的视觉盛宴,在舞蹈电影中,光影处理为舞者创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情绪。例如,在舞蹈电影《黑天鹅》中,利用灯光变化将主人公内心的黑暗和矛盾情感表现出来,通过调整明暗度和色彩饱和度参数,营造出多样的视觉效果,增强了观众对舞蹈作品的感知和理解。舞蹈电影中运用稳定的镜头、流畅地移动和精准地对焦等技巧捕捉舞者身体的细微动作和表情变化。例如,在舞蹈电影《街舞少年》中,运用快速而流畅的摄影技术,将舞者的激情和活力完美呈现,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街舞的热烈氛围之中,这些细节的呈现不仅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舞者的表演力量,同时也传递出舞蹈在电影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和主题。
(二)音乐与舞蹈的契合
音乐和舞蹈是两种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艺术形式。《乐记·乐象篇》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13]中国古代“诗乐舞一体”的艺术理论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学者吴晓邦认为:“任何舞蹈在艺术形象上都必须通过音乐,才能把它的‘意思完整地表现出来。”[14]在舞蹈电影中,音乐的选择和编排与舞蹈动作相结合,为舞者提供舞蹈节奏和调动舞蹈情绪,推动剧情的发展。音乐的节奏、旋律有助于增强演员身体的视觉美感和表现力,为电影营造恰当的情感氛围,有助于提升电影的视觉效果和戏剧性,从而实现舞蹈、音乐和电影三者的完美结合。选取适合剧情和舞蹈风格的音乐,能为电影营造出恰当的情绪和节奏。在舞蹈电影《丝路花雨》(中国,1982)英娘被强盗掳去沦为歌伎的这一片段中,以陕北唢呐作为主奏乐器,通过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深刻地传达了英娘命运的悲惨与凄凉。唢呐的音色带有的哀愁和萧瑟气息,与英娘的遭遇相呼应,为电影营造了一种悲伤的氛围,让观众更深入地感受英娘所经历的苦难和心灵的挣扎。舞蹈电影《黑天鹅》中,运用紧张、悬疑的音乐旋律,为主人公妮娜内心的冲突和压力增添了戏剧性的效果,观众能够更深入地感受到舞蹈所传递的情感。音乐与舞蹈的结合提升了舞蹈电影的视觉和戏剧效果。舞蹈动作和音乐节奏相融合,创造出视听上的韵律感,使观众在欣赏舞蹈时也能沉浸在音乐之中。音乐的节拍和旋律对舞者的动作速度和力度产生影响,从而塑造出独特的舞蹈风格和形态。例如在电影《精舞门》中,流行音乐与街舞的激情碰撞,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和听觉的共鸣,这种视听结合仿佛让人置身其中。音乐不仅是触动观众情感和记忆的语言,而且与舞蹈结合时,通过动作、表情以及音乐的力量,将情感传达得更为深刻。“电影的声音是不可见的,然而却能够潜入观众的心灵,操纵认知和感受。”[15]观众在欣赏舞蹈电影时常被音乐所引导,与舞蹈动作一同进入情感空间,加深观众对剧情的理解和对角色的共鸣。
(三)舞者的身体表现
舞者通过身体的动作和姿态来传递情感和表意。“身体的感知与身体的动作是一体的,他通过对自身动作的控制而感知到身体的存在。”[16]在舞蹈电影中,将镜头下舞者的身体动作进行影像建构,使得演员的身体获得了超越非影像化舞蹈的独特艺术表现力,与观众建立起情感共鸣,增添电影的审美价值。“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17]首先,舞者通过身体的动作和姿态来表达情感。“舞者通过对身体肌肉的控制,改变动作力的性质或质感,获得一组相互对抗又平衡的外在物理力与内在知觉力的统一,从而创造出具有表现力的舞蹈身体动作。”[18]在传统舞台演出中,观众往往坐在远离舞台的观众席,很难近距离观察舞者的细节动作;而在舞蹈电影中,运用镜头捕捉到舞者每一个动作的细微变化、肌肉运动,观众在欣赏舞蹈时能够深入地感受到舞者所传递的情感和能量。电影《皮娜》(德国,2011)中,镜头捕捉了舞者的手指、脚尖、肌肉等细节和肢体语言,清晰地呈现了舞者们的技巧和精湛的控制力,观众跟随电影镜头,近距离观察舞者的身体表现,深入地感受到他们的力量、柔韧性和协调性。其次,舞者利用面部表情和眼神表达情感。在舞蹈电影中,通过特写镜头清晰地捕捉舞者的面部细节和眼神变化,使观众能清楚地感受舞者所表达的快乐、悲伤和愤怒等情绪。在德国舞蹈电影《皮娜》的舞蹈片段《穆勒咖啡馆》中,通过分散的布局展示了五位演员的孤独和失望,镜头捕捉了他们的面部表情、眼神和身体动作。这些演员在舞蹈中展现出的悲伤和痛苦,通过镜头传达给观众,与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联系,创造出一种亲密的观影体验,让观众能与舞者一起感受情感的波动和冲击。此外,舞者身体线条、优雅流畅的身体动作以及与音乐的协调等元素,增添了舞蹈电影的审美价值,为观众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
四、推“陈”出“新”:舞蹈电影的艺术价值
舞蹈电影通过舞蹈艺术与电影艺术的结合,创造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舞者通过身体的动作、姿态和表情等元素,以非语言的方式讲述故事和表达情感,不仅拓展了舞者的舞蹈身体表现力,还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共振,从艺术创新方面为整个艺术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舞蹈电影运用镜头和剪辑手法突出舞者的技巧,使观众能够近距离地欣赏和理解舞者的表演,这种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仅丰富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也为舞蹈的传承与交流创造了新平台。
(一)艺术表达与创新实践
舞蹈电影将舞蹈与电影进行巧妙结合,综合舞蹈动作及编排与电影的叙事手法和技术,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不仅丰富了观众的审美体验,还拓展了舞蹈和电影艺术的边界。首先,舞蹈电影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享受。传统形态的舞蹈通常在舞台或传统民俗活动中进行展示,而舞蹈电影则将这些场景搬上银幕,运用电影摄影、灯光和色彩等技术手段,更加细致地展示舞蹈的形态、动作和舞台设计,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舞者的舞蹈和技法,感受舞蹈在时空中的流动和变化,增强其视觉感受。另一方面,舞蹈电影利用剪辑和镜头语言,从多个视角展示舞蹈之美,使观众仿佛亲临现场般地体验舞蹈之韵;其次,舞蹈电影巧妙地结合音乐与舞蹈,通过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舞蹈动作相呼应,从而传递出深刻的情感和意义,使观众在欣赏舞蹈电影时,能深入感受音乐与舞蹈所营造的氛围,体验二者共同带来的情感冲击和震撼;最后,舞蹈电影提升了观众对舞蹈艺术的理解和认识。舞蹈通过舞者的身体语言传递情感和含义,在电影中则转化为叙事的手段,展现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剧情的发展。“将舞蹈艺术融入电影叙事体系的举措提升了电影的艺术性,促成电影与舞蹈艺术的优势互补,从而在银幕空间里诞生了专属于舞蹈的叙事程式,丰富了电影的语言谱系。”[19]观众在观看舞蹈电影时不仅能沉浸于舞蹈的美学魅力之中,同时也能深刻地洞察和体会影片传达的深层含义与主题。
(二)对文化传承与交流推动
舞蹈电影作为跨文化的艺术形式,不仅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理解,同时还有助于推动舞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跨文化传播中,舞蹈的‘无声胜有声能够让世界各地观众理解影视作品,从而为获得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提供支撑。”[20]舞蹈电影超越了语言和地域的限制,将舞者的身体表达和动态影像融为一体,直观生动地传递电影的情感和意义。在舞蹈电影中,舞者利用身体动作跨越言语的限制,直接与观众进行心灵对话。观众无需了解特定文化背景或语言,通过舞蹈电影的艺术表达就能深入感受不同文化的美学和价值观念,這种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舞蹈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为舞蹈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传统意义上的舞蹈传播“是以现实当中的舞台为中介的。无论这舞台是仪式祭礼的举行场地,是生活舞蹈的发生地点,还是作品公演的剧场,都是舞蹈的传播者(这里主要指表演者)与接受者(舞台下的观众)共处同一时空、面对面的信息传递活动。”[21]舞蹈电影中的舞蹈改变了舞台传播结构,通过叙事手法和影像效果,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创作和展示具有跨时代、跨文化特点的舞蹈作品,借助电影镜头将舞蹈转化为影像,又以影像为中介呈现于电影银幕而及于观众,这样的创新和探索不仅扩展了舞蹈的表现形式,也为舞蹈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吸引力。此外,舞蹈电影还能激发观众对舞蹈艺术的兴趣和热爱,从而推动其传承和发展。舞蹈电影为观众提供可以近距离反复观察舞者技巧和表演的机会,感受舞蹈的魅力,这种观赏体验有助于培养年轻一代对舞蹈艺术的兴趣,并激发他们投身于舞蹈学习和创作的热情。同时,舞蹈电影还是舞蹈教育的重要资源,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案例,以及多样化的学习体验。舞蹈电影在推动文化交流、传承和发展舞蹈艺术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舞蹈传承与发展创造了新的路径。
结语
舞蹈电影是综合了舞蹈与电影两种艺术门类的电影类型,通过将故事情节与舞蹈动作融合、舞蹈场景布置以及角色塑造与舞蹈表演的相互联动,建构起电影的叙事体系。在舞蹈电影中,将影像美学、音乐和舞者的身体表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全新的视觉和听觉体验。舞蹈电影为舞蹈艺术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突破了时空阻隔,让舞蹈更自然融入百姓的生活,吸引观众注意,并激发其对舞蹈的兴趣,将数量庞大的人群领入舞蹈认知的大门,享受舞蹈带来的艺术魅力。随着技术的革新和创意的发展,未来的舞蹈电影创作将拥有更多的可能性。电影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创新,利用舞蹈艺术来传递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追求,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舞蹈电影作品,为观众带来更加多样化的艺术体验。舞蹈电影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和国家文化输出的形式,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播和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这种全球化的传播方式不仅丰富了世界电影市场的内容,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展望未来,舞蹈电影还应继续承担起肩负起文化交流和传承的责任,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舞蹈风格和文化元素,展示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推动跨文化对话交流和互鉴,进而促进人们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知和理解,从而推动世界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英]沃尔特·佩特.文艺复兴[M].李丽,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69.
[2][3]朱靖江.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J ].民族学刊,2023(03):79-88,150.
[4][9]张仪姝.从梅里爱到流媒体视频:动态舞蹈影像的一个世纪[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04):102-108.
[5]余志为,王彤.3D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标准”使舞蹈电影回归身体表达[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04):81-87.
[6]吴海清.艺术舞蹈电影缺席中国电影四十年研究[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06):92-97.
[7]李洋.舞蹈影像的哲学问题——从舞蹈绘画到舞蹈视频[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1(05):1-7.
[8]贺元.舞蹈与电影的共舞:舞蹈电影的多重审美品读[ J ].电影评介,2022(08):105-108.
[10][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
[11]贺元.主旋律电影中红色舞蹈的主题表现及叙事建构分析[ J ].电影评介,2023(17):108-112.
[12][13]吉联抗译注;阴法鲁校订.乐记[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54,29.
[14]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概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31.
[15]王敦.电影发声:声音与影像的捉迷藏[ J ].电影艺术,2023(06):136-142.
[16]高波.身体主体性与审美关系理论[ J ].江西社会科学,2010(08):127-131.
[17]陈林侠.意象美学:当下中国电影美学重建的理论[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4):139.
[18]李青.电影中舞蹈身体动作的视觉探析[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01):113-116.
[19]黎丙松.跨媒介视域下民族舞蹈的影像复现[ J ].电影评介,2023(16):108-112.
[20]廖祖峰,顾怡清.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影视作品中舞蹈价值的多元审视——评《中国电影影像表达与跨文化传播》[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02):134.
[21]尹航.舞蹈艺术的影视化呈现及其特点[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04):85-90.
【作者简介】 李 青,女,贵州遵义人,贵州省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舞蹈创作、培训和舞蹈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贵州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文旅融合视域下贵州民族民間舞蹈传承发展研究”(编号:22BE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