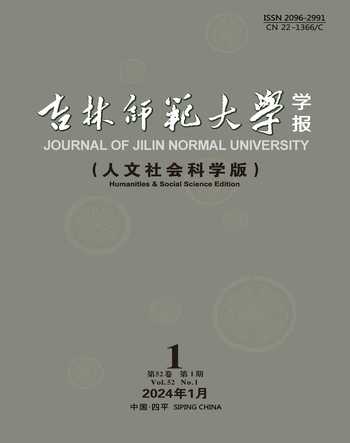佛化生日:诗词创作及其佛教文学史意义
李小荣
主持人语: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性质及其历史规律指明了方向。而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本期3篇有关中国古代佛教文学的专题论文,皆围绕“中国特色”这一关键词展开研究。
《佛化生日:诗词创作及其佛教文学史意义》一文,从中国特色的佛教民俗事象——佛化生日入手,首先,将其古典诗词创作史分成两个时段,即南北朝至唐五代和宋元明清,指出前期庆贺对象多聚焦于帝王重臣,后期则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其次,所概括的三大人伦道德主题——人臣之忠、家人之爱、师友之信,无一不是中国特色的表现。作为中国民俗佛教文学之个案研究,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木陈道忞“梦禅”思想及其诗文创作》一文,对学界鲜有关注的木陈道忞自成一家的“梦禅”之法的性质及其与诗文创作的交融互摄之表现作了较细致的历史深描,其方法、结论对明清之际禅宗文学之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论翻案诗的发展与“翻案法”的形成》一文,主要检讨了杨万里“翻案法”诗学概念形成的历史依据、禅学依据,尤其对禅宗“翻案”思想浸润宋代诗学及诗歌创作的复杂性方面,较前贤考虑得更周详,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意识。
[摘 要] 中国特色的民俗佛教,内容极其丰富。其中,与古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民俗事象之一是佛化生日,它主要指以佛事活动来庆贺的生日(包括冥寿)。就古典诗词创作而言,大致可分成两个时段:一是南北朝至唐五代,二是宋元明清。前者庆贺对象多聚焦于帝王重臣,后者则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并形成了经久不衰的三大人伦道德主题,即人臣之忠、家人之爱、师友之信。而该类作品在佛教文学史上的突出意义,重点体现在两个层面:从生死观言,虽以佛教为中心,却可兼容儒、道;从题材言,则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佛教生活和信仰的深度与广度。
[关键词] 佛化生日;诗词创作;民俗佛教;佛教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6-2991(2024)01-0056-10
佛教东传华夏,促成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佛教,它们已引起顾伟康、李四龙、王三庆、渡部正英等许多中外学人的关注。但是,对古典诗词相关题材之作品却只有陈开勇[1]的零星检讨,总体看来,尚缺少系统性。兹以唐宋以降别具审美趣味的佛化生日之诗词创作为中心,并略论其佛教文学史意义如后。
一、佛化生日之含义
中土生日的庆寿习俗,是受佛教佛诞活动启发而成 [2]。当然,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佛诞的具体日期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有农历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三种说法,而最流行的是四月八日之说 [3]2-66。
所谓佛化生日,早期主要指以佛事活动来庆贺的生日(但后期则包括冥寿,例见后文),其日期可与诸佛(以释迦牟尼佛为主)、诸菩萨(以观音为代表)诞日重合,也可以与之相邻,甚或没有太大的关联。如《颜氏家训·风操》说:“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自阮修容薨殁之后,此事亦绝。”[4]115萧绎生于天监七年(508),其生日虽与诸佛、菩萨诞辰无关,但因为母设斋讲之举,故其少时所过生日可称为佛化生日。
从传世文献看,佛化生日之设主要始于宫廷。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生日道场”条指出:“魏太武帝始光二年立道场,至神?四年敕州镇悉立道场庆帝生日。始光中是帝自崇福之始也,神?中是臣下奉祝帝寿之始也。自尔以来,臣下吉祝,必营斋转经,谓之生辰节道场,于今盛行。”[5]第5册,247结合同卷“内道场”条谓太武帝“是生日权建法会耳”[5]第5册,247,可知拓跋焘始光二年(425)至神?三年(430)在宫中以法会自庆生日,神?四年(431)后则命臣下建法会为自己祝寿。而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统一王朝的佛化生日纪念活动始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夏五月癸卯(五月初二),63岁的杨坚下诏:“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6]49其宗旨主要为纪念父母,郭绍林指出“提出断屠与文帝从小培养起佛教感情有关,因此这次庆生辰活动,体现了儒佛合璧的精神”[7],其论洵是。真正把佛诞嫁接于帝王生日庆典的是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张说《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即说:“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寻源,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8]第2册,944张说打着佛、道同尊的旗号,把李隆基诞辰比作佛祖降生(如九龙浴水等典故所示),旨在把帝王生日设成普天同庆的公共假日。玄宗满心欢喜,大笔一挥,手诏答曰:“朝野同欢,是为美事。”[8]第1册,143后来,赞宁明确指出“生日为节名,自唐玄宗始也” [5]第5册,247,其依据就在于此。
玄宗之后,历代大都沿袭帝王诞辰为公共假日的做法,即便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甚至拓展至皇太后、太子 [9]。而且影响所及,致使民间也多举办生日法会,如《太平广记》卷257“陈癞子”条引《玉堂闲话》云,营丘豪民陈氏“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10]第6册,2006,其佛道同尊、百戏并陈之举,更体现了佛化生日的民俗化和世俗化,娱乐性质较为明显。敦煌写卷P.2940《斋琬文一卷并序》目录“九赛祈赞”中又把生日和祈雨、赛雨、赛雪、满月等民俗节庆相提并论 [11]第20册,177,则知生日设斋已是敦煌十分常见的民俗活动之一。
统观古代诗词,最受重视的佛化生日,首先自然是佛诞日和观音诞日,有关作品甚多。如汪元量《婆罗门引·四月八日谢太后庆七十》、党怀英《君锡生子四月八日》的祝寿对象,其生日恰恰都在四月初八;程敏政《女以乙巳岁腊月八日生,与予生辰隔一日,人以为奇。至弥月之旦,予适署左春坊。印百晬之旦,又有赐诰之荣。人益以为不偶,因请于母,夫人小字之曰恩姐。并赋一诗,简尚宝锦衣二贤舅及宫簿弟,以私识喜,不足为外人道也》[12]第1253册,612-613尾联又说“况于阿父连生日,岁岁劳添暖寿杯”,程氏生日为腊月初十,故说隔一日,他当时喜事连连,便认为是女儿“腊八”生辰给自己带来了诸多好运。宋无名氏《汉宫春·庆寡妇二月十九》、谢元淮《二月十九日生第五孙,志喜》的庆寿对象之生日,则与观音诞日相同。
其次,是与相关佛教纪念日相邻的生日。如叶茵《秀实长子玉麟期晬》“门左蓬弧喜事新,四朝先佛庆生辰” [13]38210,表明玉麟生日在佛诞前四日,即四月初四;黄昇《鹧鸪天》“天气清和仅两旬。一旬前是佛生辰” [14]3800,则知寿主生日在三月二十八日;石孝友《念奴娇·上德安王文甫生辰》“麥秋天气,正玉杓斡暑,熏弦鸣律。浴佛生朝初过也,还数佳辰三日”[14]2626,推想王齐愈(字文甫)生日是四月十一。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二月二十日,与观音诞日相差一天,故其兄苏轼元祐九年(1094)作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清张景祁《柳梢青》词序“六月十八夜,湖上士女骈阗,笙歌达曙,盖次日为祝大士诞辰也。赋纪四阕,作华鬘色界观,可乎” [15]第1727册,255,又特别强调了创作背景是观音成道日(也称观音诞日)之前夜。
再次,是除前述两类之外的生日。它们尽管不属于佛教活动专有纪念日之序列(或与之相邻),但生日的庆贺方式仍以民俗佛事活动为主。较常见者有放生,名家之作不胜枚举:如苏轼《蝶恋花·泛泛东风初破五》(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 [16]334,说的是以家庭放生佛事来给妻子庆生;刘克庄《昔方孚若主管云台,予监衡岳,每岁瑞庆节常聚广化寺拈香。癸未此日独至寺中,辄题一绝》“同作祠官荷圣朝,年年相待放生桥” [13]36230,则追忆当年为宋宁宗赵扩诞辰主持放生仪式的往事;朱祖谋《浣溪沙·梦坡德配张夫人六十寿,作放生会于西溪,为赋此阕》、况周颐《百字令·贺周梦坡德配张夫人六十寿,作放生会于西溪,较早时梦坡扩充西溪秋雪庵以祀浙中词人》等词作,则知西湖放生祝寿的传统,从北宋以来,绵延千年而不绝。又有持斋礼佛诵经坐禅者,如陆宝《生日礼佛,水观祚公具斋》、周韩瑞《生朝礼佛二首》、黄宗羲《金仙寺僧为余设生朝供,并向佛致祝》等,尤其是黄氏之作,还深藏了特殊的遗民情怀。
二、诗词创作
较早产生重要影响的生日之作是唐中宗《十1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体联句》[17]25,它由李显起句“润色鸿业寄贤才”,李峤、宗楚客、刘宪等15人依次联句,大臣们自然不会放过歌功颂德的好机会。在唐玄宗千秋节唱和活动中,李隆基有《千秋节宴》《千秋节赐群臣镜》等诗,张说《奉和圣制千秋节宴应制》、陆坚《千秋节应制》等属于和诗,它们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除宴饮、献物、赐赏外,还有歌舞百戏之表演。嗣后,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等都置内道场,或生辰置三教讲论,故生日的佛化色彩更加浓厚。中晚唐后,诗僧为皇帝庆贺也是一大特色,如广宣《降诞日内庭献寿应制》“修斋长乐殿,讲道大明宫”、《早秋降诞日献寿二首应制》其二“瑞烟薰法界,真偈启人王。看献千秋乐,千秋乐未央”[17]2016 -2017等,描述了穆宗七月六日以佛事活动庆生的场景。栖白《寿昌节赋得红云表夏日》,又以祥瑞为宣宗六月二十二日诞辰献诗。贯休《寿春节进》,则为前蜀皇帝王建诞辰(二月初八)而作。P.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首题如是,尾题作《仁王般若经抄》),是名僧云辩长兴四年(933)为后唐明宗李嗣源生辰(九月初九重阳节)而作,并讲唱于洛阳中兴殿 [18]388-390。
上述唐五代的佛化生日之作,其聚焦对象主要是帝王。两宋以降的创作,除发扬传统以外2,更多的是创新。其突出表现有:
(一)庆寿对象的泛化
两宋以后佛化生日庆寿对象的泛化,最大变化是由唐五代以皇帝为中心转向了后世的多中心,如僧人、士大夫、普通百姓都成了庆贺的主要对象之一。
1.僧人
从创作主体言,主要分两种情况:
一是俗世诗家为僧人庆寿。如陈著《寿天宁寺主僧可举八十》“今日是何日,相庆开九秩。我亦有偈言,自知非本色”[13]40281,诗人把祝寿诗比作佛偈,旨在契合寿主可举的僧人身份。张凤翼《寿絮泉和尚端阳生日》“法轮回佛日,经榻转菩提。我欲逃尘累,东林学杖藜” [15]第1353册,572,则借端午向絮泉和尚庆寿之机,表达自己逃禅学佛之意向。王邦畿《赠旋庵阇黎》尾联云“问年才添五十一,生日盘兰斋满盂”[19]第87册,84,旋庵即释今湛,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可知是诗作于康熙二年(1663),且旋庵生日设有斋会。曹溶《实行僧生日》云“羊城西望水烟空,骤马青林入梵宫。却羡老僧高坐稳,年年拥毳六花中” [20]3第198册61,别出心裁,虽未具体描写生辰庆贺场景,却也塑造了释实行高逸不群的僧人形象。
二是僧人局内场合的祝寿。其中,作品多且独具特色者是惠洪,除《洞山祖超然生辰》《四月二十五日智俱侍者生日,戏作此授之》两首是为在世僧人创作之外,他更关注已故高僧,后者共有24题54首。周裕锴发现,其所谓“生辰”实指前辈僧人寂灭、坐化的日子,相当于世俗的“忌日”[21]108-121。若从《南安岩主定光生辰五首》其一“解说神光摩顶后,分疏死日降生时”[22]第7册,2716推断,惠洪旨在宣扬生死一如的解脱观。惠洪此举对后世僧人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雪庵祖钦禅师语录》卷1载释祖钦为其师无准师范忌日拈香说偈曰“尽道先师今日死,谁知今日是生朝”[23]第70册,603,生朝,即生辰、生日之意。
僧人又有自寿者,其主题较为多样:如居简《九月十四日自寿》(其一)“九月明朝望,思亲到鹡鸰” [13]33193、紫柏真可《生日偈》“自知今日出娘胎,今日缘何娘不来。来去觅娘无所得,莲花国里一枝开”[23]第73册,307,皆借生日自寿表达孝思之情;永觉元贤崇祯十六年(1643)66岁“诞日上堂”偈曰“今朝道是我生辰,大家齐上南山祝。前既不来今不往,两头不移中岂续?此中正好悟无生,莫道双轮如转轴……仁者若要明端的,请看多福一丛竹”[23]第72册,395-396,则重在开示信众;函可顺治四年(1647)作《系中生日二首》、顺治十三年(1656)作《丙申生日二首》,成鹫康熙四十六年(1707)作《丁亥生日自首》,均抒发了明末清初遗民僧人特殊的家国情怀;澹归今释《解连环·甘露降于丛竹,时老人疏楞严经适竟,兼值生辰》,颇有苏、辛词派的痛快淋漓,情感极其奔放。
2.士大夫
这同样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僧人为局外的士大夫庆寿,像惠洪、居简、宝昙、慧开、绍嵩、函昰、今无等诗僧,都留下了多首作品。此外,士僧交往之作对此类事情也有较充分的书写,如韩淲《赠杰宿之》“山林春雪未花开,生日何情近酒杯。似醉似醒方鹘突,上人剝吸带茶来” [13]32718,细绎诗意,作者描述了僧人以茶为礼向杰宿之庆寿的场景;杭世骏《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辰,释方珍合竹西群彦设祭寒香馆,赋诗纪事》[24]第282册,680,说明僧人也是清中叶盛行的寿苏会的积极参与者(释方珍本身就工诗善画);潘奕隽《理安寺住持澄谷上人以余七十生辰,远贶方竹杖,并侑以诗,次韵寄谢》“澄公方外最情亲,淑贶遥将庆降辰。拟向九溪十八磵,拄笻来访诵经人(余拟秋间重游西泠)”[24]第399册,381,潘氏生于乾隆五年(1740),可见本诗作于嘉庆十四年(1809),而且,澄谷上人的贺礼是双重的,有物质层面的竹杖,又有精神层面的寿诗。
二是士大夫内部的祝寿或自寿,这类作品数量极大。较有特色者,如赵抃《六弟司户生日》“我竹林翁所得奇,心传佛要面仙姿。年年六月十二日,观取高斋祝寿诗”[13]4236,“六弟”指赵抗;苏辙大观二年(1108)作《生日》,颔联云“佛身三世归依地,邻寺百僧清净因”,结合尾联句下自注“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斋僧百人”[25]第3册,1163,则知苏氏当年的生日是典型的佛化生日;刘克庄《朝中措·陈左藏生日》《清平乐·居厚弟生日》等词作,皆用“大士”语典喻寿主,故佛化色彩极浓厚;王弘诲万历三十五年(1607)作《丁未初度自述》其二云“丁未初秋月八日,吾今六十六年过……缑岭笙箫怀子晋,恒河津筏念弥陀”[20]第138册,378,可见称念佛号是王氏66岁生日当天的功课之一;何吾驺《丁丑生日二首》其一云“晓沐篆烟随境寂,午趺禅诵爱林幽”[26]第40册,398,何氏生于万历九年(1581),卒于顺治八年(1651),故知本诗亦作于万历三十五年,诗人时年27岁,却早受佛禅影响,乃至生日也要燃香打坐;黎遂球崇祯元年(1628)作《戊辰生日宿凌江上药上人禅房,七夕前二夜也》颈联“投宿满分供佛饭,染云频写画禅诗”[19]第183册,89,叙述羁旅行役中借宿佛寺而过佛化生日的情状;王庭崇祯十五年(1642)作《望远行·生日自笑》,同样抒写宦途奔波的辛酸与无奈,“佛龛灯、添爇清香一缕。无语”[27]第1册,308,聊可自慰的是他可以燃灯礼佛,自贺生辰;陈子壮《生日偈答石佣子》“瑶室璿房就里披,黄花九日对佳期。生身合掌如来日,世上齐肩大小儿”1,则以佛偈形式的生日诗答复其好友黄圣年(号石拥)之子;邓濂光绪五年(1879)作《己卯生日》“料得深闺里,频来绣佛前。焚香为我祝,细语最缠绵”[28]35,则描摹了妻子为自己庆生而虔诚礼佛的温馨的生活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以降士大夫创作的佛化生日诗词中,还特别关注女性。如王彦泓崇祯六年(1633)作《生辰曲》三首,其庆寿对象是早年的恋人,它是一组富有艺术暗示性的借佛事生活题材书写的抒情艳体诗。崇祯十六、七年间(1643-1644)龚鼎孳狱中作《生辰曲十首》,庆寿对象是其原配夫人童氏,综合其一“一林绛雪照琼枝,天册云霞冠黛眉。玉蕊珠丛难位置,吾家闺阁是男儿”,其五“博山香冷郁金钗,蔬笋看经月一街。绣佛应怜人寂寞,太常妻子更清斋”[24]第51册,46看来,其妻也虔诚信佛,过着清信女的斋居生活,并时时刻刻担忧丈夫的前程,想方设法为夫解难,真是巾帼英雄。王策《五彩结同心·生辰曲》“彩丝绣佛深深拜,湘裙展、瘦影玲珑。香台畔、锦幡新上,小名亲写当中”[29]72,孙原湘《生辰曲》“锦瑟年华似水流,赪颜犹带嫁时羞……盟香共拜如环月,稳取团圞在后头”[30]1598,樊增祥《己亥四月八日次女金粟周晬,作粥供佛,分贻朋好,伯熙以诗报谢,即次来韵》“前身龙女将毋是,小字虫娘未许同”[24]第762册,563三首诗词,无论写妻子抑或写女儿,都颇有特色,皆描写了女性佛化生日的礼佛生活细节。尤其是孙原湘之作,和王彦泓《生辰曲》可谓一脉相承,也在佛化生日诗中注入了艳情的因素。
3.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主要指庶民、市民。从存世作品看来,有的无名无姓或姓名不全,特别是涉及女性时。如宋无名氏《汉宫春·庆寡妇二月十九》“四舞阶蓂,花朝节后,二月阳春。观音降诞,当年对此良辰” [14]第5册,4799、明首座《母生日》“今朝是我娘生日,剔起佛前长命灯。白米自炊还自吃,与娘斋得一员僧” [31]800,屈大均《荔支十六首》其八“小姬生日喜含春,绣佛堂前百果陈。三爵奉卿何所祝,玉颜长似荔枝新”[32]第2册,521等,不管作者身份是僧是俗,其庆寿对象皆没有留下完整的姓名。与此同时,禅宗语录又辑有不少禅师给普通居士所说的生日偈,如释元长说《千岩和尚语录》有《方诚翁生日》曰“日暖风和二月春,鸟啼花笑庆生辰。吾侬示汝长生法,无相身中有相身”[33]第34册,224,颇疑此类偈颂用于居士诞辰的上堂说法,故相对于其他应用场合,更富于禅理、禅趣。
(二)人伦道德的普遍化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人伦道德,于此,佛化生日诗词创作也不例外。其突出主题有:
1.人臣之忠
相关重要作品,如北宋田锡咸平二年(999)作《圣节有怀》云“南山晴霭御炉烟,回望长安白日边……翠微钟磬行香寺,红叶楼台祝寿筵。吟想皇州晩来景,云间宫阙夕阳天”[13]第1册,469,诗人回忆了三年前在长安为宋真宗承天节(在十二月二日)的祝寿场景,既言翠微寺行香,则知庆典活动中定有佛事活动。滕茂实靖康二年(1127)作《天宁节有感》云:“节临重十庆天宁,古殿焚香祝帝龄。身在北方金佛刹,眼看南极老人星。千官花覆常陪燕,万里云遥阻在廷。松柏满山聊献寿,小臣孤操亦青青。”[13]第22册,14927宋徽宗赵佶生辰本在农历五月初五,以俗忌,移于十月初十,故称重十。当年金兵虏走徽、钦父子,作为使金副使,眼见国主遭难,故借佛寺庆贺圣诞辰抒发忧愤之情。
《率庵梵琮禅师语录》谓“瑞庆节上堂”禅师说偈“普天迎瑞气,遍界庆生辰。水有朝宗意,葵倾向日心。衲僧随日转,林下仰天庭”[23]第69册,555,此即为宋宁宗赵扩瑞庆节祝寿。《希叟绍昙禅师广录》卷2载绍昙禅师“满散寿崇节”说偈“幸有菩提真妙果,年年同献佛生辰”[23]第70册,424,寿崇节是宋理宗赵昀皇后谢道清(宋度宗赵禥则称她为皇太后)诞辰,因日期同于佛诞日,故曰“年年同献”。张弘至成化七年(1471)作《冬至贺圣节途次有纪》后两联云“龙亭遥祝万年寿,虎拜回瞻千佛灯。却忆明光趋侍日,瑞烟缭绕五云层” [34]第84册,262,明代把元日、冬至、当朝皇帝生日万寿圣节作为三大公共假日,并伴有祭祖、祝寿仪式,而冬至与皇帝圣节重合的只有成化七年(宪宗朱见深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二)1,即便身在旅途,诗人仍然念念不忘以前参加过的皇帝生辰大会,其衷心真是日月可鉴。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中榜元的洪亮吉,人逢喜事精神爽,撰出组诗《万寿乐歌三十六章》[35]637-645,顾名思义,其主旨当然是为了乾隆欣开九秩(即八旬万寿大典)而歌功颂德,它们虽非一时之作,不少乐章如《巴勒部第三》《坎扒洼经第四》《清字藏经第二十三》《经坛设第二十七》等,都把乾隆比作当世如来,甚至无量寿佛也为之拈香祝寿,故把此次为时甚长的生日大典视作特殊的佛诞大会也未尝不可。
2.家人之爱
华夏文明向来重视家庭伦理建设,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本质上是爱与关爱(本文统称为爱)。两宋以降的佛化生日诗词,主要抒发的是家人浓烈的亲情或夫妻忠贞不渝的爱情。其代表作有苏轼《蝶恋花·泛泛东风初破五》、韩驹《令人生日以画十六大阿罗汉为寿,仍作三颂以祝长年》、洪适《席上见姚泉寿母,诸子求诗》、洪咨夔《老人生朝为寿》、刘克庄《清平乐·居厚弟生日》、怡轩《寿母诗》、陈藻《伯温索诗,贺令姊夫生朝》、张翥《水调歌头·己丑初度,是岁闰正月,戏以自寿》、汪懋麟《一丛花·虎丘生日自寿》、金甡《四月七日大兄忌辰,荐享感咏》、张开东《唐氏姑母年八十,居茅山,追维旧爱,数十年情事历历,遂作古风长篇以叙之,且祝焉》、秦瀛《悼亡诗十八首》、汪学金《慈愿生日为赋〈禅仙吟〉》、黎简《亡妇生日》、孙原湘《生辰日》、刘凤诰《家人寄绣像观音为寿,用坡公〈子由生日〉韵》、谢元淮《二月十九日生第五孙,志喜》、俞樾《六月初三日为内子姚夫人生日,手书〈金刚经〉一卷焚寄,附四绝句》、陈夔龙《八月二十一日为先妣姜太夫人八旬冥寿,龙华寺诵经,赋此志痛》等。从创作方式看,主要有自寿和寿他,但后者更常见。从祝寿者与祝寿对象的关系看,常见伦理关系有三种。一是晚辈对长辈的庆贺,意在体现孝道,其中最突出的题材是寿母。即使是自寿者,往往也会深念慈母生育之恩,如晚明杨巍在81岁时所作《诞日寓普明寺谒毗卢佛》“永怀慈母恩难报,白首焚香古佛前”、《诞日寓回河寺兼赠慧上人》“初度客中念慈母,佛前愿施八关斋”[12]第1285册,524,可见其生日礼佛设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往生的慈母做功德。二是平辈间的祝寿,而写感情最细腻的是寿妻(妾)诗,如苏轼、龚鼎孳、孙原湘之作,都十分注重刻画女性佛教日常生活的细节;更可注意的是悼亡与冥寿的结合之作(如秦瀛、黎简、俞樾),都充满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叹。三是长辈对晚辈的祝寿,像谢元淮就对在观音诞辰降生的第五个孙儿充满无限期待,竟然连用三位佛教文学史重要人物(竟陵文宣王萧子良、苏轼、苏辙)的相关典故,这说明他对佛化生日极其重视。此外,作者在以寿主为中心的同时,也可以兼写其他家人的佛教生活细节,如张开东之诗虽以姑母唐氏生平事迹为主轴,却也兼叙叔婶、姑父等众多内外宗亲人物;刘凤诰所述虽以其妻绣观音像为中心事件,然而,“稚女添线”[24]第467册,339的辅助性画面,相当温馨感人。总之,无论寿主、颂寿者,他们与佛教思想、佛教礼仪的关系都很密切。要而言之,前举各类作品都是世俗大众日常佛教生活实践的产物,并关乎生和死的纪念性,常常呈现的是家庭(族)佛教信仰生活中的真实细节。而且,有人以游寺方式自寿(如汪懋麟),而冥寿更重仪式的庄严肃穆,多有安排在寺院者(如秦瀛、陈夔龙诗所示)。
3.师友之信
师、友在古代人伦关系中是有较大区别的,师道讲尊严,朋友讲诚信,不过,考虑到存在大量亦师亦友的社会现象,故本文在此一并论述。其代表作有苏轼《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留余,夜归,书小诗贺上》、程大昌《感皇恩·娄通判生日词》、程公许《上后溪刘阁学》(以金银字《金刚经》说偈)、释大观《寿平章秋壑师相》、敖文祯《文别驾佛诞日寿七旬》、袁宏道《五月十二日退如生辰,蒙以诗见示,聊述二章奏报》、曹学诠《七月朔日徐兴公直社九仙观,赋得定光塔,兴公诞辰也》、谭元春《寄孟诞先初度,时在兰阳》、彭贻孙《静因上人乞诗寿张道翁》、杨炤《师望生朝》、施闰章《冯相国生日同诸君移尊长春寺?坐》(公即席有诗,率尔和韵)、毛奇龄《益都夫子生日,与同门诸公共祝长椿寺饮次奉和夫子首倡原韵》、袁枚《望山尚书以七十生辰作相,仍督两江,奉贺四首》、赵翼《寿尹望山相公七十》、孙原湘《谢雪卿挽辞钱子霞姬人》、张祥河《戊申正月十四日,戚小蓉招集龙树院,是日为余生辰》、何绍基《王少鹤白兰岩招集慈仁寺,拜欧阳文忠公生日,分韵得“山”字成十绝句》、程颂万《送佛翼生日归湘》等。从这些诗词看,叙写“师友之信”时,作者、寿主对待佛化生日的态度,总体说来是肯定者居多。当然,也有个别固守儒家思想宗旨者评价不高,如在佛诞日出生陈衍的就对佛教不屑一顾,其《为刚父题唐人写经卷》即说“吾同佛生日,视佛亦平平。恶杀似萧衍,膜拜殊未能”[36]185。
本类作品的创作场域,往往与唱和特别是临时性的诗社唱和有关。如施闰章、毛奇龄之诗,皆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二者所说冯相国指冯溥,其生于十二月初五,庆寿时往往有结社唱和,且庆诞常置于长春寺,并伴有设斋、诵经等佛教仪式性活动,尤其施闰章所说“纶扉一代推元老,文字三生共宿缘”[24]第67册,553,更点出了冯氏在佛寺生日庆生唱和的社会文化背景,即后者以宰辅之尊来组织佛化生日的文学活动。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袁枚、赵翼之作。二人所说尹望山,是指满洲镶黄旗人章佳氏尹继善,其人乾隆三十年(1765)终于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封疆生涯而赴京任文华殿大学士,故有“相公”之称,并在其生日那一天(即佛誕日)得到当朝许多名家的祝贺。又如,敖文祯、曹学佺、彭贻孙、张祥河之诗,表明为士大夫庆生的僧俗结社,在一定意义上模仿了东晋慧远的(白)莲社。当然,社主往往是寿主;参会僧人若不善诗,则可向社中名士乞诗代作(如彭贻孙《静因上人乞诗寿张道翁》所示),僧人之用,在于主持或亲自实施庆生法会的仪式性活动。再如,清代有一类“名贤生日祭”的雅集,诗家、词家常以前代大文豪或名士的冥诞(即特殊的“佛化生日”)为由而举办各种诗词唱和,著名者有寿苏(东坡生日)、寿黄(山谷生日)、寿白(香山)、寿欧阳(文忠)、寿陆(放翁)、寿朱(熹)、寿王(阳明)、寿顾(炎武)等名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寿苏会,但无论哪一种,大多会涉及佛教行仪或佛禅思想。
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特定时期为特定人物所作的佛化诗词中也存在“谀寿”的情况,仅南宋而言,那些为秦桧、韩仛胄、贾似道等权相而作的寿词就因“颂美”过度而变味了。甚至某些著名诗僧也未能免俗,像释大观《寿平章秋壑师相》开篇即把贾似道比作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谓其降生(时在嘉定六年,即1213年农历八月初八)得到了过去佛威音王如来的授记,中间又谓其出世是为了续如来慧命,是“君臣道合”的最高典范,在其治下黎庶安乐,河清海晏,故立生祠是人心所向,其救苦救难之功已超越观音,等等,读来令人作呕。虽说明清两朝士大夫中也有类似的“谀寿”之作,但都比不上大观这一首,即使从佛教政治伦理看,也没有比这首更僭越的了。
当然,更常见的是写师友的日常生活,语淡情深者也不少,如苏轼、程大昌、程公许等人之作。尤可注意的是,袁宏道、谭元春、孙原湘,则涉及寿主(或冥寿者)家的女性(含姬、妾)形象,此说明晚明以降在特定的社交空间男女授受不亲的情况较宋元有较大改进。
三、佛教文学史意义
佛化生日这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它在佛教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多种意义,但我们认为最突出的有两点:
(一)从生死观言,佛化生日虽以佛教为中心,却可兼容儒、道
本来三教生死观迥然有别,传统儒家因“未知生,焉知死”而注重“此在”的现实人生而追求“三不朽”,道教多讲“长生久视”而成仙,佛教则强调“无生(涅槃)”而超越生死轮回。顾名思义,佛化生日诗词,其生死观自然是以佛教“无生”为中心,但自唐玄宗御注三教经典《孝经》《老子》《金刚经》并产生持久影响后,无论知识精英、普通百姓,他们对三教思想大多取用并尊或融合发展之态度(而且,这也是历史常态,个别皇帝的佞佛佞道与灭佛,则另当別论),具体到生死观,亦然。若粗略分之,有两大类型:
一是纯以佛教为中心者,我们可称为“单一型”。它往往和佛教仪式相结合,如苏轼为妻子王闰之生日而作《蝶恋花·泛泛东风初破五》所写放生,杨巍《诞日寓回河寺兼赠慧上人》所说八关斋[12]第1285册,524,金兆燕《小山和尚于十二月十九日张东坡先生像,邀同人作生日会,余以事未赴》[24]第344册,231所讲无遮大会等,皆如此。
二是以佛教而兼容儒、道者,可称“兼容型”或“混合型”。此类作品数量远超“单一型”,情况也更加复杂:从创作主体言,有兼写三类生日诗词,如陈著《长儿深生日,集经语示之二首》[13]第64册,40100《寿雪窦寺炳同长老》《真珠帘·寿孙古岩》[14]第4册,3843,即可分别称为儒化生日诗、佛化生日诗、仙化生日词,然从陈氏全部传世的寿诗、寿词看,其总体思想倾向是三教融合。有在佛寺、道观轮流过生日者,如赵怀玉《三月五日余生日也,早过红梅阁,流连至暮,即事有作》便云“六十与七十,流光等闲换。六十初度憩僧庐(扬州准提禅院),七十生朝游道观。红梅落尽红桃开,玄妙玄都理同贯”[24]第419册,452,可见赵氏对佛化、仙化生日并无轩轾之分,认为二教思想是可以贯通的。有在道观结社庆生却书写佛教内容者,如曹学佺《七月朔日徐兴公直社九仙观,赋得定光塔,兴公诞辰也》等。从文本表现言,同样有“单一型”的儒化、佛化、仙化之生日诗词,但更多的是三教“混合型”和佛、道兼融型:前者如无名氏《沁园春·寿长斋友人》[14]第5册,4766用“仙”“康节(指理学家邵雍)”“多宝如来”喻寿主,查慎行《恭祝皇上万寿诗四章》[37]1174-1175其一则写雍正五年(1727)皇帝的五十大寿(农历十月十三日),他把胤禛比作圣、仙、佛的化身;后者如徐枋《寿华山檗翁和尚七十初度四十韵》“西竺传优钵,南华说大椿。如来无量寿,奚止八千春” [15]第1404册,311,袁枚《书制府六十寿诗》其一“筹添海屋千枝外,佛坐莲花一瓣中。此日嫦娥来进酒,清江浦即广寒宫(公防秋汛,驻节清江)”[38]第4册,905等,用典皆佛、道对举,而王彦弘《郑超宗母七月七夕七旬初度》“无生悟后即长生”1,则直接把佛教涅槃与道教长生混同了。
(二)从题材言,佛化生日极大地拓展了女性佛教生活与信仰的深广度
在汉传佛教史上,记录女性人物的宗教历史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以佛母摩耶夫人、佛姨母大爱道、胜鬘夫人、龙女、净光天女等为叙事对象的汉译经典(含品题)及其注疏;二是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中以女性为主体的造像记、抄经记、发愿文、结社文等;三是历代比丘尼传、善女人传及部分涉佛文学作品(如诗、词、小说、戏剧等文体)。其中,第一类人物完全是印度式的,后两类则以中土女性为主,中国化色彩浓厚。当然,极个别形象也会发生巨变,如观音菩萨就是转男(印度)成女(中土)。
唐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降,生日习俗不但关乎等级森严的众多尊神,也关乎每位人世间的匆匆过客,帝王将相、贩夫走卒,皆可庆生,虽有规模与社会政治影响方面的大小之分,却都以纪念、感恩、宣扬人伦规范为宗旨。而在表现女性佛教生活与信仰的创作题材中,佛化生日诗词的深广度最值得深究:一则无论高低贵贱,人人都是母亲怀胎十月出生,即使佛祖也不例外;二则只有在该类题材中才较彻底地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较充分地展示了男女平等。此类诗词,不胜枚举:如邹应博《鹧鸪天》其一“天遣丰年祝母龄。人人安业即安亲。探支十日新阳福,来献千秋古佛身”[13]第4册,2982,李昴英《念奴娇·寿王守母》“有母能贤,生儿如此,总是前身佛”[13]第4册,3643,即把自家母亲、王太守之母分别比作千秋古佛、过去佛,其实都在暗示儿辈的非凡出身和现世成就;帅机《寿岳母六十》“堂开绮席初秋稔,历转花轮化日长”[19]第135册,300,用花轮即莲花(华)轮作喻,以半子身份祝愿岳母像佛法常新一样寿命绵长;黄汝亨《封孺人丘母张夫人七秩寿诗》“忧忘萱草人难老,业净莲花佛共生”[15]第1369册,665,其对同年好友曾城丘公元配张氏七十大寿的祝语,既是张夫人平生佛教信仰的写照,更是对后者“无量寿佛”式的长生祷告;释函可《赠王三》“长斋礼绣佛,但祝慈母年”[39]卷3,53,释今无《蔡母祝词》“兰孙满地无余事,绣佛惟闲爇马芽”[19]第186册,411-412,宋琬《李镜月太夫人寿》“手制芙蓉服,心通水月禅。盈阶看玉树,半偈礼金仙”[24]第445册,585,陈恭伊《外姑湛节母冯太君八十大寿,时旌表初至二首》其一“佛龛勤礼六时灯” [24]第125册,430,号称清初八旗第一才女高景芳《寿刘奶奶二首》其二“序当良月物华新,贤母欣逢设帨辰。供佛橘香初采摘,拒霜蓉晚更精神”[24]第204册,628,乾嘉时期才女熊琏《满庭芳·题〈松鹤图〉》“白头甘淡泊,长斋绣佛,茗碗炉香。把禅机,参透世味冰凉”1等,其描述的女性佛教生活与信仰的长斋(包括斋僧)、烧香、供佛、参禅等内容,无不和男居士一样,只有绣佛才是多数女性特有的方式。但她们绣出的佛像,同样可供居士观想禅修,甚至是夫妻同观,如前引孙原湘《生辰日》其二即如此。而姬、妾一类地位低下的女性,其在佛化生日诗词中没有丝毫地被贬低(如屈大均就写有《生日示姬人》《姬人墨西氏生日赋以赠之》等多组作品),这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大乘涅槃思想完全契合。
[参考文献]
[1]陈开勇.南朝民歌《四月歌》所反映的民俗佛教内容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47-50.
[2]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与生日称庆[J].中华文史论丛,2011(4):127-164.
[3]李童.汉唐佛诞节仪考述[C]//段玉明.佛教与民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高楠顺次郎,等.大正新修大藏经[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6]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郭绍林.论隋唐时期庆生辰[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3):89.
[8]董诰,等.全唐文[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任万平.千秋万寿祈长年:以帝后生辰为令节的考察[J].紫禁城,2015(10):22.
[10]李昉,等.太平广记: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唐圭璋.全宋词:简体增订本[Z].北京:中华书局,1999.
[15]《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集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苏轼.东坡乐府编年笺注[M].石声淮,唐玲玲,笺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7]彭定求,等.全唐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劉林魁.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9]《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Z].济南:齐鲁书社,1997.
[21]周裕锴.作为“忌日”的生辰:一个独特词汇中蕴藏的佛教理念与民俗信仰[C]//项楚.新国学:第六卷.成都:巴蜀书社,2006.
[22]释惠洪.石门文字禅校注[M].周裕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23]前田惠云,等.大藏新纂卍续藏经[Z].石家庄: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
[24]《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5]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26]何吾驺.元气堂诗集[Z]//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文献》“集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27]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全清词:顺康卷[Z].北京:中华书局,2002.
[28]邓濂.巽庵集[M]//裴可仁,编.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十辑,第39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29]王策,王时翔.香雪词钞·小山诗余[M].段晓华,戴伊璇,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0]孙原湘.孙原湘集:下[M].王培军,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1]陈衍.元诗纪事[M].李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2]屈大均.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M].陈永正,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33]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宋版碛砂明版嘉兴大藏经[Z].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
[34]张弘至.万里志[M]//沈乃文.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35]洪亮吉.洪亮吉集[M].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36]陈衍.陈石遗集:上[M].陈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37]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下[M].周劭,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8]袁枚.袁枚全集新编[Z].王英志,编纂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39]释函可.千山诗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Buddhist Birthday:Poetry Cre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content of folk Buddhism is extremely rich. Among them, one of the folk customs closely related to ancient social life is Buddhist birthday, which mainly refers to birthdays celebrated by Buddhist activities (including immortal birthday). As far as the cre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is concerned,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one is from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the other is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emperor and his important officials. While the latter expands to various social classes and forms three enduring themes of human ethics and morality, namely, loyalty to officials, love of family members, and trust from teachers and friends. The outstand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kind of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ife and death, although Buddhism is the center, it can integrat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it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female Buddhist life and belief.
[Key words] Buddhist birthday;poetry creation;folk Buddhism;history of Buddhist literature;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