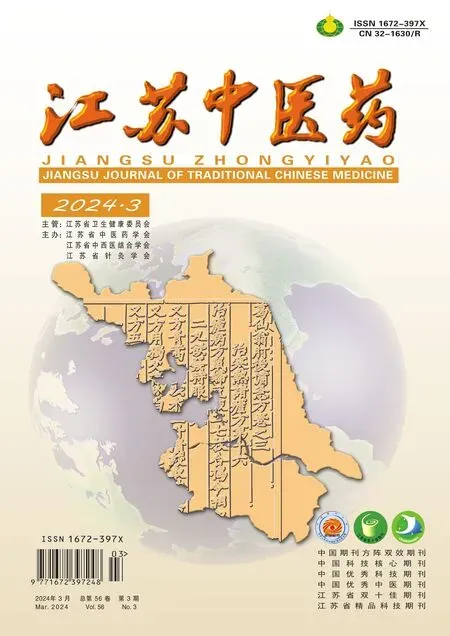胃肠肿瘤的中医防治与证治特色
刘沈林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南京 210029)
胃肠肿瘤是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高发肿瘤[1]。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发展,肿瘤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然而如何进一步预防肿瘤的发生、降低术后复发转移率、减轻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改善晚期患者的生存状态,依然是临床难点问题,任重道远。
当前,在中西医结合的背景下,充分发挥中医、西医两者的互补作用,显得尤为必要。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肿瘤的基本法则,肿瘤难治难愈,临床通常需要对病情作出分析评估,根据防癌重点、肿瘤分期,以及病程中的标本缓急,确立相应的治疗目标,提出具体的证治方药[2],这是重要的临床路径。胃肠属中焦,笔者结合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在扶正祛邪的大法之下,借鉴脾胃病理论和治法特色,灵活运用相关方药,确能在胃肠肿瘤的防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
1 癌前防变,未病先治
胃肠肿瘤的预防重点是癌前病变。癌前病变虽然还不是癌,但有可能发展为癌,作为一般消化系统疾病常因缺乏特异性症状而被忽视。胃肠镜结合病理检查,能够为临床提供诊断信息。如慢性萎缩性胃炎伴中、重度异型增生(内瘤变),以及胃腺瘤性息肉、肠道腺瘤性息肉伴异型增生(内瘤变)患者,被视为患癌风险人群,应及时治疗并定期复查[3]。对于癌前病变,目前尚无特效预防药物。一般胃黏膜轻、中度异型增生者,常可用中医药治疗而获得改善或逆转。中医药也可用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后的疗效巩固,可获得较好的效果。对于引起较多患者担忧的“肠上皮化生”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这是细胞的老化现象[4],于胃镜检查结果中普遍存在,目前看来对癌前病变的诊断价值不大。
万全在《幼科发挥》[5]中云:“胃者主纳受,脾者主运化,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故调理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也。”张元素曰:“壮人无积。”胃肠位居中焦,故临床防癌多从脾胃入手,通过调治,改善胃肠道内环境,增强防变内生能力,除患于萌芽状态。对癌前病变的用药,以辨证治疗效果为好,由症入手,结合辨病。如胃部病变:(1)中虚气滞,胃胀纳差者,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健脾理气;(2)虚寒胃痛,悠悠不已者,以黄芪建中汤加减,温中补虚;(3)肝胃气滞,脘胁胀痛者,以柴胡疏肝散或香苏散加减,疏肝和胃;(4)郁热犯胃,反酸、烧心、呕苦者,以左金丸、温胆汤加减,泄肝苦降;(5)胃阴不足,虚嘈、口干、舌红者,以益胃汤或一贯煎加减,甘凉濡润;(6)瘀阻胃络,胃脘刺痛、舌质暗紫者,以桃红四物汤或失笑散加减,化瘀和络。此外,若有幽门螺杆菌(Hp)感染,症见胃热、口苦、苔黄者,可加黄芩、仙鹤草、蒲公英等清热解毒之品。这里需要注意,Hp感染也并非全是“热毒”,尤其是抗感染治疗后13C呼气试验反复阳性,也有脾虚胃寒证者。至于常用的防癌中草药亦可适当选用。较长时间服药者,可采取“服三隔一”或“隔日一服”的方法。总之,胃以和为贵,以降为顺。
结直肠癌绝大多数是由肠道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及时摘除并防止息肉复发是治疗的重点[6]。古代文献并无息肉的病名,亦无具体治法方药。据观察,本病临床表现有三类:无症状(体检发现)、慢性泄泻、大便秘结。中医认为“久泻脾虚”“四季脾旺不受邪”,故笔者临证对肠道息肉伴久泻或便溏者,治以健脾化湿或温阳运脾,以参苓白术散为基础方,随证加减。如脾湿偏重者,加猪苓、泽泻或车前子;脾阳不振者,加制附片、炮姜、肉豆蔻。“六腑以通为用”,对肠道息肉伴大便困难者,可据虚实而治,实秘当清热通便、顺气导滞,虚秘宜滋阴养血、温通开结。常用方如麻子仁丸、六磨汤、润肠丸、济川煎等,均可随证化裁组方,以改善肠道功能,减少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的接触吸收。
近年来,笔者以乌梅丸化裁治疗肠道腺瘤性息肉,取得良好效果。该方出自《伤寒论》,由乌梅、黄连、黄柏、附子、桂枝、细辛、川椒、干姜、党参、当归等十味药物组成,其特点是酸、苦、辛杂味相投,寒热并用。方以乌梅为君,用量独重,据古籍记载乌梅能“蚀恶肉”。在该方的基础上加用莪术、炮山甲、炙僵蚕、败酱草等,可增消瘀、化痰、散结之力。此外,根据患者体质的寒热偏颇,也可适当调整辛温与苦寒药物的配比。
案1.蒲某,女,62岁,浙江宁波人。2014年4月17日初诊。
主诉:息肉反复发作3年。患者3年前结肠镜检查示:结肠多发腺瘤性息肉,较大的3枚大小分别为1.2 cm×0.8 cm、0.6 cm×0.8 cm、0.5 cm×0.6 cm;病理示:绒毛状管状腺瘤伴轻中度异型增生。予内镜下摘除。此后每半年至1年复查1次,息肉反复再生,反复摘除。2014年3月复查肠镜,仍为多发性腺瘤,最大者1.0 cm×0.8 cm,伴中度异型增生。诉有便秘史20余年,服一般通便药无效。刻下:腹部胀满,便秘难下,数日一行,食欲欠佳,舌苔淡黄厚腻,脉滑带弦。西医诊断:结肠多发腺瘤性息肉。中医诊断:癥瘕;病机为痰气郁滞,湿浊极重,腑失通降。治以通阳泄浊、降气疏腑。方选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处方:
全瓜蒌15 g,薤白10 g,桂枝5 g,法半夏10 g,陈皮6 g,枳实10 g,厚朴10 g,莱菔子15 g,决明子30 g,大腹皮15 g,莪术10 g,炙僵蚕10 g,炮山甲10 g,败酱草30 g。14剂。水煎,每日1剂,分早晚2次温服。
2014年5月5日二诊:药后患者大便已通,肚腹松快,然舌苔浊腻化而未净,食欲不振。予初诊方去厚朴、莱菔子、大腹皮,决明子和败酱草均减为15 g,加木香6 g、砂仁3 g(后下)、炙鸡内金10 g、炒谷芽15 g、火麻仁15 g,14剂。
此后以二诊方略作加减,间断服药,大便一直正常。2015年5月复查肠镜,未发现肠道腺瘤性息肉,后随访息肉未再复发。
按:该患者肠道多发腺瘤性息肉伴异型增生,属于肠癌前病变,因摘除后多次复发,精神压力较大。询知有20余年便秘史,腹部胀满不适,其舌苔黄浊厚腻,服一般通便药少效。辨为痰气郁滞、腑失通降证,方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加减,以通阳泄浊、降气疏腑而取效。方中全瓜蒌甘寒滑利,宽胸降气,决明子润肠通便,薤白辛苦,桂枝辛温,温通散结,四者辛滑相伍,开结润下;法半夏、陈皮理气祛痰;枳实、厚朴、莱菔子、大腹皮降气宽中;莪术、炙僵蚕、炮山甲化瘀散结;败酱草清热解毒。二诊时患者大便已通,腹部松快,然舌苔浊腻化而未净,食欲不振,故去厚朴、莱菔子、大腹皮,而加木香、砂仁健脾调中,炙鸡内金、炒谷芽消食开胃;因决明子、败酱草偏于苦寒,有败胃之嫌,故分别去之或减用量,加入甘平之火麻仁润下。
脾虚内生湿浊,腑失通降的便秘,临床较为多见,单用攻下或滋润之剂,均不适宜。笔者借鉴前人经验,取治疗胸痹之瓜蒌薤白半夏汤化裁,效果甚好,主要取其“下气”和“散结”之功,别具一格。对于便秘型肠道腺瘤者,治秘通便,分辨证型,以通为顺,是为临证可取之法。
2 术后巩固,需清余邪
胃肠肿瘤的首选治疗方案是手术,根治性切除有可能治愈癌肿。也有因肿瘤条件或全身基础疾病,比如病期较晚或心、肺、肾等主要脏器有严重合并症者,为缓解病情、减轻肿瘤负荷,而采取姑息性手术切除病灶。复发或转移是肿瘤的危险事件,如进展期胃癌术后复发转移率较高,5年总生存率仅为35%,Ⅱ、Ⅲ期患者的复发高峰一般在术后2年左右[7-8]。手术、化疗结束后至出现复发转移,临床有一个抗肿瘤药物治疗的“空窗期”。因此,这一阶段的中医药治疗被认为是预防术后复发的重要时点,也是中医临床研究的热点。
中医认为,肿瘤术后出现复发转移,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手术损伤气血,正气不足,免疫功能下降;二是体内“余邪”未尽,化疗失败,癌毒脱漏、隐伏、流窜,成为复发转移的核心致病因子。因此,正虚与余邪是术后需要兼顾的两个方面。
正虚方面。术后患者多有面色少华、神疲少寐、头晕心慌、纳差腹胀、舌淡、脉细等虚损表现,治疗宜补益气血、调理脾胃,可选归芍六君子汤、归脾汤等化裁。药如:黄芪、党参、白术、茯苓、淮山药、熟地黄、当归、白芍、陈皮、木香、砂仁、炙甘草等。黄芪为“补气之长”,在无内热或舌苔厚腻的情况下,可以重用而起“补气托毒”、增强免疫之效。此外,由于胃肠根治性手术后1个月需要化疗,因此中医的术后调理也包括对化疗毒副反应的处理。还要补充一点,胃肠手术后,脾胃受损,纳运功能减弱,无论是补益药物,还是膳食营养,均应调补有度,注意“滋腻碍胃”“甘能满中”之弊。术后由于盲目“过补”而致消化不良者,临床见之较多,故提此为鉴。
余邪方面。所谓余邪是指原发肿瘤虽然切除,但逃逸的癌细胞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可以再次转移至腹腔淋巴结或远处脏器。所以不仅要补虚调理,还要兼顾祛邪解毒,剿抚兼施。肿瘤祛邪之法,诸如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祛痰化湿、以毒攻毒等,这已为大家所熟知,此不赘述。笔者拟重点谈点个人对肿瘤瘀血的认识。
“腹内肿块即是瘀血”,但当癌肿切除,腹腔已无有形之物,或察之亦无舌质紫暗、腹部刺痛之征,此时是否还要用化瘀法,化瘀药物又如何选择?对此学术界历有不同观点。临床研究表明,胃癌手术病理标本提示神经、脉管有“癌栓”形成者,是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重要因素[9]。这种带有癌毒性质的瘀血,由于形态微小,瘀停络脉,不但影像学检查无法诊断,用一般中医的四诊方法更是难以辨识。因此,借助现代医学病理学检查,能够为术后中医运用肿瘤化瘀法提供微观辨证的依据。据考历代中医文献,肿瘤化瘀以三棱、莪术二味为多,认为此二味“治积聚者良”。《本草备要》提出:“宜于破血行气药中,加补脾胃药。气旺方能磨积,正旺则邪自消也。”笔者按此组方,用于胃癌根治术后抗复发转移,取得良好疗效。至于清热解毒之类的抗癌中草药,如石见穿、白花蛇舌草、石打穿、半枝莲、菝葜、蜀羊泉、肿节风,以及以毒攻毒的露蜂房、土鳖虫、蟾皮、蜈蚣、全蝎、守宫等虫类药,均可适当应用。在诸多药物中,究竟哪一种药物抗癌效果比较好,目前尚无定论,一般配伍2~3味即可,同时需注意有毒药物的用量和副反应。
案2.秦某,男,64岁,安徽马鞍山人。2015年8月4日初诊。
主诉:结肠癌术后化疗后,严重腹泻2个月。患者结肠癌ⅢC期,于2015年1月17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结肠癌切除术,术后接受6个疗程化疗。2个月前开始出现严重腹泻,每日水样便20余次,体质量下降8 kg,肠鸣如雷,腹部畏寒隐痛。多次输液、服止泻药物少效。刻下:腹泻频频,形体消瘦,面色㿠白,身倦乏力,畏寒肢冷,舌淡、苔白,脉濡细。西医诊断:结肠癌。中医诊断:肠蕈;病机为脾阳已虚,固涩无权。治以温阳运脾、涩肠止泻。方选附子理中汤合五苓散化裁。处方:
炒党参15 g,炙黄芪15 g,炒白术15 g,猪苓15 g,茯苓15 g,制附片5 g,炮姜5 g,肉桂5 g(后下),乌药10 g,煨木香10 g,淮山药15 g,炒薏苡仁15 g,泽泻10 g,炙升麻3 g,炒诃子10 g,半枝莲15 g,石打穿15 g。14剂。水煎,每日1剂,分早晚2次温服。
2015年8月20日二诊:患者服药后大便次数明显减少,仍腹痛即泻,时有不禁,不能出门,肠鸣辘辘,面色㿠白。予初诊方去半枝莲、石打穿,加赤石脂30 g、禹余粮30 g,14剂。
2015年9月4日三诊:腹痛肠鸣较少,水样便已止,食欲改善,大便仍未成形,每日2~3次。舌淡、苔白,脉细弱。再拟补脾温阳、扶正祛邪。处方:炒党参15 g,炙黄芪15 g,炒白术15 g,炮姜5 g,肉豆蔻6 g,淡吴萸3 g,茯苓15 g,淮山药15 g,陈皮6 g,木香5 g,砂仁3 g(后下),炙甘草3 g,三棱10 g,莪术10 g,半枝莲30 g,石打穿30 g。14剂。
药后症状进一步改善,后多次复诊,中药长期服用。随访5年,肿瘤未见复发。
按:该患者结肠癌中晚期,手术伤正,加之化疗引起胃肠功能紊乱,以致严重腹泻,体重下降明显。诊时患者水泻多日,腹冷隐痛,形体消瘦,舌淡苔白,脉濡细。初诊辨为脾阳不振、滑脱不禁,故治以温脾涩肠止泻为先,选用附子理中汤合五苓散化裁组方。方中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淮山药补脾益气;制附片、炮姜、肉桂温中祛寒;猪苓、茯苓、泽泻、炒薏苡仁分利水湿,“利小便,实大便”;煨木香、乌药行气止痛;炙升麻升提脾气;炒诃子涩肠止泻;半枝莲、石打穿抗癌解毒。二诊时患者水泻次数明显减少,但仍有腹痛即泻、面色㿠白,伴有肠鸣辘辘,仍属脾阳虚衰、运化失常所致,故暂去苦寒之半枝莲、石打穿,加赤石脂、禹余粮以增收涩止泻之功。药后患者腹泻旋得控制,腹痛缓解,食欲增加。三诊时继以温阳运脾、扶正祛邪以巩固术后疗效。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肠癌术后得以康复。从该案可以看出,在肿瘤的不同分期,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或扶正或祛邪,灵活用药,用之得法,是取得疗效的关键所在。
3 晚期扶正,善治为要
晚期患者,癌细胞扩散,多处转移,“因实致虚”,以致气血虚损、脏器功能逐渐衰竭。对此中西医均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其治疗目标是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黄帝内经》提出:治病用法,勿犯“虚虚之戒”。意在告诫医者,对于虚损之证,不可再用泻法,免使虚损的病体更加虚羸。晚期肿瘤患者因过度化疗或以毒攻毒而使病情恶化者,临床屡见不鲜,应引以为戒[10]。
《景岳全书》云:“若积聚渐久,元气日虚,此而攻之,则积气本远,攻不易及,胃气切近,先受其伤,愈攻愈虚,则不死于积而死于攻矣。……故凡治虚邪者,当从缓治,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清代程钟龄更提出“积聚末期”宜“善治之法”,认为“必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胃为人身至宝,“得胃气则昌,失胃气则亡”,“胃气一败,百药难疗”,古哲先贤在长期实践中总结的经验,确有深义,此对当今晚期肿瘤的治疗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因此,晚期癌症宜缓图慢治,调补脾胃,扶正固本,确为中医治疗的有效方法和明智选择。笔者临床体会,有以下情况者,以不用或少用攻邪之法为妥,应以扶正为主,争取和合共生、带瘤生存。
(1)患者形瘦骨立,气短乏力,头晕心慌,动则喘汗,舌淡脉弱,不耐攻伐者。
(2)抗肿瘤药物的姑息性治疗未能缓解病情进展,且不良反应较重,出现呕吐、腹泻、胀满、腹水、杳不思食者。
(3)因化疗毒副反应,骨髓抑制,白细胞、血小板等显著减少,贫血明显,肝功能异常;或引发原有基础疾病加重者。
此外,苦寒之品易于伤脾败胃,晚期患者阳气虚衰,消化功能薄弱,不耐重剂,故药多量重的“大处方”亦常于病无补,用药当有分寸,过犹不及。
还应指出,中医的扶正之法并不是一般的支持疗法,更不是简单的多用补药,临证必须遵从“虚则补之”“辨证施补”的原则。实践表明,呆补、蛮补、滥补的效果并不理想。晚期患者的扶正之策,重在调整患者的功能状态,为缓解病情创造条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如补气健脾、益气养血、滋阴生津、温补助阳等法,均可根据寒热虚实和气血阴阳的虚损随证而立;在方药选用上,诸如补中益气汤、归芍建中汤、当归补血汤、人参养荣汤、十全大补汤、益胃汤、左归丸、右归丸等经典名方,则可灵活选用,随证加减。如果治疗得法,对于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一般收效都较明显,这是中医治疗的长处,现代医学暂无可企及。
案3.陈某,女,58岁,江苏南京人。2018年10月25日初诊。
主诉:腹痛2月余。患者2018年3月初因胃脘不适行胃镜检查,病理示胃腺癌,遂于2018年3月19日于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行胃癌根治手术,术后病理分期提示为ⅢC期,予XELOX方案化疗6个周期。2个月前自感腹痛,于2018年8月19日复查CT发现:盆腔肿块3.2 cm×2.8 cm,少量腹水,考虑为肿瘤转移。后调整为IP化疗方案,转移瘤又增大至4.5 cm×3.0 cm,肿块触之质硬,小腹疼痛较剧,颇为痛苦。刻下:腹部疼痛难忍,口服止痛药后仍难以缓解,面色㿠白,畏寒肢冷,食欲不振,舌质淡、边有紫气,脉细涩。西医诊断:胃癌。中医诊断:癥积;病机为正虚寒凝,瘀毒内结。治以温补扶正、化瘀定痛。方选理中汤、暖肝煎、三棱煎化裁。处方:
炙黄芪30 g,炒党参15 g,炒白术10 g,炮姜3 g,肉桂5 g(后下),小茴香5 g,三棱10 g,莪术10 g,木香10 g,乌药10 g,川楝子10 g,延胡索10 g,炙五灵脂10 g,炙甘草3 g,石见穿30 g,白花蛇舌草30 g。14剂。水煎,每日1剂,分早晚2次温服。
2018年11月9日二诊:药后自觉腹部有温暖感,腹痛显著缓解,再拟扶正固本、温通化瘀。予初诊方去炮姜、小茴香、川楝子、白花蛇舌草,炙黄芪30 g改为生黄芪60 g,加当归10 g、白芍10 g、鹿角片10 g、菝葜30 g,14剂。
2018年11月23日三诊:患者诉硬块触之觉软,腹部微痛或不痛,已停服止痛药。继予二诊方调服巩固。
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半年后,再次复查CT:转移癌肿缩小至3.5 cm×2.3 cm,病情未继续进展,症状改善。
按:该患者胃癌ⅢC期术后腹腔转移,病属复发晚期。因肿块疼痛较剧,虽服止痛药而效果渐微,颇为癌痛所苦。根据病史以及诊时苔脉形候分析,患者盆腔肿块质硬痛楚,化疗不效,虚弱肢冷,舌质紫气,脉细涩,其本乃正气已虚,其标为血瘀寒凝,故治以温补扶正、行气化瘀。初诊方中炙黄芪、炒党参、炒白术、炙甘草补气健脾,炮姜、肉桂、小茴香温经散寒,乌药、木香行气止痛,三棱、莪术逐瘀消癥,川楝子、延胡索、炙五灵脂行气化瘀止痛,石见穿、白花蛇舌草解毒抗癌。二诊时患者腹痛已显著缓解,遂去炮姜、小茴香、川楝子、白花蛇舌草,改炙黄芪为生黄芪60 g以增补气托毒之力,加当归、白芍养血和血,鹿角片温补散血,菝葜解毒消肿。经中医药治疗,患者病症改善,带瘤生存。据临床所见,晚期胃肠肿瘤,以老年阳气不足者多见,而热毒实证者较少。血属阴,得温则行,得寒则凝;气属阳,得寒则聚,得温则散。故癥积表现气滞血瘀而腹冷胀痛者,以温通化瘀效好,而苦寒凝滞之品效微,临证可参。
4 辨证康复,病心同疗
肿瘤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是我国癌症防治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医的肿瘤康复疗法,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整体观念为基础,以辨证施治为方法,促进肿瘤患者走向康复的辅助措施,其中包括心理调摄、营养膳食、合理运动等内容[2]。
这里笔者重点讲述关于患者心理状态对肿瘤治疗与康复的影响。“信心是半个生命,悲观是半个死亡”,这句话用在肿瘤患者身上并不为过。因此,医者在治疗肿瘤的同时,还应重视对患者的心理疏导。《灵枢·师传》曾提出精神疏导法:“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其意思是说,对某些重病患者要通过说理分析、开导安慰,使之了解病情,树立信心,消除焦虑、苦闷、悲观、紧张等不良情绪,从而积极配合治疗,这样有利于疾病的向愈和病情的转化。药物能治疗疾病,但药物不是万能的,在诊病过程中,医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温和而同情的语言,本身就是一剂缓解病症的良药。重视情志因素,疏导心理压力,病心同调,历来是中医对待和处理疾病的一个重要方法。
5 结语
胃肠肿瘤高发,临床难点较多,治多棘手。癌前未变当阻断,既病术后防复发,晚期扶正宜善治,已是肿瘤防治的基本理念和对策。实践表明,聚焦中西医结合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借鉴和运用脾胃病的某些理论和经验,对于预防胃肠肿瘤的发生,降低术后复发转移,改善晚期生存状态,促进患者康复,具有显著作用。
肿瘤的特征是局部病变引发全身反应,机制复杂,难治难愈,目前并无一方一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肿瘤导致的所有问题,因此根据肿瘤本虚标实的病机特点,突出辨证施治的个体化治疗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医处理肿瘤的主导方法。扶正祛邪之法的运用,需要注意肿瘤的分期,病情的标本缓急,以及遣方用药的宜忌。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如何从实践中来,到临床中去,很多问题还在探讨的路上。
此外,晚期胃肠肿瘤日益增多,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目前化疗或联合靶向药物、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比较普遍,对部分患者缓解病情有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也相应增加,影响治疗效果。中医如何根据不同的毒副反应,采用相应的治法,研发有效方药,减少“药毒致损”,确是当下发挥中西医互补作用的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报道目前尚不多,中医药治法丰富,应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期待有更多的治疗经验和研究成果回应临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