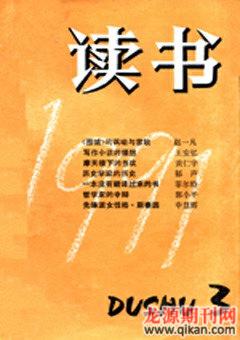哲学家的申辩
郭小平
学者圈中人,对晚年退隐似乎并不特别的忧心忡忡,不过是免掉更多不愿作或不甚愿作的俗事而已,也不必担心会失掉那些本来就不曾有过的种种殊遇,反倒能如梁实秋先生说过的:“完全摆脱赖以糊口的职务,作自己衷心愿意作的事情。”对某些哲学家而言,或许还有另一层慰藉:脱离开尘世的喧嚣烦恼,会更专注于心灵的倾听与诉说。所以,不仅晚年失意的海德格尔愿去人迹罕至的托瑙山林归隐,沿林中小路,吟荷尔德林,诵老子,静心守护着思(诗)的澄明意境,连卡尔·波普这样“功德圆满”、受世人青睐的哲学家,退休后也宁肯深居简出,大多时候呆在美丽宁静的潘恩小镇,在惬意的独处中自然地生出那些清新隽永并且注定会流芳后世的文字来。
我相信,新近读到的波普这篇“我如何看哲学”便是在这种意存高远、浊气全无的心境中写成的。视批判为哲学之精髓的波普,无论如何写出的文字都不会是“与世无争”的,但毕竟已不见年轻人带有的浮躁之气,更多了些老者的明达与透辟。坦率说,读黑格尔或胡塞尔于我并非一件轻松事。经历几番抓耳搔腮,自以为有几分所得,此时方领略到读书的那份苦中乐趣。而读波普,则不同,阅读的快感是直接当下的。老年的波普,其文如行云,恬淡,随物附形,行止自如,属于好读的哲学书那一类。
研究了一辈子哲学,再回过头来回答“我如何看哲学”,答案绝不至于如学生赶考时那般乏味,浅显的说理中的确有精言至论。
谁是哲学家?
古时,不分中外,“哲学家”常常与“圣贤”、“智者”这类名字连在一起。久此以往,在世人眼里,“爱智的人”(“哲学”一词的希腊文原意即爱智)似乎也就成了别一类人。这种“精英”意识在被称作“哲学家”的人自己那里还有了进一步的膨胀。譬如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曾经提出睿智的、有学识的哲学家应当充当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不仅如此,柏拉图还是“学院(园)”哲学的创始人。自此,哲学越来越成为特定的一类人相互之间才能交流的题目,哲学的语言也日渐艰深,非专门家而不能懂。
波普是这种哲学“精英”观的反对者。当然,无可否认,学院哲学家现在已成为一种职业,但他们只是一类哲学家。在更宽泛也是更本来的意义上,“一切男人和一切女人都是哲学家”。在波普看来,伟大的哲学之于哲学家,并不同于伟大的绘画之于画家或伟大的音乐之于音乐家。离开画家和音乐家,伟大的作品便无从谈起,而“伟大的哲学都是在全部学院哲学和职业哲学之先便有了的”。西方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东方的老庄哲学,或许都是这方面的明证。就此而言,波普更为赞同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他不承认自己以哲学为职业,更没有随“我是一个哲学家”而来的睥睨一切的优越感。他不好为人师,却又乐意在任何场合与碰见的任何一个人讨论哲学。波普指出,自柏拉图起,妄自尊大便成了哲学家的职业病。而他本人的感觉却正正相反,“我甚至觉得,我是一个职业哲学家这一事实于我是一个严重的立案:它是对我的一个指控。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过失,同时像苏格拉底那样,为自己作出申辩。”
与近现代蓬勃兴起的科学相比,哲学的声誉绝对不佳。今天,科学家完全不必为科学是否有资格存在去殚精竭虑地论证,因为科学自身的巨大进步及其现实效用就是其存在权力之不容置疑的证明。艺术和文学的景况也还算差强人意,至少它们还具有由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所决定的“使用价值”。惟有哲学,“科学之科学”已成昨日故事,学术殿堂里的第一把金交椅早已旁落。职业的包含着专门化语言和技术的哲学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自不待言,即使在职业哲学家圈内,对哲学存在的理由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拒斥”、“终止”、“放逐”一类呼声时有所闻,有性急者已作出了“后哲学时代”、“后现代文化”的预期。今天,哲学的存在本身已成为一个含有深蕴的首要哲学问题。
对学院哲学的不佳声誉,波普给出的解释倒也简明:怪它自己做得不好。即便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也犯下了一些重大原则性错误。波普举出了四位:首先是前面提到过的柏拉图,他提出了“精英”说。不仅如此,他在《法律篇》中竟然还发明了一种类似后来的集中营的机构,专用于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强制性“洗脑”。另一位是大卫·休谟。他主张理性应是激情的奴仆,而在波普看来,人类的唯一希望恰恰在以理性来节制激情。第三位是斯宾诺莎,他主张理性主义。但他的极端决定论主张包含着一个伦理学上极为危险的引伸,即人可以不为他的糊涂行为负责。最后是康德。他企图纠正休谟对理性的排斥和斯宾诺莎危险的决定论,却一无成功。波普的解释也许并不深刻,不过联系到哲学家在今天谈如何为自己辩护,他的见解就有意思了。他认为,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已将今天哲学家应当申辩的要点说出来了:哲学家并非无所不知,他的智慧只在于他不以不知为知,而是以不知为不知。如此说来,哲学家在世上的职责不过是提醒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知。哲学家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职责是批评,对那些自命不凡的“行家”、“专家”(也包括职业哲学家自己),对那些一言九鼎的王公贵胄,对那些遗忘了生活之真义的芸芸众生。向他们揭露出他们的无知与不智,让他们明白自己原本也有许多渺小之处。哲学家不是英雄,他恰恰应当劝人们放弃英雄崇拜。哲学家作此种申辩,那无疑首先就得承认自己以前未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的确是做得不好。
说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意思是指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些哲学“偏见”去生活的,尽管他或她本人或许对此并无意识。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是哲学的,那就是他或她必定要采取一种态度来对待死与生。有人认为生并无价值,因为到头终不过一死;亦有人认为生之价值正在于有死,倘若无限地生下去,生也就是无所谓的事了。有人成天练气功,寻灵丹妙药,恨不能长生不老;亦有人反过来视生为畏途,视死却如回归家园般地坦然。当然人们的哲学“偏见”还远不止于生死观一项。不过,采取某一种态度,并不等于对它作过透彻的思考——学院哲学或许由此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它需要对那些流行的、主宰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已经上升为理论的或者永远也不会上升为理论的种种观念作批判地考察。如果没有哲学家对良知的召唤,善与恶就会莫辨,法西斯也会成为正人君子。但无论如何,哲学家不是超凡脱俗的至圣先师,而是如苏格拉底所说,是与无数男男女女共同相处,和他们交谈,向他们提问题,检查他人也检查自己的一介书生。
哲学不是……
对一个卓有成就的哲学家来说,“哲学是什么”依旧是个难于说清的问题。每一种独特的哲学主张肯定都与一种对哲学的独特理解相关。由此可以设想,一百个哲学家必定有一百种对哲学的理解。波普列举了一系列曾经时兴过或眼下正时兴而他自己又不满意的对哲学的见解,标之为“我不如此看哲学”:
一、“我不把哲学看作是解决语言学难题的一项工作。”——这是针对分析哲学家的。如石里克就曾提出过,哲学的任务是对说话方式和表述问题的方法进行逻辑分析。由于波普的著作《研究的逻辑》(一九三九)(后来的英文版易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最初的出版被收入了维也纳学派石里克等人主编的“科学世界观论文集”丛书,有许多人以为波普至少曾经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为伍过。普波在本文中声明:“我从来不是持逻辑实证主义见解的维也纳学派成员”。他认为,由于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是反形而上学的,还是反哲学的。在他们那里,真正的哲学讨论不过是在说一些“无意义的”话,许多不易把握但又十分严肃的哲学命题或问题被归之于由于语言的误用而产生的谜。波普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争论是一个大故事,非三言两语能说清。不过,波普的这一见解总是对的: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因为每一个人心都面对着真正哲学的乃至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问题即使不能得到完全圆满的回答,也有加以讨论明了的必要。设若当年每个中国人都经历过一次关于“英雄”“领袖”问题的真正“苏格拉底”对话,后来文革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极虔诚极投入地去充演一出荒诞闹剧中的各自角色了。
二、“我不认为各种哲学学说是一些艺术作品,是一些匠心独具、夺人魂魄的世界图画。或者是一些描述世界之机智乖巧、不同凡响的方法。”——这种批评更是广有所指。当今许多哲学家,都已然放弃哲学家作为真理之追求者的使命。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工作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致力于消解传统哲学的真理主张。远在上世纪末,尼采便预言:“虚无主义正站在门口。”(如德里迈提出的,尼采工作的主要特征便是对形而上学的不信任和对“真理”、“意义”之价值的怀疑)上帝一死,合理性思想也不复有一个永恒稳固的基础。如此,任何理性的系统不过是一种劝说(persu-asion),逻辑不过是修辞学,形而上学不过是充满隐喻的神话,传统理性的主客二元对立一旦被取消,真理与谬误之间的严格界限也不复存。隐喻的发见使哲学与文学、艺术已不再是泾渭分明。就此而言,波普是极其“传统的”,他认为伟大的哲学家不会像艺术家那样致力于美学的追求。哲学家永远是真理的奴仆。
三、“我认为哲学不是由这样一些理智大厦组合而成的,在这些大厦中,一切可能的观念得到尝试,真理或许会作为一种副产品而被揭露出来。”——波普相信,过去的伟大哲学家总是怀着奉献真理的庄重和热诚来奉献自己的哲学的,其间绝没有仅仅“玩”点儿概念戏法一类的漫不经心。
四、“我不认为哲学是澄清、分析或‘解释概念、词或语言的一种尝试。”——在这一点上波普也是一位固守着“传统”的老派人物。他只将概念或词视作人类借以进行表达和交流的工具。他不以为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反对时下颇为流行的重“意义”的哲学。
五、“我不认为哲学会使人变得聪明。”
六、“我不把哲学看作一种理智的治疗手段。”
七、“我不以为哲学是学会如何更清楚或更准确地表达事情。”
以上诸条是针对人们对哲学的日常见解而发的。其实,哲学的“智慧”与小巧的“聪明”并非一回事。在许多时候,读哲学非但不能解惑,还会让人越来越糊涂。
八、“我不把哲学看成是一种尝试,它为那些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会出现的问题之解决提供理论基础或概念框架。”
九、“我不将哲学看作时代精神的表达”——波普明白指出他反对的是一种黑格尔主义观念。他对黑格尔似乎有很深的成见。在别的地方他甚至声称黑格尔算不得一个哲学家。我总以为他对黑格尔的理解和批评不免有些肤浅。譬如以前那篇在西方颇为著名的批评辩证法的文章(“辩证法是什么”)便是如此。他从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出发得出结论,“一种包含着矛盾的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是毫无用处的”,(见《猜想与反驳》中译本456页)并以此来批驳辩证法,似乎尚未进入到辩证法的本来意蕴之中。所以他的“胜利”只是堂·吉诃德或中国的阿Q式的。这次亦然。时代精神的内涵远非“时尚”所能包容。哲学家不应追逐“时尚”,甚至应该反对“时尚”,这本来不错的意思放在这里总让人觉得有些离题太远。
不论你是否赞同波普先生,他所道出的这种种“不是”都可以引出你关于哲学的“是”与“不是”之诸多联想来。
“批评是哲学的血液”
“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热忱,那我就没有理由做一个哲学家。”波普的自省足以令许多自以为是在搞哲学的人汗颜。早在两百年前,英国哲学家乔治·巴克莱就提到过一种他称之为“渺小哲学家”(minutephilosopher)类型的学院哲学家。他们只满足于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卖弄一些雕虫小技(minute criticism of minute Points),对许多宇宙论、人类知识、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方面的“大”问题却无所意识更不会用心去思考。“在文字的滔滔洪流中,伟大的思想已不复存。”(波普语)——一切人都是哲学家,但这些学院哲学家或许是最蹩脚的一类。还有一类“新潮派”哲学家也是波普所看不上的。“许多刊物的编辑们似乎认可了他们的傲慢自负和粗制滥造,——这在过去的哲学写作中还不曾多见——以之为思想上勇于追求和富于创新的证明。”这也成了一种时尚。追逐这一时尚的人似乎忘记了苏格拉底的忠告:我们对自己的所知原也是很无知的。在波普眼里,这两种“哲学家”都还未能为自己的存在作出有力的辩护。
哲学家是真理的追求者,但哲学家并不能成为无须再去追求的真理占有者。以往的一些哲学家从神赐起源来论证自己理论的真理性或不可更改性,而在另一些哲学家那里,则是从认识的源泉(感性或知性或理性)来作此种保证的。神赐起源属子虚乌有,能保证我们的知识永远不犯错误的绝对源泉和基础并不存在,故而我们并不能断定我们手中的“真理”永远都不会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批评,一种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批评。今天的哲学家已没有必要耗费精力为知识建造一个永恒不变的底座,而应该永不失发现并消除错误的期望和热情。真理不是一座纪念碑。它是一条流淌的河。在九曲回转中,你并不知道下一道弯后面是旖旎风光还是险滩恶浪,尽管也许你有理由相信它会通向大海。哲学家永远也无法让真理成为一座座静止而又一览无余的小山丘。他命定只能做承担着风险、奉献出自己的河上船工。只有保持批评精神,真正的哲学才不会为浅薄的时尚所淹没,理性才不会成为柏拉图式“智者统治”的根据,才不会成为权力的附庸和点缀。
和其他哲学家的理论一样,波普自己的见解也不无可批评之处。但毕竟波普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怀着奉献真理的严肃认真来构造自己的体系,但又充分准备接受各种批评,不排除有一天会有某种更好的理论来替代它的可能。无论哲学还是艺术或科学,其真正起源与神话、宗教并无二致,都与人类解释自己及周围世界的渴望相关。如果说它们有某种进步(也许这种进步只是相对于某些特定的目的或价值取向而言的,并没有终极的意义),则显然是与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自我批评和合作的批评分不开的。波普在另一篇近文中,(“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对艺术与科学中的创造性批评亦有精采的论述。具体的例子他提到了海顿的《创世纪》,舒伯特放弃《未完成交响曲》,还有贝多芬将《合唱交响曲》发展为《欢乐颂》。
即便对一学院哲学家而言,其全部“理论主张”之构筑于其上的基础或许也如在常人那里一样,是某种非理论性的“信念”。如波普就说过:“我的理性不是自足的,而是依赖于对理性态度的非理性信仰……这种信仰就是相信人类理性;或者一言以蔽之,我相信人”。(“乌托邦与暴力,”《猜想与反驳》)这种信仰决定了波普与时下许多人更为倾心的文化悲观主义论调格格不入。他选择了文化乐观主义。不过我以为,只要不是“赶时髦”,文化悲观主义未尝没有一些深刻之处。伯特兰·罗素认为,,人是聪明的,又有些邪恶,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电视、火箭和核弹,但我们所达到的道德和政治水准却不能保证我们安全地支配控制自己的巨大理智力量。波普的看法是,人本性是善良的,只不过有些愚蠢,这个世界的麻烦在于,我们渴望改善自己生活的道德热忱由于我们的愚蠢而误入了歧途,各种宗教的或狭隘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狂热便是例证。乐观主义的理由在于,毕竟有限的愚蠢比邪恶要容易改变。(“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主义的观点”)两者之间,我更属意于罗素的见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诸多灾难与不幸的的确确与我们自己人性的种种阙失相关。见利忘义,文过饰非,以力服人,以己度人,趋炎附势,苟且偷生,都非单单的愚蠢所能搪塞的。人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所创造的科学昌明不仅为人类未来幸福提供了希望,同时亦增加了人类毁灭自身的危险。毕竟,人之由文化、传统赋与的习性改变起来比人通过“明事理”而变得聪明要难得多。所以,批评的哲学家还有着伦理这一维的使命,他至少应在讨论和批评中使人们明了,我们道德上的不完满之处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这样,并非圣贤的哲学家在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些事情可做。
KarlR.Popper,How I see philosophy,in PHILOSOPHYIN BRITAIN TODAY? Groom Helm Ltd,Beckenham,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