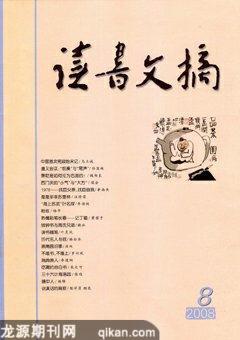钱钟书与周氏兄弟
谢泳一
一
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应当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可以成立的。鲁迅和钱钟书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太重要,一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和他发生关系的,就是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没有间接关系,也极少有在文章中不曾提到过鲁迅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从不提鲁迅的,钱钟书可能是极少的例外。
钱钟书不提鲁迅,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习惯问题,而是有意的选择,这种选择中包含了钱钟书对他所生活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在钱钟书眼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不高的。傅璇宗在《缅怀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钟书题写,他给钱钟书送去一本。钱钟书对傅璇宗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是钱钟书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本书中还引述了吕思勉的《读史札记》。虽然后来有人专门就此说法考证,钱钟书其实并非“唯此两处”。但从钱钟书对傅璇宗说话的口吻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是一个自觉的选择,选择即是判断。
二
既然钱钟书不愿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提及鲁迅,或者周氏兄弟,研究者总要找出原因和事实。因为钱钟书生活的时代,要完全避开周氏兄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一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相近,二是早年也曾有过间接的文字关系。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入,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有许多创获,而这个领域恰好和周氏兄弟重合,所以在非要涉及周氏兄弟的时候,钱钟书的办法是暗指而不明说。李国涛在《钱钟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钟书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钟书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钟书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胡鲁之书都是名著,影响甚大,钱钟书都曾寓目,可能更多地是指鲁迅。
高恒文研究指出,钱钟书《小说琐证》开篇即引焦廷琥《读书小记》卷下一则笔记,《西游记》演比丘国事本《旧唐书•杨虞卿传》,而有“此可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按语。“周氏”即周树人,即鲁迅。此文发表于1930年的《清华周刊》第34卷第4期,可见作者看到的《小说旧闻钞》当为1926年版;查该书1935年版,虽然有所增加、改正,但钱钟书以为“可补”的这条材料并没有补入。
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一方面是避免直接提及鲁迅,非要提及的时候,尽量少说或者不说,而且谈锋中颇有深意。解读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钟书作品的一个角度,也是理解钱钟书心理的一个角度,注意这个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钱钟书很有帮助。
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从目前已见到的史料判断,钱钟书最早提到周氏兄弟是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第4卷第4期)。在这一期杂志的书评专栏中,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这一年钱钟书只有22岁,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虽然钱钟书在文章中对周作人的书先做了一个抽象的肯定,认为“这是一本可贵的书”,但在具体评述中,基本是对周作人看法的否定。在文章中钱钟书有一段提到:“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模型;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命,就是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
从一般常识上判断,钱钟书读书的时代不可能不读鲁迅的书,这篇书评只透露了一个信息,钱钟书是读鲁迅的。需要注意的是,就在钱钟书发表这篇书评不久,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1933年9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本书是中国早期文学史中较早对新文学和鲁迅有明确评价的学术著作。本书中对鲁迅的评价,很有可能是钱氏父子讨论的结果。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到鲁迅时说:“而周树人者,世所称鲁迅,周作人之兄也。论其文体,则以欧化国语为建设,……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幽默大师林语堂因时崛起,倡幽默文学以为天下号;其为文章,微言讽刺,以嬉笑代怒骂,出刊物,号曰《论语》;而周树人、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之流,胥有作焉。……树人《阿Q正传》,译遍数国,有法、俄、英及世界语本。《呐喊》、《彷徨》,弥见苦斗。张若谷访郁达夫于创造社,叹其月入之薄,告知‘鲁迅年可坐得版税万金以为盛事。语堂方张‘小品,鲁迅则视为有‘危机,谓:‘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谁还有闲功夫,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即要阅目,当有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用不着雅。”
钱基博对周作人的评价是:“阿英有现代十六家小品之选。自作人迄语堂,附以小序,详其流变;吾读之而有感,喟然曰:此岂‘今文观止之流乎?作人闭户读书,谈草木虫鱼,有‘田园诗人之目。然流连厂甸,精选古版,未知与‘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之渊明何如?苦茶庵中又不知有否‘田父野老之往还也?”
请特别注意这一段对周作人的评价:“语堂又本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取袁中郎‘性灵之说,名曰‘言志派。呜呼,斯文一脉,本无二致;无端妄谈,误尽苍生!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
本段行文及意思与钱钟书在《新月》杂志上评价周作人的观点完全相同,此点可说明钱氏父子的文学观非常接近,是父影响子还是子影响父可以再作讨论,但这个事实提醒研究者注意,钱钟书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来源,很有可能与他父亲有较大关系。
鲁迅很可能没有读到过钱基博的这本书,他只是在1934年出版杂文集《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剪贴了一篇《大晚报》上署名为“戚施”所做的《钱基博之论鲁迅》。本文对此书涉及鲁迅的内容有这样的介绍:“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召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
鲁迅对此文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以《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