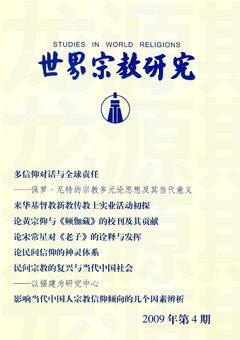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实业活动初探
近代西方新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播福音,从事经营性实业活动等所谓“世俗化倾向”长期以来是传教士讳莫如深的话题。但事实上自1807年新教入华以来,亦有相当部分的新教传教士因种种原因从事此类活动。他们一方面直接涉及地产、酒店、百货、商业贸易等领域,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以自养方式从事经营性活动,拓宽教会的收入来源。此外,部分传教士还尝试将实业活动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来使用,认为“实业工作将大力推进在华传教事业。”
关键词:近代来华传教士新教传教士实业活动世俗化
作者林立强,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近来国内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但更多涉及的是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以及在各区域的传教活动,而对于传教士所从事的实业活动或鲜有问津,或浅尝辄止。然而,历史事实是实业活动与他们的传教活动相始终。新教人华传教得到了西方商业机构及资本家的大力资助,在华期间亦有相当部分的新教传教士因种种原因从事经营性的实业活动。本文根据目前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试对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的实业活动做一鸟瞰式的分析与梳理,以求教于同行。
一
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人华伊始,即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开启了来华新教传教士个人从事世俗性商业活动的先例,而以教会为主体从事实业活动大约在19世纪末才初露端倪。实际上,通过实业活动达到自养乃至传教的模式,在新教海外传播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最早的新教组织。
18世纪新教各派中传教最活跃的是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 Brethren),他们派到加拿大拉布拉多(Labrador)的传教士以商人身份与爱斯基摩人做生意,把所赚取的钱用来发展传教事业。由于“摩拉维亚弟兄会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团体,几乎没有成员出身富裕。完全靠他们自己筹款很难支撑一个花费巨大的差会,也无法维持其众多的海外传教事业。”所以,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贸易同传教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他们必须携手共进,否则谁也不能单独生存。”1754年,摩拉维亚弟兄会派遣到南美洲苏里南(Surinam)的传教士在当地聘请了工人,并成立了以德国传教士ChristophKersten名字命名的公司(Christoph Kersten&Co;,)从事商业活动。贸易的收益促进了教会的发展,有学者评论说,摩拉维亚差会20年所做的传教工作,比英国国教与基督教会过去两百年所做的还多。
巴色会(Basei Mission)也非常注重通过实业活动进行自养与传教。1828年,该会开辟了西非的加纳(黄金海岸)为第一个海外传教区,“为了提供所属教育机构与传教工作稳定的物质支持,差会在1854年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划拨其部分利润以支持传教团。多年来贸易公司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据估计贸易公司每年可为传教团提供超过两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巴色会的第二个海外传教区是1834年开设的印度南部地区,“作为印度西南部地区最强大的教会之一,它成立了3个工业中心和7个分厂,拥有一家大型的出版社,并设立了生产砖瓦以及用来生产内衣、毛巾、织布、成衣等的工厂。”此外,染色、椰子纤维编织、制作坐垫、针织、刺绣等也是教会经营的范围。“1874年以来,巴色会在芒格洛尔(Mangalore)还拥有一家工程车间和一家现在已经交予当地基督徒管理的木工与家具制造厂。从商业意义上而言,教会经营的这些实业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其生产产品的质量上乘并行销印度各地甚至海外地区。实业的收益用于促进教会的传教工作”。
以上两个差会以及其他国家海外传教团体的实业活动经历,为来华传教士进行类似的探索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可资借鉴的先例。在福建实业传教卓有成效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蒲鲁士(William Nesbitt Brewster)坦言,在缅甸美国北浸礼会“引进实业上沉着而又实用的努力”;在印度英国圣公会1896年聘用“一个熟练的和有经验的平信徒”管理工厂的实践以及浸礼会泰卢固(Telugu)地区传道团的皮革工人在成立工厂方面的“成功经验”,使得他对实业传教的前景充满信心,并为他们“从兴办各项实业获得的净盈利中,除了给传教团留下一部分自由资金后,还可以分得红利”的成果所激励,称之为是“近年来我没有看到关于传教工作主题方面比这个(实业活动)更重要的意见了”。
事实上,当时在华新教常见的经济来源仍然是以差会拨款与教徒捐献为主,传教方式也是传统布道手段与医疗、慈善、教育等传教方法各行其道,由此看来,实业自养与传教方式的出现,还应有其外部与内部的原因。
教会从事实业活动,还与教会内部逐步增大的自养方面的压力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新教的经费来源与天主教存在较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天主教通常通过经营地产等经济活动来维持教会的开支,而来华新教几乎没有这个渠道。19世纪中叶,随着在华传教事业的拓展,再加上新教差会主要所在国英美的经济状况趋于恶化,维持教会运作的资金开始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促使来华传教士把自养问题摆上议事日程。虽然围绕自养的争论此起彼伏,但笔者发现在历次传教会议文件或发表的关于自养的言论中,未见涉及教会应该通过经营实业活动来解决教会自养的字眼,而在如何对待“信徒”捐赠方面的条文颇多。如传教士应要求和鼓励信徒参与自养;信徒应该依能力捐资参与教堂的建设;主日学校应该适当收费;当地传道人的薪酬可以由信徒承担等内容。传教士们认为,造成中国信徒对自养态度消极的原因之一是生活贫困,如何提高信徒的收入,是实现自养的关键所在。而当时中国信徒大多来自下层,显然让这些教徒负担本地教会的开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故此笔者认为,历次传教大会上虽没有明确提出把实业活动作为自养的一种方式,但强调了由信徒本身承担教会的部分经费是实现自养的重点。考虑到当时信徒的实际经济状况,那么对教会而言,除了尽量多的吸收富人入教之外,改善现有贫困信徒的经济状况就成为唯一的出路了,而兴办实业无疑是改善信徒经济状况的最有效途径之一。由于传教士与教会从事经营性的商业活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此,教会兴办实业的尝试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现有材料看,实业活动实践以山东与福建地区开展的最具代表性,其他省份亦有涉及。正如蒲鲁士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教会的实业活动在非洲或印度已经过了讨论的时机,但“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中国总是落后的。现在她正赶上来了。”
二
在谈及教会涉及的实业活动前,有必要对传教士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实业活动进行一番考察。从遥远的国度来到中国,传教士们除了身陷中西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漩涡中外,还要受到经济状况、身体健康、教会之间矛盾、教团中的人际关系等的困扰,其中经济一直是制约传教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传教效果和来华传教士
“军心”的主要原因。因此,来华传教士接触实业更多是出于自养、生存的需要。新约圣经中保罗就是以织帐篷为业赚取的钱来养活自己,并支持门徒的福音工作。“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Wiiliam Carey)接受了印度一家靛青工厂的经理职位,并开垦农场以谋生。由于在华传教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早期传教士生存处境十分恶劣,他们或接受国外商人的资助,或成为来华商业机构的长期或临时的雇员,如马礼逊任东印度公司翻译达23年;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K)受雇于英商查顿的洋行;林乐知(Young John Alien)从事煤炭、粮食、棉花买卖;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担任美商琼记洋行(Mercantile House)的茶商翻译,直接参与福州茶叶贸易等例子不在少数。这种“个人自养”的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得到了部分传教士同事以及差会的理解或默许。随着中国门户的进一步开放,加之传教士具备熟悉中国本土情况、精通当地方言这一特点,使得他们一度成为当时在华外国商业机构争先恐后雇佣与合作的对象。于是,一部分传教士介入实业的规模和范围渐渐超出了“个人自养”的范畴,开始把实业作为盈利的手段。房地产业是传教士较早介入的实业领域。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于1863年将在工部局任翻译时的原始积累三千多银元用于购买土地。是年,恰逢英美两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人口剧增,地价日益上涨,房地产成为极为有利可图的投机对象。晏玛太从此发迹,并醉心地产投资。由于“自从1870年以来,地产一业,尤其在上海,是外人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他在1877年重理传教士旧业后仍持续经营所熟悉的地产业务,获利颇丰。美国南部浸信会海雅西(J.B.Hat-twell)在上海谋生期间,也曾做房地产生意赚钱。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接触各方人士众多,旅店业也是他们投资的重点。在天津的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殷森德(JohnLnnocent)在与外侨接触中发现当地没有一个专供外人寓居与娱乐消遣之处,遂于1863年用纹银600两购买了19.9英亩的地块,创办了利顺德大饭店(Astor Hotel)的前身——“泥屋饭店”。再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都约翰(Liddell John Duff)约于1910年在江西庐山创办仙岩饭店(Fairy Glen Hotel Co,Ltd.)。在经营过程中他发现庐山长住牯岭千余人外侨之日常生活消费均依靠牯岭市场,于是他又创办专为外国人服务的“都约翰办馆”,供应各种食品及日用品,获利颇丰。此外,庐山、鸡公山、莫干山等天然避暑胜地所具有的潜在商业价值也陆续被传教士发现:莫干山于1891—1894(一说是1894年)年间由美国传教士佛利甲发现;庐山于1894年由英国传教士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发现;鸡公山于1903年由美国传教士李立生(DanielNelson)、施道格(Knut Sorensen Stokke)发现。三大名山随后都陆续进行了所谓的避暑别墅项目的“差异性”商业开发,盈利颇丰。
更有甚者,部分传教士因与所属教会意见相左,出现了自立门户经商甚至弃教从商的现象。如安临来(L.M.Anglin)原属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因与浸信会在信仰方式上产生分歧,遂自办“神召会教堂”,设“阿尼色弗之家”(Home of Onesiphorus),辅以实业;马茂兰(James Mamullan)从内地会辞职后,成立“仁德洋行”,从事花边等生意;内地会“剑桥七杰”之一的司安仁(Stanley Smith)从该会辞职后到山西晋城创立自立会,并出资开设商店,以求使信徒达到温饱。他先是在天津开设总店,组织货源。后在长治、洪洞一带开设分店,其字号叫“光道成”。长治光道成商店中全用本地基督徒,每天早晚有读经祈祷,礼拜日关门停业作礼拜。他说:“我不求给我交利润,除你们维持生活外,略有积余可奉献给教会使用,但一定要讲信用,讲道德,不能有欺骗行为使基督的名受损。”规定交易要货真价实,明码交易,童叟勿欺。“光道成”在长治一带可说是唯一的新颖时髦商店,闻名上党各县,盛兴一时。福开森(John CalvinFerguson)于1897年正式向差会提出辞去传教士和汇文校长职务,两年后他经竞拍以廉价买下英国人丹福士创办《新闻报》的全部产权,此后他担任《新闻报》监督(董事长)长达30年,并将其发展成与《申报》齐名、全国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1929年,福开森将其股份悉数售出,获利七十万元。费信诚(Robert Joseph Felgate)于1900年向内地会递交了辞呈,只身来到莫干山避暑地,“开旅馆、商店,甚而廉价收买山地,经营房地产业,牟取暴利”。传教士从事实业活动中“成就”最大也最有争议的非英国的李德立莫属,甚至有学者怀疑其传教士身份,暗喻李氏是看到传教士在拿地方面享有特权而假借传教士身份经商的。李德立在中国最大手笔莫过于1886—1929年间对庐山牯岭的开发,他强租庐山长冲等地大量土地,成立牯岭公司(Kuling Es—tate),赢取暴利。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北戴河外国人在海滨之团体组合名录上赫然出现:“庙湾会主其事者,即在牯岭最初购地之李德立”的字样,在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内还保存着当时李氏与华商土地纠纷的档案。他于1898年9月至1922年12月分数次共永租土地156.11亩,分号出售,再次获得巨利。李德立后被当时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之一的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Brunner Mond&Co;)任命为中国区的第一任总经理,这一任命也改变了传教士只能在商业机构充当翻译、向导等配角的惯例。著名民族资本家范旭东领导的永利制碱公司曾与李德立领导的卜内门洋碱展开激烈的竞争,打破了卜内门企图独占中国市场的局面,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传教士从事实业活动与同期外国人在华实业活动相比有较明显的不同:其一,传教士所从事的行业与一般外国资本投资的所谓“热门”行业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传教士进入实业领域多为个人投资行为,无财团背景,除了从事一般外人都青睐的投机性行业(如房地产)外,主要进入的行业大都是与传教士身份相符或者与其传教经历密切相关的规模较小、收益不大的行业。其二、传教士需要到各地进行所谓的“拓荒”布道,尤其是深入内地或偏僻地区的特点,使他们易于发现其他外人不易发现的商机。如当外国资本集中于沿海城市投资沿海商业城市地产时,他们却在内地发现了避暑地开发的商业价值。其三、传教士在日常的传教活动中,可以广泛的与中国民众接触,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为他们从事具有当地经济特色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代山东地区花边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传教士以个人身份从事实业活动的成功,仅对传播福音而言,客观上是起到促进作用的:相当部分传教士在赚取利润之后,将所得用于传教事业,增强了教会的实力,如
殷森德利用他在利顺德大饭店的部分营业所得,用于建造教堂与发展教徒,其所在的英国圣道公会在天津的势力大增。1875年南浸礼会在上海建筑教堂,共花费3300元,晏玛太一人独捐2500元。而传教士发现并开发成功的庐山与莫干山、鸡公山、北戴河四大避暑地,亦成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活动中心。
三
以教会为主体从事实业活动起初完全是考虑到自养的需要,目的是增加教会以及所属慈善机构的收入,改善传教士的生活水平与健康状况,而非是出于传播福音的_种策略。如山东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积极支持其长婿海尔济牧师在烟台教会推广编织花边手工业,以求教会自养;山东泰安安临来的“阿尼色弗之家”经营收入可解决全院生活费用的一半;河南新安由内地会瑞典籍传教士鲍跃渊创建的实安慈惠孤儿院有自己的实业生产基地,其收入用于补贴院内开支。清光绪年间,福建邵武美部会兴闽地方教会开办实业之先,由医师福益华(Edweerd L Biss)首倡开办养牛场,初衷是养牛取奶,补充营养,以治疗传教士因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根据相关契约显示,最初饲养奶牛主要集中在邵武东市一带,我们从下面这份教会契约中依稀窥见大致情形:
立断卖乾地空坪契字人何鸦娘子、蒋金福等,今因要钱使用,情将祖手遗下乾
地空坪二处,均坐落牛栏区大路边,坐北向南。上至余宅,下至李宅,右至大路,
左至美部会。何姓计方员二十七丈、扣银九两三钱一分五厘,蒋姓计方员七丈,扣
银二两四钱一分五厘,欲行出卖。请问房亲人等俱各不愿承交,次托中引进到美部
会,近前承买为业。当日经中三面言定,二姓乾地共计方员三十四丈,时值契价共
扣银十壹两七钱三分。其银立字之后,一并交足,分文未欠。
从收集到的其他教会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在民国四年以前,美部会购置用于搭建牛栏的民产,主要集中在东市遵道坊登云桥一带,此后则移至南郊外下南寮一带,并陆续在城西一带发展。当时福益华在东门“三公桥”附近办置奶牛场,养殖的奶牛有二百多头,雇佣人员达20余人,还把牧场发展到水北小西门头(今火车站),日产牛奶300多公斤。
从现存资料看,教会早期开展的实业活动的商业经营性特征并不明显,但其出现无疑有利于教会获得当地民众的信赖与认可,提高了教会经济的自养自立水平,使得一些地区出现“教会大富,捐款亦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为教会的发展赢得相对和谐的环境。
随着传播福音方式的愈来愈世俗化,一些传教士发现如果把实业活动与教徒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使得信徒致富,可以达到博得民众对教会的好感、提高教会在民众中的形象之效果,有利于福音的传播。于是,马茂兰夫妇、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蒲鲁士、安临来、司安仁等开始尝试将实业活动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来使用。马茂兰夫人提出应该用“在中国已有了一些实用性的实业经验,作为福音传道工作的一种方法”,她坚信“实业工作将大力推进在华传教事业。”安临来则认为孤贫院的孩子在长成并有一技之长之后,“就离开这里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之中,另外一些孩子就来接替他们在这里的空位。这样,这些(基督的)工人就像涓涓细流一样,年年流入中国社会……”。
山东烟台的马茂兰是在实业传教实践中成绩最突出的传教士之一。从1895年到1902年短短的7年间马茂兰夫妇将花边业的业务发展壮大,同时自设烟台工艺会(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开展独立的传教工作。1902年11月,马茂兰在《教务杂志》上撰文,总结了他以实业为手段传播福音这一新的传教方法,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提出实业传教理论。在文中,他以花边业为例,提出了实业传教成功应具备的三个条件:“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兼具教学与传播福音的性质,否则,传教的意义就会失去;其次,应该自养,或者以自养为目标;第三,理想的状况是,当没有外国人的监督管理下,这项工作仍应该被延续。”他非常强调实业机构应具备传播福音功能,要求每一位参与花边生产的女子都必须参加宗教仪式,“周日有两场礼拜,每周有两次”,教大家朗读圣经。如果“没有参加晨读的女孩是不允许做下午的花边工作。如果她上午待在家里,剩下半天的时间就必须学习。”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他却认为要遵循市场规律,淡化企业的宗教色彩,指出“我们不希望人们是因为我们的花边与差会工作有关才购买的,而是由于它的质量上乘,我们销售的货品都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进行的”。这种以企业化进行管理,以产品的质量与服务去争取市场的意识,是保证其实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
与马茂兰相比,同在山东传教的仲均安设计的实业计划要比前者“宏伟”得多。作为一名曾在竭力鼓吹实业建设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身边担任助手耳闻目染多年、来自英格兰的成功商人,他选择棉纺织业作为实业传教的项目。为此他不惜从棉纺织业的源头入手,撰写《山东试种洋棉简法》,该文对早年山东引种、推广洋棉起到启蒙作用。但该计划却未能取得象马茂兰花边业那样的成功,主要是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棉纺织业要求资金量虽不大,但对中国商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数目,而投资商“一旦把目光转向那些更容易获得利润的行业,而不再重视我们这个行业了,那么我们就将很难再得到其他赞助者的资金支持”,于是他的主要工作变成“被迫去寻找更多的资金赞助”。马茂兰则不然,一方面花边生产所需要的经费比棉纺织业少得多,另一方面始终强调自养的他坚持使用自有资金,他坚持“虽然可以从朋友与支持者中获得许多的经费,但我们认为最好不要这么做”。其二,花边属于手工业,容易被心灵手巧的妇女掌握,而棉纺织业含有相当高的技术含量,“中国人有对机器的复杂性以及一切新鲜事物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在他们内部采用这种新式的工具。”其三,要全力投入、经常性的管理。如马茂兰前期就曾经因为疏于管理而导致其中一个工厂“不那么成功”,仲均安也常常由于“我的教学任务,使得我无法继续迄今的监督任务”。最后,他无奈的指出,“我不得不认为由传教士完成的世俗事业或商业项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9世纪8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胶东地区缫丝业为他再续实业传教的梦想提供了契机,他决定以养蚕业为切入点,因为“养蚕业对于中国来说是熟悉的行业,在每个丝织业发达的省份里,每个农民家庭都能理解养蚕这一行业”。他似乎还在对在棉纺织业的失败心有余悸,“和其他可计划的项目相比,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不会和劳动力的使用发生冲突或者完全占据劳动力。”在1898年8月,他将自己从欧洲所购的两纸箱蚕卵送到了“12家可靠而又聪明的基督徒家庭”进行试验,结果很成功。于是他联系了欧洲的蚕卵供应商,“在1899—1900年的冬天里,由在华传教士从欧洲预定的蚕卵很快就会送达”。没有资料显示此项实业计划后来是否成功,但他提出还应该把实业范围扩大到非信徒,认为“不把善良的非基督教徒们包括在我们范围里也是毫无道理的”的理
念,与马茂兰坚持的“学校也教许多校外的人做花边”不谋而合。这种把实业传教的范围扩展到非信徒中的做法,是对福音传播工作最好的诠释。
除了上述直接利用实业活动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外,在实践中,传教士更多的是把实业活动与教育传教手段结合起来,作为教育传教的一种辅助手段来使用。蒲鲁士在这方面颇有成就,他认为仲均安在山东实业传教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实业教育重视不够所致,正确的做法应该“深入基层,并从我们教会中的儿童与年轻人开始”。蒲鲁士进一步提出借助实业教育来倡导和发展实业的设想,认为“教会学校比其他任何异教徒学校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这是因为没有实业部门和学校相联系,”只有让教徒掌握“商业技巧、热情、知识,这是放在我们使徒手上的饼与鱼,蒙基督的祝福,它将使千百万华人得以饱足”。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浦洛克(J.C.Pollock)也十分强调设立实业课程的必要,认为只有“速为学生筹备手工,列为学课,”学校才能成为“完全之学校”。北京崇实学校校长来仪庭(William H.Gleysteen)认为“工艺科之设立,其裨益约可分三。裨益于教育一也,裨益于社会二也,裨益于经济也。”据来仪庭统计,当时教会实业涉及的行业包含木工、铜工、铁工、洗衣、织布、造毯、编席、制褥、刺绣、家庭役使、罐头制造、打字、排字、印书、制糖、造烛、制皂、制鞋、制刷、筑路、筑室等诸多领域。
实业传教由于涉及教会的敏感话题——经济问题,情况较之其他传教手段要复杂得多。除了妥善处理与差会之间的关系外,还必须具备与世俗经济无异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如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敏锐的市场意识;引进懂得经营管理的专门人才;充足的资金投入等。20世纪初,部分教会开始组织教友募集资本创办企业的尝试,如“奉天长老会,设有工艺厂一所,由魏牧师经理厂中经费。以东三省中国教会捐集之一万元作资本金,其经理魏牧之薪俸,乃自西国筹给也。”1911年福建邵武美部会组织实业内利公司,由教会与教友共同投资,修造水坝。1923年美国传教士苏雅各(James E.Skinner)在福建永安集资成立“永安昭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修建水电站。个案中以蒲鲁士创办的实业最具代表性。他募股集资,设电报局,办碾米厂、制糖厂、肥皂厂,后“在黄又设织布局,建面粉厂,置行水机,以代水车……尝置汽船,增高桥梁,行驶城涵间,以利交通。”名噪一时,成为当时在闽实业传教成功的范例。
四
与天主教侧重于地租收入等单一的经济活动相比,新教传教士的实业活动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与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的联系更为密切,并且大多兼具自养与传教两种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教士实业活动一方面增强了教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信徒的拥护,对近代中国教会的自养自立以及本色化的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它作为诸种传教策略中最具有“物质化倾向”的一种崭新的间接传教方式,迎合了当时民众对改善经济状况的迫切需求,促进了福音的传播。此外,在教育传教中大量增加实业活动内容的举措,适应了近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亦为当时的中国工商界培养了大量的实业人才。
新教鼓励人们通过经济活动发财致富,加尔文(John Calvin)等认为一个人在现世对财富的积累是对上帝最大的荣耀和赞美。上述说法似乎是针对福音传播的受体而言,对如何看待作为福音的传播者(即传教士)积聚财富方面却语焉不详。在华传教士虽然有一部分是支持实业活动的,但亦有传教士以及差会对此颇有微词。郭显德支持的编织花边讲习班就遭到教会保守派的反对,差会下达指令:凡奉差遣来华的传教士不应替教友打算生计。福州部分传教士甚至上书美国总会要求再次规定“所有在华传教士都必须完全与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脱离干系,无论这些商业活动是暂时的,抑或长期的。”在对待所谓的“物质化倾向”的态度上,不论是“基要派”代表人物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还是“自由派”代表人物李提摩太、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等也都众口一词的加以反对。看来确有部分传教士把精力放在通过实业活动获取利润上而忽视了其传播福音的本职。那么,实际上从商的传教士人数究竟是多少呢?在笔者查找那些曾经从事实业活动传教士的资料时,无论是个人还是传记的作者都对涉及主人公实业活动的内容讳莫如深,我们只好从相关人士的描述中寻找答案。美国公使田贝称:“事实上在中国的传教士,从事各色各样的职业是非常普遍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曾说:“余更孰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如果说上述二人的说法是带有某种偏见而夸大其词的话,那么费正清教授与之豪人的相似说法却不可不引起重视。他认为早期数量“多得不成比例”的传教士担任了“世俗职务”(其中包括经商),结果导致“传教士的身份模糊不清”。可见,确有部分传教士没有经受住“玛门”的诱惑,利用当时来华外人的特权身份,通过实业活动达到仑人积聚财富的目的。与某些传教士在教会以及商界、政界、文化界频频受到尊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多数从事实业自养与传教的传教士处境不佳、举步维艰的情形,不禁耐人寻味。
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列强入侵,经济上遭受的侵略尤甚,人民对伴随不平等条约入华的基督教抱有抵触心理。因此,传教士们的实业活动常常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如晋城巨绅马骏在晋城开设的煤油庄因司安仁“光道成”影响其收入减少,于是马以“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不能兼营商业”的条约为依据,请求陕西省政府勒令其停办;费信诚在莫干山因“拆毁民房,赶走乡人”,被山民所杀;朱启钤在北戴河创设“公益会”与西人抗争,逐步夺回被西人侵占的国家主权,此后北戴河与庐山、鸡公山、莫干山避暑地的行政管理权陆续被中国政府收回等等。由此可见,传教士们从事的实业活动应以不损害民众与乡绅的利益、不侵犯中国的主权为底线,否则被中国民众纳入列强经济侵略范畴予以抵制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