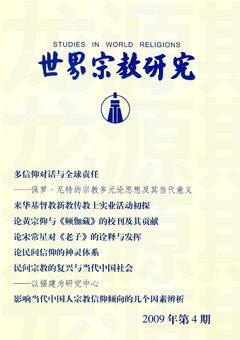论宋常星对《老子》的诠释与发挥
本文从真常之道、无为之德、修养之学等三方面分析了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宋常星所著《道德经讲义》的诠释思想。宋常星以“真常”解《老》,突出了真常之道“真”、“虚”、“和”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通贯于具体的修养实践。这一诠释理路,既体现了道教老学尤其是全真道学者解《老》的一贯传统,同时也反映出道教学者在诠释《老子》过程中所作的理论探索,而全真与老学的关联,于此亦可觅获。
关键词:宋常星《道德经讲义》真常之道
作者刘固盛,1967年生,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常星,号龙渊子,山西人,为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宋氏乃于顺治六年(1649)参加科举考试,被钦选为探花,在朝廷供职三十余年,先后担任国史馆总裁、都察院都御史、兼经筵讲官、侍读学士,于康熙十八年(1679)告老还乡,专修清静无为之道二十余年,内功圆满,特著《道德经讲义》,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由其子宋家廉进呈康熙皇帝。从其经历可以看出,宋常星是在致仕还乡后的晚年加入全真道,成为龙门派弟子。康熙皇帝见到《道德经讲义》,十分赞赏,遂令雕版印刷此书,并亲自为之作序,其序云:“朕久欲效黄帝故事,访道崆峒。今得此项讲义,崆峒之言,悉在是矣。爰《道德经》,自历朝以来,注释是经者无虑数十百家,虽众说悉加于剖析,而群言莫克于折衷。朕素钦前国史馆总裁……元老故臣宋龙渊所注《道德经讲义》,其言洞彻,秘义昭融,见之者如仰日月于中天,悟之者如探宝珠于沧海,因此特命鳗梓,用广流传。凡宗室皇胄,暨文武臣工均皆敕读。果能勤诚修习,获最胜福田,永臻快乐。敕书为序,以示将来。”康熙敕令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均须阅读《道德经讲义》,足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又据九门军都杨桐所撰《考证经注序》:“山西名士宋龙渊先生,沉潜于道,念有余年,专心致志,开示后学。分章逐句,无不诠解,可谓致详且尽。”由此看来,《道德经讲义》在当时的影响较大。他对《老子》的诠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并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本文拟对《道德经讲义》的诠释思想作较为全面的研究。
一、真常之道
关于《老子》的诠释,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准确理解并阐发那深奥难测的“道”,对此,宋常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解释《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云:
道之一字,先天先地之先不为先,在后天后地之后不为后,最极最大,最细最微,无方圆,无形象,大无不包,细无不入。极大,尚有可量,极细,尚有可指,惟道极大不可量,极细不可指。乃是至妙至玄,无极太极之大道也。可道二字,凡落于言句,便是可道。真静悠久,谓之常,可道之道,即非真常之道也。道可以分为两种,即可道与常道,凡落于言句者为可道,而不可言说、无所不在、至玄至妙者为常道,即真常之道。对于真常之道的特点,宋常星从多方面进行了描述:
大道之实际,祖万物而不祖,宗万物而不宗。五太之先,不古不今,三才之后,无先无后。其实际之妙,若言无,却又无而不无,无物不有,无时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妙有自然之机实未尝无也。若言有,又未尝见其有,空空洞洞,不有朕兆之可观。浑浑沦沦,未见象状之可指。辅万物之自然,其自然之隐妙,可以神会,实不可以言传也。立天地之大本,其大本之实理,可知其有,不可见其有也。是故乾坤内外,大主宰,大体用,造物化物者,道也。大千法界,大圆满,大本根,无欠无余者,道也。
上述注文,对道的抽象、玄妙、圆满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反映出宋常星对老子之道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他又注第32章说:“切思道之实际,本无名象,本无朕兆,不变不易,能常且久,莫可见闻,莫可名状。虽然不可名状,元而不无之真无,索存极妙,有而不有之实理,浑然全具,是以谓之道,是以谓之常,是以谓之无名,是以谓之朴。谓之常者,大道攸久之妙也。谓之无名者,大道微妙之机也。谓之朴者,大道浑全之理也。”宋常星认为,道本不可名,但为了把握道之要义,又不得不使用一些概念如无、朴、理之类来称谓之,而在各种与道相关的名称中,“真常”二字应该是最切近道之本意的,所以他说:
真常之道,即天地之心,造化之本。人能知此复命真常之妙,可通天地之微,可了生死之事。老子之大道既是宇宙之本体,又是性命之本原,而道的根本性含义,全在“真常”二字之中。真常之义,涵盖天人,一切众生,均有真常之性,修道之人,当以真常为本,“倘若不悟真常,不穷归根之理,不究复命之要,纵欲败度,不当动而妄动,失正求邪,不可作而妄作,祸之来也。”因此,“修道之人,若能取身中之金玉,养性命之真常,身外之金玉,视若尘嚣,此心自然清净,知止知足,不贪不妄,用之不穷,守之不去矣。”
真常之道的特点之一是“真”。在宋常星看来,“真”为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所以老子之“玄”是“至真至常,浑化无端”,“又玄”是“真之更真,确之更确”,修道者应该“观于无而识玄之妙,观于有而识玄之真”,追求“真知”、“真智”、“真识”、“真味”、“真心”、“真性”、“真体”。为了说明“真”的重要性,宋常星又引古道经云:“天得其真故长,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寿。”对修道者来说,“真”是一种摆脱了世俗欲念干扰、不为外物所累、纯粹自然的境界,如果体会到了大道之真,不仅寿命可以延长,而且可以超越生死,正如宋常星33章注文所言:
妄心既死,法性自然真常,是以自古圣人,不以死为死,而以不明道为死;不以生为生,而以明道为生。大道既明,身虽死,而真性不死,形虽亡,而真我不亡,所以我之法性,不死不生,不坏不灭,无古无今,得大常住,虽不计其寿,而寿算无穷矣。这里提到,尽管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真性、真我是永恒的,所以只要把握住了大道之真,便可以“不死不生,与天地为一”
真常之道的特点之二是虚。宋常星指出,“大道之体,以虚为体。”道是宇宙万物之本原,万物非道而不生,非道而不成,非道而不有,非道而不立。道如此神奇的创造力,乃来源于其虚的特性:“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荡荡无边,物声臭之可闻,空空无际,无朕兆之可见。”正因为道体虚无,故有生生之妙用,对此,宋常星反复加以强调:
无者,虚也。虚能容物,虚能生物,天地万物,俱从虚无中生将出来,所以为大道之本元,天地万物之根本。
致虚者,天之道也。守静者,地之道也。天之道若不致虚至于至极之际,则万物之气质不实。地之道若不守静至于至笃之妙,则万物之生机不有。是故虚者乃造物之枢纽,静者乃品汇之根柢也。天地有此虚静,故日月星辰,成象于天,水火土石,成体于地。象动于上,故万物生焉,体交于下,故万物成焉。所以虚静之妙,无物不禀,无物不受。出入阴阳,升降造化,与万物并作者,皆是此虚静之妙。以上对虚的阐释,可以说抓住了老子之道的关键所在,而虚又往往与静联系在一起,无论天道、地道还是人道,都是“以虚静为本”的。
真常之道的特点之三是和。“大道之用,以和为用。”道生天生地,涵育万物,总
是体现出和的特性,和也可以理解为和气,宋常星指出:“和者,天地之元气也,得此元气,天地自位,万物自育,大道可入矣。”和又常与冲联系在一起,所谓“冲气以为和”,对老子的这一著名命题,宋常星解释说:
冲者,冲之于和也,不冲则不和,是故阴阳内外,若无冲气以和之,则阳气不能变,阴气不能合,虽有负抱之理,终亦不能生成矣。譬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即是不得冲气以和之也。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者,虚也,冲气者,虚中谷神之气也。得其虚气,则阴阳变合之妙,自然和而为一,万物造化之机,自然入于无间。以天地之谷神,合万物之谷神,以天地之冲和,合万物之冲和,此所以有生生之妙也。
冲即虚,虚与和即道之体与用,在道生万物的过程中,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对于修炼者来说,其理相同,修道之人若能得此冲和之气,“天根自见,月窟自明,五气自然朝元,阴阳自然反复。久久行之,何患道之不成,丹之不就乎?”所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宋常星正是抓住一个“和”字,以此沟通天人,阐发内丹之理。对于和的意义,他在第55章之注中进一步阐发云:“和者,太和之气也。在天地,为阴阳之正气,在人身,即是谷神之元气。身中之造化,由此气而生;性命之根基,由此气而立。纯纯全全,至柔至顺,谓之和。”注文表明,太和之气贯通天、地、人,天得之则清,地得之则宁,人得之则性命双修,金丹可成。
用“真常”来诠释老子之“道”,这是南宋以来道教老学的特色。道教南宗创始人白玉蟾的二传弟子邓锜即用“真常”解《老》,他的《道德真经三解》序云:“老氏一书,真常为主。解者悉与道德混而为一,不知宾主上下,以致诸儒妄生异议,无区以别矣。今也先述真常三百字,以拟阴符之数,列于序次,庶使后之谈道德者不远迷其复矣。”邓锜认为诸儒解《老》妄生异议,是没有抓住《老子》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真常”二字,只要牢牢把握住真常之玄义,便可做到性命双修,因为“真常在命,无所不定;真常在性,无所不应”。同为南宗弟子,后加入全真道的李道纯,亦以真常性命之论解《老》,詹石窗先生称李氏老学是“无名之道真常化”,并指出:“李道纯以‘真常立宗,这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比起过去的老学来,他的最基本的概念显得更抽象概括,更富有思辨色彩。”由此可以看出,宋常星以“真常”解《老》,既体现了道教老学尤其是全真道学者解《老》的一贯传统,同时也反映出道教学者在诠释《老子》过程中所作的理论探索。
二、无为之德
老子之道,落实到社会与人生的层面,即是德,德为道之用,体现出道的特点。如果从治道的角度来看,德的主要内涵乃是无为,宋常星谓之“无为之德”。由于宋常星长期在清廷作官,所以在晚年加入全真道以后,并不能完全作方外之游,而对如何治国安民,仍然是有所思考的,这一点在《道德经讲义》中也得到了证明。
宋常星首先强调了圣人在元为政治中的关键作用。关于圣人的标准,儒、道各有自己的看法,宋常星则认为:
圣人者,秉天地之元气而生也,所以万善皆备,万德周身,无私无我,无余无欠,无亲无疏,无分无剐。
圣人之道,一贯之道也。圣人之心,无为之心也。以一贯之道,用之于天下,则万物乏数不计而自知。以无为之心,用于天下,则万事之理,不较而自得。所以圣人之大机大用,有自然之理,有无为之妙。在宋常星看来,圣人即是道的化身,道的各种特点如自然无为、至善无私等等,在圣人身上都有体现。而宋常星特别强调的,是圣人对民生的关怀,如说:
圣人养育万民之生,成就万民之性,令一切天理完全,无余无欠,其功亦莫大焉。若以此功求之于圣人,圣人忘己无私,亦不自居其功矣。
圣人心同天地,物我两忘,与天地之民,相忘于道德之中,共入于无为之化。以人治人,又安有为而自恃者?圣人仪表万民,首出庶物,可谓天下之长矣。然道同天地,恩如父母,与天下相忘于自然,相处于无事,无彼此之分,无上下之异,有何主宰之心乎?故日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由于道生万物,自然而然,并不自恃其功,圣人法道,其教养万民,亦自然而然,不求人知,不求人见,功劳至大而不自居其功,这就是“至治之泽,民不能见,不言之教,民不能知”。
其次,宋常星对无为而治的内涵进行了自己的阐发。他注《老子》第18章云:“大道之用,用之于无为而治,用之于有为,则不治也。无为而治者,各循自然,行其当行,而不自知也。是为至诚知实理,故己私不立,天理纯然,上下相安于无事之中,朝野共乐于雍熙之化,不见其为之之迹也。”强调无为即治,有为则不治,无为而治的关键乃在于“各循自然”,这是颇合老旨的。而在诠释“无为”的过程中,宋常星又特别突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在无为的政治实践中,统治者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为什么圣人能够实现无为而治,于民同化?那是因为圣人的修养已与道合一,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宋常星在诠释《老子》第3章指出,“虚心、实腹、弱志、强骨,皆是无为之道也。”虚心,即是“虚灵明妙,荡荡空空,不曾有一物所系,少有纤毫尘垢”;实腹,即是“包藏天地,涵养万物,其道也养之极深,其德也积之极厚”;弱志,即是“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守荣守辱”;强骨,即是“以道德求胜于己,不以道德求胜于人”。由此可见,虽然无为之道的目的是欲使民返朴还淳,“同入无为之化,共乐熙之风”,但施政的主体即统治者本身是否体会到了无为之真义,是否具备了与道相契的至善之德,才是至关重要的。在《道德经讲义》中,宋常星对无为的阐释,大都是针对圣人或统治者而言的,试看《老子》第18童之注:
睿通渊微日圣,知周万物日智。圣与智,任天下者必不可少矣。既不可少,岂可绝之弃乎?设使圣智可绝,道亦不能行于天下,德亦不能被于古今。经中言绝圣弃智者,意欲天下后世,以圣智自修,不以圣智施之于民,不以圣智用之于国。在上者无为,在下者无事,无为而民自富,无事而国自安。细详圣人在上,原为行道于天下,非欲沽圣智之名也,所以夫子不以圣自居,尧之稽众舍己,舜之与人为善,禹之闻善则拜,皆是绝圣弃智之妙处。
这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之注。针对老子此语,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解《老》者认为老子是反智、甚至反文化的,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宋常星明确指出,治理天下,圣与智都是必不可少的,统治者在自身的修养中,应该具备圣与智,而所谓的“绝圣弃智”,并不是不要圣智,而是不要以圣智去扰民,去干预国政。谁能否定尧、舜、禹不是圣智之人呢?他们都是凭圣智而实现了无为之治。宋常星此解,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而对统治者自身素养的强调,同样反映出宋常星政治上的远见。
其二,无为而无不为。宋常星指出,老子的无为,并非消极避世,实际上是积极有为的。他注《老子》第48章曰:
此无为之妙,非土石可比,块然而终于无为也。此等无为,乃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之无为;乃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之无为;乃是色中有空,空中损色之无为;乃是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之无为。其无为也,不言而信,不行而至,不疾而
速,不为而成,即是清静自然之道也。此清静自然之道,虽云无为,自然发见昭著,神乎其神,妙乎其妙,则又无为而无不为矣。
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含义,这一阐释是合符老旨的。宋常星还结合天道、地道、人道进一步分析说,天不言而四季变化,这是“天之无为而无不为”,地不言而生长万物,这是“地之无为而无不为”,人应该效法天地之无为而无不为,“求之于性,性理完全;问之于心,心德了明;修之于身,身无不修;齐之于家,家无不齐;治之于国,国无不治;平之于天下,天下无不平矣。”能法天地之无为者,当然是圣人了,圣人与平常之人的区别亦在于此:
为无为者,圣人之为,为之于道,为之于理。常人之为,为之于名,为之于利。为之于名利者,乃是有欲之为也。无私之为,不用安排,无为而自然成就,未当勉力,无为而自然入妙。是故圣人之心体虚静,圣人之德性浑极,不生逆料之心,不起将来之意,以无为而为,人不能知其为,人不能见其为。因不能知其为,所以广大悉备,无为而无不为也。因不能见其为,所以自然合道,无不为而无所为也。圣人比常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圣人之为,以大道为法则,不自矜其名,不自居其功,故虽为而顺自然,虽为而人不知,也就是“无不为而无所为了”。
其三,无为与儒家思想并不矛盾。宋常星身为顺治朝的探花,受理学之影响颇深,这从《道德经讲义》中屡引“理”、“天理”解《老》可以看出。同时,宋常星强调,老子的无为之德,与儒家的主张并不矛盾。他注《老子》第38章说:
未有天人之先,其至诚无妄者谓之道。受命于天,全之于性,得之于心,谓之德。至公无私,生理常存者,谓之仁,有分别,有果决,当行则行者,谓之义。天秩之品节,人事之仪则,有文有质,恭谨谦让者,谓之礼。此五者,乃是治国齐家之达道,修身立命之本始也。
注文肯定了儒家仁、义、礼的合理性与存在的必要性,并且与老子之道可以保持一致,即:“道德仁义,爱民亲贤,皆正道也。自古治国者,未有不以正;君臣父子,无不行之以正;礼乐尊卑,无不导之以正。民心之天德,由正而复,国家之风俗,由正而纯,道德既能行于中外,仁义自然化于乡帮。”宋常星进一步发挥,认为儒家的等级制度,与老子之道亦不矛盾。在他看来,圣人之无为,同样是离不开儒家的三纲五常、上下尊卑之“天理”的。这一点,在以下注文中更清楚:“天下之道,有国必有君,有君必有臣,君之尊,臣之卑,此名分不易之道也。”宋常星肯定了儒家伦理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指出:
侯王,虽然贵极九五,但不自有其贵,当以谦下自处。譬如天之道,能容于物,地之道,能养于物,圣人之道,能爱于物。容于物者,虚其体也;养于物者,虚其气也;爱其物者,虚其心也。侯王之德,配天地,侯王之道,合圣人。不自尊,不自贵者,亦是虚心之妙也。能虚其心,天必与之,人必归之。
侯王位高权重,是最大的有为了,又怎能做到无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侯王不以为贵,“虽功高于天下,心中不自有其高”。也就是说,君臣之间的尊卑秩序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君王能够谦下自处,虚心待物,则同样可以法道之自然,无为而治。
三、修养之学
朱越利先生论及《道德经讲义》的养生特点时指出,道教的养生是始终以老子思想为依托的,因此,“道教注《老》,使老子思想成为道教养生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发展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养生思想和方法。道教养生独具特色,颇有效验,与此决然难分。”作为全真道士的宋常星在诠解《老子》时,对养生修炼之事确实十分重视。全真道倡导性命双修,宋常星的炼养之旨同样不离性命二字。如他注《老子》第4章云:“修道之人,既得大道冲用之妙,则性海虚灵,心渊湛寂,可以融一真而入妙,可以混万理以归元。天外无极之眼睛,无不豁然通透,世间有限之凡情,无不了然觑破。自然湛湛清清,虚灵圆妙,浑浑沦沦,独立不移,虽劫数升沉,天地改易,我之真体如然,不变不坏也。”修道者由心性合真到真体不坏,正是全真道先性后命思想的体现。又如第40章注云:“无即是无形无色妙无之无,以性言之,即我性中不坏之元神,以大道言之,即是太极真静真无之本体。……有形有色之中,更有妙无者具焉;无形无色之中,更有妙有者存焉。人能明得此理,知反覆之妙,则元性不迷,元神自住,元气自合,元精自固,元理自得,元机自动,更能打成一片,则性命自全,金丹可就矣。”此注是对《老子》“有生于无”思想的发挥,体道者可从妙有妙无之理中悟出反覆之机、生化之玄,从而可至性命双全。宋常星继续注云:“是故养道之人,意去邪思,心除妄想,止其强大之心,习学柔弱之志,言语柔和,不可与人争强,凡事谦退,不可与人取胜,千辛万苦,昼夜不眠,亦只是为求妙无妙有之理也。此妙无妙有之理,惟大悟大彻之人,得遇真师诀破,方可知其动静体用之微,方可得其反动弱用之妙。倘若不悟此理,只徒外面庄严,不修性命实理,则性迷情妄,失却真常之道。生死轮回,陷入苦海,万劫难复本性矣。”这里再次强调金丹的修炼不是到外面寻找捷径,而应反求于身,抱谦柔退让之心,求妙有妙无之理,在师父的指引下,彻悟性命的真谛。
当然,道教的修养并非空谈心性,而是要把功夫落到实处。为此,宋常星在诠释《老子》时又突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养气。宋常星首先阐述了气的重要性:“切思万物,皆本天地一气而生,但清浊偏正之不同耳。人之与物,均有此形,均有此气。”人与万物均禀气而生,但是气有清浊偏正之分,“人生性备太极之理,身得形气之正,与天地并立为万物之灵,可谓至贵矣。”人贵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得形气之正”,此气又称“冲和之气”,“虚灵者谓之冲气,柔顺者谓之和气”,而虚灵与柔顺是不可分开的,所以冲和之气并非是两种不同的气,而是一气,即和气,“此气之妙,有体有用,有动有静。其体也,涵阴阳升降动静自然之机;其用也,有聚散屈伸变化无穷之妙。用之可见者,因用有象而为气,故可得而见之。体之不可见者,因体无象而为神,故不可得而见之。”宋常星又把此微妙之气称为“大道之母气”,而能否食此母气,乃是修道者与常人区别之所在:“修道之人,果能肖天地,而食母气,不见不闻,自然性命一贯,无人无我,自然心德周全。上则可以识天时,下则可以达地理,中则可以尽人物。”这里所谓的食母气,实际上就是养气致和,使神气抱一。宋常星指出:“吾见今之内炼者,虽敛藏神气,不过除其妄想,调其呼吸而已。神不能人气,气不能归神,真息不相依,故不能抱一。”一般的修炼者认为内丹仅仅是去除妄念,调整呼吸,这是不全面的,修炼内丹必须做到神气合一、真息相依。而养气之要乃在于“和”:
修行人,果能心不摄于邪思,意不入于妄见,守其真一之元机,养我柔和之正气。一刻工夫,可得天长地久之理,半晌时候,可入不坏不灭之门。到此天地,虽世运变迁,我之性命与道常存。故曰,知和日常。古语云,借问如何是我身,不离精气与元神。我今说破真常理,一粒玄珠是的亲。观此知和日常之妙义,悉在其中矣。
宋常星认为内丹之理,不离精、气、神“三宝”,修丹之要,乃在断邪思妄见的基础上,
“养我柔和之正气”,只要炼气至和,即可性命双修,与真常之道合一。
其二,守静。大道以虚静为本质特征,如《老子》第16章云:“归根日静,静日复命。”宋常星认为“归根复命”四字,“便是造道之津梁,修行之正路”,而所谓的归根,即是归之于虚静。他说:“若能性命归根,神气一致,常清常静,诸念不生,无欲无为,一法不立,身心自然泰定,性命自是真常,此便是天清地宁之妙处。更能涵光默默,神气充盈于上下;道(无灬)溶溶,谷神独立于虚中,此便是神灵谷盈之妙处。又能产灵苗,结圣胎,无处不见生生之理,无时不得生生之意,此便是万物生之之妙处。又能性霁神融,心清意定,保性命之真常,守无为之至道,此便是我身中之天下贞静之妙处。到此田地,无人无我,无天无地,万法皆空,一法不立,侯王不能加我以为贵,天下不能鄙我以为贱,名利不有,荣辱不生,岂非得道之人乎?”学道者如果能够体悟诸种妙处,归根复命,则大道得矣。但此归于虚静之妙,很多修道之士是不明了的,正如第29章之注所言:“大道之本体,本是清静湛寂,奈何人只在有为法中镌求,不向无为法中体认。本欲保身以载道,返致害身而失道。此皆是不守身中清静无为之神器,妄为妄执之过,故有此害身失道之患矣。”宋常星把该章之“天下神器”释为清静无为,实际上强调了守静在修炼中的重要作用。他在第37章之注中又云:
人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纯一不杂,至清至正,乃天命之性也。气质禀赋,则有偏正清浊之不同。只因天命之性局在气质之中,不得不有此偏正也。然气质之性虽不同,其本性之善则一,人能反之,天命之性自复矣。反之之功,妙在以静。静者无欲也,人能无欲,其性自静。人能性静,其性自正,性正则无所不正矣。
人性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修道过程则是一个返归天命之性的过程,而在这些修炼实践中,“守静”很关键,所谓“反之之功,妙在以静”是也。对于守静的妙处,宋常星在第48章之注中进一步指出:
此等工夫,可忘者无不忘,可去者无不去,可了者无不了,可弃者无不弃。忘之又忘,去之又去,了之又了,弃之又弃,清静中更求清静,无为中更求无为。到此天地,人欲去尽,天理纯全,性静如琉璃,不容一丝污染,心清似明镜,未有半点尘翳。本体光明,真心自在,本来之面目,方才显露,无极之真人,始见金容。其无为之妙,如无极之无形,如太虚之不动。身心内外,无时不在无为之中;天地万物,无物不是无为之道。无欠无余,无增无减,无凡无圣,无有无无,到此天地,损无可损,益无可益,法性内外,浑然都是个清静之理。从注文可以看出,在宋常星所强调的“清静之理”中,心性的清静是最重要的。宋常星指出:“心之本体,清净光明,原无一物,亦与太虚同其体用。只因忘缘,填塞虚灵之窍,遮障妙明之光,所以灵明之体不现,体用不能全彰。”人心之本体与太虚为一,与道为一,虚明无碍,但物欲与杂念会阻塞心的灵明,从而影响修道的进展。因此,修道者必须做到无为无欲,保持心的虚静,达到“心如太虚,空空洞洞,湛湛清清,内不起有为之识,外不见有为之尘,物我同然,内外如一”的状态。
其三,持戒。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弟子、后誉为龙门中兴之祖的王常月倡导戒行精严,并公开传戒,“大阐宗风”,一时皈依者众多,龙门派由此逐渐复兴。宋常星亦为龙门派第七代弟子,与王常月同辈。王常月强调持戒修道的思想对宋常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一点在《道德经讲义》中也得以体现。他在第33章之注中说:
修行之人,果能内戒于心,外戒于身,用此戒力以自胜,即有司逻十部,戒神等众,卫护戒子之身。出入动静,一切善缘相随,起居坐卧,一切恶业远避,守戒日久,道可就矣。不但学道之人,当用戒力以自胜。自古仙圣,未有不修戒果而成道者。
戒力为宋常星所谓的“自胜之力”的一种,按他的说法,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圣人先能自胜。其自胜之力有十种:一信力,二舍力,三戒力,四进力,五念力,六定力,七慧力,八智力,九道力,十德力。所谓戒力,就是持戒,这是断恶防非的有效手段,修道者如欲成道,必须持戒。宋常星继续指出:
今玄门子弟,初进步者,或持三戒五戒,初真十戒,九真妙戒可也。果能戒力坚固,功满千二百善,再修持身之戒,观身之戒,一百八戒,三百大戒可也。如此渐次进修,道无不成,道无不就者也。可以看出,注文中对玄门弟子的持戒要求,都来自于王常月。三戒、五戒、初真十戒、九真妙戒,为“初真戒律”,为初出家者所持,如果持戒圆满,可以进一步修“中极戒”,直至“天仙大戒”。按王常月的观点,戒能降魔镇妖,能护命增寿,能破暗除昏,能礼三清而超凡人圣,乃至渡众生离苦海,总之,戒乃“修行人之保障,为进道者之提纲。仙圣无门,皆从戒人,圣贤有路,皆自戒行。实系仙真之要路通衢,贤哲之中门正道”。宋常星通过诠解《老子》对修道者提出严格的持戒要求,正是全真道龙门派宗风重振的具体反映。
四、余论
全真道提倡性命双修,反对符箓、黄白之术,可以认为是对符策之类旧道派的革新,而此种革新,从实质上来说,则可能更加符合道家的内在精神。元代徐琰在《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中指出,王重阳所创全真道,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有了这样的教义,“老庄之道,于是乎始合”。徐琰认为全真道的教义教理是真正符合老庄之道的精神实质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见解。宋常星的《道德经讲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徐琰的观点。他以“真常之道”通贯全注,以冲虚灵妙、清静无为、性命双修诠释老子之道的基本内涵,不仅较好地把握住了老子思想的要义,同时又保持了全真派的道教特色,而全真与老学的关联,于此亦可觅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