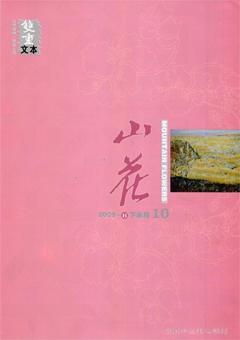人文历史背景下和文化结构中的汉字释读
语言学家们研究一种文字,最根本的首先是要弄清其书写形质究竟是象形、表意还是表音,要为它的构形原理定性。迄今已经拥有近四千年历史的方块汉字,是汉民族用以记录文化并同时以之表达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表意的汉字与人类诸多语言文字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一开始并不是语言的直接记录。汉字首先是用于记事,通过对客观事物、具体行为的记录描述转而与语言联系起来。全面正确解读数以万计的众多汉字,揭示潜藏于这个系统中的汉字构形理论,是中国学者两千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面对当前文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愈演愈烈的世界汉语热,中国学者需要做的仍然是,提供一套客观真实并且不悖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汉字构形理论模型,这是历史与现实赋予当代汉学研究的严肃学术使命。
假若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评价华夏先民的上述那些文化生活,那种极其感性的思维过程今天看起来的确显得非常幼稚而脆弱。它对事物的识读理解过程往往会因人而异,其结果当然也时常会由于受众的自身经验、认知能力的差异而可能随之发生曲解变形。与此同时,表达手段甚至书写水平也在直接影响着表达者本身的表意效果。比如,早期的先民刻写出一个“山”,在缺乏语义场的情况下,究竟是要登山抑或是要蹈火,就有待于当场的言语补充说明或是依赖于表达者跟受众双方的默契。但是时过境迁已经令后人失去了当面聆教的机会。如此一来,大量的书面语言都在所难免地产生了后世学者所说的“歧义”。这种歧义自然而然地由文字延及语句并进而影响到段落辞章。那些致力于消除或者利用语言歧义的学者,就被时人尊称为辩士。而为了避免、消除或是刻意制造这种歧义,在辩士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名辩学”。
对于名辩学以及辩士们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所作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应被认为是过誉之辞。《墨子·小取》就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庄子·天下》对惠施的“历物十事”也赞誉有加地说道:“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干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名辩家们以自己的智慧对自身所处时代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先秦文化史上形成了以比类、正名、别同异为目的的文化思潮。
以墨子的方法认识世界,首先不必关心世间万物零星琐碎的数与量,而是注重事物的形质之分。他从形与质两个方面先将事物分为两大群类,根据其性质可以明确归属金木水火土或羽毛裸鳞介的,就实行明确客观的“物以群分”;对于缺乏依据,不能依属归类的。就按照其情貌、状况、形态进行主观的“方以类聚”。应用到汉字构形的实践当中,以形为据的方以类聚。为形声字提供了立辞依据,以质为据的物以群分,为转注字提供了立辞依据。就思维方式而言,形声法依据的“方以类聚”就是借助意象思维进行事理比类,实现循名责实。转注法实行的“物以群分”则是根据逻辑思维进行实物别异,实施因实制名。两种思维方法殊途同归,用于汉字构形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精彩的还有战国时期另一名辩家公孙龙。他形象地指出了人们视石知其白而不知坚,抚石知其坚而不知白的事实。《淮南子·齐俗训》说他:“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公孙龙通过著名的“离坚白”,明确分析了众人视觉与触觉互不相干的自然道理,机敏睿智地阐述了物质世界的形质之别。
庄子则以简练的语言向世人阐述了惠施的另~种认知模式:万事万物皆备共相,同属事物各具自相。前者谓之毕同,后者称为毕异。换句话就是说,不同事物其间固有大异,同属事物之间亦有小异。惠施意识到同属事物之间互有异相,万事万物之间同有共相。其言同则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其言异则视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庄子记述了惠施不无幽默的辩辞:“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的这种万物与我皆同、与我皆异之论,分明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理性光芒。
名辩学思潮历经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之际。当其盛行之时,除了名家重名以外,儒、道、墨、法乃至纵横家、杂家,各家学派无不重视循名责实。就连儒学宗师孔夫子都郑重其事地提出;“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涌现了大批颇富思辨色彩的辩士,他们以从事“名、辞、说、辩”,也就是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研究为己任。一些人为了“别同异”而踏踏实实地因实制名,一些人为了“正名实”而轰轰烈烈地循名责实。辩士在当时着实风光。君王争相养士,诸侯群起效法,辩士深得世人推崇。王公贵族的器重以及世人的追捧,使名辩学得以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震耳聒天、喧嚣一时。
古人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在当时的文化事象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特殊载体,自然而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刻痕。然而名辩学思潮对文化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其时间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或两个特定的时代。从武王克殷、春秋力政、七国争雄到强秦富汉,时逾一千三百年的光阴里,古人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都在当时的文化事象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直至秦代贾逵李斯率领的“书同文”实践,不仅系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文化理念与哲学思想,也完整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质。
汉字作为汉文化的特殊载体,它系统完整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质。充分了解名辩学思潮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理解中国古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方法,认识汉字六书理论形成的过程及理论方法,理解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对于今天的汉语汉字研究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理论意义。
古人建立在意象思维基础之上的认识方法,乍看上去会觉得晦涩艰深,深入后却感到富含哲学思辨意义。所以《淮南子》一书说它:“不可与众同道也”。影响后世的盲人摸象谕、日谕,其实都不过是与名辩家一脉相承的通俗版而已。那些雄辩之士,或得君主恩宠而平步青云,或受士林推重而饮誉天下。在社会各阶层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了集学、政、道为一体的哲学思潮,也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方块汉字。后人对先秦辩士的思维方式多有不解,曲解了墨子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把它理解成,“方”为“物”之误,“物”为“人”之讹,将墨子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原话都径直改造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如果说殷商先民在早期汉字构形实践中运用了某些辩证思维方法的话,那毕竟只是处于萌芽时期的一种不自觉的自发状态。因而春秋战国时期在制字时,都只能达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正是源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先圣古贤间或论及汉字义理,也都往往言不及义。于是《左传》中就出现了“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之类。到了秦代,连秦始皇帝赢政都亲自参与了汉字造字的具体作业,更增添了汉字的神圣感。严谨的秦风也令李斯、贾逵等人只能循规蹈矩地制字而不能以理性的态度深入地探讨汉字构形之所以然。李斯率领的书同文实践完整系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文化理念与哲学思想。许慎则是将名辩学理论与实践引进文字学领域的语言大师。只有到了汉代,在一种优雅的时代风尚熏陶下,才有可能让刘熹、杨雄、许慎得以对汉字进行客观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研究,进而使汉字的定音、构形、表意方法及其理论最终得到系统阐释。
作者简介:
张泽渡(1954-),男,汉族,贵州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词汇学,文字学、语音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