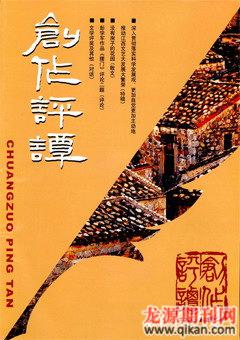一路这样走来
彭学军,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湖南吉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协会员。1990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告别小妖》、《歌声已离我远去》、《长发飘零的日子》、《蓝色滑板上的小妖精》,长篇小说《终不断的琴声》、《你是我的妹》、《腰门》,散文集《纸风铃紫风铃》等二十多部。曾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小说大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各种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集。
最初的时候——是说这三十年的最初、也就是1978年,我还在湖南吉首的自治州少年体校。
我学的是田径,专项是四百米和八百米。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在体育场铺着黑煤渣的跑道上跑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气喘如牛,汗水滴在地上摔八瓣。耳边还不时响起教练凶巴巴的吼声:快点,再快点!那架势跟旧社会的地主差不多,只是手上少了一根鞭子。日晒雨淋再加上大运动量的训练,豆蔻年华的少女出落得跟非洲难民一样,又黑又瘦。
那时,家里喜事连连。我父母都是老师,文革的时候下放到乡下去了,那一年,落实政策陆续调回了城里,母亲在卫校,父亲在自治州的民族中学,那是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周边的十个县都把最好的学生送到那所学校来读书,来读书的学生只有一个目标:考大学——那时,已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了。
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已经厌倦了跑圈子,老这样跑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呢?那么,出来读书,然后考大学,我行吗?我十一岁就进体校,基本上没读什么书,底子太差了……但最终,我还是离开了体校。
以我的成绩,民族中学就是拼了小命也进不了的,但因为是教工子女就很顺利地成了那里的学生。以前是一天到晚地跑圈子,后来是一天到晚地做功课。从早自习到晚自习,星期天也要上半天课。那个时候老师补课从来不收费,很无私也很有激情,干劲十足,只要把学生教好了,成绩提高了,他们就会由衷地高兴。
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儿童文学。
还记得我们住在操场边的一排平房里,隔壁是语文老师,和我家一样,她家也是三个女儿,大女儿和我是同学。语文老师比较重视阅读,给她的女儿们订了《少年文艺》,每期新到的杂志我都会借来读,每每读到精彩的文章就兴奋得要命,也羡慕得要命。那点可怜的阅读成了我发奋读书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
后来,我父母调动工作,举家迁到了江西赣州。
赣州是一座古城,宋代时已初具规模,至今仍有一段三千多米的宋城墙横卧在赣江侧畔。刚去的时候,觉得它宁静清洁、古风扑扑,又稍稍有点落寞。也许我该把它看成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赣州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在一所中学做老师。
我教高中的语文,和我同分到那个学校教语文的女老师还有三个。我们四个人常在一起玩。那时才毕业,都还没有恋爱,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疯玩,或商量下次去哪疯玩。
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和咖啡馆,连像样的大商场都没有。我们凑在一起多半是看电影,然后手牵手地压马路,肆无忌惮地高声说笑。有一回,玩得太晚了,回到学校铁门已经关了。看门的老头可能又喝多了酒,怎么也叫不醒,无奈,四个平时看上去还算温文尔雅的女教师只好爬铁门……爬铁门时笨拙而又轻盈的身影成了我们作为一个女孩的最后的、标志性的画面,定格在了记忆中。很快地,就有人请婚假、休产假了,然后是另一个……
我大概算不上一个好老师,教了几年书后就没了激情,而且学校越来越重视升学率,每次考试后,算总平均、及格率、优秀率……每个老师都精细得很,也不免斤斤计较,但我对这些都毫无兴趣。
我得找点有意思的事做,于是把念大学时订的杂志都翻出来:上海和江苏的《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东方少年》,也许是想延续读中学时的那种阅读感觉,我订了一堆这类的杂志。我把这些杂志重温了一遍后,心里燃起了一个希望:我要写小说,就写中学生,我有这样的生活,而我的文字一直还不错,读中学时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
那时已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是文学备受推崇的时代,能发表作品、出书。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电视台。
也许是职业和视野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注意这个城市的变化。城市越来越大了,它迅速地向郊区延伸,高楼也越来越多,人哦车哦一下子多了起来,大街上一天到晚都热闹非凡,人们的衣着也日益地光鲜、时尚。这个城市再也不会让人感到落寞了。
但我终归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我很享受去乡下采访的日子。特别是春暖花开或秋高气爽的时候,走在乡间小路,满眼葱绿,空气中飘散着植物的青涩和瓜果的芬芳。
有一回,乡里派了一辆农用车送我们,走到半路,车出故障了。那天正逢赶集,本来就不宽的马路被挤得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到了一段长长的陡坡,司机也不减速,直直地往前冲。我当时坐在驾驶室,看见司机满脸是汗,神情紧张,嘴里嘟嘟哝哝地骂着,就知道,刹车失灵了。怎么办,再这样冲下去会出人命的!我压抑着恐惧,强装镇定。指着前面路边的一堆碎石说:“冲到那堆碎石上去。”司机听了我的,让车轮陷在了碎石里才刹住了车。还有一次进山采访迷了路,顶着烈日在山里转悠了一天,天快黑了才找到出山的路:去矿山,爬了大半天的台阶,腿软得发抖,可到了目的地因为大雾天设备受潮根本开不了机……还有雨中的果园,冬天的林场。叽叽咕咕的养鸡场……有些经历其实是为着记忆存在的,为着有一个丰沛的人生。
我大概是个做事没有长性的人,电视台没呆几年,又去了出版社,那已经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了,我离开了那个已经相当繁华了的城市。
我的写作也有了一些长进,书一本一本地出,还获了一些奖,有了一点知名度。而这个和文字打交道的职业似乎也更符合我的心性,我有一种船靠码头车到站的归宿感。我一边看着别人的稿子,一边写着自己的稿子,我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表白道:“如果,必须要有一个职业并且在职业之外再做点自己愿意做的事,除了现有的状态,我不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散淡、平和,对人对事有着淡淡的疏离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只是愿意,我可以尽可能多的只面对文字,这就极大地成全了我的个性。那些优美、灵动、睿智、幽默、飘逸、洁净的文字,以及由此而结构、交织、描摹、显影出来的美丽的故事、不朽的人物、隽永的思想和写作者真切而生动的灵魂,是那样的令人愉悦和赞叹。如果读到了它们之中的极品呢——当然是就自己的欣赏水平和阅读视野来说——那就只能是深深的沉醉、艳羡和激赏了。然后,会不自觉地角色转换,一个写作者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于是,暗暗地妒意横生,咬牙切齿或万分沮丧地想:这样的东西,就是再给我两个脑袋也写不出来哦。忍不住再读一遍,心里的‘不平就渐渐被它的卓越销融了,宽慰地、感恩地想到:幸好我是个编辑,被我读到了,如果我仅仅只是个读者,泱泱书海,很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编辑这个职业应该比其他的职业更能感觉时间的流逝吧?每年几个订货会一过,到了要报年度选题的时候,就知道是年底了,又是一年要过去了。明年又该做些什么书呢?就像老农咂巴着烟斗寻思着:明年地里种些什么好呢?
我们不能说文字是永恒的,但至少,它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这样,文字就有了时间的意义。这些文字伴随着我走到了2008年。走到了可以写“我这三十年”的时候——其实只要在这个世上活过了三十年就可以胜任这个题目,但我还是觉得它有一种沉沉的岁月之感。它让我想起曾采访过的一位老人。
很多很多年以前,老人还是一个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的时候,她的丈夫就离开了她。临走时,她穿灰军装、戴八角帽的丈夫望着田里青青的禾苗说:“等着我,到了收稻子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从此以后,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她就站在高高的老门槛上朝远处张望,在她日日的守望之中,禾苗黄了熟了割了,又青了……她的丈夫没有如期归来。人们都说他丈夫战死了,不会回来了,劝她改嫁,可她不听,她只听丈夫的话——“等着我。”她为他的弟弟妹妹成了家,给他的父母送了终,后来,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没有人能活过她……她独自一个人在老屋里守着,天天站在老门槛上望着,门槛硬是被她踩得缺了一块,萎顿了下去,三十年,又一个三十年,从那萎顿下去的老门槛上溜走了。如今,她已活在第三个三十年的日子里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那里等着她的丈夫。
可是,不是人人都能像她一样坚忍地活着,至少我做不到。不过我们这样的时代也不会再有那样的故事了。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人的一生以三十年为一个单位来衡量,对有些人来说有点残酷,对有些人来说又有点奢侈。而对一个孩子来说,大概是不可思议的漫长,就像一段没有尽头的路。不过等他走过去后又回望来路时,又会是另一种感觉——怎么就到头了,沿途的风景我还没看够呢。幸而,脚下还有路……
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