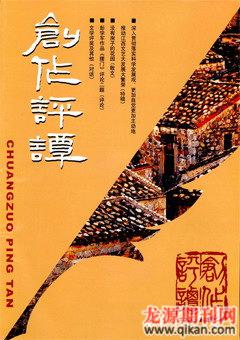故乡倒影
何立文
凉亭
它是一匹安静的兽。稻田和流水默默地守候在它周围,几十年如一日。蜻蜓的振翅、鸟雀的鸣叫、青蛙的弹奏、蟋蟀的舞蹈……都曾在这儿找到展示的机会。就在它的脚趾下,行人的鞋底,或者草帽顶上。你知道,动物总是善于寻找活动天堂的。而这些与一个经过的醉汉无关。那个醉汉,从八里地外的丈母娘家喝酒回来。他一定是喝了几大碗水酒,乡下酿的水酒后劲是很足的。往往是这样,你推辞着——不喝不喝……但是那股甜味还是俘虏了你的喉咙。那种粮食发酵的香味,肯定把醉汉的味蕾陶醉了,他操着结结巴巴的乡音,假意推辞,海碗却早已伸向了丈母娘的酒坛子。
醉汉踩着一地月光,一些虫子不甘寂寞地反复吟唱。他的脚步让旁观的月亮心惊胆战,总是在将要倾倒的时刻恰当地收回身子,仿佛躯干里面装了一根弹簧。他的舌头总是不由自主地打卷,哼着让人有点陌生的,模模糊糊的花鼓调。在月色的掩护下,醉汉东倒西歪地穿过兽的肚子。
这匹安静的兽始终敞开大门,不,拱门,铁青色的拱门,供许多行人包括醉汉们歇脚。由于风雨冲刷,墙头的石灰剥落了不少。原先刷在上面的标语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暧昧起来。黑色凝重的飞檐就是兽的角,神态自若地伸进天空的长袍里。有时候,雨密密斜斜地闪进来,濡湿了两侧的长石凳。行人依旧吸着旱烟。谈论农药、化肥和粮食的价格。雨过天晴,行人吆喝着继续赶路,大声唤一个醉汉。醉汉只是翻了一个身,如雷鼾声惊飞了黑瓦上停泊的鸟雀。
去外婆家,抄近路必须穿过两座兽似的亭。远远看见。田野中央矗立的,便是神秘的亭,它挡住了我幼稚的视线。亭子后面是一片绿油油的橘子林,火红的橘子挂满枝头,湛蓝色天幕下,浓郁的橘子香争抢着涌进我的鼻腔。我背着外婆送给我的一袋橘子,汗水渗湿了我的背心,脚步移动,心跳加快,总是幻想亭子里躺着一两个喜欢捉弄人的醉汉(他们经常捏着小孩的耳朵,逼小孩道出父亲的名字或外号),后门的一侧埋伏着几名作恶多端的妖怪。特别是夜幕四合的时刻,种种不祥的预感像一群黑压压的蝙蝠,将幼小的我笼罩。然而,待你真正深入兽的腹部,那股静谧的气息足以化解和消融最初的无谓紧张。一切都是那么安详,那么平静。它像一个长者。早早地等候在稻田一侧。我的赤脚踩在青石板上,积聚多年的冰凉沿我的神经传达周身。蚂蚁在墙缝里搬运口粮。蚯蚓蜿蜒着身子享受夏天的馈赠。蜘蛛不知疲倦地编织。我跺脚,咳嗽,跳跃,唱歌。没有行人,这个舞台很大很过瘾。
有个同事,一次喝醉了,漆黑夜晚,深一脚。浅一脚,回家。路过一个凉亭,睡意渐浓,不管三七二十一,倒下打鼾。先行回来的伙伴没见他的踪影,遂返回,将沉睡中的他拖回宿舍。第二天才听说,亭子里放了一口棺木,里头躺着一名客死他乡的年轻女子。众人笑道,你小子艳福不浅,昨夜居然演了一回《聊斋》。同事曰:酒精的作用无与伦比,女鬼拉我,也被酒气熏得逃之夭夭。一间凉亭,悄无声息地包容了阴阳两界的一对男女。它的平静之下,其实蕴藏了许多难以言说的诡秘。
如今,田间小道上的人影日渐稀少。四通八达的水泥公路上奔驰着摩托车、三轮车、小货车、面包车,它们神气地吹着喇叭,敲打摇摇欲坠的凉亭,自它身边绝尘而去。提着竹篮的村姑,油嘴滑舌的媒婆,摇着拨浪鼓的货郎。相亲回家的小伙子,荷锄晚归的老农夫……俱已遁入时间的暗流。空旷的田野。只有风的舞步潇洒而奔放。田鼠们躲在洞穴内寻欢作乐。蚱蜢正在搜寻可以栖身的草叶。麻雀侦察每一片庄稼。凉亭斜立在那儿。保持一种思索的姿势。它是一名忠诚的哨兵,看守着大地上的一切。
月光笼罩四野,收割后的田野里,金黄的草垛与爬满苔藓的凉亭对视。月色如纱,纯净得让人不敢呼吸。虫子与青蛙的合唱刚刚开始,顽强地和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喇叭对抗。我抬头,发现月亮就是一枚带着祖母体温的银币,俯视苍茫大地。一个夜行人提着一盏矿灯,从凉亭里钻出。灯柱晃动,黑夜便偶尔露出她莲藕似的赤脚。溪水复归平静,洗澡的顽童也该睡熟了吧。只有爷爷奶奶坐在竹床里,摇着蒲扇,一边驱赶结对的蚊子,一边谈论村口那家闺女的嫁期。
那匹安静的兽,遭遇现代行人遗弃的兽,孤零零站在原地。没有迎亲的唢呐从它胯下经过,也没有送葬的队伍撒下纸钱。经年累月,它与村庄维持一段固定距离。作为一个忠实的哨兵。它默默注视和认真纪录乡野里发生的一切。
门楼
门楼是一个村庄的身份证,没有它。你无法辨认自己的故乡。现在,水泥路也在村子里四通八达起来。那些阴凉的小巷全部死去,留下假模假样的砖混楼房。当你经过一座年迈的门楼底下,飞檐上的一蔸枯草提醒你,眼下的村庄正是曾经的村庄。所以,你必须记住——哪怕是一座老得驼背的门楼,他也能帮你找回那些曾经丢失的记忆密码。
西村的门楼便是这样。他把我的脚印挂起来,把我的咳嗽录下来,把我的哭泣藏起来。最东边的墙洞里有一块红色的石头,那是我从北山坑坝子上捡回来的。墙头草丛中栖息着一只绿色的蚱蜢,它的翅翼会发出“虎虎”的声音。小华的爷爷,々了寻找一夜未归的小华,在西头墙洞里放了一道符村人的犁耙、锄头、镰刀、扁担、簸箕,都曾散漫地倚靠这道门楼。
那道门楼就在蛇婆家旁边。她的丈夫是个泥瓦匠。常年在外头打工。蛇婆年轻时是很美的。难耐寂寞的她,时常引来一些老单身满眼的绿光。有几次。人们看见蛇婆将一个名叫金二的单身迎进门后,迫不及待地关门。金二醉酒后跟人说,哎呀,腥,真腥,那娘们。小华告诉我,透过门楼的洞眼,能清楚地看见蛇婆的一双大腿,连那些树枝样的青色的筋脉都一根根数得清。
我站在门楼左侧,阅读一张告示——近来发现有村民趁上山砍柴之机,偷偷挖了禁山上的竹笋。为了保护资源,根据村规,禁止村民挖笋。否则。发现一次,罚款五十。西村村民小组二00八年一月二日。有人愤怒地撕了告示的一个角。这样,告示便成了一个怪异的五角形。那人肯定是愤怒于这张告示的迟到吧,因为据说禁山里的竹笋已经被挖得差不多了。
现在很多村子没有门楼,走进村庄里。你根本辨别不出村庄的身份。瓦屋已经差不多坍塌、废弃,一排排粉刷一新的楼房,贴着光溜溜的外墙砖。村庄的名字只是标在简易地图上,一个小小的句号,表示一个规模较大的村子。它像个生硬的铁环,躺在一张也许布满灰尘的乡间地图上。
如果说门楼是一个村子的外套,那么,脱去外套的村庄在风雨的侵蚀下,全都失去了曾经的光彩迷人。裸露在行人眼前的村庄,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堡,脆弱得可以被风吹走。长驱直入的风四散奔跑,滑过墙角,跨越房顶,掀起家禽的羽衣,甚至撞翻摆在八仙桌上的青瓷海碗。我曾经到过一个村庄。那是一个小村庄。祖上出了一个历史上也算有点名气的武将,曾经跟随左宗棠征战南北,为清廷立下了赫赫战功。武将解甲归田后,为了防止外村人入侵,与乡
亲们一道在村子外构筑了一圈围墙,并按东、西、南、北方向设置四个气宇轩昂的门楼。宝刀不老、骁勇善战的武将,加上固若金汤的围墙,令不少异姓人望而却步。可是如今的村庄,门楼俱已倒塌,化为肥沃的土壤。祠堂前面的石狮子拴了母牛和它的儿子。刻有皇帝御笔的石板被洗衣妇捶击得面目全非。将军的坟茔在村外一片长势良好的棉田里,他的曾孙指着一片凹地告诉我们,这儿长眠着他的忠勇刚烈的先祖。知了在烈日的暴晒下拼命嚣叫,村庄的辉煌历史被时间无情埋葬。
门楼的背影苍老而腐朽,械斗的枪声和刀光了无踪迹。对于一座现代村庄而言,她的身份认证是水泥、天线、冰箱、网络和移动通讯。老迈的门楼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一些仿古式门楼却是那么蹩脚地出现在某个村庄的前面。仿佛一个尴尬万分的隐喻,为一段不可回溯的历史唱响一曲挽歌。
榨坊
它徘徊在村庄的外围,并用浓烈的香气将村庄熏得意乱情迷。在这种香味的挟持下,村庄的身子软得像一团洁白的棉花。
或许。没有一个榨坊能像安放在西村北部的榨坊那样。沉重地击中我的记忆神经。它倚住山脚,整天含情脉脉地俯视我的村庄。它的左侧,是北山坑水库。仙女漫步天庭时遗失的一块碧玉。我总觉得。用这样一汪碧波去灌溉山下的几百亩农田。是天底下最奢侈的事。四周青山都以这平静的水面为镜。默默注视亘古不变的容颜。站在榨坊前面的草地上,整个村庄尽收眼底。除了阶梯状分布的庄稼。便是坐北朝南的一排排的灰黑屋顶。一条灰白公路绕过村庄北端,伸向西部山坳。公狗与母狗在路边肆无忌惮地交合。牛躺在树荫下故作高深地反刍,鸡鸭的翅膀将灰尘扇得漫天飞舞……
榨坊的墙壁上刷了大幅标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那时候不知道谁是愚公,常常从字面理解——可能是一个愚蠢的老头。吃饱了撑着,还想移动一座大山,那山是一个人就能动的么?把牛赶进山里后,读着这句话,觉得可笑之至。后来上学,念到这篇课文,还是觉得不对劲。山挡住了出路,可以搬家嘛,为什么非要夷平它呢。这愚公也真够愚。榨坊里的工人可不愚,山再高关他鸟事。他们经常打牙祭,用浓香的菜油煮粉条。油是现榨的,有的是,所以他们并不怜惜,用大勺子舀了泼入锅中。再在上面撒点花椒或葱末,热气腾腾之中,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两颗起伏的头,听到呼哧呼哧的夸张的响声。我坐在门槛上,只有拼命咽口水。有时,打听哪家死了乳猪,榨坊老板(一个光头)便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有时免费,因为很多农户不吃死乳猪肉)。太阳将要落山,他们便将乳猪收拾干净,再用溪水反复冲洗。然后放入锅中爆炒,佐以料酒、辣椒、豆豉和蒜泥,我相信,他们的舌尖真是没有白长。
最好玩的当然是看他们榨油。夏天,他们通常穿短裤干活——是那种裤腿宽大的蓝色咔叽布短裤。长而粗的木槌垂吊在横梁下,随着洪亮的号子响起。木槌击打着楔子,菜油就一滴一滴地掉入铁锅中。光头榨油时,十分卖力,我们总能发现他裤裆里的东西剧烈地晃动。所以,他每一次抬起那个又长又粗的木槌,我们便盯住他胯下窃笑不已。有几次,他似乎觉察到我们笑声中蕴含的不轨,便用一杆竹梢粗鲁地将我们驱散。没过几天,我们照样聚集在榨坊门口,心照不宣地观看他的表演。
这个榨坊带了一间碾房。从北山坑水库流出来的溪水成了碾房水车的动力之源。水从一块宽大的竹匾内高高地冲向水车,水车便吱吱呀呀地转动起来。碾房里的石轮也就骨碌骨碌,循环往复地奔跑。菜油的香味足以麻痹一个人的思维,而菜菇(菜籽压榨后的残渣制成饼状)的香气更加令人沉醉。经常是这样,从榨坊里走出,分辨不出任何味道,因为人的嗅觉被那股诡秘的香味引诱得迷失了方向。
所以,榨坊永远坐落在村庄的外头,像一个怀揣无数诱惑的外乡人,它只能在孩童饥渴的目光中得到暂时的满足。大人都忙于农活。即便路过榨坊,也只是坐下来抽支烟,或者摘下草帽煽风。和光头开几句粗野的玩笑。之后,他们又扛着锄头走向另一丘田,光头却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似睡非睡。许是在咀嚼刚才的黄色笑话。
榨坊废弃后,光头回家种田。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葫芦也缩小了许多,再也无法看见那种大幅度晃动的壮观景象了。另一个伙计早已命赴黄泉。连同他非同一般的厨艺。
从榨坊身边走过,枯草自瓦楞间伸出无力的头。相比村庄的人声鼎沸,它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摸摸脑门,都能够扯下一大批气喘吁吁、日渐衰败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