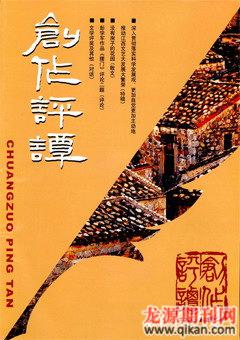绯闻,绯闻(外一篇)
樊健军
最初的绯闻是从春天开始的。一个叫左嘴的男孩站在窗口,向着寂了的雨夜喊出了第一声:XX老师和××老师唱被窝戏哟。他的嗓音沙哑,而且有了粗粗砺砺的厚度,就像他脚底的楼板一样。破旧又嘭嘭响。用楼下看门老头的话说,左嘴都做鸭公叫了。乡村的夜晚孤寂,空旷,再宏亮的声音也压不过雨声。左嘴的鸭公嗓音因此没能传得更远。很快被夜色消解了。
对于左嘴的叫喊,我,还有另外15个男孩,几乎没有人听得懂。他平常考试的成绩都在个位数,他的话却比课本上的古文还要深奥。比如他说的肉包子,比如他变着嗓子模仿的哎哟哎哟的女人叫声。我和伙伴们都以为他的脑子摔坏了,在胡说八道,他读一年级时摔过一跤,连嘴巴都摔左了。
因为听不懂,所以就没有人跟着瞎起哄。再说有我这个班长在,他们也不敢放肆到哪里去。几个胆大一点的,便披了破棉絮,在楼板上蹦来跳去,表演着左嘴说的被窝戏。谁知他们的表演不但没得到称赞,反而让左嘴笑歪了嘴,原本偏向左边的嘴巴又转向了右边。你们这帮猪。左嘴仆倒在楼板上,扯过一床棉絮盖住身子,昏黄的煤油灯下,那床被子便一起一伏动了起来。来,一个人做一遍,不做的“照旧”。示范过了,左嘴掀起被子从楼板上跳了起来。我明白“照旧”的意思,那就是谁不做就扒了谁的裤子,将他的小鸡鸡用墨汁染成黑鸡鸡。这是左嘴定下的规矩。几个被他“照旧”怕了的,赶紧钻到了被子里。那一次。没有谁违抗他的命令,15个男孩全部钻了一回被窝。
也许左嘴的叫喊是一道符咒。之后不久,村子里便开始流传××老师和××老师的闲言蜚语,比左嘴说的还要有声有色。前一个××老师是一年级的语文老师,短发,圆脸,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的歌很好听,教过我们的音乐。后来不知去了哪里。另一个××老师是三年级的数学老师,当年的秋天被调往一个更远的小山村。据说那所学校在半山腰,只有五六个学生,他是校长也是老师,还是煮饭的工友。
雨夜过后,整个乡野都在冒绿,一节一节的绿色竹笋一样往上蹿。我们似乎也在疯长。那些窄窄的棉袄,紧绷绷的棉裤,怎么也裹不住正在发育的身体。左嘴好像蹿得更快一些,操场上的篮球架,只要轻轻一跳,他就能摸到篮板。他的喉咙也起了变化,那里像是结了一个核,唇边也泛起了一圈淡淡的黑色。几个同他近乎的孩子找到了笑谑他的借口,说他的嘴巴像个老鼠洞,整天嚷着要帮他拔掉洞口的野草。死伢崽,你懂个屁,有了它们我就是大人了。左嘴对他们的玩笑不屑一顾。
事实上,春天来临之后他就很少同他们在一块玩了。他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条壕沟,再也没有那么多话要说。课余时间也很少能见到他了,有人看见,他常常跑到附近的一片田野上去。甚至有人撞见,他同一个挎了背篓的女孩子一起,在一个土坎下走来走去。还有人看到。他同一个三年级就辍了学的同学在一起。那个同学辍学后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有了一个半岁的女儿。他们坐在河滩上聊了整整一个下午。谁也不知道他们都聊了什么。后来的每个晚上,左嘴似乎躲在被窝里偷偷干着什么,有时动静还挺大的,楼板也跟着直颤悠。偶尔走近他睡的那个角落。还能闻到一股说不清楚的暧昧气味。
夏天转眼就到了。它的热度让我们对水有了一种深切的渴望。每天的傍晚,那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弦子们可以在老师划定的一片水域尽情嬉戏。我们一个个光着腚,赤身跳入水中,来一场真正的裸浴。那时候还不懂得羞涩,发育的青春离我们也好像遥不可及。老师要求我们同去同回,谁也不许提前,更不许落下。只有左嘴是个例外,同谁也不搭伴,一个人静悄悄地去,又静悄悄地回。后来,他还更改了洗澡的时间,中午一个人偷偷溜到河滩上去,晚饭后却销声匿迹,谁也不知他上哪去了。
几天后,就有人发现了左嘴的行踪。他躲在校舍后的一扇窗户下面。那个孩子看到他时,他正踮起脚,贴在窗子上向里窥视着。窗子完全被木板封死了,根本不能看见什么。那是女孩子的浴室,这幢孤独的校舍里除了17个寄宿的男生外,还有4个女生。老师就用木板在一楼隔了一间小房子,给女老师和女生当洗澡间。也许左嘴在窗台上并没有窥视到什么,很快他就变换了一种方式。有一次我偶然上楼。正巧碰见他趴在女浴室上面的楼板上,用一个钻子钻着楼板。那些女生也是敏感的,待她们发现时楼板上早就有了拇指粗的一个洞。从洞口往下看,浴室一览无遗。楼板上的洞很快被钉死了。老师们又虚张声势调查了一番,但没查出什么结果。也许他们并不真想有结果,这帮孩子离校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他们不愿在这种时候生出什么事端。
事情过后,校舍里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老师们却暗地里紧张了起来,女生寝室住进了一个女教师,傍晚时分女生浴室门口还多了一道岗哨。男孩子下河去也有了一个男教师领队。有了老师监督,孩子们玩得就不痛快了。河湾里一片死寂。有孩子耐不住寂寞,中午便偷偷溜出去玩水,但很快被老师察觉了。罚跪,训斥,写检讨书,甚至威胁开除退学,结果都没起到什么作用,仍然有孩子偷偷往河湾里跑。后来,老师们想了一个绝招,将孩子们脱在河滩上的衣服抱了回来。那几个偷偷玩水的孩子,只得光着屁股瑟瑟缩缩回到了操场上。老师们让他们来了一次裸体示众,几个人捂着小鸡鸡在篮球架下站了半个多小时。原以为再也没有人敢溜出去玩水了,可没想到三天后的一个中午,老师又从河滩上抱了一个人的衣服回来。老师站在篮球架下,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个他想象中的裸体并没有出现。老师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叫上一个孩子到河难去看看,但河湾里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
左嘴是半下午捞上来的。上岸的时候仍是赤身裸体。也许是在水里浸泡得久了,他的身体一片惨白。他被抬到操场上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他的双腿之间,竟然有了一片黑色的丛林。那一瞬间,我的内心突然充满了恐惧,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他那样,有那么一片丑陋的茅草地。
旧色小巷
进入巷子的时候,我总怀疑自己走在时间的末端。——那是一天中后来的黑暗,如果有星点,必定是稀疏的,就像一根吃剩的玉米棒子,或有几粒漏网的玉米。
这种联想对自己似乎是个暗示。
一个人相对于一条巷子,同一粒玉米相对于一根细瘦的玉米棒子,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只是玉米自始至终都在离开玉米棒子。而我呢,此刻正一步步深入一条巷子,回到一条巷子的中央。
我记得的小巷几乎都是这样子——它们同乡村集市的一条老街多么相似,一样颓旧的颜色。一样残存的建筑。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去式的,早被风雨洗刷得一干二净了。只有从高不可攀的风火墙,墙头翘耸的飞檐,飞檐下雕花的窗棂,以及窗棂两边砖雕上的图案,依稀可辨昔日的繁华和荣耀。而现在,这一切不过是我的假想,它们早成了明日黄花,美人也在风烛残年了。
一个人走在这样的巷子里,有着更多的不真实。无论用眼睛看到的,或者用耳朵听到的,它们都被岁月之手
扭曲,绞碎,搅乱,如果还能勉强凑合在一起,说不定也早被移了位,重新组合过了。就像地上的一块青石板,缺了一角,有可能也不是今天的位置。这样的时候,只有心能派上用场,用心看到的,用心听到的,那才是被遮掩了的真实。你似乎看到某个拐角处一闪即逝的背影,窗棂上红白的窗花,以及屋檐下的灯笼,和红铜的风铃。甚至能听见某个院落里二胡的乐音,素素淡淡的清唱。
这样的行走不再是身体的位移,而是心在浮动。它有了蝴蝶一样的翅膀,燕子一样的羽翼,有时越过一堵残破的女墙,有时则穿过洞开的窗棂。更多的时候是落在某扇木门的铜扣之上。它就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它看见了眼睛没有发现的物象,听到了耳朵没有感觉的声音。
某个夜晚,我从灯火辉煌处回到了一条巷子。那是一个容易恍惚的时间,我立在巷口,我的眼前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我要回到黑暗中去,我要被黑暗一丝不剩地吞没。那样的黑暗正是我喜欢的,它飘忽,游离,有了白天不可得见的动感。甚至,它更多的不可预见的潜在也是我喜欢的。我摇摇晃晃进入了一条巷子,进入了一片彻底的黑暗。
其实,那条巷子是我熟悉的,黑暗也是我熟知的。我无数次从那条巷子中走过,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两个人。那青砖的墙,墙脚下的花岗石,以及石头上模糊的浮雕。不用看。也不用抚摸,它们在黑暗中的姿态我都非常熟悉。但,那一个晚上,我走进巷子没多远就觉察了异样。我嗅到了绿色的气息,那不是花草的气味,而是另一种别的味道。走错了。我对身边的人说。没错,就是这条巷子。身边的人回答。我抬眼看了看头顶上的黑暗,那里有淡淡的光线。借助微光,我看见巷子的空隙被一片叶子覆盖,我还看见叶子下坠满葫芦状的东西。我朝天嗅了嗅。那别样的气息就来自于那片葫芦状的绿色。再往前走不到十米,拐一个角,我就到了一扇积满红锈的铁门前。
那个晚上我差点被一条熟悉的巷子骗过了。
我居住的小城共有18条小巷,都是南北走向。18条巷子有着18个被旧色浸染的名字,如铁炉巷,当铺巷,拖尸巷,余家巷,等等。它们的命名也很简单,铁炉巷是因为铁匠铺子,当铺巷是因为当铺,余家巷是因为余姓的人家,只有拖尸巷有些让人恐怖,据说是“五鬼”——杀头的,上吊的,喝毒药的,溺水的,难产死的,他们死后都由这条巷子出城。在这个有着十多万人的小城里很少有人会谈及它,不知是因为它的阴邪别人不愿提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特意去拖尸巷走过一次,那已经不能算是一条旧式的巷子了,它的一侧完全被现代的高楼所取代,而另一倒也是杂乱的一片,残垣断壁,瓦砾遍地。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进入别的小巷的心情。我去过十八条巷子中的任何一条。午后,或者黄昏,我喜欢一个人在我所偏爱的那几条巷子里行走。那种沉静,寂寥,也只有在巷子里才能体会。一个人的脚步声,一声,一声,像散落的雨点叩打在芭蕉叶上,是一种静静的空脆。它落在青砖的墙上,细细地,碎碎地,像常青藤一样蔓延。我的前面,后面,都有了类似的脚步声。那样的声音很容易让人沉醉。一个人走着,走着,就不知自己走向了哪里。
有些遗憾的是,就像拖尸巷一样,纯粹的小巷已经不存在了,我只能行走在一些旧色小巷的片断里。
一条巷子中央有这么一截——不过三五十米,低矮的木板房,黑的瓦脊。都是一些旧式小店。一样敞开的店门,一样褪色的招牌。有冥纸店,碑刻店,裁缝店,剃头店,白铁店,十几家店铺没有一家相同的买卖。他们谁也抢不了谁的营生。那是一条巷子的《清明上河图》。打金店的皮老虎喷着蓝色的火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捏着一把小锤子在敲打一根金链:白铁店内是一大一小两个男人,一大一小两把木锤子,一大一小两口白铁锅,浑厚的锤音,银白的弧光;碑刻店里是一个老头儿,弓着腰,上身俯在一块青石上,一锉一锉,一撇一画都是周周正正的楷体:再过去就是冥纸店,土黄色的纸,火红的鞭炮,还有些五颜六色的冥花,是另一世界的热闹:后来就是酿酒店,它的门口常常坐着一个老头,一个小杌子,一只白瓷酒盅,他的身后是几只暗红的大酒缸,瓦制的,像罗汉的肚子,露着酒晕似的一抹红光。碰上出锅的日子,便是满巷子的酒香,厚厚的。有如巷子里某片青石上的青苔。那样的日子,一个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会醉了,常常在酒店门口转来转去,像是被酒气吸住了,怎么也走不开。
还有那么一截简单的巷子——简单到只剩下两堵墙,青砖的墙,七拐八扭,能够看见的只有墙的背影。地上是青色的石板,长方形的,一块连着一块。眼看着到了尽头,转个弯,又是青溜溜的一片。进了巷子,就是一个寂静的世界,外面的一切声响都离得远了,能够听见的也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如果在雨天。就是戴望舒的雨巷了,那个撑着油纸伞像丁香一样的姑娘,又走在这条巷子里了。也许在前面,某个拐角。就能看见她的背影,像丁香一样轻轻浅浅地浮动、这样的画面终究是一种想象,抬抬眼。巷子的天空都被青瓦覆盖了,即使是在滂沱的雨天,走在巷子里也用不着油纸伞,所有的雨水都顺着青瓦流入了另外的方向。只有瓦脊上的雨声,一声一声,声声入耳。
最后的一个去处是另一条巷子,一条由土墙构成的巷子。巷口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从一道窄窄的木门进去。从外面看,以为那是一处房子的入口,绝想不到是一条巷子。巷子很窄,勉强通过一个人。也许是年月久了,土墙都染上了一种暗色。蹭一下墙壁,就会有土末飞扬。我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误入巷子的,,我要去一个地方,以为穿过它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巷子里阒无一人,只有一线阳光落在地板上。它就像一块路标,将我一步一步引向深入。转过三两个墙角之后,就见着了一个院落,低矮的土墙,敞开的院门,眼前豁然开朗了。院角是一棵树,枝繁叶茂着,是一种绿色的喧嚣。房前还有几株花,像是美人蕉,火焰一样开着。那样小巧的一个院子,静静的,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满地浓浓的阳光。我立在门口,没敢进去一步。我担心我任何的一,最响动都会搅碎这彻底的平静。那一刻,我失魂了,我的灵魂就迷失在那样的平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