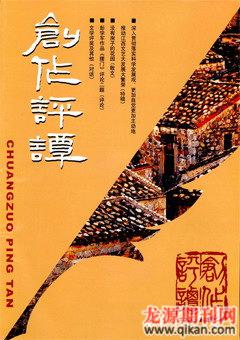记得当时年纪小(外一篇)
周 冲
我家有一面台镜,是母亲的嫁妆,长方形,边框镶着赭色的花卉鸟雀,棱沿突起处总落着厚厚的绒尘。因为年代太久,镜子后的水银陆续剥落,以至于现出的影像越来越迷蒙。然而尽管迷蒙,我还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后看清了自己那副粗鄙的形容——钝身子,糙皮肤,大手大脚,脸盘上粘着几粒深浅不一的褐色斑痕,仿佛鸡蛋上内容不明的污渍。
我颓然坐在地板上,一种剧烈的失重感令我深感绝望。幽凉的光线透过生满铁锈的窗栅栏透进来。在地板上匐匍移动。对面的几件破棉袄随意地搭在木椅上,散着怪异的体味,椅脚生着霉斑,旁边垂挂的蚊帐上沾满大块蚊血,青底白碎花的棉被倒是叠得整齐,方方正正,可惜更加地显得索然无味。
那天傍晚,我爆出一场恢宏的哭声。没有人知道乖顺的我何以会忽然地不可理喻。在我母亲看来,也许我只是没吃到一块冻米糖。或者丢失了一枚心爱的塑胶发卡。
我开始远离那个暗仄仄的方镜。梳头,穿衣,都潦草得很。不再想去寻求侧面的证明。可是,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讳疾忌医只会使我更加敏感,丝毫帮助不了我逃避内心里深刻的自卑。与此同时,我的性格逐渐出现一些负面的端倪,呆滞,木讷,口拙,见了生人窘迫不堪。
有一回我一个表姐来我家,其时她是一个丰硕的大姑娘,脑门上常绷着一个白发箍,牛辕一样勒住凸起的额骨,头发捋得贴贴的,露出一张山河浩荡的脸,看起来气势汹汹,这自然让我惧-怕。当她俯下身来和我说话时,我在惶惶间涌上一种模糊的心绪——也许,我应该向她表达一些欢迎之意。然而,我嗫嚅了半天,只逼出几个字:“你来我家,我就去你家!”仿佛拗气的口吻,我自己都要心生疑惑与不欢。表姐果然意兴阑珊,怏怏地走开了。
我独自在原地木着,秋日早来的阴凉铺开在那个六七岁的天空里,一朵血红的云朵沉沉地落下山岗,北归的大雁掠过,在光线的末梢霍霍飞翔。我在心里涌起浩荡的羡慕,它们多么好,它们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美貌,它们只需要一个方向,就可以恣意飞翔。
有一年秋天,村口的水井干涸了,村中的男人们纷纷下去捉鱼,我父亲也挤在一堆高高凸起的屁股堆里,挽着裤腿探着长臂在水间乱摸。我很是担心他会摸到一条水蛇,或者螃蟹,但父亲是灵巧而熟稔的,他每每从浅滩中直起身来,手上便是一把银光鳞鳞的大收获。
“你不要动。看好了!”他把跳动的鲫鱼黄鳝放入我手中端着的洋瓷盆里,叮嘱我说。我点了点头,俯头紧张地看着那几条长着灰黄细斑的黄鳝,很怕它会像蛇一样爬出来,爬到我的表裳里,或者是钻进我的内脏——这可真令我胆战心惊。
邻家的男孩走过采了,他们闪着精亮而滑头的眼睛,卷着裤腿,拎着叮当作响的小洋铁皮桶,也来给大人们做后应。我一阵恐慌,生怕他们又来欺负我。果然。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时,不由分说就把盆中的鱼尽数抓走,然后怪笑一声跑开了。我当时竟然不知道叫喊,更不知道追赶咒骂,只知道端着那一盆浊水木然立着。许多年以后,我一直觉得愧对父亲,他躬着腰背在井滩间辛苦忙活,自以为硕果累累,却不知道他笨拙可怜的女儿将之悉数丢失。
我的父亲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只木薯,以后只配嫁给隔壁岳三这样的人。”岳三是一个憨厚到愚蠢的农人,惯于农活,终身未娶(他未娶可不是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只是因为没有姑娘愿意嫁他,哪怕是山野俗妇)。每天天微亮,他准时赶着一头浑身癞斑的老牛经过我家门口,牛和人的脚步均是沉沉的,敲着清白的谷坪。那时公鸡正从笼中出来,在院落里盘旋了一阵,飚出一泡稀屎,他的破解放鞋踩上去,继续前行,留下一路愈来愈浅的青黑的湿渍。有时我去井边打水,遇到他经过,总是立马别开脸,仿佛多看一眼,就为父亲那个可怕的诅咒的兑现多设了一份可能。他自然不知道我的忌讳,只低着头,紧闭着黯紫的嘴,痴痴地看着那头老牛一路嚼咽——牛和人如此相似,吃草,睡觉,干活,麻木地轮转,一如无知无觉无望的植物。
我怎么可以与那呆板乏味的人扯上关系?他那么可怜,那么卑微,而我呢?我的未来尚未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然而,这种未知也让我战战兢兢,我如此恐惧命运将对我恶意作弄,或者平庸如他,或者粗鲁如村妇,那么,就真有可能应了父亲恶意的咒语。
就在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我更加紧张,并且丧失信心。我学会自虐,年少的身体上印满青瘀,像瓢虫的黑点盘踞各处——那真是一种可耻的斑痕。我的母亲奇怪我为何再也不让她帮我洗澡,后来,她给了自己好答案:女儿长大了,对自己身体有了羞耻之心。
我如同责罚一个憎恶之至的敌人一样攻袭着自己的脸蛋,大腿,以及任何能让我疼痛的地方。掐。拍,擂,后来发展到用工具作案,用针刺,用绳索勒,以至于我的手常年累月的冰冷惨白。麻木僵硬。有时候我找来细竹棍,模仿教师鞭打自己的手掌,打一下,骂一声:“周伶俐,你真蠢,周伶俐,你真笨!”肉体的疼痛能让我暂时忘却内心强大的灰暗。那一刻。我仿佛获得某种平衡,稍稍心安。
然而,这些安妥如此短暂而阴晦。回过神后,我仍然处于一个孤独而窘迫的境遇。我没有朋友,只有一个粗糙的小布偶。那是我自己用布条子做的,我给它取名叫“小玲”,我带它去河湾看芦花。去山岗捉蝴蝶。
我坐在草地上对它说话:“小玲,你喜欢我吗?”
“小玲,春天的时候,我们去东山看桃花吧!”
“小玲,今天老师又让我罚站了,因为我没有回答出七加七等于几……”
邻居家有一户人家,生了三个女儿,留着长头发,穿着好衣裳,在我的眼里,电影明星也比不上她们好看。我很害怕失去她们的友谊,于是对她们言听计听,甚至卑躬屈膝,仿佛乞求。去山野采野果,挑出大而红的全交给她们,自己只留下几个零星的青涩的小果:玩游戏的时候,她们做警察,我做小偷;还让她们用紫酱果涂满我的脸做魔鬼,或者扒下衣服任她们双手粗鲁地检阅……可是忽然有一天,她们不和我玩了,我坐在深幽的堂屋里,望着她们欢笑着走过家门口,内心充满苦涩疼痛。
我终于屈服于我的自尊。我在爷爷的园子里偷了几个大橘子,顶着烈阳走到她们家,递上青实的供品。我说:“和我玩好吗?”她们接受了橘子。我以为,她们与我和好了,没想到几天后,我又被遗弃。黄昏时,我站在一堵长满青苔的矮墙边,望着那个朱墙碧瓦的院落长久哭泣。
念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叫付芬。那是一个早熟而沉默的女孩,个子高,眉角有一大块烧伤,有着动物内脏般的色泽与皱褶。我母亲说我们两家是亲戚,可我实在记不清那迂回曲折的血缘,一直只把她当普通同学来看待。
我与付芬并不要好。悲哀者与悲哀者在一起时,仿佛在自己对面立了一面镜子,所有不如意昭然若揭,连逃避都没有余地。
那时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女生,她们无一例外地顶着一头白虮子遍布的黄头发,穿着草浆与油渍交错的破衣裳,泼野,爱饶舌,在教室里搬弄着种种是非。后
来,不知怎的,她们决定要孤立付芬,二十多个人密谋着一种单纯而恶毒的小伎俩——从此,不和付芬说一句话,谁若说了,便是叛徒。我自然是不敢敌对的,也答应加入那个同盟。
从那天开始,付芬便开始独来独往,头勾得很低,以至于她年少的身体提早出现驼背的迹象。裸着红砖的厕所与围墙上出现了无数条白粉笔或者黑炭写的污秽的句子:“付芬是条狗!”“付芬和王强搞××”……我没有写。因为我能感觉那个单薄的影子后无奈的悲哀。我为此深感同情,但我还是不敢和她说话。相比于正义,我更害怕自己受伤。
可是,终于有一天,我不得不打破那个盟约了。因为我的母亲三申五令地警告我,让我一定要带话给付芬,请她的父亲速来我家商量一件迫在眉睫的重要事。我在百般推阻无效后,赴死般上了学。事到如今,我依然记得那天清早我站在嘈杂的村小门前,法国梧桐压下大片大片的阴影,阴霾般压在我身上时我的绝望。
第二节课间。付芬趴在那个碎布百衲的书包上,头勾着,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一丛无精打采的黄头发。我们的桌子相隔不到两米。然而,这距离却仿佛成了刀山火海。我步步维艰。不过,最终我还是走过去了,轻轻地磕了磕她的桌子,她应声抬起头,惊讶与喜悦布满她的眼睛。与此同时。教室里其他二十多双警惕的目光也开始盯过来。
“我妈说,叫你爸来我家一趟。说有事。”说完,我便赶紧避邪般逃开了。
到了下午上学的时候,如我所料,围墙的红壁上多了一行歪歪扭扭的白粉笔字,内容与付芬的一模一样,只是主语换成了我的大名。我的心里轰然一声,我知道,她们把我从联盟中除名了。从此,我也成了一个异类,不仅受着她们刻意的孤立,还有种种来自于她们自造的污言秽语。
有一天傍晚,我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几只老鸦在死寂的梧桐树上扑棱着翅膀,间或发出悚人的哇哇声,一扇生着红锈的老铁门在疾风里吱呀而旋,仿佛垂垂的叹息。我就在这些沉郁的声音里低着头,专注地计算着自己的步子,当走到散着尿臊味的围墙拐弯时。一抬头,忽然发现墙根处俯着一个熟悉的人影。她弯着腰身,正在努力着什么。我走近去,渐渐把那人看清了。是付芬!其时她正用一团废纸擦拭着斑驳的红砖,硬考考的纸张与砖块摩擦着,有令人不快的嚓嚓声。我仔细辨认,发现她擦的全是那些女生们写下的关于我的污言,那些曾经触目惊心的粉笔迹渐渐化成一团模糊的白晕团,好像一场潦草的告别。
我那时被一种意外的松弛和感动侵袭得透不过气,但因为一种年少的卑怯。我竟然更加地想选避——这仿佛是一种预见,我直至今日亦是骇怕与有恩于己者面对,唯恐我拙劣的话语玷污了那份至洁的情感。
第二天上学,我再也没有在那堵墙上发现我的姓名,但令我不解的是。付芬的名字却一直赫赫地凸现其上,与一些生殖器官名和女性长辈称呼一起挤着挨着,像不能割弃的耻辱一样印在那些年少的时光里。
然而,最终的结局与童话故事里的情节相去甚远——付芬和我并没有因此开始惺惺相惜,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们仍然远远地观望着彼此,又怜又嫌,像看到自己。甚至年节里去奶奶家拜年,我们也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互不搭理,以至于长辈们甚是惊疑,怎么两个孩子同级同班,却形如陌路?
那个漫长而可怕的事件之后,我开始排他,疏离任何人,也被任何人疏离,哪怕是我的父亲母亲。但我开始心存好愿望,喜欢独自发呆,幻想。奔跑。与自己玩乐。秋收后的田野里堆着高高的稻秆垛子,像布拉格的古堡一样伫立在天空下。而我呢,我就是一个被囚禁的小公主,忧伤而华丽地奔跑着,稻桩轻轻扫过我的脚踝,带着草汁甜味的凉风摁着我的衣衫,我挥动手足,想象自己身轻如燕。一跃而起。飞到轻而亮的天堂去。奶奶说过,天堂是没有人的,只有神。和长着翅膀的天使。他们幸福而强大,他们不需要群体。独来独往,面含微笑。
冬天的早上腻在被窝里,不穿毛衣。也不动,只睁开眼睛,定定地看着楼板上不规则的斑痕。直到那些斑痕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变成人,变成风景。变成美妙的传说。我沉浸于此间,忘记母亲催起的呼唤。
如果入了夜。晚归的摩托车呼啸经过,车灯透过木槿花丛投在对墙,参差的黑影便缓缓移动。我总是屏息看着。觉得那是最美妙的影像。仿佛一场黑白电影正在开始,小伙子跟着吹吹打打的唢呐手与铜锣手,经过一湾浅浅的树林,去接一个从未见过的新娘。馋鬼的小孩在路边唱着歌:“新郎新娘。大红衣裳。成亲拜堂,快发喜糖”……
厨房里放着几只洋铁皮的开水瓶。猪肝色的底调上绘着沉甸甸的绿叶红花,可惜漆掉得七零八落,铁灰的底色露出来,斑驳的,一如生着癞疮的脑壳。瓶盖也被磕碰得瘪头瘪脑,全然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但那却是我眈眈而待的宝贝,母亲总是藏着。怕我又拿去烧得糊涂。我总是百计千方地伺机偷走,装上油盐,又拿去煮蘑菇腊肉,或者豆子花生。
秋天的田埂安安静静的,只有不知名的昆虫啁啾着,阳光俯下身来,摸摸我的脸,它有一副温柔的好声音。它说:“你好啊,我可爱的孩子!”我没有应它,我专注地趴在一个小土堆旁。抠出小灶洞,塞上干茅草,扑哧一声划亮火柴。映亮那双干涸而寂寞的眼睛。
艾地之冬
我一直不知该用什么笔调来描绘艾地的冬天。
太浓重了,唯恐失于呆滞;太空灵了,唯恐失于轻佻;太华美了,唯恐失于堆砌;太朴实了,又唯恐失于陈腐。既然一切矫枉过正都有用力的嫌疑,我还是做一个诚实而稚嫩的画者,试着给这个正在俯吻我的身体、交合我的思绪的冬天以一次拙劣的素描。
是的,艾地的最后一个季节,是从一场雨开始的。
那是一场孤傲清绝的雨,从永不干涸的水塔般的天空落下。不徐,也不疾,落满荒漠的田野,枝头。檐楞屋瓦,以及人的发肤。世界潮湿得发黏,所有的时间与念想沾上浓重水分,在渐降的气温里结成霜花。人向任何一个方向呼吸,都是一股水分浓重的冷气——空气终于成了冰汽水。
好在几天之后,雨终于停住,一个水淋淋的清晨从纯净的山峦上升起,阳光依然如故,艾地的雄鸡喋喋不休地赞叹白昼的荣光。然后。冬天正式占领了整个大地,所见的,所闻的,所感的,都成了冬天的家族成员。
天空,充满了汲取不尽的温暖与光明。无论六月。还是十二月。它投下的每一道光,天真无邪,照出人间最细最疏的经纬,屋落的轮廊,树木的形容,山川河流的举手投足。大地从一片光明中冒起,虽然霜花正在融化,虽然梧桐正在离枝。人们重整衣装,走入另一个清冷深邃之境。
散步者再也看不到翻滚的麦浪了,他们在石头和枯草问穿行,寻找一丛迟谢的白山茶。山茶在秋后开花,次年春天才谢。像是大无畏的探险者,深入极地,探知生命的终极密码。偶有晶莹的露珠落在上面,在阳光来临之前挥发。然而这点晶莹没有消失。它与花朵一起在人的心里被思念。
梅这个冬的形象大使不愿意呆在小城,她忙于应
酬,忽略了我们的渴望。然而,一朵菊唱出前奏,紧接着月季与别的杂花一齐发出和声,带着欢快的杂乱和无限的陶醉。树苏醒过来。轻轻颤动,太阳仿佛站住了。气温的低落被忘记。
在这个冬阳照耀的平原上。还有水,冒着热气的冬水,生着绿得炫目的绿萍,水面打着旋。一池幸福的碎波涛。艾地之南有一弯湖,可泛舟,也可垂钓。浅舟泊在阳光里,船上人仰面躺着,身边是一只黑色的半导体,正在流出本地新闻摘要,和由一个苍老跌宕的声音讲述的长篇评书。白日在湖水上照影。人们从水边经过,携着伴侣,或者独自前行,闻见一种纯正而清澈的气息。
村庄的溪水是不知时间的,它们我行我素,固执地流淌。妇人在岸边洗衣,丝织品堆在白浣石上,面容温淑。她身后村庄里,无声无息,只有轻烟正在屋顶上轻轻飘起来。
屋子的角炉里正燃着干枞木,灿亮的火苗舔着烹煮红薯饭的黑炉罐,空气里飘满松香与薯饭香。他们在灶台前准备竿饭,红焖棍子鱼和熏豆腐。未等食用,一屋子的辣香,就先让人热烘烘起来。孩子放了学,从堂前溜进厨房,抓起一块红烧肉就啃。姆妈揪住他的耳朵,连声骂:“不洗手就吃,不晓得干净龌龊么?还有,衣裳怎么只穿这么一点,贱骨头不冷吗?”孩子龇牙咧嘴,更加争分夺秒地咬嚼着嘴里的食物。
门口种着的银杏早已染金,朔风一起,落下叶来,宛若美人的金扇坠地。雨过,墙根院落之处,尽是灿烂。梧桐早已秃了,不管江湖纷争,进入冬眠。不远处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幕阜山,像一座披满苔藓和灌木的神灵。庇荫着山脚下的子女。
这时节,爬行动物大都入洞,然而地面上活动着的还有更多生灵。
家狗在路边行走,穿过一个肉铺,两个小杂货铺,以及三五丛人群,在一堆石块前蹲下,目光游离。和身边几株光裸干枯的杨树一样高深莫测,令人不可捉摸。
天空中有大雁在飞。这种居无定所的生灵,像为理想而生的流浪者。它们变换队形,给善感的眼睛表演群舞。我想起幼时念的课文,“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那些完美轨道,给天空划上明亮的纹线。我们总是容易产生错觉。大雁是一群聋哑艺术家。因为它们飞行时发出的鸣叫与翅膀掠风的簌簌声,被喧闹的人声所掩盖无疑。不过,这也接近神的隐喻,最完美的作品,往往无需声音的画蛇添足。间或有一两只麻雀,跳到空白的谷坪上来啄食,,它们胆怯,聒噪,一年四季不变模样,仿佛春夏秋冬都不曾发生。
然而冬天的白昼以前所未有的迅疾之势,带领我到了夜晚。
夜是适合沉溺放肆的。酒是最好的催化剂。当白天的回光还在逗留的时候,油黑的餐桌上早摆上家酿的谷烧,还有米酒,倒上一碗,就着简单菜蔬,亲友对饮几巡,就能触到四面八方吹来的暖风。路口的小酒店里。青年与姑娘彻夜长谈,把一年中最漫长的夜晚看成稍纵即逝。
冬夜里出来看月亮,山头一片净明,月亮在绛紫色的天空中散发白光。四周渺无人声。只给月与人留下私密场所。有人在孤独的夜晚唱歌,唱“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歌声仿佛浮在冰面,水气充盈又清亮动人。拉开窗帘,月还未谢幕,星星也仍然在交头接耳,编排着一个个神秘的传说。
门前的水流在拂晓前抑低了它的声音,悄悄把水气收拢,升华,弥漫。然后就有了雾。清晨凝固了,天地仿佛回到盘古挥斧之前,人们成了母体内的婴孩。朦胧一片,却有着妥帖的安全感。他们说:啊,我好像到了仙境——因为糊涂,总能感到一种容易满足的快乐。
雪是天堂撒下的梨花。
这无言的飘逸的一群,被宠幸得近乎骄傲,拿捏起身架,轻易不肯赏脸。然而,一场北风过后,它们以优雅而浩荡的姿态,跟随巨大的冬天姗姗而来。山峦与村落皆莹莹然。仿佛刚上了粉妆的脸。阳光从山岗流下,又给稀薄的雪染上了一层金红的胭脂。水在雪下轻歌,以一种不为人知的声音,但种子与根蔓听到了,它们笑了笑,转个身子又酣然而睡。待到春天时再惺忪醒来。
我想,艾地冬天的深度广度远非于此。然而,我相信一种艺术是讨巧而服众的:留白。对于一个手掌还不能完全听从眼睛和大脑的画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一来藏拙,二来留下空白,给宣纸之外的内容以无限发散的可能性空间。那,我也学着明智一回吧,放下画笔,交上这一幅并不完整的艾地冬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