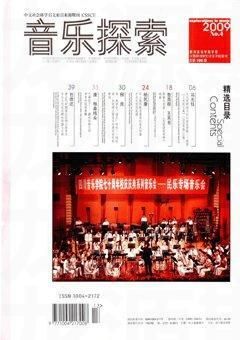夷夏音乐“涵化”研究
柳 良
摘要:历史上的南、北丝绸之路向我国中原地区输送了大量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文化特征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唐代达到了高峰,并延伸到宋代等朝代。由于丝绸之路沿线胡、夷颇具异域色彩的各民族音乐不断融入传统的中原华夏音乐,大大丰富了后者的音乐内涵,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变。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涵化”角度出发,着重探索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中胡、夷外来音乐对中原华夏音乐的影响,以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一涵化过程中的表现意义。
关键词:涵化;南北丝绸之路;夷夏音乐;唐宋时期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4-0030-03
“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人类学中有关文化交融而引发变迁方面的研究内容。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下的定义为:“由于个别分子所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持续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现象。”{1}法国人类学家瓦施忒勒认为这是“系统地研究不同文化在接触之后所产生的互相影响的种种现象”{2}。涵化也就是指不同民族因接触、交流、吸收而引起原有文化内涵的变迁演化。涵化研究则是研究不同民族的交融而产生的文化变迁过程及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对于外来文化,各民族只要发现它有适用性,又有可接受的条件与环境,就会很快将其吸纳,并通过各种途径对其予以传播。
在我国,自汉、唐达到高峰并延续到宋的第一次各民族音乐文化大融合,就是一个重要的涵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依托于丝绸之路这一重要渠道进行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北丝绸之路;而早于此两个世纪前,在中国西南地区,沿川、滇地区一线越过滇南、缅北热带雨林而达缅甸、印度直至中亚,已先期形成一条南方丝绸之路,由于后来另有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川、滇一线这条丝绸之路又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陆路。正是通过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中原华夏民族与丝绸之路沿途的众多民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政治、经济、科技、艺术、习俗等各方面的接触与交流,后者将大量的异域文化输入到中原地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特征和内涵,导致新的文化属性的诞生,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涵化意义。
“夷”或“蛮夷”,为古代对相对于华夏民族的四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有时也专称南方少数民族。至汉、唐时期,又称西域各族为“西胡”,因此西域音乐也被称为“胡乐”、“胡声”。《旧唐书·音乐志》中曾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法曲歌》中表达对外来音乐影响华夏音乐的担忧时提到“不令夷夏相交侵”{3},本文遂以夷、夏音乐的概念,泛指包括南、北丝绸之路上各民族音乐的胡夷之声和中原华夏之声。在丝绸之路文化繁荣发展的推动下,夷、夏之交带来的涵化现象愈演愈烈,至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并一直延续到了宋代以至更远的朝代。
中国历史经南北朝开始加快民族融合的步伐,当时西北边地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几个少数民族内迁后建立了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互相对峙、抗衡长达300余年。虽然这300余年征战不息,但是却为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大交流成为历史必然。中原内地诸如乐舞等原有的音乐文化,受到了从丝绸之路而来的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如被唐宋时期称为“前世新声为清乐”的“清商乐”,就已融入了西域的胡乐胡舞。到唐代,经过贞观、开元之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人的思想也极为自由、活跃、开放,引来唐代乐风中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构成了大唐多元的音乐文化局面,奏响了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盛唐之音”的音乐发展高潮。
在唐以来数百年的发展中,南、北丝绸之路为之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涵化所需的各种艺术原料。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各民族音乐家为数众多,他们带来了大量新的乐器、技法、乐律、乐舞、乐谱、乐曲、歌曲以及戏曲等丰富的形式。它们在与中原既有的音乐文化碰撞、融合之后,形成了席卷朝野、影响深远的一代新乐。引人注意的是,在唐代的这一新乐中,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外来音乐所占比重甚至已超过了传统的中原音乐,社会音乐组成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唐天宝十五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燕)乐”。但是,中原已有的雅乐已变得不重要,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乐县操雅音,雅乐替坏一至此……”{4}。清乐的情况稍好些,但武则天时期清乐还有63曲,不久只剩下37曲,也逐渐呈衰退之势。而与雅乐、清乐成对比的则是胡夷之乐的被重视——“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首,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见《隋书·音乐志》)。
在唐朝贞观十六年所设的“十部乐”中,属于中原传统领域的只有清商乐和燕乐,二者实际上也在过去融合了一定的外来因素。而胡夷之乐却有西凉乐、龟兹乐、康国乐等8种之多。以至于唐太宗时期曾融入龟兹乐而作《破阵乐》,唐代史学家杜佑描述其为:“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声,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见杜佑《通典》)。后又有唐玄宗在西凉乐和西域宗教音乐基础上润饰而编《霓裳羽衣曲》等。唐贞元年间,经西南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南诏奉圣乐》和《骠国乐》,据胡震享《唐音癸签·卷三十乐通(下)》载:“骠国尝贡其国乐,其乐人冠金冠,花鬘珥双簪……”,又将具有西南少数民族色彩的异域音乐融入中原文化,使被唐代朝庭认可推崇的外来大型乐舞进一步达到了十四部。这样多的外来文化融入中原文化中,无疑会丰富和改变华夏音乐的审美特征。此前的中原文化受儒家思想熏陶,在艺术上注重中正和平、沉稳持重的审美意味。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犹如一股强劲的新风,不仅将明快、粗犷、绚烂的色调注入中原音乐文化之中,而且一扫已日趋古板沉闷的保守礼乐风气。夷、夏文化内涵的涵化过程共同构建了劲健有力的盛唐气象,将中国艺术推向了宗白华先生所称的“伟大的艺术热情时代”{5}。
从涵化角度来说,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物质载体或特别媒介。除上述歌舞音乐之外,人们创造的种类繁多的乐器,常常也是交流和传播音乐文化的又一重要载体和媒介。其中某些独特乐器,因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和时代象征性,往往成为涵化的重要手段和标志。汉代由丝绸之路传入并于唐代走向发展高峰的琵琶,就是这样一件引领华夏音乐新时代的重要乐器。
在中国音乐历史上,先秦时期的音乐以编钟、编磬等敲击乐器带动琴、筝、瑟等弹拨乐器的发展,展示的是庄重、沉稳、从容、深沉的意韵。至汉晋时期,世俗化追求的抬头和重视生命享受的风气,又带来接近人声的吹奏类乐器的兴起,意在亲切婉转的悠长韵律。到了唐代,由汉代对世界的征服气概和魏晋生命意识的觉醒而来,秉承南北朝时形成的享乐主义和唯美主义风气,再经唐贞观、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大大刺激了中原享乐风气的蔓延。加上唐代思想自由、胸襟开放,更助长了那个时代追求繁丽丰富、色彩纷呈,甚至略带某种猎奇的刺激性的社会文化风气,由此带来了这一历史时期对具有细腻、繁富、华丽、多彩等风格特征的艺术品种的需求。
旧有的钟、琴、笛类乐器虽有重要历史价值,但都显得色彩单纯、朴素;而由丝绸之路传入的琵琶类乐器,其出音密度明显增加,演奏的灵活性和迅捷性明显加强,在琵琶推捻自如、出音迅捷的演奏中,可以通过多向网状式音响铺陈,展示华丽、繁富,犹如铺金叠彩般的音乐表现风格。因此,由丝绸之路而来的琵琶类乐器,逐渐成为唐朝最突出、最能被普遍接受的胡夷乐器。唐朝历史上有过无数对它的描述和赞美之词,从白居易长诗《琵琶行》、薛逢《听曹刚弹琵琶》、李绅《悲善才》,到刘禹锡《曹刚》、张方《朝野签载》中记载的唐太宗用中原琵琶高手罗黑黑震慑胡人等等。通过这些生动描述,我们了解到当时各阶层人们对琵琶的喜爱之情。无疑,它的独特色彩已成为一种时代象征,代表着唐朝以来已然转变的华夏音乐风格,满足了音乐历史上的特定审美追求。之所以胡夷乐器能引领时代,是因为中原音乐文化中缺乏发展所需要的音乐载体,而丝绸之路输送进来了新的适合之物,于是夷、夏相交而推动华夏音乐的演变也就是大势所趋了,这也正说明了涵化现象存在的一种客观规律。
唐以后的宋代,虽然儒学复兴,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逐渐转向安静、内敛、质朴,在形态上与唐代的华丽、繁富和开放大异其趣,但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对中原华夏音乐文化的影响依然以不同方式持续着。如宋代兴起的拉弦乐器,就来源于丝绸之路流传过来的胡琴类乐器。胡琴在唐代称奚琴,到宋代时已改用马尾拉弓,并增加了千斤,逐渐融入华夏音乐,后至明代定型。以此类乐器引发的夷、夏音乐之交,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原音乐向抒情、叙述等方面的艺术表现风格演变。黄翔鹏先生也专门著文,提到宋代仍有不少音乐实际来源于南、北丝绸之路音乐。据他考证,白石谱中的《醉吟商小品》,并非出自姜夔创作而应当是唐代胡乐遗音;柳永填词的《瑞鹧鸪》来源于西域龟兹大曲《舞春风》;而《菩萨蛮》实际上本身就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骠国古曲。他进而指出,宋代以来所谓的“夷乐淫声”,事实上构成了宋代音乐中某种以丝绸之路音乐为主的新变声体系,且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宋代音乐中,如白石谱中的新变声(二变)等。由此也可以证明,中国自古虽已有七声、十二律及变音体系,而丝绸之路的影响使汉唐以后的变音体系得到了更大的丰富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丝绸之路在夷、夏音乐涵化过程中的作用有所不同。由于历代统治者在政治、军事、宗教、血统、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各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差异,西域等地与中原有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北丝绸之路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因此显得更为重要,而且内传的意义比较突出。西南丝绸之路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稍弱一些,而且由中原地区向西南地区外传文化的记载更多见诸于史料。从唐代十四国外来乐舞的目录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音乐在对中原华夏音乐发生影响时,其自身也不断地受到了华夏音乐的涵化,龟兹、西凉、南诏等国之乐都包含有中原音乐的因素,所以涵化现象事实上也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的。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胡夷音乐文化在整个唐代新乐中所占的分量,说明了它对中原华夏音乐文化的影响与渗透结合的程度。在这一胡夷音乐对华夏音乐的涵化过程中,华夏音乐在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通过夷、夏相交构建了新的历史风格,带动了盛唐之音的繁荣,推动了中国音乐历史达到一个高峰,并辐射到宋代及其后的历史阶段。本文所作的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历史的一个层面,有关这种盛唐之音及后来的中国音乐风格中,究竟有多少从夷、夏之交而来的重要音乐表现特征,这些特征当如何定性,因此而发生变异的中国音乐风格史又该如何系统地认识等问题,还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深入研究,以期有进一步的收获。
责任编辑:郭爽
注释:
{1}M .J .Herskovits, Acculturation –The Study of Culture Contact, p10, C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1958
{2}同上。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601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
{4}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270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
{5}宗白华,《艺境》, 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参考文献:
[1](日)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M].王耀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2]杜亚雄,周吉.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3]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4]黄翔鹏.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An Acculturation Study on the Music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u Liang
Abstract:
Through the South and North Silk Road, a large number of external music and culture have been poured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in Chinese history, which enriched connotative meaning of the music and culture of Catha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topics of, from the acculturation angle in anthropology, how external music and culture affect that of Catha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rough the South and North Silk Road.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the South and North Silk Road; external music;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