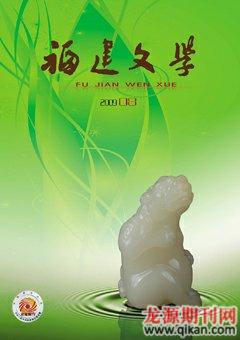旅店
李集彬
这是一个偏僻的山间小镇,说起来它还有一段辉煌的历史呢。那时候,国道324线从这里经过,算是贯穿南北的主干道了。这个小镇正处于这一条公路的中心点,长途汽车司机们习惯在这里停歇,一时间把这里的服务行业带动起来,公路两侧饭店陆续开张,长蛇一般排列开去,形成饭店一条街,成为这个小镇的一道独特风景,紧跟着旅馆、商店接连涌现,后来连镇政府也从老街搬出来了,这里便成为小镇新的经济中心。
因为一条公路,改变了一个小镇的布局,包括人们的生活,现在看起来已经司空见惯,不见得有什么稀奇了,小镇管理者,也已有意识地把它当作一方经济的发展契机。然而当时,确实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客车到这里来一般是中午,车停下,下来几十人,吃了午饭,歇憩一下,呼啦一声,一阵风走了。货车来到这里大多是黄昏,司机们拉着一车货,回家肯定不行了,那时候,只能将就在这路边旅店里吃饭和过夜。
夏日的傍晚,日头落到山尖上去了,一点点鲜红起来,公路上汽车逐渐稀疏,沿街的饭店一下子热闹起来。司机们在公路上跑了一天,那么炎热的天气,一辆车、一个人似乎都要着了火,身上挂着厚厚一层尘土,把车开到这里来,随便找个位置停下,汽车喘一声粗气熄了火,人悬着的那颗心也就安安稳稳落下来。早已是熟客,就像到家里一样方便,脸盆自己拿一个,毛巾放在那个固定的位置,到水龙头那边冲洗一下,走进店堂。肚子已经叫得很响,酒菜的香气直往你肺腑里钻,那时候,你的脚步难免要迈得大一些。找一张桌子坐下,酒也上来了,菜也上来了。跑了一天路,饭店里的好酒好菜把你的身心都安妥了,好好睡一觉,第二天跑起路来也就精神抖擞了。
这一条街里,有一间兼作旅馆的饭店,生意格外的好。老板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或者三十六,或者三十二,这一点在她身上很难分辨得清楚。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听见有人叫她阿香。从哪里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是否结过婚?更是一个谜。这么一个女人,孤身一人来到这里,租下一座两层的小楼,一层作为饭店,二层作为旅馆,雇两个本地女子打下手,开起一间叫“瑞香饭店”的旅店来。对于她身上的谜,一些人难免好奇,去问她,抿嘴一笑,似乎不便回答。那时候,你不好意思问下去,她便含着笑,招呼你吃菜、喝酒,转身忙自己的事去。
这是一个让人一看就禁不住着迷的女人:不拘穿什么衣服,总能把身上的线条勾勒得分明;一张脸不是很白,却透出一种新鲜和红润;看你的时候,一双黑的眼珠子里放出热情的光来;和你说话,永远带着微笑;五官不是那么标准,身上就是散发出一种说不清楚的魅力。为什么孤身一人?她不说,问那两个打下手的女子,也只是摇头。一般说来,这样一个女人难免要有一些风流轶事,小说里一般也要这样写的,然而她来这里好几年了,打听不到一点和她有关的绯闻,这就愈加让人迷惑。这样一个谜一般的美丽女人,对于那些单身男人便有一种强烈吸引了。一种好奇让他们觉得有必要去解开这个谜。
饭店里经营的不过一些农家菜,只是经过提炼和改造,更加原始,也更加纯粹一些。这一点,在那些吃腻了大鱼大肉的男人看来,反而别有风味。餐具是统一定制的,清洁上也做得十分到位。一切都让人觉得很满意。
司机们到这里来,走进店堂——一般说来,他们每个人老板娘都是熟悉的,问一声“来了啊”,就像自家兄弟那样亲切,端上两瓶冰镇啤酒,“先降降火。”脸上挂着微笑,“饭菜很快上来了。”都是老主顾,这个司机的性格、习惯、喜好她早已熟稔在心,自是不必问的了,除非你临时改变主意。就像到自己家里,舒展着手脚坐在那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吹着从山那边吹过来的凉风,你的心情自然好起来,喝酒的速度不觉快了些。这时候她便要走过来,提醒你一句:“填饱肚子再喝。空着肚子喝酒不好。”脸上仍然挂着微笑,言语里带着关切。这些整天在公路上跑的男人,性格被日头、风雨、尘土打造得十分粗粝。在这女人的微笑里,那颗坚硬的心一点点融化,变得柔软起来。这女人的柔情,对于他们心底的那一份寂寞,是一种极好的抚慰。那时候,对眼前这个女人,因为心底的感激,行为上也变得斯文一些了。饭店里气氛轻松愉悦起来,一切便和谐有序地进行下去。
然而,这南来北往的司机里,难免要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年轻人,由于没有经验,看老板娘身段、长相十分好看,吃了几分酒,一时动了蠢念,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语,自然一些人看不下去,就要遭来吃客的白眼,或者更甚,触了一些好打不平男人的愤怒,那时候大概就要吃点亏了。
可不是,那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也是傍晚的时候,大家正在饭店里喝酒,暑气逐渐消退下去,心情不觉好了起来。这时候,进来一个年轻人,几杯酒灌下去,舌头直起来,说了一些轻浮的话语,拉拉扯扯,非要老板娘陪他喝酒。这不,一个中年男人从角落里腾地站起来,起先只是拿一双虎眼盯着他,也不说话,看他越来越过分,横着膀子走过去。这个年轻人看来也是未经世面毛手毛脚的小伙子,看那架势并不畏惧,说一句:“关你啥事?”见他走近,一脚踢去。这大概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了。只见那只脚被中年男人一抄抄在手里,仿佛被磁铁吸住,再挣不脱;紧接着,手只一旋、一送,年轻人的身体就像一只风筝直直飞了出去,“砰”的一声摔在地上。看这架势,再打下去年轻人就要吃大亏了,老板娘匆忙过来把中年男人拉开,赔着笑脸说:“这位小兄弟或者刚上路。同在一条路上跑不容易。谁都有不经事的时候。”又去扶那年轻人。这时候,那一位愤愤不平的熄了火,这一个做错了事的自己脸也红了,那些吃客心里,对这女人,也就多了一份敬意。
接着大家继续喝酒,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说一些生意上的事、路上的事,或者其他随便什么无伤大雅的事,只要你乐意。那位愤愤不平的兄弟桌上多了两个菜,是老板娘亲自下厨为他准备的,当然也悄悄把一份心意融入在里面。只是做得不动声色,其他人并未发觉而已。
生意好做了,钱也来得容易,这些男人大手大脚起来,菜也吃得够了,酒也喝得多了,醉醺醺上楼去。
把店堂里收拾好,两个打下手的女子回家去,楼上又喧哗一阵,安静下来了。她关好店门,洗漱一下,进到底层角落她的房间里去,掩上门,把门闩上。虽然楼上那些客人她尽可以放心了,好几年了也没发生什么事,然而这一道程序她一定要做好的。
忙累了一天,放松下来了,或者太累,熄了灯上床睡去,或者精神依然很好,便要坐在那里去想这一天的事。账目上的收入她是懒得去算了。一两次,她也像其它饭店里的老板娘一样,像模像样地把那个账本拿起来,计算器备在那里,就放在抽屉里,却不见她伸手去拿,未看到一页就呵欠连连了。她到这里来开这一家旅店,完全为了一份快乐,心情愉快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不再去想那件事,把账本丢进抽屉里。她想:“这生活里,一个人每天那一根弦绷得那样紧,再没有一件可以让你快乐一些的事使你的精神得以松弛下来,那时候你非被这样沉重的生活压垮不可。”因此,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尽可能让大家在饮食和休息上得到满意,提供给大家一份快乐,多少让那些被生活挤压到角落里的人解脱出来,得到片刻精神的欢娱,而且把它当作自己的义务。这时候,她就想到今天的事来,哪里做得不够?想到明天的事去,尽量做得更周到。
这些事情想好了,再睡不着,她就坐在那里发呆了。
那一天,她提着行李踏上长途汽车一路北去,心里一片茫然。汽车在这一条公路上奔跑,不知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她知道自己是在逃离,逃离那个伤心之地。或者到了那个城市,她还要坐上另一班长途汽车北去,离那个地方越远越好。汽车越往北去,她的心也就不揪得那么疼,心情一点点好起来了。那时候,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北去,北去。
那个人到南方去,听说外面有女人了。一开始她还不信,一切得到证实,她的心冷到极点。那一夜,她不知流了多少泪。第二天,她终于选择离去,离开那个家,离开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她不敢再想下去,想下去她的心就要扭成一团,揪得很疼。不去想那些事情了。候了许久,心里平静下来,再无事做,于是站到穿衣镜前面去。屋里很热,脱到剩下一件胸衣。这时候,她就在镜子里望到自己光滑饱满的身体了,依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那样健康的身体,这样的夜里,是需要另一个身体用一种力和热情来抚慰的,这时候却被无情抛弃了。”想到这里,心里隐隐又疼起来了。到床上去,一张床空荡荡的,一夜翻来覆去。逃离那个家,她是自由了,完全可以像其他女人一样放纵一下自己,也没有必要为谁去守那个身体了,完全有理由敞开心扉去接纳自己爱悦的一个。生活里时常也有这样那样的暗示。她完全有理由去做一件符合生命要求的事,健康的身体也经常怂恿她这么去做。然而那时候,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跳出来说不,又犹豫起来了。
那天上午,长途汽车在这山间小镇停下。从车上下来,抬头望去:黧黑的远山、苍翠的近林、古老的小镇、清新的空气,一切那么爽心悦目,让人心胸一下子开阔。人们脸上挂着微笑从容来去。烦乱的心仿佛有一阵清风拂过,沐浴在透明的空气里。那一刻,她决定留下。这个决定那么突然,似乎不经过思考。在这个小镇里逗留几天,带着一份闲散的心情四处走走逛逛,最初那一个印象得到进一步证实,后来她就在这公路旁边开起这一家旅店。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她的观点产生了变化,有了新的想法:愿意从过去的生活里解脱出来,努力过一种单纯快乐的生活。这种快乐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她愿意把它拿出来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
如果说以前,一来一去的人多了,未能引起她的注意,经过这一次,她留心起那一个人来了:宽宽的脸膛,宽宽的肩膀,四肢匀称而结实。每天很准时的来到这里,一定坐在靠近后窗那个位置,从未掺杂到说话的人群里去,看来是个好静的人。叫两三个小菜、四五瓶啤酒,很少有什么变化,似乎性格里有点固执。吃了菜,默默坐在那里,一边慢慢饮着酒,似乎要从那里面品尝出什么滋味,一边把目光投向窗外,仿佛有什么心事。
其实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曾发生过。这一条路上,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这样那样的事,大家习以为常了,她原本也没必要去留意。只是这个男人看起来有点特别,他从哪里来?跑什么生意?家里有没有女人?都要引起她的好奇。一些问题是不好意思去问的,只好在心里猜想着。然而饭店里事情确实多,不允许你去为一个陌生男人花费太多心思,所以往往想到一半,想不出什么来了,就把那想头掐断,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去。
只是既然知道他的脾气,每天下午到了那个时候,她便要提前把他的酒菜准备好。一切都是在下意识里完成的,并未刻意去做这件事。那时候他一进来,饭桌上就有现成的酒菜。这样一件事,她也为其他熟悉的客人做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此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有时这位兄弟饭桌上多出一两个菜、两三瓶啤酒,因为饭菜特别可口,酒也喝得深一些,他并未去留意,算钱的时候也不去看找回了多少。他们一向大大咧咧,尤其来这旅店,吃的酒菜,算钱的时候从不去计较。或者有啰嗦一点的,一定要去算,又分毫不差,那时候心里反而惭愧起来了。有时他发现:“今日的酒菜便宜了。”要把多出来的酒菜那一份钱给她,她反而不高兴了。
这样一些情况,仿佛都为一件事:因为他帮过她,所以客气起来。看起来也没什么稀奇的。
然而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仿佛有一颗种子在她心里悄悄种下,生根发芽了,一种快乐在她心里蕴藉,绽放开来,掩饰不住,有时不知不觉笑起来,笑得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是有一种久违的感觉。那时候发现了,心里就要慌乱起来。
有时,他不知为什么事情耽搁了,来得迟一些。饭菜煮好了,又热过一遍,还不见他的踪影,她就要不安起来:“是不是汽车抛锚了?会不会出什么事……”不知不觉跑出去,朝那个方向张望。有人问她望什么,她说不清楚,一张脸就红起来。第一次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后来渐渐就觉察出那种异样。那一刻,她就意识到心底潜滋暗长的那种感情了,心里慌慌的,想把那火苗熄灭了,然而你越是想把它扑灭下去,它越是不屈不挠地一点点燃烧得愈加旺盛起来。知道再也无法把它熄灭了,那时候,她就要生起自己的气来。不仅生自己的气,还生那个人的气:“为什么不早点来?难道不知道人家……”到时候他来了,问她她不理睬,让他摸不着头脑,然而觉得好笑。那时候看他笑,她就更加生气了。
也许那种感情在心里点燃起来,越来越旺盛,燃烧得你都变得有点糊涂了,那时候便要跟自己赌气,也撒一些气在那一个人身上。幸亏那个人很宽容,乐意接受你这样的撒气,然而你就变得愈发不讲道理了。那样的情形下,这女人心里的火苗,因为那男人的纵容,也就越发蓬蓬勃勃了。
这一些都是在悄无声息之中进行的。饭店里一切像往常一样,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是细心一点的吃客或者会发现:老板娘比以前喜欢笑,饭菜做得比平常更加可口了。这些都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所以他们更高兴,酒也喝得比平日更多一些了,未曾去细想这微妙的变化产生的缘由,更不会去留意女人腮边隐约飘过的云彩,和瞳子深处跳荡的火苗了。
这一天,下午的时候,风赶着白云去了,就像赶着一群白色的绵羊,风赶着乌云来了,就像赶着一群黑色的山羊,天色突然暗下来,无数的乌云聚拢过来,压得很低。
一阵风不知从哪一条山谷里过来,纵身在公路上奔跑,卷起一阵尘土,打个旋,一个潮头往树上打去,树叶波浪一般起伏起来;在树梢站立一会儿,看看花圃那边一簇玫瑰开得正招摇,低低飞过去,不知从哪里咯吱一下,笑得花枝乱颤;看它那轻薄的样子,似乎是生气了,不想再和它纠缠,“呼”一声蹿起,耸立起来,望见公路上一个农人戴着斗笠匆忙前行,也许觉得好玩,悄悄飞过去,把斗笠掀起来,甩落地上,当做圈圈滚走很远,害得农人一阵紧追;顽皮得够了,一边笑着一边奔向田野,田野里的稻谷无尽止地起伏起来。
乌云愈压愈低、愈压愈低,终于压到山尖上了。突然一个电闪,“啪啦”一声巨响,雨点硬硬砸在人们身上。一阵哆嗦,行人脚步加快起来。“看来就要下雨了。山间气候变化真快,尤其这样的夏日。”来不及细想,一个雷在你头顶炸响,你一惊奔跑起来,风把你纸片儿似的扯来扯去,雨就像从天上倾倒下来似的泼在你的身上,躲进旁近屋檐下,来不及把脚收回来,淋了一身水。天一下子黑下来,风一阵接一阵扬起雨水向这个小镇横扫过来。
那时候,她坐在店堂里,看看天黑下来了,关好窗户,风裹着雨一下子甩过来,击打在玻璃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店堂里黑得让人恐慌,打开灯:外面已看不清人影,公路上车灯亮起来了,喇叭的声音密集、急促而又慌乱。有车停在门口,司机打开车门挣命似的逃进店堂里来,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惊呼:“好大的雨!从没见过这么大雨!”她这才想起来:“他呢?他在哪里?有没有找个地方避雨?”接着又忙碌起来:招呼客人,端酒,炒菜。天越来越黑,公路上车声逐渐稀疏,饭馆里人多起来。他还没来。这时候,一个司机遇了赦似的逃进店里来,仿佛受到很大的惊吓,坐下来,喘着粗气,说:“有一段公路塌方了,一辆货车车头都砸扁了。只听一声巨响,车都颠起来,我就知道后面出事了。幸亏我跑得快。”吃客们听他这样说,心里一震,嘴里的酒抿得很紧。那司机又说:“听说不止那一段路。”听到这里,她的心一阵揪紧:“他还没来?”丢下手里的饭勺,慌慌地跑出门去。
公路上已看不见汽车的影子,天地之间仿佛扯起一块巨大、深黑的幕布,把整个世界遮得严严实实,只听见风声和雨响。公路淹水了,在那黑的底下泛起一层白,到处是流水的声音。偶尔“哗啦”一声,大概是广告牌倾倒下来了。有树被风吹倒,砸在人家屋顶上。她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攫住,揪得愈发紧:“他呢?怎么还不来呢?”她都快要哭出来了。这时候她才发觉,那个人对她来说如此重要。也许那种感情早已契入她的心底,并在里面发芽滋长;也许那个人早已把她的心占据了,拆不开,赶不离。这时候,一切突兀显露出来了,让她慌乱、担忧、惧怕。雨抽打在她身上,有人喊:“你等谁呢?”她浑然不觉。
那个人已经往回走了。天气预报说这一天有雨。天气预报有时准有时不准,司机们干脆不理会它了。然而这几天天气确实异常,一连几天高温天气,阳光硬得砸不开。他想:“该有一场大雨了。”傍晚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凉风,他隐隐嗅到一丝雨的腥气,车跑快起来了。没想到车还是跑不过雨。这雨来得太快,不一会儿就来了,那样猛,几乎要把车窗玻璃砸破了。天一忽儿就黑了,雨越来越大,雨刷不停地摆动,前面的路还是模糊起来了。“这样跑路很不安全。这雨下起来怕是没完没了了。”前面有个加油站,他把方向盘一转,车拐进去,“看来晚上得在这里歇息了。”整天在公路上跑的人,难免要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早已习惯了。跑了一天路,有点疲倦,靠在那里刚想眯会儿,肚子打鸣了,“这该死的天气。幸好车里有面包,啃啃吧,只能这样了。”把面包找出来,啃一口,又干又硬,把它扔到一边去,生起气来。他一向沉稳,不知怎么,也许这天气惹恼了他,这时候那么喜欢发脾气。他想起那个旅店:“要不是这雨,早就可以吃上可口的饭菜了。”不知为什么,这一条路上饭店多了去,他就是吃不惯?每天傍晚,卸完货,急急往那里赶,就像以前回家去。“那个旅店为什么那么吸引你呢?除了酒菜,还有……”想到这里,那种感觉让他仿佛回到年轻时候,把面包扔出窗外,发动汽车,钻进雨里。
那个家已不值得他留恋,他越来越不想回去。他原本想:“赚够了钱,把房子买下来,从老房子里搬出去。”每一天,浑身充满力量,把一辆车跑得飞快。他几乎看到未来的美好生活了。这时候,一切不同于以前了。在外面跑了一天,一身疲惫,谁不想回到家里看到女人的笑脸、热乎乎的饭菜?可是每次回到家里,门锁着,女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他一颗心是冷了。吵过几次,后来那个女人干脆彻夜不归了。他的梦完全被毁坏,一个人变得沉默起来。现在好了,他决定把一切烦恼抛弃到脑后。他又有了新的念想。虽然这个念想因为未经那一个人的同意而显得茫远不可确定,然而他决心开始去追逐这个新的梦想,因此,这时候显得毅然决然了。
雨越下越大,车灯很亮,还是照不开这又厚又重夜的雨幕。他把车开得很慢。路旁偶尔可以看见抛锚的汽车,还有几处塌方,有车砸在里面,他的心悬起来了。风裹着雨一个潮头打过来,车身一个趑趄,他开得更小心了。汽车在这一条公路上、在这风雨中、在这黑暗里缓缓移动,让他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暴风雨,没有雨具,一个人一步一步挣着身子往家里去,那时候多么勇敢。他想起那个旅店:“喷香的饭菜,谜一般的女人……”他是企图打开那个女人的谜的。想起她,一颗心柔软起来,身上一种力量悄然滋长,这种感觉让他兴奋。
车到小镇已是半夜。在那巨大的雨声里,小镇瑟缩着睡去,只有一盏灯亮着,在风雨中瑟瑟发抖。他把车朝那个方向开去:“该是那个位置。”“瑞香饭店”,他想起那个亲切的名字。“她该睡下了。”想到这里,他又犹豫起来了,“不会吧,不会的。”车子驶近,车灯下,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雨里,就像一尊立体的雕塑。他惊呆了。车停下,他奔跑过去。“你来了。”她含着笑,一颗泪滚落下来,心里绷紧的那一根弦松弛下来,一个人软在他的怀里。四下里一片寂静,唯有风雨肆虐,他抱起她,向灯影里走去。
好大的雨。人们在惊惧之后安然睡去,谁也不知道夜里发生什么事。巨大的雨声把一切颤动、缠绵、欢欣淹没去。第二天起来,天放晴了,小镇被雨清洗过,变得洁净、透明,让人神清气爽,仿佛一切疲惫、倦怠、烦愁也被冲刷去,人一下子精神起来。大家像往常一样,各自忙自己的事去。日子像往常一样行进,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旅店里的生意也像往常一样。只是自从那一夜,老板娘的心里似乎有藏不住的快乐,一张脸更加光彩照人了。那个男人脸上有了笑容,有时候也加入到说话的人群里去。夜里,老板娘不再闩门。到了半夜,或者更晚,楼上鼾声四起,周围一切安静下来了,这时候,就有一个宽肩膀的黑色身影溜下楼来。也许赤着脚吧,仿佛有夜猫子一般灵便,悄无声息推开楼下那扇门,光着身子钻进被窝里,搂住那个光滑的身体。经过一阵慌乱的喘息和急促的摸索,终于找到了着落,两个健康的身体十分放纵地尽一切力和热情去做一件蒙生命悦纳又充满活力的事。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一切缺失弥补上来,这是那么重要和可值得珍贵,因此他们不肯浪费一点点时间,甚至来不及去想明天的事。
然而,这样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多久:那个人突然消失了,就像一粒尘土被风吹走,让你再寻不着。她的脸色黯淡下来了,眼角似乎也多了一道皱纹。那个男人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她去打听了。然而在这一条路上跑的司机不知几千人,每一天都有人加入进来,每一天都有人从这一条路上退出去,悄然隐没,消失在茫茫人海里。生活终将继续,谁也不会去介意另一个人是存在还是消失了。
后来,这一条公路旁近又开辟了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封闭式的,入口、出口都不经过这小镇,从国道324线经过的长途汽车越来越少。没有了主顾,这盛极一时的饭店一条街也渐冷清下来,饭店一家接一家悄然关闭,喧闹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时间过去很久,那些店铺门前已长满蒿草。然而小镇的人们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叫“瑞香饭店”的旅店最后一家关闭。关门那一天,老板娘就要离去,还站在门口,朝公路那边张望。
责任编辑 练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