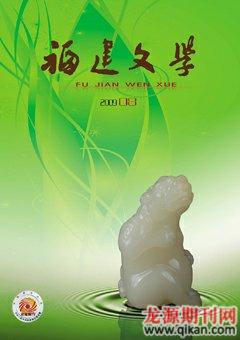禾源散文小辑
禾 源
两条蚯蚓
我办公的地点,地势相对高了些,上班的路有一段近百米的斜坡。多年来来去去,路边景物和常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都成了老相识。既然相识,总有些事会让人挂心,诸如:老伯好几天没遇见了,小妹身边换男士啦。树皮擦破,电话亭遍体鳞伤,等等,等等。当然几天过去,这些挂心的事,就如落英流逝,片片流来,瓣瓣流走。
昨夜一场雨真大,整个小城,巷为溪街当河,一个夜晚的横流,还不过瘾,直到第二天上早班,那截百米斜坡还流淌着一些迟到或来不及退去的水流。水量不大,倒觉干净和矜持,它紧紧地依靠在人行道边,波波折折,向低处款款移去。
这水吸引了我,就像飞鸟在地上行走一样吸引我,我真怕脚步重了把小鸟惊飞,于是放轻脚步,呵护似的边走边看着水流的细节。有两条蚯蚓,我俯下身来细看,是两条蚯蚓。我想起它的来历有些伤感,一定是那场大雨灌进它安身的家园,它死命地伸缩着身子从洞里爬出,只为了不至于被水淹死,只为了还能天天啃着土,可它万万没想到才从洞里爬出,又被水带到这里。对于这两条蚯蚓来说,这水流无疑是条江河。蚯蚓在求生中居然有着鱼的习性,不随水而漂,奋力逆流而游。我真想念个咒语,让它能像鱼一样长出鳍,这水泥路能像河一样长出水草。然而就在我这荒唐想象里,蚯蚓不见了。想救它于水火,已经用不着了。
水中的两条蚯蚓被流走了,可是埋在记忆土壤中的几条蚯蚓又浮现在眼前。蚂蚁,一群蚂蚁前堵后截,半抬半引,那条蚯蚓仿佛半推半就跟着蚂蚁爬的方向挪动着。我知道这样下去蚯蚓的结局,便拾起路边的竹枝赶着蚂蚁,嘀咕着:我来救你,蚯蚓。爷爷则说:“救走蚯蚓,不就饿死蚂蚁,你又何必?事情既然是这样,就顺它们命定吧!”我说:我的眼睛见不得死亡,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蚯蚓被蚂蚁一口口蚕食,没看见则罢了。我还是救下那条蚯蚓。山间的沙土路上一条很大的蚯蚓被砂粉裹着,艰难地挪动。爷爷说:“蚯蚓滚泥沙,大概要下雷雨。”边说边用手中的木棍把蚯蚓拨弄到路边的树荫下。我不解地问爷爷:我救蚯蚓,你说顺它天命,怎么您自己也救蚯蚓呢?爷爷叹了叹气,说:“这条蚯蚓是因为地里干燥闷热,跑出来觅水的,是落难蚯蚓,当然要救!”我依旧不解,被蚂蚁抬走的难道不是落难吗?想想蚯蚓,不管是瀼水,还是干燥,爬出洞穴都是要落难的。啃土的蚯蚓啊!怎能离开土!
我到了办公室,刚坐下,茶水还没倒好,手机就响了。是村子里一起长大的伙伴打来,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他身处困境。果然就是这样。他问:“你石狮有朋友吗?我弟弟在石狮打工,被摩托车撞了,肇事者看是个外地农民,居然跑走。弟弟躺到医院,报案又没记下车牌号,怎么办啊!好在是土命,贱着,断了下肢,命还能保下。可几年来打工挣下的钱,填不满这个窟窿。”我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我真的无力找根竹枝,像赶蚂蚁救蚯蚓一样,救他于劫难中。
才过几分钟,又一位远房的堂弟在沙县打来电话,说孩子想回来念书,是否能帮助联系一下学校。这件事我想并不难做,大概就像爷爷救滚泥沙蚯蚓一样,把它挑到树荫下,它就能获救。但我此时无心去做这些事了,我感觉很累,就像失眠的深夜,听着叽叽叽叽的蚯蚓声,让我想得太多太多。
蚯蚓喜欢温湿肥沃的土地,蚯蚓断了一截还能生存,蚯蚓很少见光晒日,蚯蚓松土活土……啃土的蚯蚓啊!不离开土也许在夏夜会叫得更欢。
有这么一眼泉
那眼泉有名字,而且是一个很本性的名字,“美女献花泉”。名字是乡村人取的。乡村人学着古人象形字的造字法,依形而托声。我凭着这个名字,站在与山泉对面的山上,仔细审视,觉得老祖宗眼真毒。
孕育这眼泉的山体,只是鹫峰山脉的一根经络,然而这根经络之梁,撑起的天,铺下的地,就养育了好几个村子。我的村子就在支起这道梁七腿八爪中段的两腿间,两条腿不算修长,抱下一片田,抱住一个几百号人的村子。
我的目光如流水,从村头村尾两片风水林逆流而上,经过脚掌,小胫,大腿,一汇合注入到那眼泉。学着母语骂了一声:操!老祖宗!大情种,就凭这,把一个姓氏种到这山旮旯,逼得子子孙孙,出门翻山,回家越岭,不论男女都长得头小腰粗脚板厚。
也许选择本身就是无法选择,只不过是适应生存而没有放弃偶然的相遇,就如这眼泉在山体内不知道拐过多少弯,翻过多少坎,会在这道梁的腹腿间溢出一样。见这里蓝天很高,太阳很亮,觉得山风清凉,天籁和谐,也就没有往回流的意思,再说泉眼前又寻个大沼泽,泉水爱出则出,爱隐也还有个去处,可算是有个迂回的余地,于是泉水就股股而来,终年不断。当然从沼泽出来,就不再是泉水,而是池水,是溪水,变得有声有色了。
阳光下的世界,热闹多彩,出山的泉水,一步步被诱惑,走上了水道,沟、渠,溪、河,涌入大江,渐走渐远,跌跌撞撞,汇入大海。再经过几天的潮起潮落,此时从这里打起水,大家都说是海水,就是桶有海大,一下子打起,大家还是一句——海水。泉水从此失去了本名,失去本性,成了海中一滴无根的水。
泉水失根失性,可水路有极有端,雾读云看,那枝枝蔓蔓的水路,如一棵天树倒地。江为杆,河是枝,溪如根,泉则为根须,就是这棵天树绿荫着大地的四季,水树丰茂,大地皆绿,水树干枯,大地皆秋。乡村虽然山高皇帝远,鸡鸣是晨读,犬吠当夜诵,读不懂大书名著。但山里雾霭蒸腾,乡村人开门雾抱,启窗雾呛,大概跟雾学得更多,认识了水性,早早知道泉是水根之须,须糜根烂,溪河将枯。保住一眼泉,就保住一条溪,保住这条溪才能保住自己的村。
树要活着,就要有阳光和水,一个需要,就逼得树有了智慧,要照到阳光争着长高,要汲取水分学会蓄水。人知道有蓄就有放,有纳就有吐,一切的生命大概就是在吐纳的更新中存在。只要树活着,这个地方就有水,树越多水越多,于是那眼泉水周围数里山地,成了乡村的封山育林地。请神明看树,请鬼怪抓盗伐,乡村人受用受用,泉水则安然如婴。如婴的泉吸着立地之树琼汁,又哺养伏地水树——溪、河源远流长。一立一倒,都心系泉眼。泉是老儿,泉是老根,他们争论不休。还是轮回“哈哈”,打了圆场。树,一站一伏架通了泉水轮回的通道。
多次的巧合证明老祖宗的眼光不仅有独到之处,且有着透视天地玄机之能,虽然乡村占据在小山岗上,背依泉出山梁,门朝顺流而开,与泉一个坐向,一反许多村子以溪相隔对岸而居,临溪开户,或坐北朝南的传统。如是奠基架梁,确实发展很快,反客为主,原来同居在这眼泉流过的小盆地几个小村慢慢消失,房舍变为田地,姓氏留给田山,于是在我父亲的记工薄上有“周家洋”犁田,“吴厝坪”耕地等。村子中老人常会说:“门向东,了了空;门顺流,满屋满仓财宝留。”但我在乡村中找不到一点东西,能显示富贵,就连村弄的铺路石没有一块是人工开凿方正之石,没有一座楼房有雕梁画栋,这财宝留到哪去了?大概他们认为人丁兴旺就是财宝,一个姓氏种下,能生根,且枝繁叶茂,就等于拥有了大财宝。“金人仔,银人仔,不如穷人活人仔”。“人丁”重于财宝,这块地的的确确盈实了我的姓氏。
村子人口多了,姓氏开基的东山岗显得拥挤,有的人把房舍建到溪的对岸,也就在原来“周家洋”这块地上。而且是十几户一同起建,有着一个小村子的规模。村里的老人就在凉亭里说,左青龙,右白虎,溪对岸建房起居,乡村大概不会安宁。不过从抱村的两条如腿山脉看,左山粗壮,也伸得长,相对右山就弱,在“周家洋”起居,不过二十年又会搬迁的。事实又印证了老人的话。溪岸的十几座房屋如今只有一对老夫妇在居住。不过东山岗近百户人家也只有二十来户老弱病残在守着。
那眼泉还是股股地出,小溪依旧潺潺地流,但村子越来越小,人丁越来越少。是不是“美女献花泉”老了,流不出天地玄机?凉亭里的老人长叹:唉!现在的人都有红眼病啊,都有猴性子,读什么书,学些粗字就行了;怕什么做农,最公道的就是田地,有种有收。偏要学着人家,读书,打工。一个个,一家家向外搬。你不理这块地,这眼泉也不会留你,最后也像别的村子一样,留个姓氏给田地吧!
河床边的一株草
那株草我说不出它的学名,叶如茅草,秆是芦苇,穗如稻禾,不结果实。稻禾之穗又如橄榄瘦身,仿佛把一粒青橄榄拉长,拉长,拉到原身长的十几倍,两端尖尖腹部丰盈。孩提时说是刺猬身上的箭刺。这箭刺绿色为主,色彩从晒太阳的一端流向包在秆中的一端,色泽从浓到淡,到端头近乎嫩白。它含苞灌浆时,也给我们灌满了甜蜜。剥开那层皮,里面软着鲜活白嫩的穗芯。我们喜欢把它倒提起来,仰着头张大嘴巴伸出舌尖去迎接穗尖,然后不断卷动舌头,提穗的手也随着舌头卷动的节奏配合着下降,直到卷入整根草穗。慢慢咀嚼,淡淡的甜味,软软的质感,在咀嚼中渐渐地传导到满足中杻,洋溢周身。一张张红扑扑的脸如葵花一样,向着太阳欢笑。
这些记忆是我们的,也是这株草的。草记着乡村的孩子喜欢那饱满的穗,记着小青虫喜欢在绿叶上结茧,记着蜻蜓喜欢在摇摆的苇秆上荡秋千,记着河水喜欢捎带像蒲公英一样的花絮,还记着……因为草有了这些记忆,有着生活的乐趣,所以就年年守在河边,背诵着一岁一枯荣的定律,解释着河水流动的生命几何。
初秋,我带着许多生活琐碎的事,走到河边,想边走边扔,借助一场洪水把烦恼流到很远的地方去。然而,河成了河床晒在太阳下,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再圆滑也只能一个姿势躺在一起。一只蚂蚁从一块鹅卵石爬向另一块,一直爬不到岸边,着急中一定在咒骂,这里是什么法难,要这么多的沙弥聚在这里禅定。我跟着蚂蚁来到河中一块大石上坐下,记忆也像蚂蚁四处乱爬,寻找相识和知己。是的,记忆中的一切全都遇难了,就连菖蒲也枯干。那位把河边草珠串成项链的姑娘,早就嫁到他乡,大概正用着那串草珠当念珠,诵读着《大悲咒》超度着河里众生的亡灵。当年从我鱼钓脱钩的那条鱼一定也在超度的途中。怪不得河有着死一般的沉静。河断流了,关于这截河的记忆也许有了绝版,我要问问那株草,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
那株草生命力极为顽强,俗话常说:“女人无力斗过垢,男人无力斗过草。”这草大都就是河边的那类草,只要根不斩绝,它年年生年年长,而且会从一株长到一丛,一丛长到一片,最后成林。但今天找到它时,那根蜻蜓荡过秋千的苇秆拦腰折断,旁边的叶子大都挂到了河边的堤岸上,就因为对母体还有依稀的恋情,没有飘远,最贴近根部几叶还有几丝病奄奄的绿意。问它对河的记忆。有片叶子随风抖了抖,叶尖指向源头,风一停就耷拉下来指到了根部。我读不懂草临终前的表达,但村里许多老人临终的交代会成为对全村人的交代,我听到最多的是,要喝碗村头的泉水,见见每个儿孙,尔后安然而去。这株草是不是也渴求一碗水,或见见儿孙,若是这样它得不到了,只能带个遗憾埋在自己出生的地方。
一株对河有着记忆的草枯了,它成了别人的记忆,成了河床的记忆。但草告诉了我,记忆永远比人年轻,又比人长寿。若说记忆是河床,人就是那株草,一天天的生活就是河里流动的水。
蚂蚁沿着石头爬到了我的鞋面上,它大概感觉这里没有石头那种焦热,有了生命的气息,它停了停,头上两根触须不断地摇晃,本能地探测着所处环境的情况。我迅速拔腿就走,把它带到河床岸边,岸边是块园地。我想有了这块园地,既使它回不了家,也许能生存下去。它走它的,我想我的。此后,谁也顾不了谁了。
只要脚步迈得开,脚下都有路,不要太在乎所走的路,我知道凭一个人的脚力是不会走到太远,更何况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在这随缘行走中我遇到了一位退休的阿姨,惊讶相互传染,同时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到这!”我决定让她先回答。可是一个老问题她又提上了:“你在哪上班,那次老年大学活动,你参加了吧,你的歌唱得真好。”我告诉她好几回了。大概在她记忆里藏储的我,就是那次的歌声。许多人常说:人老了,记起的老是过往,忘记的总是当下。
阿姨老了吗?用我的记忆历程测量,凭她回忆的旅程计算,是老了。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阿姨时我不超过十岁。当年我仰慕村里的工作队,用现在孩子们的话来说,他们是我的偶像,我学着他们腔调讲普通话,学着他们把手扳在背后走路,学着他们点头向人招呼。当然更想学着穿上白衬衫,皮带裤。把衬衫操在裤子里面,胸前的口袋插上一把钢笔。
那年我姐订婚,我得了一元钱的红包,就决定买上一支钢笔插插。伙伴们每人量上半斤米,走上九公里路,便到县城百货商店。一头扎进钢笔的那个柜台,选中了一款四毛六分钱的。便大声呼叫阿姨拿笔。阿姨来了,笑眯眯看着我们,拿笔,拿笔水,教我如何吸水,如何使用,还拿上纸写写画画,给我挑了一支。我扯起袖子一边擦汗,一边看着阿姨。阿姨真高,牙齿很白,脸又干净。真好看的阿姨。当时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就是阿姨。后来国庆节、新年,我们都到小城里玩。常常去看看她,当然她没看我们。但有一次她看了,还笑话我,因为我胸前口袋插了三支笔,又到她柜台前去看钢笔,她说我是学修钢笔的。再后面的日子我和阿姨的关系,也如那只蚂蚁和我的关系,各自生活在自己轨迹中。
老年大学活动结束了,阿姨说我歌唱得好,问起我的工作单位,也许是我的工作单位与她的经历有着一种什么关系,她听完后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她的经历。详细辑录可以写成一本小说,提炼出的关键词大概就是:年轻、活跃、任职、公社、机关、干部、领导。当然也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其中的细节许多知青小说都写过了。阿姨说脑筋不转弯,她等来的与等待她的是公司改制,买断、下岗,接着退休。生活上有些困难,好在父母将她从北方带来时也传给她手艺——包饺子。如今在家里包些饺子出售。因为没有任何营业许可,只在小弄里钉上一块三合板写的“××水饺出售”。像当年的投机倒把,阿姨说得轻松,笑得开心。阿姨的脸不再白净,斑点、皱纹,这一笑全给挂出来。阿姨大概知风知雨,有着一种承受过后的轻松,她拍着我肩膀说:你的歌唱得真好,下次活动再来唱。
就这样每当相遇她总是询问我在哪个单位,歌唱得真好!
经历是条流淌的河,也许我唱的那首歌对于阿姨是一股清新的泉水,当年她喝到了心中。至于别的大概对于她不再重要,就如河床中的鹅卵石。多漂亮的鹅卵石也浇不活河床边的那株草。草又怎么能记住呢!
责任编辑 贾秀莉林芝